歷史淵源
 寧波走書
寧波走書 早期寧波走書
早期寧波走書據藝人所傳,其最早從上虞流入(註:有另一說法,稱其形成於清光緒年間的餘姚農村,清末明初流傳入寧波城區,繼又向鎮海、舟山地區拓展。)
又名蓮花文書、犁鏵文書,流傳於寧波、舟山、台州一帶,深受當地民眾歡迎,寧波走書約誕生於清同(治)光(緒)年間。據藝人傳,最早從上虞流入。當時,曾有佃工在農作中你唱我和,自我娛樂,藉以消除疲勞。後由唱小曲發展到唱有故事情節的片段,當時伴奏只用一副竹板和一隻毛竹根頭敲打節拍,曲調也十分簡單。光緒年間,這種演唱形式已流行餘姚農村。後餘姚有農閒時從事曲藝演唱的農民、小販和手工業者成立“杭余社”,交流演唱經驗,研究曲藝書目。其中有位許生傳老先生,吸收紹興蓮花落的曲調,率先採用月琴伴奏,自彈自唱,很受民眾歡迎。在其影響下,許多藝人也都採用各種樂器伴奏,並從四明南詞、寧波灘簧、地方小調中引進不少曲調,加以改造套用。同時,書目方面也有發展,出現了《四香緣》、《玉連環》等一些長篇,演唱活動範圍逐漸擴大到寧、舟、台地區。
寧波走書表演開始為一人自拉自唱的“坐唱”。後出現簡單伴奏的形式,演員坐於桌後,樂隊坐桌子兩旁;演員因於桌後表演,動作幅度較小,故稱“里走書”;再後,演員與樂隊相對各坐一旁,演員在台上有較大空間作表演圈,稱為“外走書”。時鄞西謝寶初的表演,城裡段德生的唱腔,慈北毛全福的武功,各有千秋,名噪一時,在民眾中很有影響。
由於蓮花文書從坐唱發展到站立表演,分口飾角色,這樣演員在台上動作的幅度比較大,走書之名也由此得來。建國後,寧波走書表演發展到男女雙檔,伴奏力量也得到加強。
寧波走書曲調常用有四平調、馬頭調、賦調三種,俗稱“老三門”。有時也用還魂調、詞調、二簧、三頓、三五七等。“四平調”一般作為一部書的開頭,末句常由樂隊和唱。“賦調”隨內容情節、人物性格,有緊、中、慢之分。如慢賦調節奏緩慢,曲調下行為主,多用於哀訴之類的敘述或回憶。“馬頭調”據藝人所傳,系從蒙古民間曲調中轉化而成。“三頓”節奏較快,鏇律高昂,大都用於人物心情激動或情節急迫之處。走書演唱伴奏樂器中,四弦胡琴為必不可少的主樂,也是寧波走書音樂具有獨特風格之處。其他樂器有二胡、月琴、揚琴、琵琶和三弦等。寧波走書的主要傳統書目有:《白鶴圖》、《黃金印》等。
奉化、鄞州文化館有文藝幹部。都組織專業和業餘創作骨幹,專門從事寧波走書的劇目創作並創作了多部現代新書;寧波走書演員超過百人,演出書場達13家之多。寧波走書以蓬勃的發展勢頭逐漸走向繁榮。當時,曾有幾個佃工,在農作中你唱我和,自娛自樂,藉以消除疲勞,後由唱小曲發展到唱有故事情節的片段,並在夏夜乘涼或冬日閒暇之時,湊攏幾個人到曬場、堂前演唱。也有一些人,逢年過節出外演唱,賺一些“外快”。當時並沒有什麼樂器,只有一副竹板和一隻毛竹根頭,敲打節拍曲調也十分簡單。光緒年間,這種演唱形式已流行餘姚農村。後來,餘姚有一些農閒時從事曲藝演唱的農民、小販和手工業者,成立了一個“杭余社”組織,經常交流演唱經驗,研究曲藝書目。其中有位叫許生傳的老先生,吸收了紹興蓮花落的曲調,率先採用月琴伴奏,自彈自唱,很受民眾歡迎。在他的影響下,許多藝人也都採用各種樂器伴奏,還從四明南詞、寧波灘簧、地方小調中引進不少曲調,加以改造套用。同時,在書目方面也有了發展,出現了《四香緣》、《玉連環》、《雙珠鳳》、《契約紙》以及《紅袍》、《綠袍》等一些長篇,演唱活動的範圍也逐漸擴大到寧波、舟山、台州三個地區。
藝術特色
寧波走書的唱詞用寧波方言,有說有唱,說唱並重,輔以形體動作,表演富有生活氣息。在鄉村深受歡迎,有“文書唱華堂,走書唱農莊”的說法。寧波走書常用的基本曲調有四平調、馬頭調、賦調等。四弦胡琴是主奏樂器,也有琵琶、打琴等樂器。伴奏者有時為主唱者幫腔、隨唱和對白,是具有獨特風格的曲藝走唱形式。今曲種存少量民間職業藝人從藝(大多數為半職業藝人),個別有成就的老藝人已年至古稀,近30部傳統曲目瀕臨失傳。
表演形式
 道具
道具寧波走書的表演形式可分三個發展階段:開始時是一人自拉自唱的“坐唱”;後有簡單的伴奏,演員坐在桌子中間後面,樂隊坐在桌子橫旁,演員在桌後表演,動作幅度較小,稱為“里走書”;再後,演員與樂隊相對各坐一旁,演員在台上有較大空間作表演圈,稱為“外走書”。當時,鄞西謝寶初的表演,城裡段德生的唱腔,慈北毛全福的武功,各有千秋,名噪一時,在民眾中很有影響。由於蓮花文書從坐唱發展到站起來表演、分口飾角色,這樣演員在台上動作的幅度比較大了,走書之名也由此得來。建國後,寧波走書進行了多次改革和創新,在表演方面已發展到男女雙檔,伴奏的力量也加強了。
寧波走書曲調常用的有四平調、馬頭調、賦調三種,俗稱“老三門”。有時,也用還魂調、詞調、二簧、三頓、三五七等。“四平調”一般作為一部書的開頭,末句常由樂隊和唱。“賦調”隨內容情節、人物性格,有緊、中、慢之分。如慢賦調節奏緩慢,曲調下行為主,多用於哀訴之類的敘述或回憶。“馬頭調”據藝人所傳,系從蒙古民間曲調中轉化而成。“三頓”節奏較快,鏇律高昂,大都用於人物心情激動,或情節急迫之處。走書演唱伴奏的樂器中,四弦胡琴是必不可少的主要樂器,也是寧波走書音樂具有獨特風格之處,其他樂器有二胡、月琴、揚琴、琵琶和三弦等。
傳統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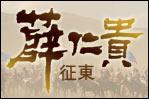 《薛仁貴征東》
《薛仁貴征東》寧波走書的主要傳統書目有:《白鶴圖》、《黃金印》、《四香緣》、《十美圖》《玉連環》、《何文秀》、《胡必松》、《雙珠球》、《三門街》、《大紅袍》、《綠袍》、《珍珠塔》、《麒麟豹》、《玉獅子》、《天寶圖》、《文武香球》、《包公案》、《狄青平西》《紫金鞭》、《小五虎平南》、《薛仁貴征東》、《薛仁貴征西》、《乾坤印》、《薛剛反唐》、《金魚缸》、《穿金線》、《盤龍鐲》、《綠牡丹》等。
解放前夕,專業從事走書演唱藝人僅二、三十人。1950年寧波成立戲曲改進協會,對曲調、書目、表演各方面進行了研究,並組織藝人參加政治文化學習,提高素質和水平。1958年,市戲曲訓練班中又專門培訓了一批新生力量,寧波走書出現了一片嶄新面貌,當時著名藝人有應蘭芳、許斌章、朱桂英師承三代,另有邱伯揚、范秀英等,樂師劉仁福獨擅二胡,有“活胡琴”譽稱。1958年,由應毅執筆、許斌章和朱桂英雙檔演唱的《四明紅霞·李敏》,參加了省會書,並得了獎;後又出現了一批創作和改編的新長篇書目,如陳白楓執筆、朱桂英演唱的《三斗六老虎》,唐小毛整理、許斌章演唱的《白鶴圖》等。
輝煌時期
 寧波走書
寧波走書雖是城裡人,可四十出頭的沈健麗老愛往鄉下跑,她和丈夫一起唱了20多年的寧波走書,他們在寧波甚至舟山的鄉鎮已蠻有名氣。
“我們就以唱走書為生,跟民間藝人差不多吧!”沈健麗說,她12歲就會唱越劇,18歲跟了進村唱走書的師傅2個多月,又學會了走書。在其後幾年間,這對夫婦親身感受到了寧波走書耀眼的一頁。
“那時,城裡聽走書的地方多。彩虹北路邊那時有個書場,200多人的座位場場客滿,不少人硬擠在門外看。旁邊還有個菜場,菜農們早上來賣菜時都帶著便當,菜賣完了也要捱到下午,把走書聽完了再回去。在鄉下,幾乎村村都有搭台唱走書的,我們也趕場,下午在這村唱,晚上又到那村,人們聽得有味,我們唱得也有勁。”
在市群藝館研究員陳炳堯腦海里,那時走書可用“多”字形容:書場多,不算鄉間的,光城區就有20多個;唱走書的人多,光鄞縣就有50多組演員,愛聽的人則更多。這時期,走書走出了寧波,北跨錢塘、南達雁盪、東到舟山海島。在鄞縣,20多組走書藝人走鎮串鄉演出,有人形容是“鄉鄉走書聲,村村聽書人”。
收入對比或許也能反映當時走書熱的程度。在春節期間,沈健麗夫婦可唱到400多元的收入,而當時一般人月工資僅40多元。幾年前,這對夫婦就買了房子,孩子也正在讀大學。
寧波走書已有兩次發展小高潮。解放初期,成立有曲藝改進會,創作了大量作品。1964年,由傳統書改唱現代書,把走書唱上了電台。
曲藝困境
 《寧波走書》精彩片段
《寧波走書》精彩片段時代的變化悄然無聲地來了,20世紀80年代末,在新文化的衝擊下,寧波走書逐漸走向衰退。
“人都忙了,空閒時也被精彩的電視節目吸引去了。書場都被改作了商店、餐館等,很多走書演員也下海經商,寧波走書好像一下掉進了冰窟窿里。”鄞州曲協主席王建剛說起這些時很無奈。目前,全寧波只有鄞州五鄉文化中心一家固定書場,其餘只有農村一些老年活動室兼作演出場所。另一個嚴峻的現實是,在民間演出的走書藝人也只剩20餘名。
“這20多人大多數是老藝人,最年輕的也有40多歲,而且後繼乏人,有天賦又肯學的年輕人幾乎沒有。這個寧波最有特色的地方曲藝就承載在這20多人身上,真的讓人覺得沉重無比!”市群藝館研究員陳炳堯憂慮地說。
“以往是人家爭著請我們去唱,以後我們只能到處找地方唱啦。”這是沈健麗對走書衰退最直觀的感受。因為喜歡唱走書,在其他藝人紛紛轉業時,她和丈夫卻堅持了下來。他們背著行囊出去就是幾個月,去過台州偏遠的山村,上過舟山的海島,只要有人聽,再少的錢他們也願意唱。
對寧波走書的寂寥,愛好這門曲藝的人們有著一種勢單力薄、孤掌難鳴的感傷。鄞州區曲協老編劇陳少康老師曾作詞感嘆:
說古今,道古今,書唱英雄滅鼠精,滿堂喝彩聲。翁篤情,翁篤情,握別愁後無繼人,依依老淚盈。
21世紀以來,寧波走書在鄉間有所“轉暖”。沈健麗覺得,這與農村生活好了,老年人念舊等有關。
探研困因
 藝人們在一起探討曲藝
藝人們在一起探討曲藝對寧波走書一蹶不振的原因,業內人士其實看得很清楚。“原因不外乎兩點,一是它所處的社會條件變化,二是它本身不能適應這種變化而顯現出來的諸多不足。”市群藝館研究員陳炳堯這樣歸納說。
在電視等多種娛樂文化的衝擊下,寧波走書跟不上時代步伐;在快節奏生活下,人們無暇坐下品茶聽書,有限的業餘時間只會花在更為精彩的娛樂上;商鋪更值錢了,誰也不會再把房子便宜租給書場。
在這種條件下,走書更顯出自身的不足。藝人表演仍以傳統劇居多,一場唱下來要幾小時,全劇唱完要幾十天,現在的人即使想聽也沒時間聽。內容脫離時代,與現實格格不入。王建剛記得有年春節演出,有幾個青年進去聽了一會就出來了,問他們怎么了,一個回答說“聽不懂”,另一個則說“唱書先生亂講,哪有這種事情!”
用寧波方言唱是走書最重要的特色之一,可現在這個特色也成了其步履維艱的一個原因。陳炳堯研究員說,走書的唱詞中,非常多使用俚語和土話,還要求平仄聲律,不要說在甬的外地人,就是年紀稍輕的本地人也聽不懂。
聽不懂,就更別說有興趣唱了。沈健麗告訴記者,學唱走書要能吃苦,還要有興趣和天賦,這些年也曾有幾個青年跟他們學走書,可因種種原因,學不到多久就打起了退堂鼓。
2000年後,在走書創作和演出上的經費投入十分有限。把走書搬上舞台,除了創作費,場地、燈光、道具、服裝等也要投入,對曲藝人來說,這些僅靠熱情是解決不了的。
重振曲藝
 讓民眾一起學習曲藝
讓民眾一起學習曲藝“紹興有蓮花落,蘇州有評彈,我們不能眼看著寧波的特色曲藝走向敗落。”陳炳堯說:“重振走書,華山一條路,只有創新。”
鄞州區曲協的陳少康早有“創新”的想法。他提出,走書音樂也要汲取民歌和戲曲的鏇律,使其既有小橋流水,亦有大江東去,讓聽者會唱、肯學;避免用純土話鋪敘情節,不用俚語,讓外地人也聽得懂;表演要融入淨、末、旦、生、醜等戲劇動作,增強觀賞性等。
2004年開始,走書藝人已經在摸索中創新。沈健麗說,幾年前她就開始學說杭州話、紹興話,一些老土的寧波話也不用了,還編排進好多表演動作。據鄞州區曲協介紹,他們曾嘗試用國語唱走書、用鋼管樂隊伴奏等,還有意識地把走書表演與旅遊景點結合在一起,拓展走書表演空間。
與此同時,發掘、創新工作也在進行。去年,市曲協完成了《寧波傳統曲藝精選》集稿工作,蒐集了經典走書作品。民間曲藝活動也豐富多彩,去年,鄞州區組織了“文化進百村”曲藝展演,全部為寧波走書表演,讓民眾過了把走書癮。
走書人才培養也有了好的開始。奉化曲協在2002年初就建起寧波走書培訓班,先後在三所國小挑選了50多名學生進行培養,這給寧波走書的傳承和振興帶來了希望。
“十五貫一齣戲救活了一個劇種,紹興藝人胡尚海一個開篇救活了紹興蓮花落,走書作為寧波最具特色的曲藝,我們絕不能看著它的失傳。”鄞州區曲協陳少康堅定地說:“事在人為,只要大家肯努力,我相信辦得到!”
傳承意義
寧波地方曲藝的形成有著深厚的歷史基礎。曲藝在寧波很有可能是地方文化文野分流的產物。曲藝是老百姓的藝術,它講述老百姓自己的和愛聽的故事。寧波當時的民諺說,“南詞唱華堂,走書下農莊,評書進茶坊”就很生動地反映了這一分野的特點。從串客到甬劇,反映了寧波曲藝其中的一個發展方向。發展最成熟的形式莫過於走書,這種融說唱表演於一體的形式深受民眾喜愛。節慶農閒在一個村子裡可以連續唱七天七夜,有時一位好藝人可能在一個場子裡唱上一個月,除了它本身的藝術魅力外,另一個原因是它的表演班子人少,只有兩個人,可以輪流在各家各戶吃“派飯”,這很適宜於在農村“生根落腳”,而且藝人也因此與當地民眾建立起一種特殊的親情,他們互相需要,互相欣賞。當然,寧波走書、蛟川走書、餘姚雀冬冬等,同時也都依據著自己作為地方藝術的地域特點完成著各自的藝術發展軌跡。
完善鼓曲類詞條
| 曲藝是中國民間藝術中的一朵奇葩,特別是鼓曲,種類繁多,各有說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