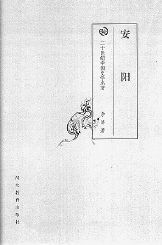作者簡介
 李濟
李濟李濟(1896—1979)是20世紀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和古史學家。 他於1918年由清華學堂選送留美,1923年在哈佛大學獲我國第一個人 類學博士學位後返國工作。一開始在南開大學教書,1925年回母校清華大學的國學研究院任人類學導師,1928年10月“入伙”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任專任研究員兼考古組主任。李濟一生活動以主持我國近代考古學第一次田野工作——山西西陰村遺址發掘和領導河南安 陽殷墟十五次考古發掘最為著名,為近代科學意義上的中國考古學的 奠基作了重要的開拓工作。李濟畢生致力考古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室內研究和教學,共發表專著十餘種,論文150餘篇。此外更主編考古發掘報告、學術集刊近80種,並主纂《中國上古史文集》。1940年,他當選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榮譽會員。他一生培養了許多著名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如夏鼐、張光直、許倬雲等。
作品簡介
 《安陽》
《安陽》《安陽》一書共分十五章,前三章從甲骨文在晚清時期的發現及一些中外收藏家的研究(代表傳統學術的研究方法)和近代考古學、地質學及古生物學等田野工作方法的輸入中國這兩方面談起,把形成現代中國考古學的兩條脈絡作了扼要的介紹,闡明了現代科學考古學在中國的建立決非偶然。
第四至八章的內容是關於李濟親自領導和參加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安陽的田野工作、發掘的出土文物的整理保管和幾次遷徙、室內研究的開展和研究成果的出版等方面的敘述。在這幾章里,李濟用的不是寫科學報告的方式,而是以第一人稱來談工作的經歷,對20年代末直至70年代中期這幾十年內考古組工作的種種方面(主要是殷墟的發掘和研究)的成績、失敗和不足作了詳細介紹。作為一個認真嚴肅的科學家,他對這段歷史的描述是很忠實感人的。
第九至十五章分別從安陽發掘與中國上古史和古史傳說關係的角度,以及70年代中期以前的研究成果的角度出發,探討了這樣幾個方 面的問題:殷墟的建築遺存,殷人經濟生活,殷代的裝飾藝術,譜系、貞人以及親族關係的一些方面,祖先崇拜和對其他神崇拜的問題。最後還有一章關於殷商人的體質人類學研究。
《安陽》一書是一本向國外宣揚介紹現代中國考古學產生和發展狀況的入門指導。作者以親身的經歷對安陽曆次田野發掘的工作目標和工作重點以及採用方法的改進乃至整個考古組的歷程作了清楚的介紹;對安陽殷墟十五次發掘的收穫和研究成果作了概要的回顧和總結。應該說,這是一部很有學術價值又通俗易懂的、論述和史料兼備的書。
張光直教授曾對這本著作給予中肯的評價,對長處和不足的地方都有涉及。請讀者參看1982年《考古學參考資料》第五期所載張光直教授評論的中譯文。他在1991年曾稱道此書“在中國考古學的園地里是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的。”
在《安陽》一書中,作者試圖把科學考古的觀念融進中國上古史的寫作。遺憾的是,作者寫《安陽》一書時已進入耄耋之年,雖神智弗減,但體力已日衰,沒有可能把畢生的經驗和學識全部都投進這一工作,材料的分析綜合也不是那么得心應手;還有一些帶有作者個性特點的獨到見解,也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現,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這一遺憾讀者或許能從附載的十幾篇論著中得到一些補償。比如,從《中國文明的開始》的一文可以見到他寫科學理論文章的高度概括的手法;從《中國古器物學的新基礎》一文可以體會到他對田野工作的細緻精確的要求;在《黑陶文化在中國上古史中所占的地位》一文中,他提倡比較法和全盤觀點,注重引用大量的發掘成果,但也決不苟同證據不充分的推論。李濟既提倡有充分證據的結論,又主張有節制地發揮想像力,這可參見他的多篇文章(如討論殷文化多元性的文章)。
近80年前李濟就提出了檢索系統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以及方塊字難於檢索而影響中國的現代化的觀點(見《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60餘年前他大力倡導培養考古人才要注重基本功訓練、尤其是人品的訓練(見《中國考古學的過去與將來》)。李濟提倡考古工作者自身決不收藏古物,要求史學家處理資料要有“寧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不為吾心之所不安”的勇氣。
總之,李濟在史學工作中的貢獻涉及理論與實踐諸方面,《安陽》則是他的成就的集中體現。
閱讀報告
如果上帝在1928年10月之際俯瞰人間,他會看到在巴掌般大小的中國的雞蛋般大小的河南的黃豆般大小的安陽的土地上,有六個如螞蟻般的人正在這顆黃豆表面上挖挖刨刨——他們是董作賓和他的工作隊員們。他們正在進行著對安陽的首次有計畫的發掘。在上帝的眼中,他們也許是微不足道的,因為他們只不過是很無謂地將他早就司空見慣的東西重新給刨了出來而已(當然,前提是這是一個中國的上帝)。但對我們而言,董作賓、李濟、石璋如、梁思永這一個個的名字,卻代表著一個個巨人,他們如盤古一般,劃破混沌,讓清氣上浮為天,讓濁氣下沉為地。然後,在剛剛沉澱下來的大地上,我們看到了安陽殷墟,一部沉寂了數千年的地書。
而全賴李濟們的發掘,才使得這部地書得以重見天日。而全賴李濟先生所寫的《安陽》一書,才使後人得以概括性地認識到這系統的發掘,也才使得我們認識到了前人的貢獻。
竊以為,我們可以把《安陽》一書籠統地劃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至三章,概述安陽發掘乃至是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的背景;第二部分,第四至六章,概述安陽殷墟的發掘過程;第三部分,第七至第十五章,概述對安陽發掘的研究。但正如所有的分類一樣,這樣的分類是難以避免人為的割裂的,如第二部分雖主要介紹的是安陽的發掘過程,但也涉及到了對安陽發掘的研究;同樣地,第三部分中也有對發掘過程的簡短介紹。所以,這樣的劃分只求得其大致輪廓,以便初學展開論述而已。
一、在第一部分,李濟先生詳細地闡明了殷墟科學發掘的學科背景與社會背景。一是甲骨的發現以及對甲骨的研究,形成了一門全新的文字學——甲骨學。這一方面增進了人們對於殷商與中國文字的了解,另一方面也誘使史語所對頻繁出現甲骨的安陽進行發掘,並最終導致了殷墟的發現。二是西方現代考古學在中國這篇土地上的演練,喚起了中國學者掌握這種新方法的熱潮。這便為殷墟乃至中國現代考古學提供了必要的學科知識基礎。如是種種,李先生在《安陽》一書中有著更為深刻的闡述,初學在此也便不再贅言了。二、《安陽》第二部分所載的殷墟科學發掘對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建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古代並非不存在對於出土古物的研究,但這種研究有其專有之名:金石學,而並非近代意義上的考古學。論者可能會感到疑惑:為什麼同樣是對古物的研究,金石學卻不同於考古學呢?
傳統的金石學,充其量只能對出土古物進行基礎的描述和分類,且往往局限於對出土古物本身進行純文字學研究,而其文字學的研究成果最終之取向也只是回歸為歷史學的材料,而沒能提供基於這些材料的獨特理論與經驗,從而形成獨特的學科方法,使文本史料與物質史料之間形成互動關係。另一方面,金石學的關注對象旨在於古物之上,而對古物產生之情景、古物之用途以及因其用途而產生的特定表述都默然無視。在金石學的範式下,古物的發掘者往往都是盜墓者,故而不注重對發掘過程的記錄,與對古物進行研究的知識分子階層完全脫節,不存在信息交流:故而古物在什麼地方出土,其出土地這一信息背後所隱含的對古物的說明也便泯滅無聞,不為研究者所知,而即便為其所知,也多半會將之略過,正如他們略過了對古物具體功能的考察一樣。兩者之區分在於學科的研究範式之上。而金石學是為了尋找支持先驗性結論的證據,而考古學是為了了解文化的過程並獲取有意義的解釋等等差別,不一而足,亦不再贅述。
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李濟先生所主持的殷墟科學發掘便顯現了突出的學科意義。在《安陽》的第四章中,李濟先生記錄了第二次發掘時的幾個步驟:1.聘用稱職的測量員描繪出以小屯為中心的詳細地形圖;2.繼續對若干地點進行挖深溝的試掘,從而了解地表下底層情況;3.系統地記錄和登記發掘出的每件遺物的確切出土地點、時間、周圍堆積情況和層次等;4.每個參加發掘的工作人員堅持寫關於個人觀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發生的情況的日記。
上面的這四個步驟或者說原則體現的便是不同於中國傳統金石學的西方現代考古學方法:不僅關注文物本身,還關注文物的出土過程,文物的出土環境。如此,才能對出土文物形成之情景有系統的、全面的認識,才能減少對出土文物的誤讀。
而在隨後的對於文物的研究中,李濟等人在進行解讀之時,總會時刻先考察文物的功能是什麼,才進一步通過其功能對於其所體現的文化過程進行解釋,而不是像在金石學範式下那樣,僅僅以之作為文字史料的補充。
因此說,在這方面,李濟、梁思永、石璋如等學人為後人確立了卓越的學科典範,為中國考古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功莫大焉。尤其是整個殷墟科學發掘的主持人發掘李濟先生,實不愧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
而初學認為,李濟先生對中國考古學乃至對中國學界的貢獻,不僅體現在他的學科貢獻上,還體現於他的學術風範上。
如果說確實存在著所謂的“中國靈魂,世界眼光”的人,李濟先生必當添列其中。擁有著西方考古學素養的李濟先生,卻始終不忘生他育他的土地。同樣是在此書的第四章中,在參加弗利爾藝術館的田野調查以前,李濟先生便要求一定要與一個中國學術團體合作並在其主持下進行工作,並且應在中國研究所有的發現物。最終,在得到弗利爾藝術館“不要求我乾我認為是不愛國的任何事”後才參與到考古發掘中。而李濟參加殷墟工作伊始,就跟同仁們約定一切出土物全部屬於國家財產,考古組同仁自己絕不收藏古物。對這條不成文的規約他自己身體力行,至死不諭而且這已成了海峽兩岸中國考古界和博物館界的一個可貴傳統,並影響及民族、民俗學等一些田野工作領域。
如今的我們其實已難以想像當時的學人們對學術的追求。在此書的第七章中,李濟寫下了這么一段話:“與梁思永一樣,在昆明和李莊我也遭受了一些個人的不幸,但一有時間我就堅持研究。”[李濟:《安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1到112頁。]不知底細者很可能會不經意間就將這句話略過,卻不知道李先生在這樣一句看似平淡的話後面會有著怎樣的心底波瀾。“在一個沒有醫院、只有一個靠步行看病的現代醫生的邊遠小鎮,當然會有悲慘的死亡,尤其是婦女和兒童。除了其他人以外,中央博物館的李濟五年中死了兩個十幾歲的女兒,……”[參見費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7年,第二十二章《戰爭的結束》。]——這便是所謂的“一些個人的不幸”。“但一有時間我就堅持研究”這句極端平常的話,曾被無數的人也正在被無數的人所使用到,但恐怕沒有一句能如李先生所說的這般重若千鈞。而李濟們的學術風範,今日之吾輩亦只可以模擬而得之矣,願略窺其一二而已。
三、《安陽》第三部分所載的對殷墟發掘的研究對於中國新史學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首先從歷史研究方法上而言,殷墟的科學發掘破除了此前的中國歷史學在研究有文本記載的歷史時對於文本記載的依賴。有論者言,殷墟的發現是對於當時轟轟烈烈的古史辨派運動的一次沉重打擊。表面看來,這句話確乎言之有理:殷墟的發現證明了晚商的存在,使古史辨派所謂商周皆不存在的主張不攻自破。然而,初學認為,這樣的看法其實存在著可供商榷之處。古史辨是什麼?並不在於普遍所認為的那樣對古史進行破壞。古史辨真正的意義,在於破除人們對於古書古史的迷信,揭開層累地形成的古史,看到顧先生們所認為的“本真的歷史”。
而所謂的層累的形成的古史又是如何構建出來的?顧先生所提及的種種偽史之所以得以層累形成,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便在於中國傳統史學甚至是古代所有的史學都存在著極其嚴重的文本依賴。古人研究三代,靠的只有記載三代歷史的文本。誠然,古人對於文本也並非毫無保留地照單全收,也會對文本進行考據,通過各文本之不同記載而理清各文本的真偽。然而這么做畢竟有所局限。例如,古書許多時候都是傳抄舊辭而成,因此一旦史源出錯,則後面的文獻也會跟著出錯,這么一來即便再怎么比較文本間的敘述也不可能找出問題。於是,一旦用以研究的文本是偽造的話,人們得到的也便是偽史了。
這時,物質史料的作用便顯露了。然而正如上文中曾提到的那樣,中國古代無考古學而只有金石學。而金石學的目的基本而言只有三個:一、在出土古物上尋找銘文,並拓下以供研究——創造新的文本,如對金文著錄等;二、修正文本。如通過漢熹平石經校定儒家經典,糾正俗儒的穿鑿附會和臆造別字。三、印證文本的正確。金石學的這三個作用顯示出了其存在價值:為文本服務。
在殷墟的科學發掘以前,也並非不存在著通過科學的考古成果以研究中國歷史。但無論是安特生對仰韶文化的發掘,還是魏敦瑞對北京人化石的研究,其範圍都在中國原有的文本記載以外,並沒有對中國史學對三代以降的研究產生深刻的影響。
這種情況最終為殷墟科學發掘所打破。殷墟大量考古材料的出土,以及隨後對這些考古材料的研究,向人們指出了這樣一個原則:文本材料與物質材料是平等的。文本並不具有先天性優勢,可以讓物質材料來證明其正確性。這正是中國古代金石學的一個重要的癥結所在。
例如,在《安陽》一書的第九章《史前遺物和有關古代中國的傳說》中便出現了文本材料與物質材料所體現的信息的不對等的情況:文本材料如《書經》、《竹書紀年》等顯示出中國上古存在著夏商周三代,而物質材料則只能證明晚商的存在。換作中國古代的史學家,定然會取《書經》之說宣稱三代的存在是毫無疑問的,進而以物質材料加以佐證:瞧!這不就證明商代是存在的了嗎?則夏代的存在又有何值得懷疑的呢!然而,李濟先生並沒有這樣做。他在指出兩種材料不對稱的情況之下,並沒有以哪一方為標準,以另一方予以佐證,而是通過研究甲骨上的朱筆痕跡,並結合此前發現的彩陶文化中“彩繪技術較刻劃出現為早”[李濟:《安陽》,第131頁。]而提出中國最初的記載是用毛筆寫就而墨水等痕跡容易消逝這一假設來解釋這種信息的不對等。這其中所體現的,便正是文本材料與物質材料平等對待,不以一者否定另外一者的原則。
這種原則的貫徹對於破除對文本的依賴是至關重要的,這使得中國史學研究者認識到:原來可以對商人的陵墓結構進行研究並結合“亞”字的意義得知商人軍事制度的大致輪廓,而並不是簡單地得出“亞”字的又一新意。
人們對於古書的迷信正是建立在對古書的依賴之上的。而破除對這些文本即古書的依賴,正是破除對古書的迷信的第一步。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殷墟科學發掘對於文本依賴的破除正是與古史辨派的對古書古史的迷信的破除是一致的。
其次,殷墟科學發掘的成果為中國歷史提供了另一種可能的闡釋。古人普遍認為,傳說中的夏商周是三個不同的朝代,是一個統一的文明——華夏文明的不同階段發展階段。現實經驗對於人們對歷史的認知具有著巨大的干擾。古人生活於治亂輪替,王朝更迭的時代,也便自然而然地認為上古三世不過是同樣的王朝更迭;而今人看中國的古史,同樣觸眼皆是王朝更迭,也便自然取信了古人的說法。即便是古史辨運動的領軍人物顧頡剛先生,也將商周兩代理解成為從“鬼治主義”到“德治主義”,實際上就是將商周視為同一個文明的不同王朝。的確,商文明無疑是華夏文明的源頭,如《安陽》中提及的商人按各自的“族”相聚而居,死後也聚葬在一起的情況,明顯便與後來華夏文明中的宗族制度有著密切的關係,又如殷商陵墓中厚葬的傳統,便是日後的周禮以及儒家所倡導的禮的一個重要內容。如此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然而,這種種的證據能夠證明商文明是華夏文明的源頭,卻不能夠證明商文明是華夏文明的唯一源頭。在存在同質的背後,商文明與日後的華夏文明同樣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例如,而《安陽》中提到的(一)商人通過占卜以行政,(二)發展到極致的祖先崇拜,(三)大量的人牲等等方式在後來的華夏文明便沒有體現出來的。後來的華夏文明,更多地體現的是周文明的敬德保民,即顧頡剛所言的“德治主義”,而非商文明的“鬼治主義”。這些考古證據向我們展現了歷史的另一種可能:所謂的商周可能並非同一個文明的不同時段,而可能是兩個不同的文明,而商周本身,可能並非兩個不同的王朝,而可能是兩個不同的共主時代。所謂的武王滅商,可能只是奪得作為共主的地位,而並非建立一個嶄新的王朝。所謂的武庚三監之亂,可能並非所謂的叛亂,而可能只是商人為重奪共主權而作的努力。華夏文明,可能並不是一脈相承的,而可能是如長江黃河一般,是多源匯進而成的。
我常常想,如果這個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一個上帝,那么他的生活該會是多么的無聊與無趣啊。因為,他什麼都知道。他必然目睹過安陽的盛況,也必然目睹過安陽的衰亡。於是,他就失去了體驗一種樂趣的可能——閱讀《安陽》的樂趣。《安陽》一書,對於初涉考古學的我們來說,難免有些許的晦澀。然而細讀之下,你會覺得你在體驗一項偉業。一項毫不遜色於羅馬建立的偉業。羅慕路斯與雷莫斯用他們英雄般的無畏與智謀建立了羅馬,而李濟們則以他們的常人之軀通過堅忍與不懈的努力重構了安陽。我想,我們是幸運的,因為我們不是上帝,我們是如李濟一般的常人。於是,我們便有著如李濟們同樣的機會,以有限的人生,建造出一座不朽的城市。
盤點考古書籍
| 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的實物資料,來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一門學科。中國近代“考古學”一詞,可能是從西文Archaeology一詞翻譯而來的。考古學是歷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其研究的範圍是古代,所以它與近代史和現代史是無關的,自人類的起源始,下限隨考古學的發展而有所變化,又由於各地區文化發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所以無法統一,各國考古學都有它們的年代下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