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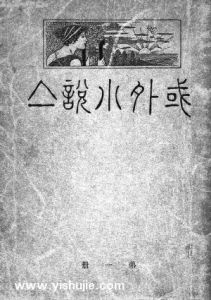 《域外小說集》
《域外小說集》周作人與魯迅同為譯介日本文學的先鋒人物,他同樣也注重翻譯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他與魯迅合譯的《域外小說集》,開了翻譯弱小民族文學之先河。這薄薄的《域外小說集》,像黑暗中的一豆燈火,照著中國荒漠的長夜,也閃現著周氏兄弟的精魂。偶然翻看那發黃了的著作,細細品味,是可感受到一種愛意的。他們的譯著,潛在地釋放著新文化的夢想,說那些作品影響了白話文寫作,以及後來的文人,並不誇大的。
出版
1909年,魯迅與周作人在東京出版了他們的第一部譯作《域外小說集》,共兩冊,收作品16篇。譯文為文言。魯迅後來說它詰屈聱牙,似有不滿的地方。初版時,曾有序言一篇,作者云:“《域外小說集》為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為常俗所囿,必將犁然有當於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濤之微漚與,而性解思維,實寓於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暮之感矣。”《域外小說集》第一冊於一九零九年三月出版,收小說七篇;第二冊於同年七月出版,收小說九篇,周氏兄弟譯於一九零八年至一九零九年間。就中魯迅據德文轉譯三篇,余為周作人據英文翻譯或轉譯(《燈台守》中詩歌亦由他口譯,魯迅筆述)。書在東京付梓,署會稽周氏兄弟纂譯,周樹人發行,上海廣昌隆綢莊寄售。序言、略例,皆出自魯迅手筆。魯迅曾說,當時他們“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於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南腔北調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總括一句,旨在標舉“弱小民族文學”。以後周作人繼續從事譯介,一九一零年至一九一七年間共完成二十一篇,一九二一年《域外小說集》由上海群益書社出版增訂本時一併收入。《域外小說集》中,只有三篇小說是魯迅所譯,安德烈夫的《謾》和《默》,以及迦爾詢的《四日》,其餘均出自周作人之手。作者大多是俄國及東歐弱小民族的,像波蘭的顯克微支,波思尼亞的穆拉淑微支等。這些小說,均有一種苦難的意識,作品深處是底層的痛感,以及蒼涼的精神。魯迅後來寫小說,多少也受到了這類作品的影響。他自稱自己的一些小說,分明還帶有安德烈夫的陰冷,看來初期的翻譯,確實對其小說的寫作有所暗示,所謂精神表達式的某種滲透,正是這樣的。
廣告
《神州日報》在表示“志謝”的第二日,又刊登了魯迅自擬的“《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廣告,他當時推廣介紹的努力並不止於贈書。這則廣告又曾刊登在《時報》上,時間比《神州日報》還早一天:“是集所錄,率皆近世名家短篇。結構縝密,情思幽眇,各國競先選譯,裴然為文學之新宗,我國獨闕如焉。因慎為譯述,抽意以期於信,繹辭以求其達。先成第一冊,凡波闌(蘭)一篇,英一篇,俄五篇。新紀文潮,灌注中夏,此其濫觴矣。至若裝訂新異,紙張精緻,在近日小說中所未覩也。每冊小銀員(元)叄角,現銀批售及十冊者九折,五十冊者八折。總寄售處:上海英租界後馬路乾記弄廣昌隆綢莊。會稽周樹人白。”可是儘管在報上刊載了廣告,這本書的銷路卻不好。魯迅於1920年所作的《域外小說集序》中說:“至於上海,是至今還沒有詳細知道。聽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冊上下,以後再沒有人買了。”至於銷路不好的原因,魯迅則歸於當時讀者尚未習慣於閱讀短篇小說,“那時短篇小說還很少,讀書人看慣了一二百回的章回體,所以短篇便等於無物。”但篇幅恐怕並不是主要問題,如光緒三十二年灌文書社出版了《短篇小說叢刊》,同年鴻文書局出版了《短篇小說叢刻》初編,二編則於翌年出版,宣統元年時報館出版了《短篇小說合璧》,宣統二年群學社《短篇小說十五種》;至於各書局不斷再版、三版的各種偵探小說集,其中相當一部分作品也都是短篇小說。在晚清1075篇有標示的小說中,標“短篇小說”、或“短篇”的共178篇,占據首位,標“偵探小說”、“社會小說”與“言情小說”的依次列於其後。可見當時短篇小說並非銷路不行,魯迅在這個問題上可能有點誤解。短篇只是篇幅上的劃分,若論其題材,當時流行的其實主要還是偵探小說、社會小說與言情小說,而《域外小說集》所選的作品,與讀者中流行的口味並不合拍。魯迅在1920年的那篇《序》中曾說,他後來看到某雜誌上登載《樂人揚珂》,竟標示為“滑稽小說”,“這事使我到現在,還感到一種空虛的苦痛。但不相信人間的心理,在世界上,真會差異到這地步。”但出版商之所以如此標示,目的就是想引起讀者的興趣。銷路不好的另一重要原因,當是寄售處的選擇。晚清時書籍寄售一般都是委託書局和書莊,那兒讀者來往多,銷售自然較為捷易,而當時書局與書莊大多集中在四馬路一帶。可是,魯迅委託的寄售處卻是“後馬路乾記弄廣昌隆綢莊”,筆者曾檢閱過晚清各報數百則售書廣告,惟有《域外小說集》的寄售處不是書局或書莊;而且,那時報上刊登的小說廣告多有內容提要,擬稿者往往煞費苦心,故弄玄虛,或製造懸念,使讀者產生閱讀的衝動,可是魯迅所擬的廣告只是抽象地稱“名家短篇”,“結構縝密,情思幽眇”等十餘字,一般讀者即使讀到這則廣告也弄不清作品內容究竟是什麼,不特地到那家綢莊去購買也是情理中事。
序言
我們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一種茫漠的希望:以為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因為這意見,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事。但做這事業,一要學問,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資本,五要讀者。第五樣逆料不得,上四樣在我們卻幾乎全無:於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經營,姑且嘗試,這結果便是譯印《域外小說集》。
當初的計畫,是籌辦了連印兩冊的資本,待到賣回本錢,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冊的。如此繼續下去,積少成多,也可以約略紹介了各國名家的著作了。於是準備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冊,到六月間,又印出了第二冊。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東京。
半年過去了,先在就近的東京寄售處結了帳。計第一冊賣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後可再也沒有人買了。
那第一冊何以多賣一本呢?就因為有一位極熟的友人,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所以親去試驗一回,果然劃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試驗了——但由此看來,足見那二十位讀者,是有出必看,沒有一人中止的,我們至今很感謝。
至於上海,是至今還沒有詳細知道。聽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冊上下,以後再沒有人買了。於是第三冊只好停板,已成的書,便都堆在上海寄售處堆貨的屋子裡。過了四五年,這寄售處不幸被了火,我們的書和紙板,都連同化成灰燼;我們這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
到近年,有幾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說集》,因而也常有問到《域外小說集》的人。但《域外小說集》卻早燒了,沒有法子呈教。幾個友人,因此很有勸告重印,以及想法張羅的。為了這機會,我也就從久不開封的紙裹里,尋出自己留下的兩本書來。
我看這書的譯文,不但句子生硬,“詰誳聱牙”,而且也有極不行的地方,委實配不上再印。只是他的本質,卻在現在還有存在的價值,便在將來也該有存在的價值。其中許多篇,也還值得譯成白話,教他尤其通行。可惜我沒有這一大段工夫,——只有《酋長》〔3〕這一篇,曾用白話譯了,登在《新青年》上,——所以只好姑且重印了文言的舊譯,暫時塞責了。但從別一方面看來,這書的再來,或者也不是無意義。
當初的譯本,只有兩冊,所以各國作家,偏而不全;現在重行編定,也愈見得有畸重畸輕的弊病。我歸國之後,偶然也還替鄉僻的日報,以及不流行的雜誌上,譯些小品,只要草稿在身邊的,也都趁便添上;一總三十七篇,我的文言譯的短篇,可以說全在裡面了。只是其中的迦爾洵的《四日》,安特來夫的《謾》和《默》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譯的。
當初的譯文裡,很用幾個偏僻的字,現在都改去了,省得印刷局特地鑄造;至於費解的處所,也仍舊用些小注,略略說明;作家的略傳,便附在卷末——我對於所譯短篇,偶然有一點意見的,也就在略傳里說了。
《域外小說集》初出的時候,見過的人,往往搖頭說,“以為他才開頭,卻已完了!”那時短篇小說還很少,讀書人看慣了一二百回的章回體,所以短篇便等於無物。現在已不是那時候,不必慮了。我所忘不掉的,是曾見一種雜誌上,也登載一篇顯克微支的《樂人揚珂》,和我的譯本只差了幾個字,上面卻加上兩行小字道“滑稽小說!”這事使我到現在,還感到一種空虛的苦痛。但不相信人間的心理,在世界上,真會差異到這地步。
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寫的事物,在中國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於迦爾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幾於極無,所以更不容易理會。同是人類,本來決不至於不能互相了解;但時代國土習慣成見,都能夠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鏡一般明,照見別人的心了。幸而現在已不是那時候,這一節,大約也不必慮的。
倘使這《域外小說集》不因為我的譯文,卻因為他本來的實質,能使讀者得到一點東西,我就自己覺得是極大的幸福了。
一九二○年三月二十日,記於北京。
評價
翻譯域外小說,在魯迅先生看來,是輸進新精神的途徑,小說乃感化民族的良藥,這在周氏兄弟眼中,是精神世界的第一要義。魯迅棄醫從文時,想的第一件事,便是辦一份文學雜誌,但不幸流產,中道而廢。後來便想在翻譯上多有建樹,以此引起國人的注意。20世紀初的中國,文學凋敝,並無多少佳作可讀,老朽的八股體和文言小說,不僅內容貧乏,情趣亦殊為乾癟。他與二弟周作人著手從事翻譯,用意頗為明顯,就是“轉移性情,改造社會”。許多年後,魯迅在為該書的再版本做序時,提及了這一點,那文章流出的情感是讓人感懷的。譯書和寫書,是兩種不同的勞作。有人說翻譯是媒婆,創作是處女,或許有一點點道理。但在周氏兄弟那裡,翻譯的意義,恐怕不亞於創作,周作人在自己的集子中,將譯文也收進去,這在現代作家中,是少見的。查魯迅的譯文字數,和創作字數相等,此可證明其做“媒婆”的熱情。我一向認為,魯迅首先是個翻譯家,其次才是個作家,在中國這樣一個文化荒蕪的地方,引進外來思想,確是急需的。在翻譯領域,魯迅做的工作,多有開創的價值。像《域外小說集》這樣的書,無論在趣味上還是品格上,均異於林琴南,有一種選擇上的自覺。它不僅改寫了小說翻譯史上的色調,也開啟了文學翻譯新的風氣,僅此,同代人中,是沒有人能與他們比肩的。
初版數量
關於初版《域外小說集》存世的數量,一直以來大家都依據魯迅的說法——“半年過去了,先在就近的東京寄售處結了賬。計第一冊賣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後可再也沒有人買了……至於上海,是至今還沒有詳細知道。聽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冊上下,以後再沒有人買了”(《域外小說集》合訂版“序”,上海群益書社,1921)。由於初版《域外小說集》分第一冊和第二冊,所以魯迅說的在東京賣出的四十一本,折算應為賣出二十部(何以多賣一本第一冊,魯迅也有說明),而在上海賣出的“二十冊上下”,魯迅沒有具體說明第一冊賣了多少,第二冊賣了多少。這“二十冊上下”是不該計算為二十部的,但長期以來“冊”與“部”一直被混淆,連嚴謹的唐弢先生也沒能注意這個計算方法上的誤差,他寫道:“根據魯迅後來的回憶,《域外小說集》第一,二冊在東京只賣去二十冊(筆者按:唐弢在此處引文有誤,應為四十一冊),上海也不過二十冊左右。‘於是第三冊只好停版,已成的書,便都堆在上海寄售處堆貨的屋子裡。過了四五年,這寄售處不幸被了火,我們的書和紙板,都連同化為灰燼;我們這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從這個統計看來,東京版《域外小說集》流行於人間的,似乎只有四十部左右”(唐弢:《晦庵書話·域外小說集》)。胡從經先生也曾寫道:“……但東京僅賣出各式十本(筆者按:胡從經此處亦計算有誤,應為“各式二十本”,才能與魯迅說的數對得上),上海寄售處也不過銷出各二十冊上下……傳世的印本也不止四十部左右”(“大濤之微漚巨響之先聲——《域外小說集》”)。胡從經將魯迅的原話“聽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冊上下,”理解為“各二十冊上下”。有可能胡從經察覺了“冊”與“部”的計算差距,加了個“各”字,顯示了他的細心。有了這個“各”字,留存於世的“四十部”才說得通。可是魯迅的原話是我們計算的基礎,按照魯迅的原話來計算,《域外小說集》的存世量應是三十部左右,換個說法就是六十冊(本)上下。事實上,實際的存世量是多於六十冊的,因為除了代售處賣出的那幾十本,魯迅、周作人、蔣仰卮(《域外小說集》出版的資助人)都拿書送過人。唐弢寫道:“魯迅每印一書,常好持贈知音,而蔣仰卮回國後,也曾托浙江省立圖書館大批捐贈,在卷首空頁上蓋一印云:‘浙江省立圖書館輔導組代紹興蔣仰卮先生捐贈’。”據胡從經統計“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的《魯迅日記》均斷續有贈書記錄,所貽友好或同僚有董恂士,錢稻孫,戴螺舲,季自求,劉靂青,游百元,夏揖顏,袁文藪,黃季剛,陳寅恪,張春霆,宋子佩,許詩堇等。”應該注意的是,魯迅此時已在北京,他用於送人的《域外小說集》是二弟周作人自老家紹興寄給他的,兄弟倆在日記中有一發一收之記載。周作人1917年4月到北京後所記日記中非但有送友人《域外小說集》的記錄,竟還有賣書的記錄“……以域外小說集四部交半農代售”(1918年12月4日)。魯迅所說“四五年後”存書全燒了,這個燒書時間應在1914或1915年,那么周作人1912~1914年間給魯迅寄的書是應算在上海的“二十冊上下”之內還是之外?
再有,光是周作人就寄了超過二十冊的《域外小說集》,而且火燒之後的1917年魯迅日記還有收到周建人寄該書十冊的記載。看來魯迅在老家存書的數量應該很可觀。寄到北京的書有日記可查的是19套,送給13個人,那還應有餘書,但卻不知下落。我所說不知下落的不只是北京的余書,還有存在紹興的余書。
還有一個細節,魯迅說的“過了四五年,這寄售處不幸被了火,我們的書和紙板,都連同化為灰燼;”此處“被了火”的書是已出版的第一冊和第二冊已無疑議,可是連同化成灰燼的“書板”,卻不是屬於第一第二冊的書板,它只能是未及面世的第三冊的書板(也就是今天說的“紙型”),因為魯迅在這段話的前面還有“於是第三冊只好停版,已成的書,便都堆在上海寄售處堆貨的屋子裡”的話,這句里的“都”字很清楚地點明了“書和書板”的區別。
拍賣價格
《域外小說集》自3萬元起拍,在15萬之前有好幾位競標者,爭奪可謂緊張激烈,叫價過了20萬之後,只剩下兩個人舉牌了,一對一的較量到拍賣師喊“27萬,27萬,最後一次”,拍槌落下,全場掌聲。
現在,這本珍籍拍賣了29.7萬元(含10%佣金),高出大家想像的價位很多。以近三十萬元的價錢買一本平裝書,儘管是珍本,但畢竟不是壤內孤本,難說物值相匹。況且此書有兩大缺陷:一,只有第一冊,只能算半部書,若論印數,第二冊(500本)比第一冊(1000本)倒稀罕得多。我的意思是,若是全本兩冊且為毛裝,三十萬還能理解,現在是兩本書的錢買一本書,只能理解為“不惜代價,志在必得”了。二,此書非毛裝本。魯迅說“裝釘均從新式,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故雖翻閱數次絕無污染。”很明白地說明該書是毛裝書,至於1500冊是不是全部毛裝,現在無法查證(筆者傾向全部為毛裝本),但是不能以為現在見到的是切邊本就斷定當年出版時即有毛裝和切邊的兩種。因為也很可能是讀者買回毛裝本後自己切邊的,換言之,證毛裝易,證切邊難。永遠不會有一大堆的《域外小說集》擺在這讓我們舉證對核,這事就永遠存疑罷。
周作人相關著作
| 長期以來,周作人在中國文壇上可謂是寂寞的,在辭世後相當長的時間中,他的作品幾乎被人們所遺忘,但這絲毫不影響他現代散文開山大師的地位。本集精選了周作人生平書稿、散文及翻譯著作等,旨在揭開塵封的歲月,為今天的讀者們呈現出一篇篇平和寬容、樸實有諧趣、飽含難以言說的美的知堂真味散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