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余英時著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1-1
內容提要
本書所收各文中,最早發表的是《(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時在一九五四年。此文揭出了郭沫若掩襲錢先生著作的事實,是現代學術史上一樁極有趣的公案。由於此文未經重印,故流傳不廣。此次收入集中,校勘和考證的部分一仍舊貫,但在行文方面則作了較大的修改。大陸曾間接反擊此文,採取變被告為原告的策略,反過來誣指《先秦諸子系年》由抄襲而成,更為學術史添一趣聞。因此我又補寫了一篇跋文,供讀者參考。
《錢穆與新儒家》一文近四萬言,最近才寫成,是本書中最長的一篇,此文較去年所寫的兩篇悼念文字為詳實,咽之也許可以更進一步說明錢先生的治學精神。但是為了避免引起無謂的爭端,我沒有讓它先在報章雜誌上露面。所以這是第一次刊布的文字。
本書《附錄》收入錢先生論學論文的書簡三通,這是從我手頭尚保存著的信中挑選出來的。我因為屢次遷居,師友書簡損失最多。錢先生給我的信也頗多遺失和殘闕,現存的幾十封信是我在錢先生逝世後,翻箱倒篋找到的。《附錄》第一、第二通寫於一九六○年,那時錢先生正在耶魯大學任客座教授。這兩封信都是對我的《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初稿的批評和討論。
作者簡介
余英時,1930年生。美國哈佛學史學博士。歷任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2001年,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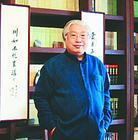 《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本書目錄
序猶記風吹水上鱗——敬悼錢賓四師
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
錢穆與新儒家
《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
附《跋語》
《周禮》考證和《周禮》的現代啟示——金春峰《(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新考》序
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香港中文大學廿五周年紀念講座第四講(一九八八年九月)
壽錢賓四師九十
附錄一: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
附錄二: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手跡
精彩書摘
猶記風吹水上鱗——敬悼錢賓四師海濱回首隔前塵,猶記風吹水上鱗。
避地難求三戶楚,占天曾說十年秦。
河間格義心如故,伏壁藏經世已新。
愧負當時傳法意,唯余短髮報長春。
八月三十一日深夜一時,入睡以後突得台北長途電話,驚悉錢賓四師逝世。悲痛之餘,心潮洶湧,我立刻打電話到錢府,但錢師母不在家中,電話沒有人接。所以我至今還不十分清楚錢先生(我一直是這樣稱呼他的,現在仍然只有用這三個字才能表達我對他的真實情感)逝世的詳情。不過我先後得到台北記者的電話已不下四五起,都說他是在很安詳的狀態下突然去的,這正是中國人一向所說的“無疾而終”。這一點至少給了我很大的安慰。今年七月我回到台北參加“中央研究院”的會議,會後曾第一次到錢先生的新居去向他老人家問安。想不到這竟是最後一次見到他了,走筆至此禁不住眼淚落在紙上。
最近十幾年,我大概每年都有機會去台北一兩次,多數是專程,但有時是路過。每次到台北,無論行程怎么匆促,錢先生是我一定要去拜謁的。這並不是出於世俗的禮貌,而是為一種特殊的情感所驅使。我們師生之間的情感是特別的,因為它是在患難中建立起來的;四十年來,這種情感已很難再用“師生”兩個字說明它的內容了。但最近兩三年來,我確實感到錢先生的精神一次比一次差。今年七月初的一次,我已經不敢說他是否還認識我了。但是他的身體狀態至少表面上還沒大變化。所以他的突然逝世對我還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
我對於錢先生的懷念,絕不是短短一兩篇,甚至三五篇“逝世紀念”那種形式化的文字所能表達得出來的,而且我也絕不能寫那樣的文字來褻瀆我對他老人家的敬愛之情。所以我現在姑且回想我最初認識他的幾個片斷,為我們之間四十年的師生情誼留下一點最真實的見證,同時也稍稍發抒一下我此時的哀痛。以後我希望有機會寫一系列文字來介紹他的思想和生平,但那必須在我的情緒完全平復以後才能下筆。錢穆草創新亞書院時,校舍簡陋,學生不超過二十人。
我在前面所引的詩是我五年以前祝賀錢先生九十歲生日的四首律詩的最後一首,說的正是我們在香港的那一段歲月。我第一次見到錢先生是一九五○年的春天,我剛剛從北京到香港,那時我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學歷史系讀書。我最初從北京到香港,自以為只是短期探親,很快就會回去的。但是到了香港以後,父親告訴我錢先生剛剛在這裡創辦了新亞書院,要我去跟錢先生念書。我還清楚地記得父親帶我去新亞的情形。錢先生雖然在中國是望重一時的學者,而且我早就讀過他的《國史大綱》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也曾在燕大圖書館中參考過《先秦諸子系年》,但是他在香港卻沒有很大的號召力。當時新亞書院初創,學生一共不超過二十人,而且絕大多數是從大陸來的難民子弟,九龍桂林街時代的新亞更談不上是“大學”的規模,校舍簡陋得不成樣子,圖書館則根本不存在。整個學校的辦公室只是一個很小的房間,一張長桌已占滿了全部空間。我們在長桌的一邊坐定不久,錢先生便出來了。我父親和他已見過面。他們開始寒喧了幾句。錢先生知道我願意從燕京轉來新亞,便問問我以前的讀書情況。他說新亞初創,只有一年級。我轉學便算從二年級的下學期開始,但必須經過一次考試,要我第二天來考。我去考試時,錢先生親自出來主持,但並沒有給我考題,只叫我用中英文各寫一篇讀書的經歷和志願之類的文字。交卷以後,錢先生不但當場看了我的中文試卷,而且接著又看我的英文試卷。這多少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知道錢先生是完全靠自修成功的,並沒有受到完整的現代教育。他怎么也會看英文呢?我心中不免在問。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他在寫完《國史大綱》以後,曾自修過一年多的英文,但當時我是不知道的。閱卷之後,錢先生面帶微笑,這樣我便被錄取了,成為新亞書院文史系二年級第二學期的學生了。這是我成為他的學生的全部過程。現在回想起,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引以自傲的事。因為錢先生的弟子儘管遍天下,但是從口試、出題、筆試、閱卷到錄取,都由他一手包辦的學生,也許我是唯一的一個。
錢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個子雖小,但神定氣足,尤其是雙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同時還有一個感覺,就是他是一個十分嚴肅、不苟言笑的人。但是這個感覺是完全錯誤的,不過等到我發現這個錯誤,那已是一兩年以後的事了。
當時新亞學生很少,而程度則參差不齊。在國學修養方面更是沒有根基,比我還差的也大有人在。因此錢先生教起課來是很吃力的,因為他必須儘量遷就學生的程度。我相信他在新亞教課絕不能與當年在北大、清華、西南聯大時相提並論。我個人受到他的教益主要是在課堂之外。他給我的嚴肅印象,最初使我有點敬而遠之。後來由於新亞師生人數很少,常常有同樂集會,像個大家庭一樣,慢慢地師生之間便熟起來了。熟了以後,我偶爾也到他的房間裡面去請教他一些問題,這樣我才發現他真是“即之也溫”的典型。後來我父親也在新亞兼任一門西洋史,他常常和我們一家人或去太平山頂或去石澳海邊坐茶館,而且往往一坐便是一整天,這便是上面所引詩中的“猶記風吹水上鱗”了。錢先生那時偶爾還有下圍棋的興趣,陳伯莊先生是他的老對手,因為兩人棋力相等。我偶爾也被他讓幾個子指導一盤,好像我從來沒有贏過。
一年暑假,錢穆患嚴重胃潰瘍,孤零零躺在教室地上養病,內心卻渴望讀王陽明文集。
這樣打成一片以後,我對錢先生的認識便完全不同了。他原本是一個感情十分豐富而又深厚的人。但是他畢竟有儒學的素養,在多數情況下,都能夠以理馭情,恰到好處。我只記得有一次他的情感沒有完全控制好,那是我們一家人請他同去看一場電影,是關於親子之情的片子。散場以後,我們都注意到他的眼睛是濕潤的。不用說,他不但受了劇情的感染,而且又和我們一家人在一起,他在懷念著留在大陸的子女。但這更增加了我對他的敬愛。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裡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他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我跟錢先生熟了以後,真可以說是不拘形跡,無話不談,甚至彼此偶爾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嚴永遠是在那裡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鐘忘記。但這絕不是老師的架子,絕不是知識學問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這是經過人文教養浸潤以後的那種自然。我想這也許便是中國傳統語言所謂的“道尊”,或現代西方人所說的“人格尊嚴”。
這種尊嚴使你在他面前永遠會守著言行上的某種分寸,然而又不覺得受到什麼權威的拘束。說老實話,在五十年代初的香港,錢先生不但無權無勢,連吃飯都有困難,從世俗的標準看,哪裡談得上“權威”兩個字?這和新亞得到美國雅禮協會的幫助以後,特別是新亞加入中文大學以後的情況,完全不同。我們早期的新亞學生和錢先生都是患難之交。以後,雅禮協會和哈佛燕京社都支持新亞了,香港大學又授予他榮譽博士學位,錢先生在香港社會上的地位當然遽速上升。但是就個人的親身體驗而言,錢先生則依然故我,一絲一毫也沒有改變。發展以後的新亞遷到了嘉林邊道。我仍然不時到他的房間裡聊天,不過常不免遇到許多形形色色的訪客。有一次,一位剛剛追隨他的文史界前輩也恰好在座,忽然這位先生長篇大段地背誦起文章來了。我沒有聽清楚是什麼,錢先生有點尷尬地笑,原來他背誦的是錢先生幾十年前在北平圖書館館刊上所發表的一篇文字。這一切都和錢先生本人毫不相干。一九六。年春季,錢先生到耶魯大學任訪問教授,我曾兩度去奉謁,他和錢師母也兩度到康橋來作客。他們臨行前,還和我們全家同去一個湖邊木屋住了幾天。我們白天划船,晚上打麻將,這才恢復到我們五十年代初在香港的那種交遊。錢先生還是那么自然、那么率真、那么充滿了感情,但也依然帶著那股令人起敬的尊嚴。
上面描寫的錢先生的生活的一面,我想一般人是不十分清楚的。我能比較完整地看到這一面也是出於特殊機緣造成的。錢先生從來不懂得譁眾取寵,對於世俗之名也毫無興趣,更不知道什麼叫作“製造社會形象”或“打知名度”。這些“新文化”是向來和他絕緣的。因此他不會在和人初相識時便有意要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尤其不肯面對青年人說過分稱譽的話。除非有五十年代香港的那種機緣,錢先生的真面目是不易為人發現的。他對《論語》“人不知而不慍”那句話,深信不疑,而近於執著。五十年代初他和我閒談時也不知提到了多少次,但他並不是向我說教,不過觸機及此罷了。
上面說到我得到錢先生的教益主要是在課堂以外,這也有外緣的關係。我在新亞先後唯讀了兩年半,正值新亞書院最艱困的時期,錢先生常常要奔走於香港與台北之間,籌募經費。一九五○年年底,他第一次去台北,大約停留了兩三個月,好像五一年的春季,他沒有開課。五一年冬他又去了台北,不久便發生了在聯合國同志會演講而禮堂倒塌的事件。錢先生頭破血流,昏迷了兩三天,幾乎死去。所以整個五二年春季他都在台灣療養。五二年夏初,新亞書院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我是三個畢業生之一。但錢先生還沒有康復,以致競未能趕回香港參加。所以我上錢先生的課,一共不過一個半學年而已。事實上,我有機會多向錢先生私下請益是在他傷愈回港以後,也就是我畢業以後。
錢穆是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但同時又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
大概在一九五○年秋季開學不久,我為了想比較深入地讀《國史大綱》,曾發憤作一種鉤玄提要的工夫,把書中的精要之處摘錄下來,以備自己參考。我寫成了幾條之後,曾送呈錢先生過目,希望得到他的指示。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課外向他請教。錢先生的話我至今還記得。他說:“你做這種筆記的工夫是一種訓練,但是你最好在筆記本上留下一半空頁,將來讀到別人的史著而見解有不同時,可以寫在空頁上,以備比較和進一步的研究。”他的閒閒一語對我有很深的啟示,而且他透露出他自己對學問的態度。《國史大綱》自然代表了他自己對一部中國史的系統見解。但是他並不認為這是唯一的看法,而充分承認別人從不同的角度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論點。初學的人則應該在這些不同之處用心,然後去追尋自己的答案。用今天的話說,錢先生的系統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這個意思,他在《國史大綱》的“引言”和“書成自序”中也隱約地表示過,但是對我而言,究竟不及當面指點,直湊單微,來得親切。從此以後,我便常常警惕自己不能武斷,約束自己在讀別人的論著——特別是自己不欣賞的觀點——時,儘量虛懷體會作者的用心和立論的根據。
這次以後,我曾不斷提出《國史大綱》中的具體論斷,請他說明為什麼要這樣說,而不那樣說。每一次都是我“小扣”,而他“大鳴”。我漸漸明白原來他多年在北大等校講授中國通史的過程中,讀遍了同時史學專家在一切重大關鍵問題上的研究文字,然後根據他自己的通史觀點而判定其異同取捨。有一次我們討論到西魏府兵制,他便向我說明他和陳寅恪的看法有何異同之處。他認為陳寅恪過分強調了宇文泰個人私心在府兵製成立上的作用,而他則寧可從胡漢勢力的消長上去著眼。他很推崇陳寅恪的貢獻,但認為專題考證的具體結論和通史所需要的綜合論斷未必能完全融合無間。我舉此一例,以見《國史大綱》並不易讀。因為錢先生寫通史時惜墨如金,語多涵蓄,其背後不僅是正史、九通之類的舊史料,而且也包含了整個民國時期的史學史。
我們討論的範圍幾乎無所不包,但重點總是在現代史學的演變方面。我從他的談論中,逐漸領悟到中國傳統學術一方面自有其分類和流變,另一方面又特別注重整體的觀點。這是“專”與“通”的大問題。但是這一傳統和現代西方學術的專門化趨勢接觸以後,引起了許多有關如何溝通和融化的困難,一時無法解決。如果單純地依照西方的分類,各人選一專門的範圍去進行窄而深的斷代研究,當然也會有成績。但在熟諳中國傳統的人看來,總不免有牽強和單薄之感。如果過分注重“通”的傳統,先有整體的認識再去走專家的道路,事實上又是研究者的時間、精力、聰明都不能允許的。錢先生走出了自己獨特的“以通馭專”的道路。現在大家都把他當作學術思想史家,其實他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會經濟史各方面都下過苦功,而且都有專門著述。《國史大綱》中“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三章尤其有絕大的見識,顯示了多方面的史學修養和現代眼光。在錢先生門下,以我所認識的人而言,嚴耕望先治政治制度史後治人文地理,都是受到錢先生的啟發和指導。一九五三年錢先生得到亞洲基金會的資助,在九龍太子道租了一層樓創辦研究所,這是新亞研究所的前身。當時只有三四個研究生,我也在其中。但我當時的興趣是研究漢魏南北朝的社會經濟史,由錢先生任導師。錢先生仍一再叮嚀,希望我不要過分注意斷代而忽略貫通,更不可把社會經濟史弄得太狹隘,以致與中國文化各方面的發展配合不起來。這仍然是“通”與“專”之問的問題,不過錢先生的道路並不是人人都能走得通的,所以這個大問題也一直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他也承認這個問題恐怕無法統一解決,只有憑各人性之所近,分途摸索。
有關國學的新書
| 國學是指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國學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學術,也包括了醫學、戲劇、書畫、星相、數術等等。國學以學科分,應分為哲學、史學、宗教學、文學、禮俗學、考據學、倫理學、版本學等,其中以儒家哲學為主流;以思想分,應分為先秦諸子、儒道釋三家等,國學以《四庫全書》分,應分為經、史、子、集四部。本期任務要盤點的是有關國學的新著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