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宗璞,原名馮鍾璞。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之女,1928年生於北平,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退體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既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學厚淵源,又得外國文化長期
 宗璞
宗璞耳濡目染,她的作品蘊含東方傳統哲學文化和西方人文主義思想相結合的精神內涵,具有獨特的藝術氣質和高雅格調。主要作品有小說《紅豆》、《 魯魯》《三生石》童話《尋月記》《花的話》《總鰭魚的故事》散文〈西湖漫筆〉〈奔落的雪原〉〈花朝節的紀念〉〈三松堂斷憶〉等,出版了多種小說散文童話選集。由〈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北歸記〉組成的四卷本長篇小說〈野葫蘆引〉,是宗璞創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作品介紹
宗璞在病中苦耕,歷時7年,《南渡記》的第二部《東藏記》終於面世。計畫中尚有《西征記》、《北歸記》,是總書名為《野葫蘆引》的多卷長篇系列。
宗璞以她細密從容的敘述方式,建立起優美溫婉的語言風格。眾多的人物命運和世相心態,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情境和細節中緩緩展開,伏有大氣磅礴的布局。宗璞筆下的戰爭沒有刀光劍影,卻烙刻了深重的精神創痕,並具有一種柔性的書卷氣息。那種浸入骨髓的文化質感,在閱讀中竟令人有如置身於《紅樓夢》的語境之中。讀《東藏記》這樣雋永而精緻的小說,真是受益又享受。
《東藏記》是四卷本長篇小說《野葫蘆引》的第二卷,並可獨立成篇。這部作品以抗日戰爭時期西南南聯合大學的生活為背景,生動地刻畫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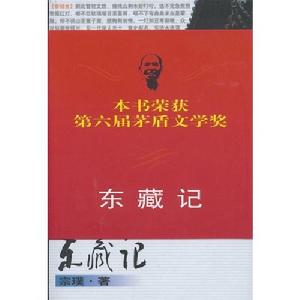 《東藏記》
《東藏記》對親人朋友的大善、對祖國民族的大家、對入侵這敵的大恨、對亡國之禍的大痛,都得到深刻細膩的表現。作品的結構嚴謹合度、語言優雅蘊藉、情節暗設玄機、人物豐滿真切,具有臻於完善的思想物藝術品格。《東藏記》描寫明侖大學南遷昆明之後孟越一家和師生們艱苦的生活,刻畫了一系列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 對教授間亦雅亦俗的人情世態,對青年人朦朧純真的思想、情感、均施以委婉細緻的筆墨,既有妙趣,又見真情。
作品背景
東藏記的背景是抗戰時的西南聯大,中國現代歷史上,有兩個關於大學的神話,一直為知識分子“念茲在茲”:一個是蔡元培掌校時期“兼收並蓄,兼容並包”的北京大學,一個是抗戰南渡後的西南聯合大學。聯大當貞元之際,作育英才,為中國文化留下一些種子,雖在橫逆之中,自有生氣勃勃,東藏記 起筆看天看雲、寫花寫樹,一開始便和這股生氣溝通。
作品材料來源
《東藏記》的材料,一些來自宗璞的親歷,一些來自她和親友的談話。以真人實事為材料做小說,無礙於小說的成就;但我們若只從小說中看出真人實事,則無異於買櫝還珠。《東藏記》的獨特之處,卻在於宗璞以一種明澈的眼光看世界,筆下的人物一個有一個的個性,一個有一個的優點和缺點——但那些缺點,除了極個別之處外,都沒有郁滯凝固為不可化解的鬱結,所以雖然人事紛紛,昔人縱勝於今,卻仍是大千世界,林林總總,“無毛雙足動物”該有的種類,那時也並不少,但所有這些人事的缺陷、人本身的缺陷和性格的缺點,並沒有阻礙這部小說總體的明朗的基調。
宗璞曾說:“寫戰爭,不能只著眼戰爭,還要超越戰爭。戰爭使人異化,人應該還原為人。東藏記 就表達了這個意思。”
鑑賞指導
宗璞《東藏記》取“東躲西藏”之意,以抗戰期間西南聯大的生活為背景,生動地刻畫了在民族危難時刻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文字淡雅,筆致委婉。她的文字有點像剛剛去世的台灣女作家林海音,飽含了那個遙遠時代的溫熱,但在某些特別的片斷里卻暗藏著閃閃的機鋒。總體風格的溫婉與某些片斷的銳利,形成了一種奇妙的對立,讓人感覺到某種不協調"的味道。
作者談創作
我與《東藏記》
宗璞
《東藏記》是《野葫蘆引》的第二部(發表於《收穫》今年第6期)。《野葫蘆引》這部小說五十年代就在我心中發芽了。法西斯侵略戰爭給我們民族的創傷太深了,給我們這一代人的影響也太大了,全面地記載這次戰爭是歷史家的事。我只能從一個方面,一個學校,幾個家庭,一些人物,來反映那山河都在動盪的時代。《野葫蘆引》分為《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和《北歸記》四卷。《南渡記》已於198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東藏記》刊於《收穫》1995年第三期。我將它獻給抗日陣亡將士,和在戰爭中一切遭受苦難的人們,並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
記得馮至先生讀過《南渡記》後,說這部書有《紅樓夢》的影子。我當然受到《紅樓夢》的影響。我們有自己的文化可繼承,是我們的福分。我們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攀高。但絕不能讓舊文化成為一種枷鎖。只有不斷吸收外來的東西並不斷融合,我們自己的文化才會是有生機的、流動的河。
書中有時人物的內心獨白,是想讓手法豐富些、活潑些。
我確實寫得很苦,近年目力大壞,全憑口授,寫到後邊忘了前邊,只好多次修改,我改得實在太多,太累了,多么羨慕出口成章一氣呵成。我覺得像一隻螞蟻,很小的螞蟻,認真努力地在搬沙,銜一粒,再銜一粒,終於堆起一座小沙丘。《東藏記》發表了,我現在已轉身向西,要“西征”了。
著名女作家張抗抗的評論
柔性的戰爭:讀宗璞長篇《東藏記》
張抗抗
戰爭在女性筆端被重構,那種炮火下的冷酷與殘忍,自然不會有本質的改變。但體驗戰爭的視角、思考戰爭以及描述戰爭的方式,卻具有別樣的風采。
宗璞在病中苦耕,歷時7年,長篇小說《南渡記》的續集《東藏記》終於面世。計畫中尚有《西征記》《北歸記》,是總書名為《野葫蘆引》的多卷長篇系列。
此前還未有這樣一部完整的大書,將抗日戰爭中的知識分子,里里外外地刻畫得如此透徹。儘管大學南遷之後,在日軍的轟炸和追擊下,仍然沒有一處可放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人和書籍始終都在不停地顛沛流離、東躲西藏,直至無處逃遁。戰爭雖然能夠消滅無數肉體和生靈,但暴力卻無法征服一個民族的文化與精神。知識和教育在炮火硝煙中延續傳承,才使得這片土地上擁有一代代不屈的靈魂。
小說人物以明侖大學歷史系教授孟樾,夫人呂素初和女兒孟離己、孟靈己等一家人為軸心,放射至孟樾教授的親朋好友同事周圍近百人,寫出從京城南下的一群知識分子,在抗日戰爭中的個人遭遇、情感經歷,以及心靈成長的歷史。孟樾一家在戰火的脅迫、物質的匱乏和教業學業的艱難中,始終堅守的仍是知識分子的良知、氣節、正義和真誠。即便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下,他們從未放棄爭取自由和民主的另一種“戰爭”,那是真正“藏”在人內心深處,不會被戰火湮滅的理想。在《東藏記》的歷史氛圍中,孟樾一家帶著他們的書本,在流浪中創造著心靈家園。鄉村與河流,天空與自然,賦予了他們新的“家園意識”,那是永遠不會坍塌的精神城堡。
很久沒有讀到如此純淨的文字了,所有的人物和故事,都是用宗璞獨有的才情來講述的。她從容洗鍊的語言,把苦難中的一切繁複都化為透明和單純。以宗璞深厚的文化教養,她對世事的理解,從來是寬宥的,她的文字無須劍拔弩張的激烈與刻薄,更無須喧譁與矯情,只任其自然而然地流淌,從不虛張聲勢,卻能不動聲色地把故事講得入味,似有一種看不見的磁性在吸引你,讓你隨行。
宗璞的語言是柔情的,被一種母愛的仁慈與博大的情懷包容。書中眾多的女性人物,無論是至情還是至善、是古怪還是任性,都傳遞出30年代知識女性的新鮮美好與青春氣息。警報與飢餓,在女性溫暖的雙手撫慰下變得能夠忍受;女性的柔情化解了恐懼與憂煩,消融著恥辱與絕望,使得西南偏遠的窮鄉僻壤,都籠罩著溫馨的家園氣氛;炮彈下的鮮血和死亡,也被覆蓋著淒迷的美感———所以,宗璞筆下的戰爭,是柔情的戰爭。宗璞以平和的心態和優雅的筆調,描述了知識和書本對戰爭的抵抗。山岙里不堪一擊的書桌課本,和天上狂轟濫炸的鋼鐵炮彈,形成了極大的反差。然而,宗璞正是從這裡發現了戰爭所激發的另一種美———人的抵抗與不屈,男人和女人共同的堅韌和頑強。正是由於文化在戰爭中的不可毀滅性,戰爭才會煥發出另一種光彩———戰爭在另一種意義下的審美性,這也許至今都是被人們忽略的。
宗璞以她優美溫婉的語言風格,確立了《東藏記》與眾不同的藝術魅力。眾多的人物命運和世相心態,在看似平淡的生活情境和細節中緩緩鋪開,伏有大氣磅礴的布局。第五章插入的“流浪猶太人的苦難故事”和第七章的“衛凌難之歌”,在文體上亦有突破,像一曲憂傷的詠嘆調,令人落淚。宗璞筆下的戰爭沒有刀光劍影,卻烙刻了深重的精神創痕,並具有一種濃郁的書卷氣息。那種浸入骨髓的中國文化質感,在閱讀中竟令人如置身於《紅樓夢》的語境之中。行文的調子雖有明清小說之風,包括小說結尾處的“間曲”,但在作品的整體把握上,仍能體會到宗璞深厚的西學功底,在對歷史認識的理念上,隱含著鮮明的現代意識,將中西方的文學精髓,融合得如此天衣無縫。
讀《東藏記》這樣雋永而精緻的小說,真是受益又享受。
年和中間停頓的5年,兩部小說前後用時15年,其間甘苦,實在是難以言說。“人道是錦心繡口,怎知我從來病骨難承受。兵戈沸處同國憂。覆雨翻雲,不甘低首,托破缽隨緣走。悠悠!造幾座海市蜃樓,飲幾杯糊塗酒。痴心腸要在葫蘆里裝宇宙,只且將一支禿筆長相守。”這首自述生平的散曲,唱出了宗璞的執著、頑強和創作的艱辛。她的作品幾乎篇篇是同疾病鬥爭所得。《東藏記》的寫作開始不久,她視網膜脫落,無法用筆寫作,所剩篇幅均由口述而成。這對於長篇小說創作,簡直是無法想像的。就像她在《東藏記》的後記中所寫的那樣,“我寫得很苦,實在很不瀟灑。但即使寫得淚流滿面,內心總有一種創造的快樂。我與病痛和干擾周鏇,有時能寫,有時不能寫,卻總沒有離開書中人物。一點一滴、一字一句,終於釀成了野葫蘆中的一瓢汁液。”
說起《野葫蘆引》的創作源起,宗璞說,那是很久遠的事了。“七·七”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宗璞和全家隨父親馮友蘭自北京南渡昆明,在西南聯大度過了8年時光。亡國之痛、流離之苦,西南聯大師生們於逆境之中弦歌不輟,父兄輩堅韌不拔、以國家民族的命運為己任的精神給少年宗璞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為她以後的文學創作儲備了豐富的素材,從1985年春到1987年底,她完成了《野葫蘆引》的第一卷《南渡記》。
高貴人物動人心
宗璞至孝。其父馮友蘭先生臨終前完成了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這一巨著。為了照顧父親,宗璞毅然擱下寫作,用全部的精力伺奉老父。然而,用盡心力也無法阻擋死別。1990年11月,馮友蘭先生乘鶴西去,宗璞大病,直到1993年秋天,才繼續《東藏記》的寫作,後來視網膜脫落,最終只能用口述的方式繼續創作。
在研討會上,作家蔣麗萍說,在閱讀《南渡記》和《東藏記》的時候,自己時常被書中人物的高貴所打動,心中經常被一撞一擊,眼眶經常濕潤。令她難過的是,我們只能在這不可多得的作品中遇到這群主人公了,而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再也沒有機會結識到這樣一群人。研討會上,有多人拿宗璞的語言文字和“紅樓”作比,宗璞把瑣碎的生活場景寫出“味”兒,把詩詞散曲的優美注入小說,有對生活的透徹的認識,往上蒸騰的那種自然,“看了這樣的小說,讓我們看到現實生活中人們的粗鄙”(陳村)。一些年前,王蒙看了宗璞的小說,曾用“口吐蘭花”四個字來形容;李子云著文評論宗璞,借用了古人的“蘭氣息,玉精神”六字,用這六個字形容先生真是再貼切不過的了。
因為身體的緣故,在整個作品研討會過程中,宗璞只是靜靜地聽,在大多數時候面無表情,更無言語。在《東藏記》後記中,宗璞寫道,“路還長著呢,只不知命有多長。”
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宗璞的心裡不斷地構築著新的七寶樓台,願宗璞先生心愿得成。
評論
在一次研討會上,嚴家炎先生說宗璞的小說像玉一樣溫潤,引來了許多讚許。在小說里透出晶瑩之狀,有一股秀美之氣,那是惟有玉一般氣質的人才有的吧?有人說宗璞的作品缺少衝動,有一點沉悶,我卻覺得她的成就來自於這一節制,要不是深切地沉到歷史的洞穴里,就不會有《東藏記》這樣渾樸的文本。我在這裡讀出明清小品的影子,也有歐洲古典小說的靜謐。宗璞在自己的園地里,以從容溫存之筆,代無數死去的亡靈發言,復原出一道道抗日的圖景。那么多的知識分子群像,那么多文化的愁思,你讀著它,像浸在深深的湖,找不到它的邊際。
《東藏記》的敘述筆致是奇異的,那是心靈之光的輻射,散落著無數精神的碎片,攪動著文化史中困頓的一頁。小說在韻律上有一點“京派”的餘緒,通篇凝重,史筆的背後有著文化的關懷。廢名、俞平伯、知堂當年在北平著述時,有過類似的敘述語態。文字儒雅,不狂不躁,平靜中卻有不安的悸動。比之於舊“京派”的文人,宗璞顯得大器。《東藏記》寫了眾多人物,時空多變,線條紛繁,民國中的苦難與知識群落的追求都點染出來。“京派”文人的身上,冷的氣息要多於熱的氣息。他們像生活的旁觀者,有超然於物的冷靜。追求一點學問,醉心於心愛之物,生活又悠然閒淡,於是文章與生活都遠離著火爆的市井。“京派”文人是特殊的群落,厚重的文化感和獨立的品位,非一般人做得來。但一面又顧影自憐,不能飛揚起來,被舊物所累,就少了清峻灑脫之韻。宗璞是超越了“京派”孤傲的。《東藏記》感人的是流動著股股熱浪,孟樾為代表的讀書人,憂患很深,沒有歷史看客的超然。孟樾等人的理想是盡倫盡職,在逆境裡做自己想幹的事。這一類人物既不像魯迅那樣直面著黑暗去做鬥士,也不像知堂那樣閉戶讀書,躲在“苦雨齋”里苦住。宗璞注意到了普通知識人的價值,在那些有道義感的教授、學者間,發現了一個民族精神的美質。有一點儒家的情思,一點個性主義的意識。《東藏記》寫了那么多的人物,給我印象深的是,作者顯示了自己的一個夢想,即知識分子只會空談是不好的,重要的是用自己的專業,“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用知識與思想,撐起一片天空,使荒蕪的世界閃現著智慧的光澤。我讀這一本書,想起了一群人物:聞一多、朱自清、馮友蘭、傅斯年……宗璞似乎暗示著讀者,日本侵略者所以無法征服中國,乃是民魂抵抗的偉力。而那民魂,在一些知識分子的文字里,何嘗中斷過呢?
我讀過宗璞的許多書,印象都很深刻。小說能像《東藏記》那么寫,不是人人可以做到。友人高遠東說,在小說里能寫出學問來,有兩個人物,一是曹雪芹,一是金庸。我覺得宗璞是有這樣天賦的人。讀其作品,亦深味學識的淵博。雖然她不是曹雪芹,也不會是金庸。她以特有的文字,指示了文學的另一條路徑。如今在這樣一條路上走著的,只此一人。
茅盾文學獎歷屆獲獎作品
| 第一屆(1982年 六部長篇小說) |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 周克芹 | 《東方》 魏巍 | 《李自成》(第二卷) 姚雪垠 | 《將軍吟》 莫應豐 | 《冬天裡的春天》 李國文 | 《芙蓉鎮》 古華 |
| 第二屆(1985年 三部長篇小說) | 《黃河東流去》(上下集) 李準 | 《沉重的翅膀》 張潔 | 《鐘鼓樓》 劉心武 |
| 第三屆(1988年 五部長篇小說) | 《平凡的世界》 路遙 | 《少年天子》 凌力 | 《都市風流》 孫力、余小惠 | 《第二個太陽》 劉白羽 | 《穆斯林的葬禮》 霍達 (榮譽獎二部) 《浴血羅霄》 蕭克 | 《金甌缺》 徐興業 |
| 第四屆(1989-1994年 四部長篇小說) | 《戰爭和人》 王火 | 《白鹿原》(修訂本) 陳忠實 | 《白門柳》(一二部) 劉斯奮 | 《騷動之秋》 劉玉民 |
| 第五屆(2000年 四部長篇小說) | 《抉擇》 張平 | 《塵埃落定》 阿來(藏) | 《長恨歌》 王安憶 | 《茶人三部曲》(1、2)王旭烽 |
| 第六屆(2005年 五部長篇小說) | 《張居正》 熊召政 | 《無字》 張潔 | 《歷史的天空》 徐貴祥 | 《英雄時代》 柳建偉 | 《東藏記》 宗璞 |
| 第七屆(2008年 四部長篇小說) | 《秦腔》 賈平凹 | 《額爾古納河右岸》 遲子建 | 《暗算》 麥家 | 《湖光山色》 周大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