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震中在人心 第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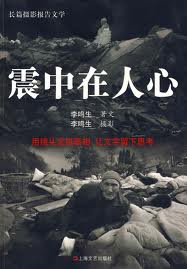 《震中在人心》
《震中在人心》汶川大地震,據有關專家測算,其摧毀程度,是當年唐山大地震的三倍;其經濟損失,是唐山大地震的19倍;其殺傷威力,相當於當年美國投放在日本廣島的5000顆核子彈!那一刻,人性像從地心蹦出的碎片,萬般奇妙,色彩紛呈,先騰空而起,再沉入廢墟。這些“碎片”有血跡,有淚痕,有傷痛,有悲憤,有情感,有體溫。
第二幕 面對親人的“戰爭”
汶川大地震,像一場突然爆發的戰爭,一場大自然向人類發動的戰爭,一場不是戰爭的“戰爭”!這場“戰爭”與軍事戰爭的根本區別,就是拼搏的地點不在沙場,而在廢墟;面對的不是荷槍實彈的死敵,而是情同手足的親人;軍人既是勇士,也是“傷兵”!
第三幕 祖國的“花朵
汶川大地震,6000餘所學校變成廢墟,2萬多個孩子墜入地獄!祖國的“花朵”瞬間變成白色的紙花,爹媽一生的希望從此變成半生的絕望!當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化作一串長長的數字,我們還說什麼呢?有人說,汶川大地震和唐山大地震的最大區別,就是唐山大地震留下了一大批失去父母的孤兒,汶川大地震留下了一大批失去孩子的父母!
第四幕 死去的與活著
的汶川大地震中,無數災民因失去家園而捶胸頓足痛心疾首;無數災民因失去親人而悲痛欲絕生不如死。面對如此沉重的打擊,多數人咬著牙抹著淚扛過來了,挺過來了,雖痛苦依舊,卻還能正常地生活,正常地工作,正常地活著;然而另有一部分災民,卻實在承認不了如此沉重的打擊,因此他們失去家園失去親人後,又失去了一個正常人原有的正常精神!
作者簡介
 李鳴生
李鳴生李鳴生,四川人,1974年入伍,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現供職於解放軍出版社。已出版各種文本20部。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說《火箭今夜起飛》、《花太陽》;長篇報告文學“航天五部曲”(《飛向太空港》、《澳星風險發射》、《走出地球村》、《風雨“長征號”》、《遠征赤道上空》)以及《中國863》、《國家大事》、《全球尋找“北京人”》;“李鳴生專訪”系列:《與智者聊天》、《毛澤東的隨行攝影記者》;電影紀錄片劇本《東方神舟》;電視劇《長征號今夜起飛》;電視專題片《血印》、《撼天記》、《軍旅人生》、《祖國不會忘記》(合作)等。《走出地球村》獲第一屆魯迅文學獎;《中國863》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風雨“長征號”》入圍第三屆魯迅文學獎;《飛向太空港》、《澳星風險發射》、《國家大事》分別獲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另獲“五個一”工程、中國圖書獎、巴金文學院優秀作品獎、馮牧文學獎、全軍文藝獎、《當代》文學獎等。
《震中在人心》作者李鳴生創作談從天上到人間
汶川大地震中,無數災民因失去家園而捶胸頓足痛心疾首;無數災民因失去親人而悲痛欲絕生不如死。面對如此沉重的打擊,多數人咬著牙抹著淚扛過來了,挺過來了,雖痛苦依舊,卻還能正常地生活,正常地工作,正常地活著;然而另有一部分災民,卻實在承認不了如此沉重的打擊,因此他們失去家園失去親人後,又失去了一個正常人原有的正常精神!
作為一名軍人,沒有上過戰場,如同一個船員,沒有下過大海。即便有一天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我想也不會輪到我了。要說遺憾,恐怕這得算一件。但汶川大地震偏偏爆發了!於是我很想去,就像一個戰士渴望撲向戰場。故鄉遭難,不去看看,良心上過不去--事情,就這么簡單。
去災區一看,初衷變了。汶川大地震的死亡人數儘管不及唐山大地震的一半,但“震波”卻至少是唐山大地震的100倍!中國的事一夜間動靜鬧得這么大,除了汶川大地震,還有什麼?震驚世界不說,單說中國,5000年的歷史上有哪朝哪代的龍旗為百姓下降垂落?有哪朝哪代的帝王為百姓低頭鞠躬?但公元2008年5月19日,共和國的國旗為百姓下降垂落,共和國的領導者集體站在中南海,為百姓低頭鞠躬,默哀3分鐘!我說過,短短3分鐘,足以勝過3000年!僅這3分鐘,便令世界刮目相看,讓我血液沸騰!為什麼?這是對死亡的尊重、對生命的尊重、對百姓的尊重--中國的百姓什麼時候受到過如此高貴的禮遇啊!而尊重死亡,便是尊重高貴的生命;尊重高貴的生命,便是尊重高貴的國民;善待生命,善待國民,正是一個國家高貴的國格所在!此外,一場大地震,居然震出那么多的愛那么多的善,那么多的美那么多的真,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與傳統美德如同汶川大地震本身,同樣震撼了世界震撼了我的心靈。我不僅看到了人性的複雜,也看到了人心的單純;不僅看到了大難與大悲,也看到大愛與大美;不僅看到了絕望與死亡,也看到了希望與新生!作為一個寫作者,在故鄉的廢墟上、屍體的氣息中、死亡的陰影里,親歷了人類歷史上如此驚天動地的一場大劫難,不用文字留下點什麼,說得過去嗎?於是震驚變成了責任,悲痛變成了良心。我決定寫點什麼。
接著的問題是,這樣的“大題材”怎么寫?我想做一次小小的努力,於是便有了如下幾點很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我想逃避概念寫作。誰都知道好作品是從生命的血液和生活的土地里長出來的,而不是由概念生成的。但歷史每天都在生產概念,人類每天都在複製概念,我們早已進入一個複製概念的時代。比如一寫汶川大地震,腦子裡很可能便裝上了“抗震救災”這個概念。因此如何逃避“大題材”概念化的寫作,我想在本書中做點探索。
第二,我想有點屬於個人的思想。優秀的作家首先是個思想家。思想的基點是對歷史客觀的審視與真誠的反省;思想的意義既屬於個人也屬於人類。
第三,我想儘量說點真話。真實是報告文學的前提。但報告文學走到今天,或者說今天的報告文學,如果還僅停留在“內容真實”這個最基本的層面上,恐怕已經不夠了,也很難滿足讀者的需求了。在我看來,真相比真實更為重要;與其強調作品的真實,不如強調作品的真相;而不管真實還是真相,均取決於作家是否虛假,是否講真話。因此,在我看來,作家的真實比作品的真實還要重要!如果連作家自身都虛假或半虛假了,在這個早已謊言為患的世界裡,還需要報告文學嗎?當然我知道,弄虛作假容易,實事求是很難。但我還是想讓自己真實一點,儘量說點實話、真話。
第四,我想讓報告文學的敘事有點變化。
第五,我想在文本上做點嘗試。
總之,此次“抗震救災”以人為本,該書便以心為本。大地震令人心碎,心碎之後如何重構心靈的家園?大地震讓人心痛,心痛之後痛出什麼樣的國民?痛出一個什麼樣的中國?是我最關心的問題;而一個民族的精神與力量、本真與大愛,為什麼在大難之時才轟然閃現?假設沒有汶川大地震,今後災難也不再降臨,一個民族的精神與力量、本真與大愛,難道就永遠不見天日、深藏心底嗎?倘若大難與大愛真是這樣一種因果邏輯關係,我們又到哪裡去尋找這筆民族的財富呢?諸如此類的問題,也是我最感興趣的。至於我的這部小書,不過像地震後的一塊碎片,倘若能為遇難的同胞帶去一份安慰,為活著的人們引出些許反省,為日後研究汶川大地震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地震學家留下一個“標本”,幸矣,足矣!
李炳銀讀李鳴生紀實文學新作《震中在人心》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後,立即就有不少的報告文學作家奔赴地震現場,實地進行採訪報導。這種及時抵達熱點現場,對於重大事件迅速進行真實文學報導的行動,很好地表現了報告文學作家的社會承擔精神和責任感。但是,作家畢竟同救災的軍隊任務不同,也和新聞記者的視角具有區別,如何在一次次的抵達現場之後有自己的成功收穫,這也許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多年以來,我們的文學曾經歷了不少大的社會事件的寫作,像1998年的抗洪鬥爭、三峽工程建設、2003年的抗擊非典災難、西氣東輸工程、青藏鐵路建設、南水北調、北京奧運會、2008年華南地區的冰雪災害和汶川大地震等,在當時,對這些題材對象的寫作,都是情動心切,轟轟烈烈。過後也確實出現了一些很好的作品,像何建明的《國家行動》、徐剛的《國難》、徐劍的《東方哈達》、趙瑜的《晉人援蜀記》和李鳴生的這部《震中在人心》等。但是,這樣優秀的作品數量太少,大量的作品卻是陷入平庸的層面,不是直觀表層的描述,就是對事件囉嗦冗長的記錄。很少看到作家自己接觸對象的新穎角度,看到作家文學藝術地處理表現對象的方法。此種現象也許可以清楚地說明,我們的報告文學作家,每遇大事,只有積極地抵達現場的努力和熱情或許還是很不夠的,還必須尋找到報告事件的途徑,創造出真正符合自己個性品質的藝術作品來。
在讀過李鳴生的這部來自地震前沿的《震中在人心》之後,我明顯感到它與不少同類題材作品的不同。首先,這部作品將報告的對象比較集中地鎖定在地震的災難性和對於受害者的影響方面,使得作品始終在一種悲涼和痛苦的記憶中展開,是一種真正接近了地震本身的報告。它明顯地區別於很多將災難只是作為背景,而只關注於搶險救災行為的作品,更區別於一些明顯是借救災在表功的功利宣傳的文字。所以,李鳴生的作品,更加接近地震災難的本身,更加容易使人在一些直觀的死亡、血淚、痛苦情景背後感受到地震的深刻危害性。作品寫到一個在經歷了地震之後,走路不會拐彎的人;寫一個在地震中嚴重受傷,平時只能夠躺在床上行動不了的人,如何在感到餘震時,奇蹟般地迅速逃到室外的情形;以及那些精神嚴重被刺激而患了精神病的患者和大量因為地震的恐怖情形及親人的突然傷殘離去不同程度地患有多種心理疾病的人們,等等。這些帶有個性和能夠說明地震可怕和持續危害性的細節,是注重現場和直觀訊息的新聞鏡頭所時常忽略的,所以,獲取這樣的細節對象,恰恰是報告文學發揮自己優勢的地方所在。報告文學是一種文學創作活動,它不應該類同於新聞傳播那樣要緊追著對象的腳步走,將自己簡單地變成一種機械的對象記錄。所以,在報告文學創作中,作家的主體性、操控性必須得到確立,讓作品的展開、進展和表現一定要把握在自己的手裡。而使人遺憾的是,這些年來,不少報告文學作家,在自己的創作過程中放棄或失去了這些主體精神和自我掌控能力,將自己簡單地變成了事件對象或人物的跟班差役,變成了採訪對象的機械記錄者。因此,就有許多作品,變成了工程建設的流水賬,變成了人物生平經歷的資料羅列,變成了跟在新聞宣傳身後的矯情伴唱。沒有主體選擇和個性發現的報告,自然會成為平庸的記錄。而李鳴生是在自己充分的主體發現感受和理解中面對和描述地震災難的,他的作品中,既包含了自己作為一個四川籍作家,對家鄉發生地震災難的悲痛憂傷感情,也突出表現了一個作家以自己的眼光發現、感受、理解和描述地震災難的個性。所以,在這樣的作品中,地震是同人們的生死命運、同人們的獨特感受、同文學細膩真實深刻的表現渾然一體的。
難得的是,作者在這樣的作品中還自覺地運用了理性的武器,從而使人們在面對地震災難時,有了反省的空間。在真實的基礎上認真地理性拷問和思考,是報告文學的靈魂,是人們在新聞報導之外還需要和喜歡報告文學的重要因素。可惜,我們的報告文學作品,如今在這方面表現得很不充分。報告文學,不管是記事寫人,還是述史,再現客觀真實的對象,只是最基礎的層面,能夠顯示作品價值和意義的是作家獨立、特別、準確、深刻和文學的理性表達。
從文學的角度看,李鳴生的這部作品,不是只在直觀的層面運行,它是深入到人們的特殊遭際、命運和心靈中的記述。所以,作品中有不少可供大家言說傳播的人物故事。而正是在這樣的人物故事中,地震災難對人的打擊禍害才變得真實具體,文學的特性和力量才能很好地得到張揚,作品也才不會隨著地震災難的過去而消失。大量真實圖片的配合,無疑在視覺上增強了作品的衝擊力,這也是這部作品的特別之處。
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家和作品
| 台北時間2010年10月19日,經過第五屆魯迅文學獎評獎委員會的評定,從130篇(部)經過公示的作品中選出了30篇(部)獲獎作品,其中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報告文學、詩歌、散文雜文、文學理論評論各5篇(部)。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首次空缺。 | |
| 獲獎作品 | 作家 |
| 《最慢的是活著》 | 喬葉 |
| 《國家訂單》 | 王十月 |
| 《手銬上的藍花花》 | 吳克敬 |
| 《前面就是麥季》 | 李駿虎 |
| 《琴斷口》 | 方方 |
| 《伴宴》 | 魯敏 |
| 《老弟的盛宴》 | 盛瓊 |
| 《放生羊》 | 次仁羅布 |
| 《茨菰》 | 蘇童 |
| 陸穎墨 | |
| 李鳴生 | |
| 張雅文 | |
| 關仁山 | |
| 彭荊風 | |
| 李潔非 | |
| 劉立雲 | |
| 車延高 | |
| 李琦[作家] | |
| 傅天琳 | |
| 雷平陽 | |
| 王宗仁 | |
| 熊育群 | |
| 鄭彥英 | |
| 王乾 | |
| 陸春祥 | |
| 南帆 | |
| 張炯 | |
| 趙園 | |
| 《中國文學跨世紀發展研究》 | 王純菲 |
| 《童年再現與兒童文學重構:電子媒介時代的童年與兒童文學》 | 譚旭東 |
| 高楠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