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期刊名稱 文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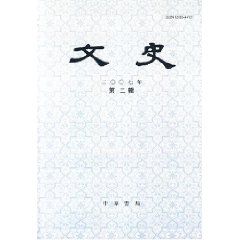 文史
文史主辦單位 中華書局
地址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中華書局
郵政編碼 100073
電子郵件 [email protected]
國際標準刊號 ISSN0511-4713
國內統一刊號 CN11-1678/K
刊期 季刊
開數 16開
期刊介紹
辦刊宗旨:存史、資政、育人,讓歷史告訴今天與未來,全面奏響愛國主義主鏇律,促進兩個文明建設,為改革開放服務。
抗日戰爭時創辦的文史學術刊物。1941年1月在重慶創刊,先後由獨立出版社、重慶商務印書館(1941年1月一卷三期起)、重慶中華書局(1944年1月三卷一期起)出版。該刊原由朱家驊發起創辦,隸屬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受秘書長吳鐵城領導,社長為葉楚倫,但都不過問社內具體事務。創刊時主編為盧逮曾。1941年6月顧頡剛任副社長兼主編,自一卷九期起直至停刊。史念海、魏建猷等都曾擔任過編輯。1945年2月,因顧頡剛在文化界對時局宣言上籤名,秘書處停發經費,刊物與國民黨的關係就此中斷,由顧頡剛自任社長,艱苦支撐至抗戰勝利,出滿了五卷。抗戰勝利後,曾兩度在上海復刊。第一次在1946年,由中國出版公司出版了兩期;第二次在1948年,由文通書局出版了三期。顧頡剛堅持自主辦刊的方針,認為“文與史是民族文化的結晶,是喚起民族意識的利器”。因此,《文史雜誌》雖系純學術刊物,但內容力求通俗,討論的問題亦能和時代相聯繫,受到讀者的歡迎。
《文史》誕生的艱難歷程
沈玉成
1959年以後的三年嚴重經濟困難,是1957年“反右”擴大化和之後的“大躍進”、“反右傾”的直接產物。值得思考的是,經濟上的困難卻帶來了學術上的繁榮。全國學術界如此,中華書局也如此。從1960到1963年,中華書局的出版物,無論數量、質量都出現了高潮。1964年“四清”以後,這勢頭就逐漸衰減。如果用過去的政治術語“馬鞍形”作比喻,這一段歷史時期在中華書局出版史上可以算是一個倒轉的“馬鞍形”。聶紺弩先生詩有“吾謀全是亦全非”的警句,昔日之非,今日之是,這當然是觀點上的根本歧異。
《文史》這個和某些人心目中的“馬列主義”格格不入的刊物,醞釀於1962年春,出版於1962年冬,到“文革”以前,掙扎著出過四輯,可以算是“大躍進”和“四清”之間夾縫中的產物。
1962年開年不久,調老(徐調孚先生)就在我們幾個人中間透露過小道訊息,說是要創辦一個《文史集刊》,由文學組來搞。這是他老先生的一貫作風,凡是碰上高興的事情,總要跑到程毅中兄、傅璇琮兄和我這個“三角地帶”(當然不是“金三角”、“鐵三角”的意思,不過是三個人的辦公桌拼成三角形而已)來嘀咕嘀咕。過不久,小道訊息更加豐富而具體,大致說,內容可以歸結為三點:一、近一兩年來,有不少單位和個人向中宣部反映,一些很有學問的老先生過去搞過不少東西,由於沒有“馬列主義”,這些東西儘管有學術價值,卻找不到地方發表。為此,周揚同志和齊燕銘同志商量,要辦一個大型刊物,專登資料、考據的文章,並決定由中華書局出版。吳晗同志是這一意見的堅決擁護者,並和金燦然同志商量(後來叫做“密謀”)了幾次,連刊物的名字都定了,即《文史集刊》。
二、刊物由中華書局出版。最早想“獨家經營”,後來由於稿源、人力的考慮,決定由《新建設》雜誌社和中華書局合編。《新建設》是哲學社會科學部的機關刊物,時常有一些出之無門、退之可惜的稿件需要找一塊園地。兩家於是一拍即合。
三、稿件由《新建設》編輯部編定後送中華書局。中華書局分工負責的副總編輯是蕭項平同志,管具體工作的編輯就是沈玉成。 調老還透露,原來想成立一個單獨的編輯組,把我調出去,他表示不願意,後來就決定附屬於文學組,我還是文學組的人。對領導上的器重,我曾經沾沾自喜了一陣子。
上面所說小道訊息的內容,事過二十年再重新體會一下,可以說確實是煞費苦心的安排。通向學術的聖地可以有種種不同的途徑,可是1957年以來,其他的通路都先後被堵,只留下一條階級鬥爭的大道,哲學上是唯物、唯心的鬥爭,歷史著作中要廢除封建王朝的斷代,古典文學領域裡民間文學是主流,不是現實主義就是反現實主義。在這熱火朝天的鬥爭之中,本來就被長期冷落了的考據和資料工作,又被統統驅逐到一間黑屋子裡加以禁閉。不過,資產階級總是“頑固地表現自己”,1961年政治上的壓力稍稍鬆弛,各種議論就通過不同渠道冒出來了。最尖銳的一個意見是由共產黨員、歷史學權威陳垣先生提出的。他在一次會議上說,寫文章只講理論,沒有材料,等於炮彈中沒有火藥,是放空炮,令人遺憾的是現在放空炮的文章太多。周揚、齊燕銘同志都是學者,自然贊成這樣的意見,因此就商量要開闢這一塊園地,然而他們同時又是政治家,所以又儘可能謹慎小心地來辦這件事。按照他們的原則指不,又經過不知道幾次的慎重研究,金燦然同志告訴我兩條:第一,它不是刊物,是書籍,所以不必向中宣部正式登記。由此,在名稱上不宜有“刊”字,即使“集刊”也不行。它就叫《文史》。在第一輯《前記》的徵求意見稿上,齊燕銘同志親筆把“刊登的文章”中“刊登”二宇改為“輯印”,可以證明金燦然同志的意見決非一時的心血來潮。第二,“三不”,即不組稿、不登廣告、印數不超過三千。自上而下,用心可謂良苦,可惜依然沒有能在“文革”中為他們“開脫罪責”。
既然不能放手大幹,原先考慮成立的編委會也隨之告吹,擬定的一份編委名單,至今仍然完整地裝訂在中華書局的《文史》卷宗里。不過儘管如此,編輯會議還是要開的。這年四月,《新建設》編輯部來了幾位同志在金燦然同志的辦公室開會,我最後被叫進去忝陪末座。會上談到了編輯、出版的有關事宜,內容全然記不得了,只有王慶成同志身穿一套毛料制服的翩翩風度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據俞筱堯同志介紹,我知道他是研究太平天國史的專家。這次會議以後,我就開始了和慶成同志的交往。和這樣一位聰明能幹而又溫和的同志合作是十分愉快的。可惜不久他又被調去乾別的,繼任者是趙幻雲和黃品蘭同志,但合作的融洽氣氛則和慶成同志主持時完全一樣。
這裡不能不談到《文史》的“發刊辭”,即題為《前記》的短文。因為它在後來曾經引起過一場軒然大波。經過幾個月的忙碌,第一輯的稿件已經準備得差不多了。一天,金燦然同志把我叫去,告訴我為《文史》起草一個發刊辭。他口授大意說:“材料和觀點是研究工作中不可缺一的兩個部分,也就是史學家正在討論的史、論關係的問題。有的老專家辛苦了一輩子,搞出來不少有用的東西,可是現在沒有地方發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只要老老實實做學問,考據資料也是有用的,也可以算一家。現在有一種不好的學風,空話講得太多,我們要反對這種學風。”言簡而意賅,我就根據這段話回辦公室冥思苦想。道理不難說清楚,文章也可能做得漂亮,但是要為這一層中心意思找出完整的、使人不易指摘的經典理論根據卻是很費腦筋。最後決定在“二百”方針的大纛之下立論,以收理直氣壯之效。於是初稿中就從“二百”談起,談到《實踐論》的原理,感性和理性、材料和理論的諸般關係,並且對乾嘉樸學進行時代和階級的分析,提出應當進行批判繼承等等,全文約三、四千字。經調老之手,初稿送上去,第二天就打了回來,說是太長,不概括。於是改寫第二稿,送上去,還說太長。我不知所以然,直接找金燦然同志有點不方便,於是就找俞筱堯同志去從側面摸底。筱堯同志說,金燦然同志的意思大約是文章長了不容易說圓滿。我這才恍然於我竟然忘記了“言多必失”的古訓。這本《文史》本來就不“馬列”,我非要講出“馬列”來,這如何能討好?我決定改弦更張,寫成一個技術性的交待,說明它的整體風格和刊登文章的範圍,其中關鍵性的一句話是,“我們要求《文史》具有這樣一種鮮明的風格,即崇尚實學,去絕浮言”。這八字方針並非我的創造,說真的我也沒有膽量創造,只是把半年來有關領導的意圖、指示,不論大道、小道,融會貫通,終於概括出了這八個字。後來第三稿通過,經燦然同志親筆修改後列印,分送有關領導審閱,竟沒有一位對這八個字提出意見,可見我的揣摹得當。
不過這樣的說法還是表明了我的餘悸未消。因為在“文革”中,這是我的第一項大罪,被鐵定為“反對毛澤東思想”,為此不知道做了多少交待檢查。所謂“鐵定”,因為確實無可逃遁。文章前面講材料和理論的關係,後面卻要“去絕浮言”,豈非要“去絕”理論?理論,除了毛澤東思想,哪裡還有第二種?邏輯嚴密,無須乎像《海瑞罷官》之類還要繞幾個彎子。我以十年待罪之身再加新罪,這回看來要斷送老頭皮了。不過人不是那么容易絕望的,面臨滅頂還總要掙扎撈根稻草。我所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態度好。於是我如實說明了當時所了解的背景,給我所作的指示,並老實承認這八個字是我概括出來的,而根據當時修正主義的甚囂塵上以及我沒有改造好的立場,我雖然沒有直接想到反對毛澤東思想,但這“浮言”客觀上可能是指毛澤東思想,罪責難逃。經過如是云云的幾次反覆交待檢查,加上我是“死老虎”,追查此事也顯然意不在我,最後就算過了關。金燦然同志其時腦子已受損害,他如何交待檢查,我一概不知,只從大字報上經常看到對“去絕浮言”的批判,也多少體會到他的日子很不好過。到後來要給他定案,還有人問我,知道不知道關於《文史》的密謀。我說根據大字報的揭發,吳晗、金燦然等的密謀是在四川飯店黑會上策劃的,我沒有資格進四川飯店吃飯,所以不知道。調查者認為我的話頗合情理,也就不加深究。
現在,痛定思痛,還有十一屆三中全會給我壯了膽,可以說實話了。五十歲以上的知識分子都可以回憶起1958年“拔白旗”的情況。三年困難,物質生產領域裡的豪言壯語傳染到精神生產領域裡,學術論壇上氣勢甚為壯盛而內容甚為空泛的文章不時可以見到,而一切對古文獻的傳統整理方法則被貶得一錢不值。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以後,政治風向有所變化,我自然也不會無所感覺。從大道、小道傳來的各種對於不良學風的批評,真可謂實獲我心,因而對《文史》的創辦深感興奮,認為是一個英明決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認真做一點材料考辨工作,也許可以校正學風上的一些偏向。這八個字的概括,雖有上級的原則指示,而在我則是蓄之既久,所以隨手拈來。“文革”中批我“心領神會”,確實毫不冤枉。不過這裡還要鄭重聲明,我不僅當時毫無一絲一毫褻瀆毛澤東思想的念頭,在今天我還是那么看,那些空話泛言,那些洶洶氣勢,和毛澤東思想如南轅北轍,正是背道而馳的東西。
我的興奮心情說明了少不更事的天真或者愚蠢。對燕銘同志細心的更改和燦然同志的“三不”,我多少感到了他們“各有隱憂”,然而又竊笑其過於小心怕事。其實這些不祥的預感並不只存在於齊、金兩位身上,何其芳同志在給那篇“發刊辭”後來叫《前記》所提的意見中已經透露出這一訊息。《前記》的改定稿列印分發給有關的領導、專家提意見,名單是金燦然同志親自擬定的。提了意見送回來的有吳晗、何其芳、林澗青、馮定等五、六位,其中以其芳同志的意見最為尖銳。他在列印稿中“改進我們的學風”一句旁邊批註了大段的意見,其中說到:“這種說法也可斟酌。我們的學風也並非不重視資料,不認真地研究、辨別資料”。其芳同志是我最尊敬的前輩學者之一,他主持文學研究所的工作,在客觀情況允許的條件下,也很有當年蔡孑民先生“兼容並包”的氣魄。據我所了解,他一向尊重資料的蒐集考訂,對《文史》的創辦是贊成的。然而在眾多的意見之中,唯獨以他的冷靜給像我這樣的人潑點冷水,其遠見卓識在二十年之後我才能領略得稍微深刻一點。
《文史》第一輯和讀者見面是在1962年底。這輯的作者陣容十分堅強,有陳垣、游國恩、於省吾、段熙仲、朱謙之、楊寬等老一輩學者,其中有的是多年沒有發表過文章的,文章的內容也相當充實。這種獨樹一幟的面貌當然引起了學術界的很大興趣,在專家中的反映是學術品格高,參考價值大。三千冊很快銷售一空,許多讀者來信要求購買,還有的專家要求寄贈,但由於金燦然同志頑強地堅守“三不”,只好由我寫信一一表示抱歉。也由此,在“不組稿”的前提下,稿件還是源源而來,第二輯很快出版,其中顧頡剛先生的《<逸周書·世俘篇>校注、寫定與評論》一文,無疑是顧先生解放以來的第一篇力作。之後的三、四輯,也保持了第一、二輯的水平。
《文史》中收錄的文章,固然有一些為多數人所注目的內容,但總的來說,生、冷、僻的題目還是多數。發表這一類文章,原本是創辦目的之一,因為這些都屬於其他刊物上所不能發表的文章。由此,審稿也成了一個大問題。《新建設》編輯部的工作做得認真,然而按規定在中華書局還需要審稿。這么多專門而深奧的問題,學識淺薄如我如何應付得了?好在金燦然同志有言在先,所有編輯部的專家都可以做後盾。說實在的,在燦然同志的辛苦經營之下,當時的中華書局也真是人才濟濟,擁有各方面的專門家,傢文學組的王仲聞、程毅中、傅璇琮,古代史組的孫人和、傅振倫、陳乃乾、趙守儼,近代史組的李侃,哲學組的章錫琛、童第德、馬非百、陳金生等各位前輩和同輩的專家,都給《文史》看過稿子,提出過詳盡中肯的意見。除了極少數過於專門、冷僻的稿件需要請教社外專家,其他都可以“內部消化,就地解決”。文學組的領導徐調老,由於事情太多,通常只是就我編完的稿子翻閱一下就送給蕭壩平同志。蕭項平同志是一位學識淵博、性格寬厚的老革命,但對稿件的質量從不馬虎,每輯幾乎都有被他打退回來的稿子,或是決定不用,或是要我找專家重新審讀,對稿件的學術水平作出更恰當司靠的估價。由於他藹然可親的長者之風,在他領導之下工作,總有一種穩定和舒暢的感覺。1970年他因心肌梗塞突然逝世,當時我正遠在鹹寧幹校,訊息傳來,想起《文史》一段往事,除了哀悼以外,心裡還湧現出一陣難言的空虛和惆悵。
隨著政治寒流的逐漸加劇,《文史》的處境一天天艱難。這種氣候的變化,在北京的學術界,反映是比較敏銳的;然而在外地,尤其是一些只懂學問而不懂政治的老先生,感覺都依然遲鈍,各式各樣的稿件還是不斷賜寄。這不僅使我不安和抱愧,也為金燦然、蕭項平這兩位共產黨員正直的良心上增加了負擔。好不容易苟延殘喘,擔著風險勉強在1963年10月和1965年6月再出了兩期,從此無疾而終。
1980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華書局領導以充分的勇氣恢復了《文史》的出版,其時我已離開中華書局,主其事者為吳樹平同志。樹平同志的學力和能力都比我強得多,他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在乾。再以後是年青的李解民和盛冬鈴同志,同樣也是精乒簡政,人少而辦的事情多。這些都使我由衷地佩服。現在《文史》第三十輯已經編成,我這個第一任責任編輯回憶往事,更增添了對未來的信心,並聊以這篇不成樣子的短文紀念中華書局成立七十五周年和《文史》第三十輯的出版。
與歷史、考古、文物相關的雜誌
| 中國歷史悠久,地下文物豐富。現在與之相關的期刊雜誌也相當地多,一下就讓我們盤點一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