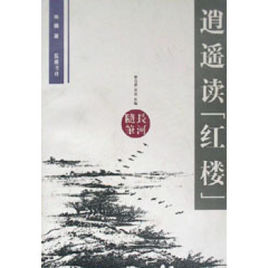概述
 《逍遙讀紅樓》
《逍遙讀紅樓》比起古之《金瓶梅》今之《廢都》自是小巫,但的確屬“嫖妓的語言”。嫖客和娼婦床上“交易”,當是只能這樣吆喝,才“醜態畢露”,一絲不掛。不止一位評點家指出,這段文字寫賈璉醜態,自然會聯想想到與之旗鼓相當的鳳姐,謂之“寫賈璉是寫鳳姐也”;甚至說“聲聲多姑娘,目視鳳姐也”。匪夷所思,有失恕道。不過,把這段文字視“送宮花”一節的“補白”、補其未寫之處,實文中已有之義。更有大者,曹雪芹不屑以“性”媚俗,這段“嫖妓”文實可直通四十四回“變生不測鳳姐潑醋”。貫串其間者是永遠不倒的“醋瓶子”多姑娘變成了鮑二家的,登堂人室,上了鳳姐的床。由此引發風姐平兒鮑二家的賈璉打出手的大混戰。重要的是賈母史太君以“史家”口碑對這場混戰所下結論。她老人家積數十年相夫教子理事治家之經驗,面對這場倏然而至的“桃色風暴”,處變不驚,淡然一笑,說道:
什麼要緊的事。小孩子年輕,饞嘴貓兒似的,那
里保得住不這么著.從小兒世人都打這么過的。
老太君輕輕巧巧一席話把“世人”全都打人“饞嘴貓”動物系列。當然包括榮、寧二府上上下下數百號人物,也不排斥老太君把自己擺進去現身說法(有的評點家早就懷疑當年史侯家大姑娘變成賈母之後,不幸早寡,很可能和“榮國府國公的替身”、“先皇御口親呼為‘大幻仙人”、“當今封為‘終了真人”’的清虛觀法師張道士有一手)。此“法”即賈府祖傳秘方的性道德觀。永遠不倒的“醋瓶子”多姑娘是人證,傻丫頭拾到的繡春囊是物證。所以,寫賈璉和多姑娘用“嫖妓的語言”,經史太君上升到理論高度,豈止適用於一鳳姐,簡直是賈府老鴰一般黑、打擊男女一大片的“語言”,和柳湘蓮所謂“只兩個石獅子乾淨”同一機括。那么,這短短數百字“嫖妓的語言”,實則為偌大“嫖妓世家”傳神肖形、樹碑立傳。一句“醜態畢露”,目光四射,痛心疾首,筆下多少沉重激憤之情:誰解其中味?
我師何太痴耶?若雲無朝代可考,今我竟借漢唐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奠若我這不藉此道者,反倒新奇別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 由是觀之,曹雪芹“時間觀念”的模糊化,並非信筆一揮的即興之作,而是深思熟慮一以貫之的藝術構思。“旨評”所謂“慣用此等章法”,於曹翁之用心有戚戚焉。至於所謂“年表如此寫亦妙”之“妙”,則在於“如此寫”始能生出無始無終的“無限”,安置那“大荒山,無稽崖”,營造出“太虛幻境”,:抒寫作者“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通靈”、“夢幻”,於《紅樓》全書美學品格,至為緊要。曹翁生恐眾人不解,特特申言:“此回中凡用夢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脂評”之“妙”字,應是對一部大書之“夢幻”意境潛研含玩後而心有所會吧。心會意通,於書於人,均非易事,是要有幾顆“藝術細胞”的。光靠“學問”,往往越做越遠。比如《紅樓夢》中人物年齡模糊、事件時序錯亂,向來使某些紅學家頭疼,不得其解而硬要去解,終歸還是解不開。據有心人計算,書中“時間”有“誤”者前八十回中達五十三項。後四十回一項也沒有。那么,高鶚續修全書,為何不把前八十回的“誤差’’予以更正?難言之矣。如果我們遵循曹翁提示,體察“夢幻等字’’是“此書立意本旨”,“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則五十三項“誤差”是否可化然得解呢?不敢自專,還是“信由你”為妥。“脂評”所言“年表如此寫亦妙”,僅供參考。
去年夏天,“紅學”界最轟動的莫過於通縣張家灣“曹雪芹墓石”一案子。迄至於今,真真假假仍辯爭未休。大概還會辯下去。我想說的是;上海某大報發布這一訊息。時,嚇得我出了一身冷汗。不知“北京專電”傳媒哪個軟體感染了風雅之至的“米開朗琪羅病毒”,白紙黑字赫赫然曰:墓石鐫刻著“曹公諱爹墓壬午”數字。撰者並強調:儘管關於曹雪芹有種種爭論,但其“姓曹名諱奓字雪芹”乃世所公認。嗚呼!石破天驚之語,讀之欲不冷汗,豈可得乎?偏偏這個偉大的“奓”之音讀、本義,我已忘得乾乾淨淨。知也無涯,趕緊查《辭源》。手到擒來,“奓音奢,開啟也”;書證引的是《莊子·知北游》。一卷在手,隨之游去,卻引出一樁不忍釋之的故事。在莊夫子無奇不有的冊頁中,竟讀出一則“紅樓小品”:
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幾闔戶發行晝
瞑,婀荷甘日中奎戶而入,日:“老龍死矣!”神農隱
幾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日:“天知予僻陋慢施,
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於之狂言而死矣!”
接下去是借人弇垌吊之口發哲學講義,不管它了。神農不去嘗百草到這裡幹啥?除非甘當呆鳥,最好別去考證。只說這婀荷甘,好清爽的名字,定是風露清愁綽約秀逸神仙般人物。與神農關係看來很不一般。大白天男同學正關門睡午覺,竟破門而入,大喊大叫。殊料神農同學聽說老師死了,竟丟掉手杖大笑。不悲不戚,實屬咄咄怪事。幾句沒頭沒腦的話,勉強譯之:“咱們秉自然大德的老師,知道咱混小子神農怪裡怪氣,自由散漫,沒啥出息,丟下咱們撒手去了。這下好了,咱老師沒揭我那些狂言的老底就去了,永遠地去了。”關鍵是“狂言”二字。成玄英疏曰:“狂言,猶至言也。非世人之所解,故名至言為狂言也。”原來如此!我的心忽然感到悲涼。似乎從這百十來字的生動場景、跌宕情感中,讀出了“滿紙荒唐言”四句
血淚交進之言。而潛台詞則尚有“老師死了,而今而後知我神農者,其惟同窗眤友、至愛親朋婀荷甘乎?”誰解其中味?定要類比紅樓阿誰,便是附會。然讀莊讀紅,未必不可用同一讀法。既莊生夢蝶、蝶夢莊生,當然也可莊夢紅樓、紅樓夢莊。於是此曹彼莊兩位說夢大師,神通對
語。或清辭麗句,或汪洋恣肆;千古情會,都把追求精神的超越、生命的飛揚、靈魂的自由作為人生最高境界——自然之美與美之自然。且知其永遠難臻此善境而永遠追求不止,如夸父大神然。如此追求,當然有夢幻,有破滅,有虛無,有絕望;-然也有執著,有憧憬,有歡欣,有生生不已的活力。說句二百五瞎抬槓的話:如果莊曹釋老之屬全是不可救藥的悲觀、虛無主義者,他們還嘮嘮叨叨說那么多話,寫那么多書做甚?天地為心,生民是育。我看他們其實都是胸懷大志、幹勁十足地表現自己,·要用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改造世界與中國濟世拯民呢。或黃鐘大呂,或絲竹佳妙,主鏇律乃至誠之音、溫煦之聲。當然,莊少了些人間煙火,多了點仙風道骨,往往使人產生此曲只應天上有之疑慮。曹則三教九流,廣結善緣,歌哭同之,歡言與共,更能走進肉胎凡骨者的心。——奓,“開啟也”;歪打正著,錯得其理。
立此存照,暫毋庸議。想來《中國小說史略》中關於《紅樓夢》的評說,吳先生·應當讀到,《日記》中似未言及。無論如何,魯迅聽說“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應屬不刊之論。吳宓以其獨特的身世境遇,“悲涼之霧”,容有同感。然其“呼吸而領會之者,則與賈寶玉大異其趣。因為按吳宓《年譜》所引“中國之家庭是一政治組織”的說法,賈寶玉的的確確是賈府唯一的“持不同政見者”。這樣一位相隔兩個世紀的“前衛’’人物身影,離吳宓實在太遙遠、太遙遠,亦可謂之不可企及吧。
何以故?:陳寅恪先生是真正“讀透”了吳宓的。而且,比吳宓自己更懂得這一個“吳宓”。1930年4月22日,吳宓記稱:
正午在葉君處午飯。陳寅恪同餐,謂昔在美國初
識宓時,即知宓本性浪漫,惟為舊禮教、舊道德之學
說所拘系,感情不得發抒,積久而瀕於破裂。猶壺小
受熱而沸騰,揭蓋以出汽,比之任壺炸裂,殊為勝
過。彼謂宓近來性行驟變者,實未知宓者也云云。
《日記》第五冊,61頁
陳寅恪臧否人物,頗富詩意。吳宓先生“詩意悖論”悲劇之由來,或可稍得其解乎?
……
目錄
逍遙讀《紅樓》(代序)賈府眾姨娘
沒話找話論賈赦
話說邢夫人·鴛鴦事件
繡春囊之變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真假有無說“太虛”
秦可卿生死謎
子虛烏有“龍禁尉”
似有若無“秦可卿”
“我師何太痴耶”?
查考“嫖妓的語言”
“張本”《紅樓夢》
姑妄聽之“脂硯齋”
俞平伯善解“風姐夢”
孤證不立
“素有瓜葛”解
碎紅一片說“曹奓”
曹雪芹的“級”
《吳宓日記》中之《紅樓夢》
與《紅樓夢》相關的圖書
| 《紅樓夢》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藝術性的偉大作品, 代表了古典小說藝術的最高成就。與《紅樓夢》相關的著作燦若繁星,下面我們就來盤點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