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書名:身份
 《身份》
《身份》作者:米蘭·昆德拉
譯者:董強
書名編號:JCDSL22
版本:VX/VN
發行時間:2010
語言:國語
出版年:2003-02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內容
十六七歲的時候,她特別喜歡一個隱喻;是她自己想出來的、聽來的,還是從哪裡讀到的?沒有關係。她想成為一種玫瑰香,一種四處擴散的香味,四處去征服。她希望就這樣空透所有男人,並通過男人,去擁抱整個世界。玫瑰四處擴散的香味:那是對艷遇的隱喻。這個隱喻在她即將成人之際開放,就像是對溫柔地與男人混雜的浪漫許諾,對空越所有男人之旅的邀請。可是,她天生又並非是一個常煥情人的女人,這個朦朧的、抒情的夢,很快就在她寧靜而幸福的婚姻中沉睡過去。
《身份》是米蘭·昆德拉用法文所寫的第二部小說。作品完全擺脫了昆德拉用捷克文寫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等名作的政治背景,講述的是一對情人之間微妙的感情生活。昆德拉利用一對情人在海邊度假的偶然經歷,巧妙地融現實與虛幻為一體,從哲學的層面探討了人與人的另外一個“他者”之間的複雜關係,從而對“身份”這個富有特殊意義的定義作出分析。
編輯推薦
最細膩真摯的文字,最鮮明震撼的觀念,讓您深切體悟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獨家中文簡體字著作權
·北京、南京、上海翻譯大家聯手
·作者特別指定、根據2002年最新修訂法文版全新翻譯
什麼是“身份”?
《身份》的主題在作品名中已說出:“人的身份”問題。人”總是以某一身份出現,一個女人,在家以“母親”的身份出現,
 米蘭·昆德拉作品
米蘭·昆德拉作品在公司以“員工”身份出現,在愛情關係中以“別人的情人”身份出現,在政治共同體中她以“公民”身份出現。與“身份”對應的是“關係”,人總是得處於和他人的關係中,“身份”就關乎個體在與他人的交往中怎樣建立“自身”。儘管以“身份”作為題目到法國時期才出現,但昆德拉對“身份”的思考從來沒有停過。“在捷克時期,“人”更多地被放到時代背景中去看待,在一個抗拒隱私、求同、“共產主義”理想與責任的重負下的社會下,人如何存在?對人的思考跟更多體現在,人的個體性與社會的同化的對抗。而到法國時期,時代背景變得不重要,個人依然要與社會對抗,但社會已不再是某一社會,社會不再代表某一“真理”,但個體仍然無法逃離他人的目光,個人還得與“交際文化”下的“共同體”對抗。在捷克時期,“人”要逃避的是被“單一化”,在《身份》中,問題不再停留於逃避淹沒在大眾中,還涉及到“身份”建立的問題。《玩笑》里,路德維克因不願意和大眾一起“嚴肅”,所以他被孤立。那么是否意味著,法國的自由社會能為個體逃避“隨大流”提供空間。結果還是“不”。
《身份》中,昆德拉的兩位主角,和他以前的人物一樣,不喜歡“同流合污”。尚塔爾的“不喜歡”是在“隨大流”面紗後的,她有無數的面具(無數的身份?),以致她的情人讓-馬克常常要尋找“他的尚塔爾”。尚塔爾和昆德拉以往討厭“大眾”的角色不同,她和“大眾”相處得很好,在同事眼中,她有權威但也親切,在大姑子眼中,她和善喜歡和大伙兒待在一起。但尚塔爾心底卻討厭這些“大眾”:她常在開會的時候胡思亂想,看不起同事的發言;她憎恨大姑子一家,以致和前夫分開後再不和他們來往,大姑子找到她,她卻忍無可忍地把他們趕走。甚至,她慶幸孩子的夭折,正是孩子的離去使她“自由”了,可以勇敢面對這個她“不愛的世界”,使她不必假惺惺地喜歡這個世界。讓-馬克坦然接收自己的“不喜歡同流合污”,甚至樂於被世界拋棄。他不斷地想像自己處於“邊緣”,他說自己和乞丐是一樣的,都是無家可歸的人。他先是把象徵著“回憶”的朋友拋棄了,F是他中學時代的好朋友,但是F“背叛”了他,很久以後F病了,讓-馬克去看他,但找不回“回憶”了,最後F死了,而他卻不感到一點震動。然後,他把夢想也拋棄了:醫生的理想使他挫敗,其他職業也不再勾起他的興趣。最後,他把全世界壓在尚塔爾身上,只有“她”才使他的人生有意義,他為“她”活著。
情人的目光
“我的目光再也不放開你。我要不停地看著你。”最後,尚塔爾久久注視著讓-馬克。
“情人的目光”是弗朗索瓦•里卡爾評論《身份》的文章題目,“情人的目光”,既表示尚塔爾與讓-馬克的愛情,也暗示著他們的自我“身份”確認——在情人的目光中確立“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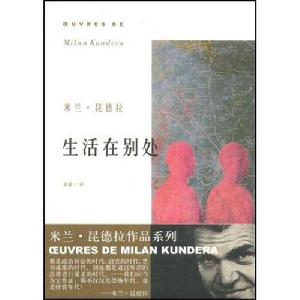 米蘭·昆德拉作品
米蘭·昆德拉作品儘管尚塔爾和讓-馬克面對“大眾”選擇了不同方式,尚塔爾主動融入形成一層虛偽的面紗,讓-馬克選擇逃避,但無論如何,他們都不認為這是真正的“我”,他們都把真正的“自我”留給了對方。是的,他們寧靜的愛情關係中,通過對方的目光找到了自己,直到,直到有一天,讓-馬克的遊戲破壞了這種目光。隨著年齡的老去,有一天,尚塔爾突然陷入到“男人們不再回頭看我了”的驚慌中,為了把她從這種慌亂的心態里解救出來,讓-馬克決定給尚塔爾寫匿名信,他虛擬一個暗戀者的身份,向尚塔爾表達越來越狂熱的愛情。尚塔爾深為自己仍被人暗戀而陶醉,她從這虛無的“艷遇”感受到了內心的激情與欲望。而讓-馬克開始因尚塔爾對艷遇的沉醉迷茫。最後,尚塔爾發現了真相,陷入失望與憤怒。
昆德拉給了尚塔爾兩個意象,一個是被“白色籠罩著的寧靜的大陽台”,淡然、寧靜、美好;一個是“穿著紅睡衣,就像一把火焰的欲望酒神”。前者是尚塔爾和讓-馬克的愛情關係,除他們外的世界只是一片空白,隔絕了激情,而寧靜永恆。“跟讓-馬克一起生活了很多年,有一天跟他一起來到了海邊:他們在露天用晚餐,坐在一個搭在水上的木版陽台上。在她的記憶中,那是一片白色:木板、桌子、椅子、桌布,一切都是白的。路燈柱漆成了白色,在夏日的天空下,燈光也是白色的。天還沒有全黑下來,天上的月亮也是白色的,將周邊映得一片白。”後者是尚塔爾的欲望,是對外界的強烈欲望,是對“一切男人”的追求。讓-馬克寫的匿名情信首先提出這個意象,“我用一件大主教的胭脂紅的大衣遮住您雪白的身軀。我將這樣裹著的您送到一個紅色的房間內,放到一張紅色的床上。我紅色的女主教,美不可比的女主教。”從此,尚塔爾數次穿著紅色的睡衣和讓-馬克做愛,甚至想像他人觀看。
作品開頭,讓-馬克一出現,就在沙灘上尋找尚塔爾。在沙灘上,在漫步者遙遠的身影中辨認尚塔爾,他想像尚塔爾的死亡,想像她就在他眼前了,他向她招手,直到那女人轉過身來,“這位被他誤認為是尚塔爾的女人變得越來越老,越來越醜,嘲諷地變成了另外一個女人。”而且,這種誤認不是偶然的事。“將自己心上人的模樣跟另一個人混淆起來。這在他身上已經發生過多少次了!”“混淆”與“尋找”。讓-馬克知道尚塔爾的不同面具,他害怕這種面具,他問自己,“假如在這次單獨的相見之前,他與她已經很熟,而且每次都是見到她與別人在一起的樣子,他是否還能夠在她身上找到他所愛的她?假如他只熟悉這張她向同事、上級、下級展示的臉,這張臉還會讓他感到,讓他著魔嘛?”面具使讓-馬克在人群里分不出“她”與其他人。他混淆了,混淆了尚塔爾與其他人,混淆了他的尚塔爾與他人中的尚塔爾。這使讓-馬克必須不斷地尋找尚塔爾,在人群中找回尚塔爾,撕掉尚塔爾的面具,讓她重新成為“他的尚塔爾”。
 米蘭·昆德拉作品
米蘭·昆德拉作品讓-馬克把尚塔爾外的世界徹底拋棄了,他的唯一任務就是不斷尋找尚塔爾。他唯一的擔憂就是找不到尚塔爾。“讓-馬克做了一個夢:他為尚塔爾擔心,他去找她,在街上跑,最後他看見她。她背對著他,正在走路,越走越遠。他在她後面跑著,呼喚著他的名字。……他看到前面是另一張臉,一張陌生的、讓人看了不舒服的臉。然而,那並不是別人,是尚塔爾,是他的尚塔爾,一點疑問也沒有,但他的尚塔爾有著一張別人的臉。……(他)想給這張變了形的臉注入她原先的樣子,她那喪失了的特徵。”尚塔爾同樣需要讓-馬克,每當她對外面的世界迷失時,她向讓-馬克求救:“她覺得被救了,因為讓-馬克的聲音是愛情的聲音。”但是,尚塔爾並沒有徹底離棄愛情外的世界,她依然有“夢”,有著對外界的渴望,“她向成為一種玫瑰香,一種四處擴散的香味,四處去征服。她希望就這樣穿透所有男人,並通過男人,去擁抱世界。”尚塔爾對外面的世界是矛盾的,一方面她厭惡這個“無聊”的世界,另一方面,她仍渴望從中找到驚喜。正是這種矛盾使她陷入“男人不再看我”的失落中。如果她只擁抱和讓-馬克一起的世界,她不必介懷“一切的男人”,但是她捨不得放棄“夢”,“夢”燃點了她的激情使她保持在人群中,但同時毀了她的寧靜。
尚塔爾和讓-馬克在彼此的愛情中找到“身份”,但這身份是“脆弱”的。讓-馬克經常找不著尚塔爾,換言之,他也經常找不到自己。尚塔爾期待著“艷遇”,而虛偽的“艷遇”最終也破壞了她脆弱的身份。讓-馬克假扮暗戀者的行動,使人想起了昆德拉在《好笑的愛》里的短篇小說《搭車遊戲》。一對年輕情侶出於遊戲的目的,在搭車過程中虛構了另一場“愛情”,男孩為了考驗女孩的愛情,讓女孩扮演一個與真實的她完全相反的角色。結果他們在愛情的考驗中迷失了,男孩被女孩扮演的“真”激怒了,不顧女孩的反對,以對女孩扮演的角色的態度來對待女孩。最後,女孩驚恐地哭喊,“我是我,我是我。”女孩的哭喊是那樣強烈,使我們不得不一次次地想,在愛情里,我們的愛情對象是誰?哪一個才是他/她?我心中的他/她與真實的他/她一樣嗎?還是我一直錯以為“這就是他/她”?同樣,讓-馬克的假扮,使他們對心目中的他/她產生了懷疑。而幸運的是,這一次,昆德拉多了份溫情,尚塔爾有著和《搭車遊戲》的女孩不一樣的結局。她也經歷驚慌,在超現實的結尾里,尚塔爾走進了一個群交的房子,被釘死的門,七十歲的男人改掉了她的名字;但不必在驚慌中結局,全書如此結尾,尚塔爾在讓-馬克的呼喚中醒過來,她注視著他,“我的目光再也不放開你。我要不停地看著你。”他們在對方的目光中,找到了自己的“身份”。
邊界在哪裡?
昆德拉用尚塔爾在夢中醒來作為結局,但是全文找不到入睡的文字,是哪一刻從現實進入到非現實的?昆德拉和我們一樣迷糊。“於是我問自己:是誰做夢了?誰夢見了這個故事?誰想像出來的?是她嗎?他嗎?他們兩人?各自為對方想出的故事?從哪一刻起他們的真實生活變成了兇險惡毒的奇思異想?……究竟確切地是在哪一刻,真實變成了不真實,現實變成了夢?當時的邊界在哪裡?邊界究竟在哪裡?”昆德拉一連串的發問,使人從尋找變為絕望,難道真能找到邊界嗎?也許,根本沒有邊界,真與偽之間根本不存在那一條清晰的邊界。沒有那么清晰的一刻,我從“真實的我”變為“面具的我”。真實的身份與假扮的身份間,並沒有那條清晰劃分的界。
書摘
她再也無法忍受這位看不見的觀察者的嘲諷的目光,一回到家中就向衣櫥走去。她看到她的那一堆胸罩,有件東西讓她吃驚。當然,昨天她就發現了這一點:她的圍巾沒有像她折的那樣摺疊著。她昨天那種興奮的狀態使她很快就忘了這一點。可這一次,她可不能讓這一隻不是她的手留下的蛛絲馬跡從她眼皮底下溜過。啊,太清楚了!她讀那些信了!他在監視她!他像個間諜一樣在窺視她!
她心中充滿憤怒,衝著不同的對象,衝著那個陌生男人,他也不說聲對不起,就拿一些信來煩她;衝著她自己,居然傻乎乎地把它們藏起來;也衝著窺視她的讓-馬克。她取出那堆信,走向(她已經多次這樣做過!)洗手間。在洗手間撕毀它們、扔到水裡沖走之前,她又看了最後一遍。她越看越有疑心,覺得筆跡很可疑。她仔細檢查一下,每一次都是同一種墨水,字元都很大,微微向左傾斜但每一封信又都不同,仿佛寫信的人沒能保持住同一種字型。這一觀察讓她感到十分驚訝。她不撕信,坐到桌前,又讀起來。她停在第二封上,那是對她上洗染店時的描寫:當時是怎么發生的?她當時跟讓-馬克在一起,是他拿的手提箱。在店裡,她記得很清楚,也是讓-馬克讓那女老闆發笑的。她的通信者提到女老闆的笑聲,可他怎么能夠聽到這笑聲?他說是從街上觀察她的。可有誰可以觀察她而不被發現呢?沒有什麼杜·巴洛,沒有什麼乞丐。只有一個人:那個跟她在洗染店裡的人。那句“某種人為地添加到您生活中的東西”,原先她以為是針對讓-馬克的一種笨拙的攻擊,實際上是讓-馬克本人帶有自戀性質的獻殷勤。
米蘭·昆德拉作品集
|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捷克小說家,生於捷克布爾諾市。1967年,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玩笑》在捷克出版,獲得巨大成功,在捷克當代文壇上的重要地位從此確定。於1975年移居法國,曾多次獲得國際文學獎,並多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代表作品有《笑忘錄》、《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