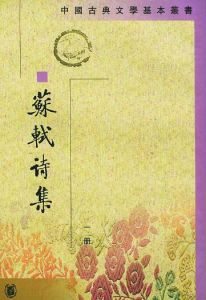書籍簡介
《蘇軾詩集》蘇軾詩集,宋代流傳的主要有全集本(收在《東坡前集》卷一至十九,《東坡後集》卷一至七及《東坡和陶詩集》中)、集注本(包括四注、五注、八注、十注等)、分類注本(王十朋《百家注分類東坡詩》二十五卷)、編年注本(施元之、顧禧合撰的《注東坡先生詩》四十二卷)以及《超然集》、《黃樓集》等選本。元、明兩代,全集本與分類注本迭經翻刻,集注本與編年注本未見流傳,選注、選評蘇詩成為社會風尚。
清人宋葷、邵長蘅、馮景、查慎行、翁方綱、沈欽韓、馮應榴、紀昀、王文誥等,分別在蘇詩編年、箋注、評論、考訂、刊行方面儆了許多有益的工作,而馮應榴與王文誥可以說在清朝中葉做了總結。
新版說明
新版《蘇軾詩集》正是歷代流傳的各種蘇詩刻本的合情合理的延續,尤其是繼承了清人的校訂成果而又有所發展,進行了新的整理加工。本書在校訂文學古籍方面提供了成功的經驗,也留下一些有待探討的問題,頗引人注目,特加以評介。
一、底本的選擇
清人段玉裁云:“校書定是非最難。”又云:“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後可斷其立說之是非。”校點古籍首先必須慎重挑選底本,這是校點工作的基礎,有時關係到一部古籍整理的成敗。底本選得好,校訂整理,事半功倍;底本選不好,則會帶來一系列麻煩。
《蘇軾詩集》用清王文誥(1764一?)的((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道光二年武林韻山堂王氏刊本,以下簡稱集成)作底本,而不用久負盛名的清馮應榴(約1740-1800年)《蘇文忠公詩合注》(以下簡稱合注),這是一個十分大膽的抉擇。
校點者孔凡禮同志在本書《前言》和《點校說明》中陳述了選用集成做底本的理由。認為集成比合注問世晚二十年,“它比較合理地調整了查注①、合注中一些篇目的次第”;“刪去了合注中繁冗的部分,增加了紀昀的一些評語和他自己的案語(即[誥案])”,“詩注部分的篇幅,略減於合注十之二,比較簡明”。
但是前人對集成也有過截然相反的評價。最早的責難來自馮應榴之孫馮寶圻,他說集成對合注“陰據之而陽熬之”,進而批評王文誥:
考核事跡,排次年月,自謂於論世知人之學加密,而多失之鑿且固。元刊《王狀元集百家注》本,宋刊《施顧注》本及影鈔本都未目睹,但據此書(合注)所采,翦截移易,自謂簡明該括,而多失之陋且略。至於《南行集》及“他集互見詩”、“補編詩”,恣行刪削,一變查注本來面目,顧詡詡然以為搜剔淨盡,永斷葛藤,又何其專輒僭妄耶?②針鋒相對的兩種意見擺在面前,從而要求我們必須對集成與合注的得失認真加以考查比較;也只有對兩書各自的優劣短長做到心中有數,才能揚長避短,合理地綜合地利用它們。下面就此做些初步的探討。
首先,王文誥確實沒有廣搜異本,更未曾目睹宋、元諸善本,這一點馮寶圻說對了。王文誥對蘇詩正文,自注及各家箋注的采輯彙編,主要依賴合注提供的資料,他確實是坐享其成,只搞了些“翦截移易”的編輯加工。他在蘇詩的校訂方面絕少建樹,充其量不過在查注、合注提供的異文之間做出自己的取捨。於是,合注自身的某些疏誤,集成往往因襲不改。例如《梅花》(其一)“一夜東風吹石裂”句③,合注誤“石”為“破”,致使句意難通,集成竟從誤仍作“破”。本書據諸本校改為“石”是對的。更有甚者,由於王文誥刪略不當,“翦截”失誤,還增添了某些新的訛謬。例如《百步洪》(其一)“描四山眩轉風掠耳”句④,合注原本有雙行小註:“(施注)《文選》班孟堅《西都賦》:‘目眩轉而意迷。’風掠耳‘用’耳後生風’意,見後卷二十《安國寺尋春》詩施注。”這裡的“風掠耳”云云,是馮應榴的說明文字,做敘述口氣。王文誥見不到施注原刊本,無從校核,對合注採取注文互見的體例亦未加辨析,竟將馮應榴所說"風掠耳"云云兩句話,刪後句存前句,合併到該條施注中。除此類荒唐的合二而一外,刪改舊注乃至蘇詩正文的現象,在集成全書中亦不乏其飼。因此,用集成做底本,必然在校勘方面留下更艱巨的任務。
不過也應指出,王文誥生活於清朝乾嘉年問,他從公開流傳的《蘇詩合注》中,無所顧忌地轉錄有用資料,也是無可非議的。況且他直接採用“榴案”(馮應榴的“補註”)時,一般也標明所自(集成改稱“榴案”為“合注”)。合注也同樣“合”進了施注、類注(王注)、五家注、邵注、查注等各家注文,並有所“翦截”。這不是抄襲。通讀集成全書,王文誥掠前人之美而不標出處者實不多見,因而也談不上“陰據”。唯有上述王文誥因治學粗疏而“翦截”失誤者,應由他本人承擔“陋且略”的文責,不應委過於前賢。幸而此類失誤並非大量存在。
公平地說,王文誥對合注的“翦截移易”,大體合情合理。例如《雙鳧觀》詩“王喬古仙子”句(卷二,82頁),合注先引馮景注《後漢書·王喬傳》云云,說明蘇詩原句化用了古老的傳說故事,本已經夠了。但它接下去又引查注,據《列仙傳》、《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學林》等書,考訂《後漢書》有誤。這種考訂,於闡明東坡詩旨無補益,徒增篇幅,浪費筆墨。集成只保存馮景注而刪查注,確實比較簡明。又如合注中對“區區”、“歷歷”、“書生”、“苦辛”等詞語,亦加注日“字習見”,這類無聊的注釋均被集成翦除,也是理所當然的。
合注資料翔實,某些考訂亦頗見功力,為校注蘇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但在清朝考據學風影響下,馮應榴對諸家舊注兼收並蓄,務求詳備,不避重複,有些脫離詩旨的考索甚覺乏味。誠如前人所說:“徵引太繁,往往喧奪。”⑤將讀者的注意力引進煩瑣舊注的汪洋大海,對蘇詩的意境主旨的理解反覺淡薄了。比較起來,集成創見不多,也有失於煩瑣處,但比合注簡明,切合實用。特別是遞補了紀昀評語和“誥案”,充實進新見解新資料,校正丁包括合注在內的前輩注家的某些錯誤,確有勝於合注處。校點者從節省篇幅,務求詩注之簡明、減少印製負擔著眼,舍合注而取集成,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說到“考核事跡,排次年月”,一向被認為是王文誥的一大專長。王文誥有《蘇詩編年總案》四十五卷,就是擴編的東坡年譜,提供了調整部分蘇詩編年的史料依據,受到人們的重視。例如《贈上天竺辨才師》(卷九,464頁),宋嘉定刊《施顧注蘇詩》將它編為卷十首篇;而卷十所收詩乃“時守高密作”。蘇軾守密州在熙寧七至九年間(1074-1076年)。可是,這首《贈上天竺辨才師》題注又云:“疑悴杭日所作,誤置此卷”。施注對此詩編年似乎舉棋不定,故兩說並存。查注卷七引《鹹淳臨安志》等書,考出“東坡■杭時,辨才正住天竺,贈詩必於此時”,並說:“宋雕本及施氏本俱載此詩於密州卷中,訛矣。”④合注從查注,將此詩移編於熙寧五年(1072年)《雨中游天竺靈感觀音院》詩後,進而指出查慎行“刪施氏原注⑦,而為己之考證,非也。”體現了尊重事實,不掠他人之美的學術道德。王文誥獨闢蹊徑,先據詩中“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腹。師來為摩頂,起走趁奔鹿”等句,確認此詩應是蘇軾於次子蘇迨(長頭兒)四歲那年所作。《蘇詩編年總案》卷九援引元豐八年(1085年)蘇軾赴登州時《與楊康公書》云:“某有三子,其次者十六歲。”上溯十六年,則蘇迨當生於熙寧三年(1070年),他四歲時(虛歲)應是熙寧六年,故《贈上天竺辨才師》寫於這一年(1073年)。由此可知,王文誥考核蘇詩編年時,千方百計求內證,即從蘇軾詩文本身的內容聯繫上找線索,這無疑是細密可靠的方法。因而他的意見有較大參考價值。他比施注、查注、合注高明之處,正在於此。仍以上詩為例,合注編者馮應榴同樣看到過蘇軾《與楊康公書》中的自述,他在合注卷首《東坡年譜》內的一條“榴案”中,據《斜川集·送仲豫兄赴官武昌敘》誤算出蘇迨應生於熙寧二年(1069年)。明知這與《與楊康公書》推導出的生年(1070年)有矛盾,卻據查注“考《贈辨才師》詩為熙寧五年作”,認定“以二年生為確”,進而疑《與楊康公書》,“安知非六字有訛耶?”總之,寧信蘇過不信蘇軾,寧信查注對編年的考證,不信東坡自述,未免本末倒置。王文誥對合注的疏誤發出"此是何見解耶"的反詰⑧,駁正有力,令人信服。
我們承認王文誥對蘇詩編年的考訂“大體可信”,但也不應盲從。集成武斷臆改、“失之鑿且固”的情況也是有的。如《和陶雜詩十一首》(卷四一,2272頁),查慎行編為元符三年庚辰(1100年)作,合注從之。集成曰:“查注於《和陶》全未了,又以此三年⑨詩少,概以《和陶》填入輳數。合注知之,又以逐首拆改,難以藉手,故不肯明言其事,但朦朧委過於查也。”王文誥將《和陶雜詩》定為“丁丑秋冬海外之作”,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斷不能誤。”可是宋慶元間黃州刊本《東坡先生和陶詩》卷三,在((和陶雜詩十一首》後,附載了蘇軾弟蘇轍(子由)的“繼和”十一首,子由繼和之詩題下有注云:“時有赦書北還。”題注與詩內容是相合的。子由“繼和”之詩,總是在得到東坡新作後即次韻唱和,兩者的寫作時間不會差距三年。東坡的((和陶雜詩))顯然也應作於子由繼和《和陶雜詩》的稍早,即元符三年(1100年)赦書下達時。王文誥未做考訂,無根無據,硬把《和陶雜詩》寫作時間提前到紹聖四年(1097年),又厚誣查注、合注,實不足取。
通過以上對比可知,馮寶圻說集成“陰據陽豁”,不全屬實。合注原有誤編、誤收、誤校、誤刊,並非盡善盡莢。集成也有立論不周密,武斷自信的弊病。兩書各有所長,又瑕瑜互見。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避免片面性。重要的是破除門戶之見,設法取長補短,綜合利用。
集成刪去合注所收的絕大部分補編詩、他集互見詩及見於《南行集》的某些早年詩作,馮寶圻斥此為"專輒僭妄",強烈不滿。其實這部分作品中,只有少數詩可定性(確係東坡作品或定非蘇軾所作),更多的詩還待考辨研究。王文誥企圖快刀斬亂麻。一刪了之,其刪詩體例,確如《前言》所說:“不夠謹嚴”。為了彌補底本的這一缺憾,同時也“為了使讀者看到蘇詩的全貌,掌握有關蘇詩的比較完備的資料⑩”,校點者回收了被王文誥妄加刪削的這些詩,單編一冊(第八冊)。其中卷四十七收入一至四十六卷已見合注而集成未收諸詩;卷四十八收入除已編入集成外的全部合注“補編詩”;卷四十九和卷五十收入合注“他集互見詩”。這四卷還參照集成體例,採用合注注文,一樣詳加校核。只是排版格式上與“王文誥輯注”的前四十六卷稍有不同,這四卷的輯注者題名也改為“馮應榴”了。換言之,本書最後四卷暗用合注作底本而重新編排,並使之成為全書的有機組成部分。於是新版的《蘇軾詩集》,既有集成的詩注較簡明、編次較合理的優點,又有合注的資料較豐富,收詩較完備的特長。這種新穎獨特的處理方式,可謂校點者選用底本方面的新嘗試。
王文誥的《蘇詩編年總案》,是自可單行的詳細東坡年譜,它對東坡一生立身行實,進退升沉,考訂頗詳。其中有新見解,也有謬說。鑒於《蘇軾評傳》已有專著,《東坡年譜》有待重編,《蘇詩總案》也需再訂補校正,故此次整理《蘇軾詩集》暫不收總案部分,我以為是明智的。今見集成詩注部分與總案聯繫密切的可互為發明的內容,校點者已酌情摘引了總案相關條文附於注後,這何嘗不是行之有效的"補救措施",同時也從總體上照應了集成體例之統一。
在收詩範圍和編注體例上,做了上述兩方面"善後處理",再用集成做底本,就比較妥當了。
二、關於校勘
新版《蘇軾詩集》的最大特點和優點,在於它審慎細密地校訂了全部蘇詩的正文和東坡自注。校勘古籍首先應廣徵異本,詳緬占有資料。在這方面,《蘇軾詩集》的成績是顯著的。該書使用了今所知見的(包括美國、日本公私藏書在內的)十餘種極珍貴的蘇詩宋、元刻本及有參考價值的部分明。清刻本,做為主要校本;又參考了存有蘇詩真跡的金石碑帖與著錄金石詩文的專著;還充分利用了清人,近人校訂蘇詩的成果。全書採用匯校方式,整理出四千餘條校勘記,分載各卷之後。這些校勘記忠實錄存下各種蘇詩珍本、善本、孤本、秘本的異文資料(惟缺台灣獨存的宋刻蘇詩殘卷的異文)。這就使本書在資料價值、學術水平上超過以往任何一種蘇詩版本。
本書《校點說明》列舉的校本和校勘資料中,有些特別值得重視。如集甲--《東坡集》四十卷、《東坡後集》二十卷,宋孝宗時刊刻的十行大字型,是今存最早的較完整的東坡文集。傳世者僅兩部:一藏北京圖書館,殘存前集的三十卷(詩缺卷三),沒有後集,存者亦有漫漶處;一存日本內閣文庫,前、後集全,雖亦有殘缺處,但與北圖藏本互為補充,便得到一份比較完備的宋版《東坡集》異文資料。又如施乙——施元之、顧禧合編《注東坡詩》四十二卷,宋景定問鄭羽補刊本,出自怡王府,今由翁同和玄孫翁萬戈(現居美國紐約)收藏,存三十四卷(在各施本傳世諸書中,此本存卷獨多)。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曾目睹之,嘆為人間奇寶”。馮應榴知有鄭羽補刊本而未見過。此書是今存較早的編年注本之一,可補嘉定原刊殘帙(清人宋犖獲見者)之佚缺。今用此書訂正了清人校編施注時的諸多疏漏。再如類甲=二宋黃善夫家塾刊本《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是今存最早的蘇詩類注本,與通行的四部叢刊影印所收的元虞平齋務本書堂本頗多不同,富有校勘價值。……總之,本書使用的校本,大都成為秘籍珍本,其中某些書專家也無緣得見,更無機會通讀通校。本書校點者以得天獨厚的便利條件,在中華書局編輯部協助下,獲睹諸多善本,細心比勘,汲取了各家之長,收集了各本有參考價值的全部異文,從而在蘇詩正文及其自注的訂誤、補闕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足以為本書增輝。單從減省讀者翻檢之勞這一點看,也已功德無量了。現在讓我們略舉數例以說明本書的校訂成果。
《九月十五日……進詩一篇》(卷二十九,1541頁),是蘇軾應制詩的代表作。詩題與正文的“紫薇花”,眾本多作“紫微花”。按“紫薇花對紫微郎”,出自自居易《紫薇花》詩《見白氏長慶集》卷十九)。紫微郎為唐中書郎的別稱,唐開元元年(713年)改中書省為紫微省,蓋取象於紫微星。後又於省中種紫薇花,白詩遂有此句。“紫微郎”或作“紫薇郎”,亦本於此。但“紫薇”是落葉小喬木,夏開紅紫花,至秋方謝,故又名百日紅,可供觀賞。“紫薇花”的“薇”不能寫作“微”,各本多誤,本書據集甲校改,是。
《次韻劉貢父獨直省中》詩:“筆老詩新疑有物,心空客疾本無根”(卷二十八,1505頁)。“詩新”原作“新詩”,不合律詩對仗法則。本書據類甲等校改,好。
《獄中寄子由》是蘇詩名篇,結句原作“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此詩異文頗多,唯“世世”二字,各本皆同。著名書法家啟功教授鑽研蘇詩有獨到見解,他據文義及佛教因果之說指出:子瞻與子由只能今生此世為兄弟,怎能說“世世為兄弟?”事理不通,中必有誤。他懷疑第一個世字是“此”字因形近而誤。我們覆核了十幾種善本,雖無作“此”字者,但施乙此句作“與君今世為兄弟”,也使啟先生的高見有了版本依據。本書據施乙將“世世”改為“今世”,從而糾正了諸本的誤刊。
東坡在其詩作中留下某些自注,那是研究蘇詩編年或進行考索箋注的直接依據,是第一手資料,因而受到人們的珍視。可惜歷代刻本中自注往往與它人箋注或編者校語相混,因而標明“自注”、“坡雲”的雙行夾注文字,是真偽雜糅的,有時拙劣的箋注家還故意偽造自注,竟能以假亂真。為了鑑別出真實的東坡自注,校點者花了不少心血。其中一項重大發現是:全集本、分類注本及底本中的某些所謂自注,在施顧編年注本中,時有不標“坡雲”字樣者。它們是否蘇詩原有的自注,很值得懷疑。這有時可能是施乙漏標了“坡雲”二字,有時則確屬後代箋注家及書賈所添補。添補的依據,不外乎東坡題跋、宋人詩話,筆記雜說之類。有關自注的各本異文情況,詳細保留在本書校勘記中。讀者有志於辨偽時,可參考利用這些校記提供的線索。
匯校雖有利,並非人人皆贊同,有人就認為匯校是煩瑣而多此一舉的。本書的校勘實踐證明了匯校方式對某些文學古籍的必要性。研究蘇詩的前輩學者中,清人馮應榴所見善本最多,但他引為自豪的校本,不外乎宋刊《施顧注蘇詩》(影鈔本)與元刊《類注東坡詩》劉辰翁批點本,皆為殘帙。我們今天可以獲見的宋版《東坡集》、《和陶集》、《類注東坡詩》等,絕大多數馮氏都未見過。因而合注中"某一作某"的校記,遠不能令人滿意。本書校點者在掌握資料之全面豐富方面,超越前人,因而能在校勘方面有所前進,有所突破,解決一些疑難問題。為了勘定是非,某些校記順便做出簡略的考證,寫進了校點者的研究心得,對讀者很有啟發。
不足的是,校記分條過於細碎,一句詩或一句詩注,有時出兩條校記;一卷的校記,有時多達二百多條。既占篇幅,又隔裂正文。個別校記旁徵博引,長達千餘言,簡直成了考據短文,有悖於校記必須簡明扼要的慣例。還有些校記,是多餘的,如《點校說明》已交代過異體字、避諱字、明顯誤刊,徑改不出校,但從校勘記中看到仍有出校的。如:1141頁校記(五七)的"■"一作"■"、1418頁校記(九七)的"裙"一作"■"、1419頁校記[一二二]的"版"一作"板"、1520頁校記(九二)的"歡"一作"■"、1518頁校記(六三)的"■''一作"愧"……都是異體字出校。又如:1727頁校記(四一)云:"新芽,原作'新茶'。各本作'新芽',集成目錄亦作"新芽'。'茶',誤刊。刀這樣明顯的誤刊,徑改就是了,何必出校?諸如此類的校記有損於本書校勘體仞j之謹嚴,違背了《點校說明》自定的條規。
校點者對使用的校本和校勘資料用簡稱是必要的,唯應在《點校說明》中有所交代。本書這方面有疏忽,如校記中常見的《法書贊》是岳珂《寶真齋法書贊》的簡稱,用的是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但在《點校說明》中沒做說明,而是在卷二十校勘記(三二)中順便指出。又如將《鹹淳臨安志》省稱為《志》,是在卷七校勘記(五七)予以點明的。如果不是自始至終通讀校勘記(還得細心查找,粗枝大葉不行),猛一見到個《志》或《鑒》,簡直不知是何書。對偶一用之的校勘材料,這種省略書名的做法,實無必要。因為徒添混亂,利多弊少,為省幾個字,反增讀者負擔。
《點校說明》第四條列舉的集丁(宋黃州刊《東坡先生後集》和集戊(宋刊《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是分藏兩地的同版書(宋慶元間黃州刊本《東坡全集》中的兩種);施甲和施丙又都屬於宋嘉定刊《施顧注蘇詩》。仿集甲(包括北圖、日本分別收藏的同一刻本)標名體例,均應合併。以上兩處的"一分為二"的分標方式,說明校點者對所使用的某些善本之版刻源流似未全搞清。
三、注文的整理
新版《蘇軾詩集》是校點本,不擔負補證和新注的任務,故不能、也無必要逐條覆核諸家舊注。注中存在的思想性、科學性、技術性的局限,只能一仍其舊,這是無可奈何的。有識別能力的讀者,也不會因此而苛求於校點者。
舊注中有些涉及史料和史實的明顯錯誤,造成“詞句和事理難通”(見《點校說明》),甚至影響句讀標點。凡此,校點者查閱有關資料後做了校改,一般也反映在校勘記中。如卷二十《陳州與文郎逸民飲別》“河水渺綿瓜蔓流”句(1017頁),下引“(王注子仁曰):《水衡記》”云云,底本原作《永衡記》。史無《永衡記》其書。校點者經過考訂,知有《水衡記》,乃“記一年中各月雨水之特點並因以區分之書”;再查施乙、類本,“永”正作“水”,遂據以改正。又如卷一《竹枝歌》“滿船哀唱似當年”句(25頁),底本引“(合注]《史記·司馬遷傳))”云云,事理難通,司馬遷怎能為自己在《史記》中立傳?校點者將《史記》改為《漢書》,糾正了錯誤。類似這樣的校改,我以為很有必要。
本書整理舊注的成績之一,是將注中涉及十三經、李白詩、杜甫詩的條目,基本補齊了篇名。這就更便於讀者使用舊注了。但是,注中常見稱引的還有韓愈詩文等,其篇名未做添補,因為缺乏相關的索引,不具備校補的便利條件。底本據合注援引的施注注文,原有闕文,王文誥曾妄加添改。這次由校點者據施乙做了校訂,未全寫入校記。類注中同樣的脫誤,則不校改,大約是由於類注有四部叢刊影印本,較通行習見吧。總之,以上兩項增補,均屬盡力而為,對讀者有利,值得歡迎。可惜在校改體例上還不夠嚴密。
反之,校點者對舊注的某些刪削,可能招來非議。譬如“誥案”中妄自尊大、誹謗前賢的那些話,校點者以“占篇幅”、“於詩義闡釋沒有補益”、“對讀者則可能有不良影響”等理由而予以刪削,又不出校記,很多人就不贊成。因為王文誥的文風和集成的特點,正在於“誇大嚕哧而絕少新見⑾。”刪去這些引人生厭的文字,客觀上反而美化了王文誥,拔高了集成的水平。況且按照上引刪注的“理由”,集成中“占篇幅”、“有不良影響”的話還很多,如侮罵王安石變法,攻擊農民起義的那些議論,都沒有刪,保留原樣。可見刪注的“理由”不能成立。其實這些議論,只要在適當場合(例如《前言》)中做出總的概括的批評,原話照錄也無;妨,讀者決不會持異議的。刪了,反而使讀者不放心。這牽涉到整理古籍與研究古籍(校點與評論)的關係,在技術性的校點工作中,不應摻進個人的好惡之感,是非之見。如對校點對象_古籍,想有所議論,應通過撰寫專著或評論文章等方式表達出來,而不必刪書改注。處理今人著述強調文責自負,對待古籍亦應如此,替古人改文章豈不是越俎代庖,節外生枝?
與上述不必要的刪削恰成對照的,還有一種不必要的校補。卷二十三《歧亭五首》其三“合散更主客”句下,底本原有小字夾註:“更,平聲”(1207頁)。這個音注究竟是東坡自加還是後人添注,已難確改。本書卻在正文中插入“集本施乙原注”六字括注,殊無道理。正文中的雙行夾注,除作者自注外,均為古代箋注者所加,插進校點者的括注,就混淆了校、箋的界限。其實把此六字括注改為校勘記置卷宋,也就可以了,不宜徑改正文。此外又見到一種校補,是在舊注中括注校點者按語。如卷四十八《過濰州驛》詩,將翁注攔腰斷開,中間插入長達一百二十字的按語(2614頁);又《讀後魏賀狄乾傳》詩,查注末附長達八十來字的按語(260l頁)。這些都是校點者的話,今竟混在舊注文字內,也不倫不類,損害了舊注本身的體例完整。校點者在正文和舊注中穿插括注,是超越校點職責範圍的,因而是多餘和不必要的。
四、標點及其它
點斷蘇詩並不難,難的是為一百幾十萬字的舊注加新式標點。《蘇軾詩集》的標點,基本正確可靠。但也有不少可商榷處,分舉如下。
1.書名號的使用致誤例:
603頁第七行:“王安石《次韻》詩”;倒數第一行“《欒城集.次韻》詩”。這裡的“次韻”二字不應視為省略的詩題,也無必要加書名號。它如“詩敘”(引)之類,亦以不標書名號為佳。
2621頁第九行:“《古樂府》:木蘭詩。”古樂府是文體名,不是專書,無須標號;“木蘭詩”則是樂府名篇,應加書名號。正確標法應是:“古樂府《木蘭詩》”。
1881頁倒四行:“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引》”。這可能使人誤以為東坡寫過《和陶詩引》了。其實東坡只寫了“和陶詩”,而由其弟蘇轍撰寫了“詩引”,收在《欒城集》卷二十一。按《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是可以單行的宋刻蘇詩善本,即本書《點校說明》提到的主要校本“集戊”。故這裡的正確標法應是:“《<東坡先生和陶淵咀詩>引》”。
2.因不熟悉佛學知識而致誤例:
1245頁第十行:“《法華經解》:‘世尊十號具足世出,世間之所。宗主,故名世尊,’”有人指出第一個逗號應在“具足”後,因為“世出世間”是世間和出世間的意思。而校點者可能不很精通佛教術語,遂出現失誤。
3.因不熟悉古代地理、名勝而致誤例:
1267頁第九行:“先住江州之承天,繼遷淮之斗方,廬山之開先,歸宗潤州之金山、焦山。_”按“開先”下應頓,“歸宗”下應逗。校點者未核《廬山志》等書,不知歸宗寺在廬山下,誤以為它與潤州有關,因而點破。
4.因不熟悉古代官制而致誤例:
1591頁第九行:“趙清獻奏留之,入為三司驅磨官從副使。蹇周輔計度江嶺鹽還,除漕廣東。”施注系節引《宋史》,刪去了“從副使”前的幾句話,又將原文“磨勘”引作“驅磨”。這一點已被校點者發現了,但仍將“從副使”連上讀,似以“從副使”為“三司驅磨官”的副職。這是不應有的失誤,也說明校點者不熟悉吏制。
5.因誤解文義而致誤例:
1303頁第六行:“黃■歷轉運副使。哲宗議召用曾布,陰阻之。”據《宋史》,“召用”對象是黃■,而曾布阻之。“曾布”後的逗號應移到“召用”後面。校點者誤以為“哲宗議召用曾布”,而黃定阻之了。
2354頁第一行:“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按“擔簦”本義是背著傘,引申指奔波、跋涉。這裡“擔簦萬里”宜連讀,不應從中點斷,致使文氣不順。
綜上所述,我們感到《蘇林詩集》整理者似把主要精力花在校勘上,而標點斷句方面稍欠功夫。上列各項失誤舉例中,有些顯然是不應出現的(如1591頁、1881頁),有些似又難於避免(如2145頁)。標點古籍是一項枯燥乏味而又吃力不討好的差事,兢兢業業者亦難免千慮一失。因此有些專業作者不敢涉足其間,或不屑於此道。這是很令人遺憾的。我們指出《蘇軾詩集》標點上某些可議之處,旨在協助校點者尋找致誤原因,總結經驗教訓,以利改進工作。決不想輕率否定該書標點上的功績。
本書所收蘇軾詩,若包括他集互見詩與補編詩,則有二千八百二十多首,為目前收詩最全、資料最富的一部蘇詩全集。
校點者見各本坡詩均有漏收者,又千方百計收集到"輯佚詩二十九首,"做為"增訂",附於卷末。其中見於《永樂大典》的若干首,與欒貴明《蘇軾蘇轍集拾遺》(載《文學評論》1981年第五期)不謀而合,其餘皆首次披露。由此可見出校點者在輯佚方面的專長。校點者為佚詩所作的校注和考訂,很有參考價值。如剔除了見於((永樂大典》的《游南嶽》詩,以其"不可信",就是言之有據的。當然這方面還有不少資料有待挖掘和鑑別,本書的輯佚還只是初步的,難免有漏輯者。
近接友人欒貴明函告:“近來偶然發現我所輯蘇詩中,《寄汝陰少師》和《和南郡趙少師》二首,見於《蘇魏公集》卷八。故應予註明或刪除。”準此,本書增訂部分,似應刪去這二首詩,或仿《游南嶽》之例,在校注中予以說明。校點者的疏失顯然是由於未查《蘇魏公集》,由此也可知輯佚之難。
蘇詩數量多,查起來不方便。本書附了《蘇軾詩集篇目索引》對讀者使用該書,當有裨益;但還不夠用。如能再編制出蘇詩人名地名索引,以及"堪靠燈"式的字詞索引,更可造福於蘇軾研究者,加快研究步伐。我們期待著更詳密的東坡集索引早日問世。
【注】
①指查慎行《補註東坡先生編年詩》。②引自同治九年(1870年)《新刻蘇文忠公詩合注》卷首。
③見《蘇軾詩集》卷二十、1026頁。以下凡引本書只註明卷頁數。
④卷十七,892頁。⑤見李慈銘《荀學齋日記》辛集上五七。
⑥宋雕本指宋嘉定六年原刊本《施顧注蘇詩。施氏本指清宋犖重刻的《施顧注蘇詩》。
⑦指施本此詩題注"疑■抗日所作"等語。見上引。
⑧見《蘇詩編年總案》卷一。⑨指的是戊寅至庚辰1098-1100年。
⑩見《點校說明》。
⑾引自錢鍾書《宋詩選注》7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新版《蘇軾文集》書後
《蘇軾文集》七十三卷,孔凡禮點校;《蘇軾佚文彙編》七卷,孔凡禮輯錄。二者的合編本,最近已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
鑒於《蘇軾詩集》已經出版,《蘇軾詞集》準備另編,這部《蘇拭文集》便成為只收東坡散文、韻文的專書,並與詩集、詞集配套。
點校者經過深思熟慮,選用了明萬曆間茅維編印的《蘇文忠公全集》做底本,不失為一項比較明智的抉擇。
久負盛名的蘇軾詩文全集當推許“東坡七集”,今所見足本有明成化間程宗刊本,其《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等采自宋刻,《續集》十二卷乃明人新編。此書刻印精良,然有三點不足。其一是收文不全,如題跋雜記“或者具有比較高的文學價值,或者在其中就歷史上的、現實中的、以及其它領域的問題,提出自己的卓有見地的解釋和論斷,是蘇軾散文的必要的和有機的組成部分”(引自《點校說明》),可惜“七集”中此類文字收錄太少,缺佚過甚;又如尺牘系考查東坡交遊與思想的第一手資料,“七集”也收錄不全,舉《與程正輔書》為例,《東坡續集》只有二十四篇,底本卻保存七十一篇。其二是編次欠佳,由於“七集”是分集合編,致使賦、記、銘、贊、碑、傳、書、啟及雜文等散見於《前集》、《後集》和《續集》,不按時序排比,又不以類相從,分隔數處,查找起來,頗為不便。其三是版刻有誤,校訂任務太重。
此外,明刻一百十四卷本《蘇文忠公集》及清蔡士英刊一百十五卷本《東坡全集》,皆分類合編的蘇軾詩文全集。前者因"編輯無法"而受到《四庫提要》的貶斥;後者是《四庫提要》著錄之本,但取材不足(如尺牘較通行本少數百篇),體例不純(如題跋、志林分類失當又有重出),且原本難覓,因之皆不宜做底本。
茅維刊本也曾被《四庫提要》斥為"陋略尤甚",點校者認為這是偏見。按茅維刊本印製不精,誤字較多,也有脫題漏句重出現象,這是明版書的通病。經過校對,可知茅維刊本有兩個長處:一是資料齊全,尤以題跋、尺牘收錄最多,乃至清初以來廣為流傳的《東坡尺牘》、《東坡題跋》等專書,皆據茅維刊本相關內容抽印單編而成。二是編排大體合理,全書按文體及內容分類,大類下又列細目,同類文章多數還能按寫作時問排比(如尺牘),便於尋檢和研讀。點校者認為茅維刊本"瑕瑜相較,瑜遠勝瑕",是有一一定道理的。
本書的校勘比《蘇軾詩集》又有所發展。詩集主要用不同版本對校。文集情況複雜,除採用九種主要校本通校外,還使用了金石碑帖、宋人別集、年譜、筆記等多方面資料以解決個別篇目的疑難問題。文集中的制、奏議、尺牘、題跋雜記各類,又尋覓了各自的參考校本如《宋大詔令集》、《歷代名臣奏議》、《蘇長公二妙集》、《東坡志林》等等。總之,點校者將傳統的本校、對校、他校、理校諸法綜合利用,融匯貫通,從而訂正了底本的某些誤脫衍倒,錄存下大量有參考價值的異文資料,並對部分篇章的寫作時間乃.至重出疑偽問題做出了簡要交代。茲舉二例:
《後赤壁賦》有云:“夢二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皋之下。”《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八指出:“前後皆言孤鶴,則道士不應言‘二’。”《朱子語類》卷一三0亦疑“二”字系“筆誤”。但是《東坡集》作“二”,況且“東坡親跡亦然”(朱熹語),雖於事理不合,一般選家仍不敢遽改。後點校者看到《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及《宋文鑒》皆作"一",遂據改,於是文義始暢通。
《議學校貢舉狀》首句:“熙寧四年正月口日。”底本和《東坡奏議集》、《經進東坡文集事略》等書均同。點校者依據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指出:“四年正月”應作“二年五月”。雖未敢徑改正文,但在校記中有所交代,對讀者研究本文很有參考價值。
由於進行了全面認真的校訂,《蘇軾文集》從文題到字句各方面都優於通行本,可以說已向蘇文“定本”的目標邁出了至關重要的一大步。當然,該書的校勘並非盡如人意。其校勘體例稍嫌繁瑣,某些校記寫得不夠精煉,表達方式也不盡統一。對底本的個別改動以及不影響文義的文言虛詞的出校,總令人感到點校者對所謂墨跡刻石資料有所偏愛和偏信。
本書對互見於《蘇軾詩集》的篇目採取了刪文留題的處置辦法,這是因為點校者視二者為姊妹書,避免重複。只是給未備詩集的讀者增添了閱讀上的困難,或許這些讀者會認為這種"互見"不一定是最佳處理方案。對於另外的一些疑偽或互見的篇目,點校者在校記中大都做了交代,這是完全必要的。偶爾也有漏校者,如《鳳味硯銘並敘》(550頁),又見於《欒城集》卷十八,未能出校。
《蘇軾文集》內容包羅萬象,涉及經學、史學、佛學、水文地理、中外關係、政治經濟、典章禮儀等專門知識,標點起來頗多困難。幸賴社會各界人士關注,諸多名家協助把關,因而該書標點當比詩集更趨準確完美。但仍不敢確保萬無一失。至於因對文義理解不同而產生句讀上的差異.更有待於進二步探討了。
《蘇軾佚文彙編》是孔凡禮先生費數年之功潛心搜輯的結晶,他翻查過上百種文獻和文物資料後,輯得東坡佚文(包括殘篇斷句)約四百篇,遵正集體例,按類編排,厘為七卷。各篇文末註明其出處,又在校記巾交代寫作時間,考定文章標題,匡正誤字謬句,並對兩存疑似之作加以必要的說明。《艾子雜說》、《漁樵閒話錄》、《續雜纂》等有爭議的作品則編為附錄。由於《彙編》的宗旨是"期於全而後已",所以歷史上凡傳為蘇軾作品者,包括零章斷句在內,已大體搜羅齊全,庶幾省去研究者翻檢之勞。
這裡確實蒐集了不少珍品,值得重視。如建中靖國元年六月的《乞致仕狀》,諸家年譜均曾言及,正集卻未收入。今從《東坡外集》覓得此文,彌足珍貴。又如《與錢穆父書》,正集只存二十八篇,今於《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發現另外的二十九篇;總數長出一倍有餘,這對考查蘇、錢交遊及東坡思想必將大有裨益。尤其是《西樓帖》保存的幾十篇文章,內容比較可靠,更富參考價值。可以預料,《蘇軾佚文彙編》對有關專家學者將有更強烈的吸引力,更使人感興趣。
《蘇軾佚文彙編》尺牘部分內容豐富,題跋雜記稍嫌蕪雜。有些見於詩集注文或校記的敘跋短文,均予回收。而按照正集體例,這類文字是該刪文留題的,到了《佚文彙編))中改為擬題以存文,大約是為了求“全”。出於同樣的考慮,某些疑似之作也被採錄了。筆者認為,當個人的校訂考辨不足以做出最後案斷時,先將它們收入文集,是行之有效的簡便措施。而其為偽存真,只能留待各路學者其同承擔了。
作者簡介
蘇軾:(1037-1101)北宋文學家、書畫家。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蘇洵子。嘉佑進士。神宗時曾任祠部員外郎,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職,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後以作詩“謗訕朝廷”罪貶黃州。哲宗時任翰林學士,曾出知杭州、穎州等,官至禮部尚書。後又貶謫惠州、儋州。北還後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時追諡文忠。與父洵弟轍,合稱“三蘇”。在政治上屬於舊黨,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在藝術表現方面獨具風格。少數詩篇也能反映民間疾苦,指責統治者的奢侈驕縱。詞開豪放一派,對後代很有影響。《念奴嬌·赤壁懷古》、《水調歌頭·丙辰中秋》傳誦甚廣。擅長行書、楷書,取法李邕、徐浩、顏真卿、楊凝式,而能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與蔡襄、黃庭堅、米芾並稱“宋四家”。能畫竹,學文同,也喜作枯木怪石。論畫主張“神似”,認為“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高度評價“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藝術造詣。詩文有《東坡七集》等。存世書跡有《答謝民師論文帖》、《祭黃幾道文》、《前赤壁賦》、《黃州寒食詩帖》等。畫跡有《枯木怪石圖》、《竹石圖》等。
論文寫作參考書籍大全
| 學術論文是科學或者社會研究工作者在學術書籍或學術期刊上刊登的呈現自己研究成果的文章。學術論文往往強調原創性的工作總結,但當然也可以是對前人工作總結的回顧及做出評價,後者也往往被稱為綜述性文章(Review)。學術論文的出版正在經歷著重大變化,出現了從傳統的印刷版到網路上電子格式的興起。 論文中最重要的就是論點、論據和論證,所以在寫作中,一定要對這三點加以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