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信息
 中國現代藝術展
中國現代藝術展展覽名稱:中國現代藝術展
展覽城市:北京
展覽地址:北京市東城區五四大街一號
開幕時間:1989年2月5日
展覽時間:1989-02-05 至 1989-02-19
展覽地點:中國美術館
策 展 人:高名潞(展覽籌備委員會負責人)、栗憲庭(負責展廳設計)、費大為(負責對外聯絡宣傳)、孔長安(負責藝術作品銷售)、唐慶年(負責經費安排)、王明賢(負責其他日常事務)、劉驍純、范迪安、周彥、侯瀚如
組織:《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中華全國美學學會、《美術》雜誌、《中國美術報》、《讀書》雜誌、北京工藝美術總公司、《中國市容報》
印刷:山西太原包裝廣告美術發展公司印刷贊助
參展人員
藝術家
谷文達、肖魯、黃永砯、林嘉華、廈門達達(焦耀明、俞曉剛、許成斗、蔡立雄、林椿、陳承宗、李世雄、吳藝名、曾潁宏)、“觀念21”(盛奇、鄭玉珂、趙建海、康木)李為民、尤涵、張永見、范叔如、、顧雄、李山、梁紹基、朱建新、董建華、董建明、秦嶧寧、何方、王義榮、馮秋愫、顧德鑫、沈遠、劉安平、張培力、孫人、張富榮、裴晶、孫良、景國、高兟、高強、李群、祝錫琨、魏光慶、王魯炎、李強、吳迅、吳山專、宋海東、王度、楊詰蒼 、侯瀚如、丁德福、潘德海、曹丹、毛旭輝、陳剛、朱小禾、葉永青、任小林、肖豐、張曉剛、呂惠州、武平人、劉陽、曹涌、汪江、楊述、曹勇、李新建、王友身、江海、蘭正輝、忻海洲、黃偉光、劉永剛、李亞非、劉曉東、王衍成、廣曜、李繼祥、張育生、馬路、張悅、王發林、施本銘、葉菲、柴小剛、肖小蘭、夏小萬、吳少湘、郭大龍、陳宇飛、李邦耀、孔翔、張立濤、吳志春、耿建翌、矯健、梁越、方力鈞、朱祖德、王原、宋永紅、劉溢、余積勇、蘇新平、羅瑩、左正堯、徐累、楊志麟、舒群、徐冰、朱岩、成肖玉、楊迎生、劉彥、劉衛東、陳文驥、周鐵軍、馮國棟、劉向東、渠岩、寶樂德、董超、未明、沈小彤、王毅、凌徽濤、尹燕君、戴光郁、盛軍、檸寧、羅麗芳、黃雅莉、徐進、任戩、王廣義、丁方、毛愛華、孟碌丁、顧黎明、楊茂源、徐虹、余友涵、王子衛、丁乙、呂勝中、朱艾平、劉正剛、馮良鴻、倪軍、建君、周長江、馬剛、王魯、尹齊、宿利群、宋永平、張捷、顧震岩、邵普生、袁順、沈浩鵬、區欣文、朱墨、宋鋼、王新平、李津、子建、閻秉會、王川、楊傑昌、沈勤、於志學、呂佐耕、孟昌明、胡建平、邢同和、楊君、艾身、吳德富、齊康、鄭嘉寧、呂俊華、張萍、關肇鄴、傅克誠、項秉仁、柴裴義
非正式參展藝術家
藝術展的緣起
1986年4月,由中國美術家協會主辦的官方會議“全國油畫藝術討論會”破天荒的首次邀請了舒群、李山、張培力等’85運動中的群體藝術家代表,這與持開明姿態的靳尚誼、詹建俊等此次會議核心人物有關。在會上,高名潞的作品幻燈展不僅使幾位群體藝術家萌生了舉辦幻燈展的想法,對於老一輩的藝術家而言,“儘管他們不了解,但至少這些介紹是他們對’85美術運動有所了解,而其中開明者則表示願意理解。”
受此次討論會中幻燈片特殊作用的“誘引”,1986年8月由《中國美術報》社和珠海畫院共同主辦了“’85青年美術思潮大型幻燈展”並召開與此話題相關的討論會,“這次大型幻燈展是一九八九年現代藝術大展的序幕。事實上,也正是在這次展覽上,與會的批評家與藝術家共同倡議搞一次大型的中國當代前衛藝術展。於是,一個艱難而複雜的展覽籌備歷程即從此開始。而當時恐怕沒有任何人會想到這一構想在兩年半後方才實現,而且也沒料到它會引起那樣強烈的社會衝擊力”,[v] “作為一個推遲將近兩年才舉辦的全國性展覽,中國現代藝術展成了中國80年代十年現代藝術的一個句號,這是籌委會組織者最初沒有預料到的。如果展覽的舉辦是一年以前,也許它就只能起到一篇文章中的重要語句後邊的逗號的作用。
它成了所謂句號,是因為展覽是在一個特殊的背景中舉辦的。” 而在這個籌備(萌芽、準備)之初正如高名潞在文章中所寫的那樣是由“與會的批評家與藝術家共同倡議”。而這種形式也是歷史所趨,藝術家在新的思潮面前,容易推出一位批評家或者藝術史家作為他們的“代言人”,以推動其藝術的發展,由此也就逐漸產生了中國早期的“策展人”。作為這個時期的重要藝術家,舒群接受了筆者的提問:“有人說89中國現代藝術展是高名潞的個人‘作品’,高在《瘋狂的一九八九——中國現代藝術展始末》一文中寫道89中國現代藝術展是從86年開始準備的,是否是從‘85青年美術思潮大型幻燈展’中得到的靈感並從此開始準備的?”他說:“嚴格說來這個展覽實際上是舒群、王廣義、高名潞三個人的‘作品’,最初,舒群、王廣義通過策劃‘珠海會議’樹立起高名潞的權威地位,目的是為了確立理性繪畫在’85運動中的權重地位,因我們認為只有理性繪畫才對當時的時代要求做出了明確的回應,對此高名潞持同樣看法(參閱《口述史?“85美術新潮”之舒群》,《藝術世界》2005年3月號)。
接著,舒群通過策劃中國藝術批評史上第一部《中國當代美術史1985-1986》更強化了高名潞的權威地位。為了進一步推動運動的發展,舒群1987年3月由黑龍江省文聯借調到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並提出出版中國當代美術史的計畫。然而,該書寫作完畢後社長撤消了原出書計畫,此後舒群又通過聯繫該書的出版與《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建立了聯繫,結識了甘陽、劉東等哲學界的精神領袖,並向他們介紹了八五美術運動的情況,同時向他們推介了高名潞的工作,目的仍然是強化高名潞在八五美術運動中的領軍作用。於是,《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中華美學學會才出面舉辦“89中國現代藝術展”,並推舉高名潞做該展的總策劃人。”
展覽籌備
展覽的準備工作主要包括展覽資金、展覽場地和作品等方面,而前兩項是先決條件。
 1989中國現代藝術展請柬
1989中國現代藝術展請柬關於資金的籌集,高名潞有兩次表態,一次是在籌委會上:“以前是政治上不可抗拒的原因辦不了展覽,那實在是無奈。但如果這次是因為經濟原因是展覽不能開展,我將宣布永遠退出美術界。” 另一次是當《中國市容報》的曾朝瑩(阿珍)告訴其哈爾濱市政府建委有可能提供贊助的訊息時,當晚高便乘車北上,並發誓若帶不回分文就讓自己則變成冰雕。
這些話表明當時資金的極度缺乏,也更加顯示藝術家們為自己喜愛的藝術事業不惜克服一切困難也要辦好展覽的決心。直到展覽開始前, 《中國市容報》借給組委會5萬元。“資金籌集的難度,遠甚於學術的準備。場地與經費是籌備現代藝術展的雙架馬車。這樣一個大型的展覽,資金全部得自籌,雖然有六個主辦單位,但只是名義上和道義上的支持。且那年頭,這些文化單位也是自身難保。”
在展覽的作品方面,“89中國現代藝術展肯定是前衛藝術家的‘意願所歸’,首先是前衛藝術家第一次有機會在傳統藝術的聖殿‘興風作浪’、‘胡作非為’;同時藝術家能在這裡遭遇來自競賽中的‘他者’的挑戰性刺激,導致興奮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以至於造成戲劇性事件疊起,險相環生的局面。造成這種局面的社會背景是當時的自由化氛圍,幾個月之後就是‘六四’學潮的升級與夭折。就藝術家的心理因素來看與其長年受到的話語禁錮有關,’85前的藝術寫作場域對表達自由的限制是非常嚴厲的,藝術家完全沒有藝術寫作的自由,如果藝術家企圖表現某種個性化的追求,就會遭到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甚至迫害,於是八五時期的自由化氛圍便促成了藝術家自由化表現的畸形膨脹。但不能認為這種膨脹是沒有價值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畸形膨脹是必然的,它與專制體制下的話語運作邏輯密切相關。”
進入中國美術館
自1988年4月起至9月22日止,以高名潞為首的籌委會與中國美術館經過近6個月的協商終於達成協定——大年三十開展。然而在最後中國美術館向籌委會提出三個條件:(1)不許有反對黨的四項基本原則的作品;(2)不許有黃色淫穢作品;(3)不許有行為藝術。對於這些條件,作為籌委會負責人的高名潞在《瘋狂的一九八九》一文中寫道:“當時,我很不情願接受第三項,但考慮到展覽的整體,於是答應並提出‘行為藝術’將以圖片形式展覽。”
為藝術事實一個很重要的藝術現象,不讓進美術館本身是荒唐的,這不是籌委會的初衷,是籌委會的妥協。
從策展到開展,除了關於“現代”標準的確立外,籌委們之間的商討從未超出展覽工作的範圍,也從未真正的就展覽思想做過任何實質性的討論,我以為如果是現代展,它就必須帶有前衛性,展覽本身就是對現實的主動出發而不是被動總結。這種主動出擊並不是憑空構想一種勢頭,而是把握一種具有萌芽狀態的東西。從高名潞與中國美術館談了時間、條件後,諸如離展出只有5個月的時間,不許行為和性意識作品參展等,我已經覺得實現前衛性的想法是不可能的了。內心儘管很矛盾,但既然參加了籌委會,對社會就負一定責任,這使我在整個展覽過程中都處於一種騎虎難下和左右為難的境地中。
無法實現前衛性,展覽的意義就只剩下面對社會了……就這種意義上說,展覽便有了一個切實的角度,我內心的戰場也開始轉向社會。所以,我一開始就不太在乎展覽中個別作品和細節,而是企圖造就一種氣氛,一種與以往所有一般觀眾看到的展覽不同的新鮮感和刺激感。當幾十年的文化傳統和展覽造就了整整幾代人的審美趣味時,強調刺激遠比強調所謂“學術性”更具有現實意義……在中國,這種審美趣味背後是整個文化價值體系乃至文化習慣的強大約束力,沒有很強的刺激力實在難以出動這種文化習慣的惰性。
作為負責展館布置設計的粟憲庭的這種心理代表了很多藝術家們的心態,畢竟在非常的困境之中獲得在中國美術館展出,給這批藝術家注入了一劑強心劑。而展覽負責人高名潞在坎坷地尋找場地的過程中,處處的碰壁越發顯得中國美術館的彌足珍貴。中國美術館不許有行為藝術的規定讓包括高名潞在內的籌委會和藝術家背上了“被招安”的“臭名”,然而這種妥協的目的只有一個——做好此次來之不易的展覽,這是一次集體意識的行為。
粟憲庭等人在爭得展地的前提下,採用更為隱蔽的方法去爭得他們應得的“學術”價值與前衛思想,但是由於沒有與所有籌展人尤其是高名潞保持操作上的一致(或許是無法達成一致,此時的高名潞已經從完全站在藝術家的角度轉換成介於藝術家與美術館的中介人身份。當然他們的目的非常明確——為了展覽),使得在展覽過程中出現展覽負責人失控的事情,同時也為展覽的“混亂”埋下了伏筆。
展覽布置
栗憲庭作為展廳負責人,在談到展覽設計時寫道:“在展覽布置上,波普、裝置這些非傳統繪畫樣式集中於第一展廳;二樓中廳強調一種宗教式的崇高氣氛。二樓兩廳把關注理性,荒誕感的傾向集於一廳,強調‘冷’二樓東廳則強調情感表現的‘熱’這三個廳的布局主要是對’85以來新潮美術基本傾向的概括,三樓中廳的水墨畫也是近十年出現的典型樣式。在展廳布置設計上,我強調‘強烈’。”
當那些藝術權威和高雅之士在指責新潮藝術時,想沒想過他們是在怎樣的環境中進行創作的?而現代藝術展又是在怎樣的缺乏資金和時間等條件下進行的?但也許正是這一點,使新潮藝術和現代展保持了某種生命的活力。這是什麼時候我都不會猶豫的基本準則。
展覽現場
1989年2月5日9時,中國現代藝術展開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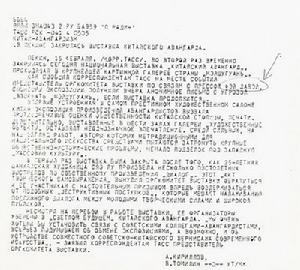 1989年2月蘇聯塔斯社對《中國現代藝術展》的報導電文
1989年2月蘇聯塔斯社對《中國現代藝術展》的報導電文11時10分左右,來自上海的年輕女藝術家肖魯與其男友、藝術家唐宋,朝自己的作品《對話》開槍,以完成預先設計的作品。《對話》是兩個鋁合金製作的電話亭,裡面分別有一男一女在打電話的等人大的照片。電話亭之間是一玻璃鏡,第一槍擊中玻璃鏡,第二槍擦過鋁合金框邊打中玻璃,兩槍都沒有留下作者想要的長條裂紋效果,僅僅留下兩個不大的彈洞。
“槍擊事件”驚動了公安局,來了許多警察,氣氛突然緊張起來,展覽被通知暫停。“槍擊事件” 很快引起國內外新聞界廣泛關注,2月10日展覽重新開幕,2月14日《北京晚報》、北京市公安局和中國美術館分別收到用報紙上的鉛字拼剪而成的匿名信,內容是馬上關閉“中國現代藝術展”,否則在美術館三處放置引爆炸彈。不排除有藝術家又在進行“藝術創作”的可能,但為了安全起見,中國美術館全館關閉兩天。2月17日展覽再次恢復,《中國美術報》也於當天報導了肖魯和唐宋的聲明:作為(槍擊事件)的當事者,我們認為這是一次純藝術事件。我們認為藝術本身是含有術家對社會的各種不同的認識的,但作為藝術家我們對政治不感興趣,我們感興趣的是藝術本身的價值,以及用某種恰當的形式進行創作,進行認識的過程。行為藝術本質上是一種具有強烈的社會性的藝術,通過現實允許的一個界線在社會生活中創造一個社會事件,以展開對人民的提醒,但前提是現實允許的一個界線,可是按照槍枝管理法令等規定,現實是不允許的,但中國的法律在特權的面前只不過是個奴僕,特權的界線才是現實是否允許的界線。“槍擊事件”是個很好的證明。
《對話》在嘲笑法律方面的動機比作為一件純藝術作品更加明確,也可能就是一個法律問題,《對話》本身以及作者的意圖不存在一個所謂的“文化取向”的問題。相反,它經過象徵性的方式和形式對不能“對話”的現實問題的抨擊,而由此深入到對文化現實的批判。 “槍擊事件”成了此次展覽最重要的標誌和符號。著名藝術批評家栗憲庭對“槍擊事件”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兩聲槍響標誌著中國前衛藝術第一次明確地體現人的機智作為藝術的追求。它把這種體驗與社會最敏感的問題的揭示融為一體,顯然比杜桑《泉》僅僅是對社會審美意識的揶揄搞出一籌。同時標誌了中國前衛藝術的獨特性格。”“槍擊事件”創造了一個極為特別的記錄,但同時也使展覽的其他作品“黯然失色”,很少被人關注,被媒體報導。衝擊力強是行為藝術的一大特徵,《大生意》也不例外。
浙江的吳山專是’85新潮中湧現出來的一位出色藝術家,他的《紅色幽默》曾在’85新潮期間產生重大影響,這次中國現代藝術展他要做的是一筆《大生意》,在2月5日展覽開幕時《大生意》出現在了展廳,他使用的物品有一塊小黑板、2個木板箱,一條長板凳和400斤對蝦。藝術家本人和購買對蝦的顧客是作品的一部分。吳山專特意為此而打出了有趣的廣告:
親愛的顧客們,在全國上下慶迎蛇年的時候,我為了豐富首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從我的家鄉舟山帶來了特級出口對蝦(轉內銷)。展銷地點:中國美術館;價格:每斤9.5元,欲購從速。
美術館成了“黑市”必然招來了經警的盤問,並打算沒收吳山專的對蝦,但他掏出了單位的介紹信,證明對蝦是用於展覽的藝術品,最後還是依法罰款20元,並要求停止售蝦,吳山專將介紹信和罰款單往黑板上一貼,用粉筆寫上“今日盤貨,暫停營業。”吳山專為《大生意》作了兩點說明,一是以美術館為象徵的藝術評判:
在美術館賣對蝦,即對審判美術品的法院——美術館的反抗。因為美術館的這種權力,將導致美術品這一無“罪”的羔羊受到了法律般程式的審判;導致藝術家作為現場的見證人出庭作證;導致時間浪費。另外,第二個針對性是藝術理論:在美術館賣對蝦,既對美術理論家的反抗,因為理論家評論美術品的權力,將導致美術品這一什麼都不是的東西成為什麼都是的悲劇;導致藝術家作為“貨”的生產者到處推銷;導致稿酬浪費。
《大生意》反映藝術對理論的突破傾向,這種傾向包括在作者的動機當中,吳山專認為:既然在商品社會中“誰都可以在一筆生意中成名,誰都可以在一筆生意中成為萬元戶“,文化領域裡也包含這種現象,《大生意》作為普通生活中的行為,藝術家無意去創造文化,豐富文化,但現實中,反文化的選擇只能是一種文化的選擇,1917年,杜桑將小便池搬進了展廳,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賣蝦這一生意活動不得不轉化為藝術行為,藝術家有目的的將“生意”放在美術館,作為“生產者”必然是在對自己行為的推銷,那么,他在對現實和理論進行批判的同時也包含著對自身的批判。
李山的《洗腳》、張念的《孵雞蛋》、張盛泉(大同大張)等的《一個白衣人》等行為作品在觀念上與《大生意》沒有多大的不同,李山身穿紅色衣服,雙腳放入一個貼滿里根總統照片的木盆洗腳。張念頭戴小帽,肩上披寫著“孵蛋期間,拒絕理論,以免打擾下一代”的紙衣,盤腿坐在稻草上。他的周圍地上散放著十幾個雞蛋和寫著“等待、等待”的紙片。藝術家面臨的現實問題太多了,以致他們只能用自己的身體來儘快直接地反映問題。當一些對諸如社會、歷史、現實、文化、生命、人類問題進行痛苦思索的藝術家不得不用自己的身體甚至犧牲自己的尊嚴來展示內心時,可以感受到一種特殊的批判方式,這種方式導致了文化成為反抗的犧牲品。
中國現代藝術展因為其中的行為藝術而引起了廣泛非議,不僅是來自普通觀眾的批評(當然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有來自藝術批評界的更加激烈的批評,簡直就是在嘲笑和揶揄,顯而易見,行為藝術家受到的壓力是多方面的,也是極為難堪的,這跟當時中國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社會背景是密切相關的。從組織者的角度上去考慮,他們希望更多的觀眾以及官方能夠接受行為藝術,然而事與願違,理想之夢破滅,時至今日,也沒有更多的人理解行為藝術。人們常常眷念傳統的美術標準而執著於現代藝術作品,在舊的美術標準之下現代藝術顯得醜陋、粗糙、脆弱、單調,它“在逐漸分離於實用的、形式性的美化功能,而直接訴諸人的理性和理性外的境界,在視覺形式的外表之下,揭示出人的本性,在人自身的感官授受之中,深化生命的狀態”。
創作背景
後89
所謂“後89”,系指把1989年的“中國現代藝術展”作為80年代中國大陸新潮藝術的階段性終結,其後出現的具有反叛80年代傾向的新藝術現象。
 1989年2月5日《中國現代藝術展》首日封
1989年2月5日《中國現代藝術展》首日封以紛雜迭起的社會思潮為表現形式,是80年代新潮藝術的基本傾向。因為它是建立在兩次價值觀念失落的文化背景上:被西方列強用炮火轟開大門後,在“五四”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中,失落了士大夫文化傳統;1978年門戶再度開放,隨著西方現代文化的湧進,近代至“文化大革命”建立起的革命現實主義傳統,又在大多數尤其青年藝術家的心裡失落了。
於是,不斷地尋找藝術中的新的精神支柱便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作為動力源於思想——藝術觀及社會的精神變化——的思潮藝術,在1989年初北京舉行的“中國現代藝術展”上幾乎窮盡近百年西方現代藝術的各種觀念之後,觀念的危機也隨即產生。無論弗洛伊德和尼采,還是薩特和加繆,都不再能給藝術提供遮風蔽雨之處。
尤其進入90年代,那種試圖以西方現代思想拯救和重建中國文化的理想主義思潮受到普遍懷疑之後,人們似乎再也找不到一個完整的世界了,只好無可奈何地面對這精神的破碎狀態。
正是這種精神背景,使1989年的中國現代藝術展,同時成為80年代現代藝術運動的謝幕禮。
其實,“後89”現象首先是在中國現代藝術展上初露端倪的:其一,作為“政治波普”的先導,80年代現代藝術的代表人物王廣義展出了他的《毛澤東》;其二,新一代藝術家,即“玩世寫實主義”④的代表人物劉曉東、方力鈞、宋永紅展出了他們的早期作品。而且在他們心裡“1989年參與中國現代藝術展,一種不介入感油然而生”。他們“不再相信一些現成概念能解決藝術家的靈感問題”而轉向“有許多燒灼感的直覺中的現實’’(摘自宋永紅筆記)。
尤其,近年畫展中出現的一批頗引人注目的新作和新人,更驗證了他們不同於80年代新潮藝術家的心態。如北京1990年初的劉曉東和喻紅畫展;1990年底的宋永紅、王勁松畫展;1991年初的方力鈞、劉煒畫展;1991年中的新生代畫展;武漢1991年初的曾凡志畫展;以及近兩年嶄露頭角的四川青年畫家沈曉彤、忻海舟等,加之1991年夏季風靡北京等地的孑L永謙創作的“文化衫”,讓我們看到一種新的潮流已悄然盛行起來,而且心態和語言都有著驚人的趨向現象——無聊感及潑皮式的幽默㈤、玩世的寫實風格。再橫向與王朔的“痞子文學”,劉震雲等人的“新現實主義文學”,搖滾樂中的後崔健群的崛起相比,新思潮的特徵就很明顯了。
無聊感和“文革"後的第三代藝術家 這是一個自1979年後的第三代藝術家群。第一代是知青群,他們是經受過心靈創傷及藝術上接受革命現代主義教育的一代,他們的心態和藝術都依重於純樸的現實,他們是“傷痕”、“鄉土”、“尋根”思潮的主將。把真和善作為美的核心,對普通人的同情和對陰暗面的敏感構成了這群人藝術的特色。第二代是80年代中期崛起的現代思潮群。這群人大多出生於50年代中、後期,80年代初他們大學生涯時,正值西方現代思潮大量湧進之際。另外他們大多或多或少有過知青代藝術家的經歷,但這種經歷又不足以達到刻骨銘心的程度,反而成為他們在80年代初接受西方現代思潮時反省的對象和起點。這構成了他們藝術的特徵,即從西方現代藝術和思潮中獲得了觀察角度和語言樣式,以形而上的姿態關注人的生存意義。
第三代藝術家即“潑皮群”。他們出生於60年代,80年代末大學畢業,這造成他們在成長和走上社會的背景上與前兩群發生了很大差異。“文化大革命”的結束是知青群成熟的背景,現代西方思潮的湧進是“85新潮”成熟的背景,無論是追求善,還是引進西方現代思潮,這兩群藝術家的藝術,都屬於企圖建構新的中國文化的理想主義社會氛圍的產物。而“潑皮群”從他們生下來,就被拋到一個觀念不斷變化的社會裡,而他們童年的記憶,又是隨著社會的開放一起成長的,1989年,在他們相繼走上社會時,代表80年代現代主義思潮的中國現代藝術展以西方各種語言模式為榜樣,大喊大叫登上舞台。無論社會和藝術,拯救中國文化的理想只是子虛烏有,無論是生活,還是藝術,現實留 給“潑皮群”的只是些偶然的碎片。幾乎沒有任何一種社會事件、藝術樣式及其價值,在他們心靈中產生過恆定或深刻的影響。
生存狀態
所有敏感的藝術家幾乎都面對一個共同的生存難題,即生存的現實被以往各種文化、價值模式賦予的意義在他們心中失落後,統治他們生活環境的強大意義體系,並不因為這種失落而有所改變。但在對待這個難題上,“潑皮群”與前兩代藝術家發生了根本差異,他們既不相信占統治地位的意義體系,也不相信以對抗的形式建構新意義的虛幻般的努力,而是更實惠和更真實地面對自身的無可奈何。拯救只能是自我拯救,而無聊感,即是“潑皮群”用以消解所有意義枷鎖的最有力的辦法。
而且,當現實無法提供給他們新的精神背景時,無意義的意義,就成為他們賦予生存和藝術新意義的意義,就成為他們賦予生存和藝術 新意義的最無奈的方法和作為自我拯救的最好途徑。他們拋棄了此前藝術中的理想主義與英雄色彩,把“傷痕美術”和“85美術新潮”時期藝術家對人的居高臨下的關注,放回到自身周圍無可奈何的現實,以平視的角度看待人生,用潑皮的方式去描繪自己及自己周圍熟視、無聊、偶然乃至荒唐的生活片斷。這種視角的轉換,極敏感地把握了當下中國普遍的無聊情緒和潑皮幽默的處世方式。正如方力鈞說的:“王八蛋才上了一百次當之後還要上當。我們寧願被稱作失落的、無聊的、危機的、潑皮的、迷茫的,卻再也不能是被欺騙的。別再想用老方法教育我們,任何教條都會被打上一萬個問號,然後被否定,被扔到垃圾堆里去。”(摘自方力鈞筆記)
潑皮式的幽默無聊即無意義,無聊感即在心靈和感覺中對現實世界意義的消解。既然這個現實世界是無意義的,就不必以嚴肅的態度對待它,這是形成“潑皮群”藝術的那種玩世不恭和潑皮幽默風格的內在原因,也是消解前兩群藝術家作品中因責任感帶來沉重和悲壯感的原因。
王朔的代表作《玩的就是心跳》,驚心的事件卻是一個無聊的玩笑,它甚至在啟示當代社會所有令人心跳的大事件,都不過以玩笑告終,而且幾乎所有作品都在嘲笑過去曾給予許多嚴肅、高尚意義的作家、英雄乃至人自身,諸如他小說的一連串的題目:《別把我當人》、《沒有一點正經》等。搖滾樂中的後崔健群以一種嘲弄和無所謂的情緒替代了崔健的濃厚的參與意義和政治情緒。如他們的代表人物之一何勇在《垃圾場》中唱道:“我們生活的地方/像個垃圾場/人們像蟲子一樣褓爭我搶他的是良心,拉的是思想。我們生活的地方/是個屠宰場/只要你知道骯髒褓已夠斤夠兩。”
“潑皮群”代表畫家們的作品,是通過兩種選擇的視角來把握幽默感的:一種是直接選擇“荒唐的”、“無意義的”、“平庸的”生活片斷;另一種是本來“嚴肅的”、“有意義”的事物滑稽化。
前者如方力鈞精心描繪“打哈欠”的自己朋友的畫像,並創作了獨特的語言符號——光頭的潑皮形象;宋永紅善於以一種漠然、嘲諷和窺私般的旁觀態度,在普通的生活中發掘那些百無聊賴、噁心,又裝模作樣的滑稽場景,揭露出日常生活中人的猥瑣、可鄙、可笑的行為;喻紅筆下的女青年,多是神情恍惚、無所事事的狀態,沉浸於內心的臉部表情中又流露著一種無所謂的神態;劉曉東是他們之中感情最投入、最細膩的,因而也是作品最具悲劇色彩的畫家。他多以城市青年群像為題,表現他們的百無聊賴、無可奈何的狀態。他的畫充滿了對矛盾因素的運用:相聚的場面卻各想心事,開心的表情卻伏著悲哀。尤其在充滿潑皮、無聊氣氛的畫面中,有一種難言的極力想超越和逃離現場的尷尬情緒,標誌他的藝術對人生的把握,進入了某種境界。這幾位畫家的作品都趨向於內向和自嘲,他們在一種極現實的生活片斷中,以一種非親切感、非生活味的渲染,造成畫面的矛盾感。
即畫面情緒並非著眼於那個生活片斷本身的生活味,而是把一種情緒——尤其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情緒注入每一個人物和每塊色彩、筆觸中,造成像劉曉東說的“模糊性的東西”或“雙重結構”。這種矛盾因素的雙重組合,更多的是以潑皮幽默的喜劇形式,去體現那種不得不面對荒唐的悲劇境界。如劉曉東的《田園牧歌》中的一對出遊的情侶,卻是一種茫然無可奈何地等待一個無希望結果的狀態,而且畫面造型、筆觸追求悲劇式的力量感,而非牧歌式的輕鬆。畫面以畫家自己和女伴為模特,也是他自嘲的心理寫照。宋永紅《清淨環境》是一種凝固了的騷動,把對性的渴望壓抑於不得不的安靜中,顯露出焦灼的幽默和荒唐。喻紅用廣告畫法處理的青春女子的肖像,給人以流行性和及時性的感覺,是把美置於轉瞬即逝的偶然性之中;而方力鈞則把所有的形象都剃光了頭,並用一種詩意的手法去處理,把不美的滑稽形象置於美的藍天白雲大海的詩境中,同樣達到嘲諷、荒唐、幽默的效果。
傾向另一種方法的畫家如王勁松,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調笑世象百態,尤其是大眾習以為常的卻又是具有某種正兒八經乃至轟轟烈烈的偉大事件。劉煒以合影式構圖畫光榮軍人、革命家庭,把那種莊嚴自信畫得有幾分滑稽和傻裡傻氣,並創造了歪瓜裂棗式的人物形象作為自己的語言符號。顯然這幾位畫家的作品是趨於外向的嘲世的,所以畫面處理多漫畫化、戲劇化和更具輕鬆感,不同於前者因多趨內向自嘲帶給畫面的緊縮感。如王勁松漫畫化的人物造型、隨意輕鬆的線條,以及人物形象的空白處理,能使作者“在觀眾之間形成一種合謀關係,其意義不在畫面本身,而在於我和觀眾存有共同的現實文化背景,以及對這種文化背景所持的共同態度。從理論上說它是對現實人心態中蒼白一面的把握,同時又是我個人在表現對象方面有種力不從心的焦慮,而著意留有空白後帶來的不完整感,這種力不從心的失落同樣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如同他把《大合唱》、《大氣功》滑稽化一樣,這種現實心態的蒼白是不言而喻的。而劉煒畫面的造型、色彩、筆觸和他潑皮的心態如此協調,仿佛使人感覺到他在整個繪製過程中都保持著那種頑皮和“一點正經都沒有”的幽默狀態。
現實主義的模式
理想主義帶給知青群和“85新潮”群的使命感和參與意識,使他們對於芸芸眾生和現實始終抱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也造成了他們作品的沉重感和悲壯
 《北京青年報》中國現代藝術展CHINA/AVANT-GARDE專版
《北京青年報》中國現代藝術展CHINA/AVANT-GARDE專版氣氛,以及注重自身以外有某種意義的現實和永恆、終極、形而上問題等傾向。所有這些,隨著“潑皮群”對自身無可奈何的領悟,便在他們的作品中消失了。尤其是藝術家職業的神聖和崇高感在他們心中的失落,是一個具革命意義的變化。應了王朔“流氓改當作家”的話,藝術家也不過一介群盲而已。“人說藝術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難道人的靈魂不是生來平等的嗎?這太牽強、太做作、太狂妄。
另有人說藝術品不過是藝術家的排泄物,這話聽來不入耳,卻很恰當,人們正是從這排泄物中看出你是否健康,有什麼病,就像醫生從病人排泄物中看到的一樣”(摘自方力鈞筆記)。既然藝術不再具神聖的社會職能,那么自己和自己周圍的現實,便成為他們視野的聚焦點和心靈的重頭戲,加之多年寫實技巧的訓練,如此他們作品趨向現實主義樣式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同時形成了他們隨意摘取熟視、平庸乃至荒唐的生活片斷,以及多把自己和自己周圍的人作為描繪對象和題材的特點。如宋永紅說:“我的投注目標是我對自身環境的興趣,超越理性的習慣勢力,實在是件令人興奮的事情,因為自身生活環境提供給了我基本的創作因素。”(摘自宋永紅筆記)劉曉東更明確在《尊重現實》一文中主張:“生活中我是個現實主義者,所以我覺得藝術應該是現實主義的。”“我堅持現實主義是因為現實主義對於我來說具有紀實性和直接性。我依託在這個基點上,心中感到實在”(載《美術研究}1991年第3期)。因此,這也導致了他們大多數拋棄80年代中期對西方各種現代語言模式的模仿,而重新從寫實主義——這個近代從西方引進,今統治中國藝壇的寫實主義中尋找新的可能性。
當然,這個現實主義中的現實,是被他們不恭、荒唐和幽默化的。其實現實主義是所有藝術現象中最複雜、名目最繁多,也是最多被濫用的一個名詞。實際上,任何現實主義中的現實,都是經某一特定時代、環境的文化氣氛和社會心理篩選後的結果,現實主義作為中國近現代最盛行的主潮,更多關注的是作為語言層面的寫實樣式;194年後受前蘇聯影響的革命現實主義.關注的是以社會層面的事件和人物的報導性描述;“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現實主義,著眼於宗教式理想主義中的“高、大、全”和“紅、光、亮”的現實;傷痕美術的現實主義,視野又轉向充滿社會陰暗面的現實。
“潑皮群”的現實主義,是對“85新潮”過於關注一些大而無當的哲學問題的矯正,切實地面對當下現實的普遍失落、無聊的心態。同時拋棄了此前所有主義的那種社會參與意識,把此前的居高臨下的姿態換成現實平等的旁觀的姿態,去體驗自己和自己周圍的人的生存狀態。而只有以這種平行旁觀的態度,才能對現實有不恭敬的潑皮態度,才能感到現實本來就有的荒唐的一面,人本來就有的複雜和混蛋的一面,和人生本來就沒有意義的一面。這一點王勁松說得很到位:“一旦將我自己變成旁觀者式的作者,我就感覺到了眾生共有缺陷乃是溝通人的隱蔽根源,它就像一個假設的點,將我自己置於整個現實文化背景之中,這裡的人的種種缺陷帶著某種悲劇成分的戲劇性。”“然後用旁觀者的興奮去體會這種極具魅力的精神現象,因此我常常以一種超然的使人感到輕鬆愉快的幽默方式來表現現實人的真實心理。”劉曉東亦認為:“這些客觀物象本身就放射著光彩,我將自己心中的‘內容’直接插人他們當中。”‘這就和傳統現實主義產生了某些差異,看後讓人幽默之餘又心有餘悸。'’(引言同上’所以,我稱他們的藝術為“玩世現實主義”。
從以上角度去看孔永謙創作的“文化衫”,從它的“煩著呢,別理我”、“一事無成”、“特累”、“拉家帶El”等字樣,戶口本、身份證、糧票等典型的中國生活標記,它與潑皮幽默現實主義殊途同歸,而且它找到真正的波普途徑——消費文化。它迅速在北京及其他城市流行,並招致國際新聞界以及國內有關部門的普遍關注的事實,又是最準確最有力度地把握了當下中國社會的某種普遍性——無聊感和潑皮幽默的處世態度。
作為先行的新文人畫的“玩藝術”和“85新潮”的“荒誕潮流” “潑皮群”的心態和語言,都不是偶然的產物。其中“新文人畫”和“85新潮”為他們登上社會舞台作了鋪墊。
1985年,南京的朱新建以他賴賴的大頭小腳光屁股的古代仕女造型,肆意誇張了的文人墨戲的線條,東拼西湊半文不白的題畫詩,裝傻和東倒西歪的題款字型,以及“採花大盜”、“脂粉俗人”的入畫印,標誌了“潑皮幽默”風格的新文人畫的基本取向,並迅速在中國當代畫壇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這種風格以藝術不過是“玩玩的”(朱新建語)作為信條,確實把握了中國當代精神中某種本質性的傾向,即以追求個人輕鬆感掩蓋著的信仰危機。這是幾年後社會上泛濫“玩前途”、“玩生活”、“玩……”心態的行導。但是,一方面,人及其個性、私生活還得不到社會普遍尊重時,無形的壓力仍然對他們構成一種自覺不自覺的心理負擔,這使他們的藝術充滿了既嘲笑社會又嘲笑自己的痞氣和幽默。另一方面,對於傳統藝術源遠流長的南京畫界,人們對新潮藝術的反感,導致他們順理成章地拾起了傳統的文人墨戲。既可“玩藝術”以避免負荷過重的社會包袱,又免涉模仿洋鬼子之嫌。然而,當他們拿起傳統筆墨時,又深感自己的心態、學養、技巧甚至用以題款的毛筆字,都無法企及這座傳統的高峰,自覺不自覺的尷尬心理把他們逼上玩世不恭的道路。
從某種意義上看,這種“潑皮幽默”式的新文人畫,幾乎是社會心理與文化形態逼迫成的一種“文化畸形兒”。因為他們不敢正視現實,只能借古代題材和形式聊以自娛,只能在玩把式的小品里小打小鬧。
與新文人畫相比,“潑皮群”走出了新文人畫的畸形心理。他們從認識自身開始,正視並直接表現他們共同意識到的現實,還是健康和有力度的。但作為一種文藝思潮,新文人“玩玩的”在心態和語言上都為後來者起了開路的作用。
“潑皮群”與“85新潮”美術之間有更多的血緣關係。“潑皮群”並未完全脫出“85新潮”中對於生存的荒誕處境把握這個大框架,只是把其中英雄主義的自我介入狀態,換成一個旁觀和玩世的狀態,把關注人類的那種普遍的形而上的角度,換成關注自我和自我環境的角度。這使潑皮群能超越文化上的束縛更真切地通過關注可觸摸的實,去把握人的普遍的生存現狀,從而脫去了“85新潮”藝術中的現代主義哲學的外衣。“潑皮群”在語言上更多地受惠於“85新潮”對超現實陌生語境的試驗,只是他們去掉了刻意構建的玄妙和晦澀的語言,在他們自己和自己周圍的場景中,去體驗和反映真實存在的獨特的陌生感和荒誕感。政治波普與解構意識.
1989年以來,“85新潮”的一些代表人物紛紛放棄形而上的姿態,不約而同走上波普的道路,而且大多數以幽默的方式去解構對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對象和政治事件,所以我稱其為“政治波普”。如王廣義繼《毛澤東》後創作的《大批判》系列;任戩創作的《抽乾》等系列;舒群畫了《+一X÷=0》等系列;張培力畫了《中國健美》、{1989標準音》等系列;耿建翌創作的《合影》、《書》等系列。
這又是一個趨同性很強的現象。如果與“玩世寫實主義”關注的無聊感進行比較,兩者實際是當下中國文化中的孿生兄弟。兩者都關注消解某種意義體系,都關注現實,玩世寫實主義關注自身無意義的現實;政治波普直接把握被消解的那種意義的現實。兩者都採取幽默的方式,區別在於靈感的來源。玩世寫實主義多來自對自身和自身周圍的現實的體驗;政治波普多傾向體驗大的社會和文化框架中的現實。因此這影響了政治波普中的一些作品無法擺脫“85理性思潮”的那種本本主義的尾巴,其中尤以當年提出“理性繪畫”、“北方寒帶文化”,後大多南遷武漢的“北方藝術群體”的成員們為最。他們習慣了看好流行的最新國際思潮,1989年前後,正是解構主義在中國最流行的時候他們先後在多家雜誌和報刊上連篇累牘發表作品和文章,以頗似“85新潮”式的革命架勢,舉起西方解構主義的大旗,高呼“清理人文熱情”(王廣義語,載《北京青年報》等報刊)、“清理和消解”、“運用全新的能指復興遠古神話的光環”(舒群語,載1991年第2期《藝術廣角》)的口號,撕下了“85新潮”時形而上的崇高面紗,企圖以“物質性和即時性”的波普藝術的新圖式,掀起一股新的浪潮。但作品過多地流於圖解,如舒群以數碼組成的《+一×÷=0》。王廣義沿用他1987年以來的黑色方格畫《毛澤東》,而用“文化大革命”大批判宣傳版畫和當今流行的西方商品標誌組合,寓意明確,才真正代表了他的政治波普的風格特徵。
相比之下,上海余友涵的《毛澤東》系列,採用中國民間年畫、印染花布的圖案、色彩和部分印製的方法,把握了一種更具中國特色的“文化符號”。藝術為政治服務和為工農大眾喜聞樂見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基本要點。就樣式而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後的一切文藝運動,都是以吸收民間藝術為核心的運動,諸如《黃河大合唱》為代表的音樂民歌風,以《開國大典》為代表的油畫年畫風等。因此余的《毛澤東》不是一種簡單的文化批判,民間符號包含更豐富深刻的人文內涵。
張培力的《中國健美》,尤其{1989標準音》,也更深刻準確地把握了中國當代文化的一面,西方人心理上較多地受到商業的傷害,而中國人則更多地承受了政治宣傳的壓力。所以,渥霍能以一連串的可口可樂和夢露的形象去象徵美國文化,而中國則沒有比電視台新聞聯播的播音員更能夠成為家喻戶曉的形象了。張培力發現了一個中國的“國家面孑L”,那種完全意識形態化了的臉龐、表情和聲音,在感覺上能反映和包含中國國家意識形態的一切。
耿建翌1991年11月參加上海“車庫藝術展”的《書》,是許多本陳列在書架上的重疊印刷的書,信息量由於重複印刷而增多,又由於重疊而互相消解。畫面由滿版重疊印刷的頭像組成,這種人像即中國隨處可見的諸如布告、身份證、各種政審表格中的一寸免冠人像,一個中國人一生中不知要填寫多少個表格,不知要遇見多少次諸如此類的人像模式,通過它中國人與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任戩的裝置《檔案》,以公開檔案的手法,把中國人普遍心理的“檔案情結”作為嘲笑和消解的對象,而《抽乾》、《集郵》則把國家本身作為消解對象,《抽乾》系列是一個個似沒有生命的沙盤式的國家地形圖,《集郵》系列均是國旗組成的郵票,“條形碼提供視覺的流通感,在流通線中的國旗將被分解”(摘自任戩筆記)。周細平用中國舊賬本的形式,記錄了近代以來歷史人升降變遷的賬目。劉大鴻最接近玩世現實主義的潑皮幽默狀態,但用民間鬥神畫馬克思等革命導師的肖像,依然更接近政治波普的方式。
政治波普的出現,標誌了中國現代藝術運動的重大轉折,這種轉折在於藝術家從對西方現代思潮和藝術的關注中,從對大而無當的人的、藝術的普遍追問中清醒,轉而關注中國人生存的真實空間。而政治波普以幽默的方式出現,帶有對政治情結的自我消解的傾向,這是中國現代藝術走上自己的道路的標誌之一。
中國現代藝術與藝術家
| 嚴格地說,“85新潮”並非一個藝術流派,主要是一場藝術運動。而後,中國現代藝術界誕生了一代新藝術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