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范仲淹
范仲淹范仲淹喜好彈琴,然平日只彈履霜一曲,故時人稱之為范履霜。他工於詩詞散文,所作的文章富政治內容,文辭秀美,氣度豁達。他的《岳陽樓記》一文中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兩句,為千古佳句。也是他一生愛國的寫照。
 范仲淹陵園
范仲淹陵園他不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統帥,也是—位卓越的文學家和教育家。他領導的慶曆革新運動,成為後來王安石“熙豐變法”的前奏;他對某些軍事制度和戰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線邊防穩固了相當長時期;經他薦拔的一大批學者,為宋代學術鼎盛奠定了基礎;他倡導的先憂後樂思想和仁人志士節操,是中華文明史上閃灼異彩的精神財富:朱熹稱他為“有史以來天地間第一流人物”!千載迄今,各地有關范仲淹的遺蹟始終受到人們的保護和紀念。
詩詞正文
 《蘇幕遮》
《蘇幕遮》范仲淹
簡介
 《蘇幕遮》
《蘇幕遮》上片大略云:秋天到來時,天高雲談,碧空澄澈,落葉枯黃,萎積滿地,寒涼浸透河水,水面騰起涼絲絲的薄霧。黃葉滿山襯著斜陽,一齊倒映於河水之中;枯乾了的離離野草,鋪向看不見的天邊。這實在是一幅肅諷悲涼的秋來塞外景物圖。“夕陽”與“秋色”相映,都是暖去寒來、生氣漸弱的意象極易喚起人們的愁腸;“芳草”本無感情,但在僅靠野草點綴的荒原上,卻令人無限依戀。這一來是因為芳草鋪向斜陽之外的遠方,直接溝通內地家鄉;二來是因草枯了,明年還會綠,人卻一年年老去,誰知下一次春草萌發時,征人是否還能看得見呢?李賀詩云“天若有情天亦老”,永恆的自然界與短暫的人生,怎能不引發人們深深的感慨?
下片大略云:塞上秋景一片淒涼,不由得征人鄉思纏綿,心緒黯然,憶別念新,長夜難寐,只要一合上眼皮,便夢見與家人團聚。夜半夢醒,格外悽苦。算了吧,算了吧,任它月色溶溶,樓高望遠,還是不要登高縱目、觀賞月色吧;還是借酒消愁,來排遣這漫長孤寂的秋夜吧。只是借酒消愁愁更愁,醉意更深地觸動心中的離愁,化作點點相思之淚,幽幽地滴落胸前。這實在是典型的遊子秋思意緒。“黯”,黯然失色,指精神受到強烈的刺激而覺消沉悲切。“旅思(sì)”,即在外作客的惆悵。“思(sì)”,意念。“黯鄉魂”與“追旅思”是下片的中心,是一種心緒的兩個方面:懷鄉思親,令人心魂不安;傷別念遠,令人憂思悵惘。“黯鄉魂”,是對內地的懷想;“追旅思”,是對邊愁的體味。
不過,此詞不是普通的遊子秋思之作,而是邊關統帥寫的征人思家之作。張惠言云:“此去國之情。”(《詞選》)許昂霄亦云:“鐵石心腸人亦作此消魂語。”(《詞綜偈評》)從感情基調來說,屬纏綿“柔情”、兒女風情,是淒切而非悲壯。繼昌云:“希文宋一代名臣,詞筆婉麗乃爾,比之宋廣平賦梅花,才人何所不可,不似世之頭巾氣重,無與風雅也。”(《左庵詞話》)這本是允洽的評論,有人卻格於作者身份,硬要予以分辨,認為其中是關係軍國的嚴肅感情。“按文正一生,並非懷土之士,所為鄉魂旅思以及愁腸思淚等語,似沾沾作兒女想,何也?觀前闋可以想見其寄託。開首四句,不過借秋色蒼茫以隱抒其憂國之思;‘山映斜陽,三句,隱隱見世道不甚清明,而小人更為得意之象;芳草喻小人,唐人已多用之也。第二闋因心之憂愁,不自聊賴,始動其鄉魂旅思,而夢不安枕,酒皆化淚矣。其實憂愁非為思家也。文正當宋仁宗之時,揚厲中外,身肩一國之安危,雖其時不無小人,究系隆盛之日,而文正乃憂愁若此,此其所以先天下之憂而憂矣。”(黃蓼園《蓼園詞選》)這一說法,論者多不以為然。胡云冀《宋詞選》即云:“從具體的詞看,除了反映出‘去國之情’,很難找出其中有什麼‘憂天下’的含意,黃蓼園所賦予這首詞的思想意義完全是外加的。”的確,此詞只是邊關將士思鄉念親之情的抒寫,並未寄寓指斥小人的軍國之憂。
 《蘇幕遮》
《蘇幕遮》況周頤《蕙風詞話·論詞》指出:“善言情者,但寫景而情在其中。此等境界,唯北宋人詞往往有之。”范仲淹的《蘇幕遮》,正是北宋初年的代表詞作,也確能借景抒情,寓情於景,情景交融,真切感人。
詞牌:蘇幕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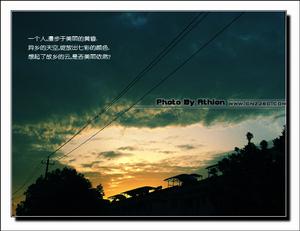 《蘇幕遮》
《蘇幕遮》《新唐書•宋務光傳》載呂元泰上唐中宗書曰:“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為《蘇莫遮》。”可見此曲流傳中國尚在唐玄宗之前。後來衍為長短句。
敦煌曲子詞中有《蘇莫遮》,雙調六十二字,宋人即沿用此體。
《詞譜》卷十四謂“宋詞蓋因舊曲名另度新聲”,誤。此詞黃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三作“別恨”。
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
注釋
 《蘇幕遮》
《蘇幕遮》黃葉地,----下句寫地,黃葉地顯見是秋天,首句的爽朗過後、黃葉地的悲涼傷感被明顯削弱,這正是詩人的高超所在,有別於北宋當時盛行的“館閣氣象”,不使讀者陷入一種憂淒、悲涼的主觀思路。
以對景象的描繪開篇,碧雲天,黃葉地”二句,一高一低,一俯一仰,展現了際天極地的蒼莽秋景,後為元代王實甫《西廂記》“長亭送別”一折所化用,常被人誤記為出處。
讀詩,必須要學會體會其中每一個字眼的妙處,去想像每一個關於狀物形聲的描寫,這樣才能真正的融匯體驗詩意,與作者感同身受,而且往往越是高明的詩歌、越是不容易復原作者本來描繪的情境,這就是為何需要:“熟讀百變、其意自現。”
秋色連波,----此句落筆於一天一地開闊視野間濃郁的秋色,可以想像秋色延伸出去相交於天邊。
波上寒煙翠。----所謂寒煙,從我的想像來看,秋波是暖色的泛著黃橙色澤、而依偎著秋波的則是空翠而略帶寒意的天際的顏色,淡淡的藍。
藍色天空,一地的黃葉,一派暖黃的秋光延伸至天際越來越淡顯出淡淡的藍,又接上望高處的天碧藍碧藍。不難想像作者是在著實感悟了眼前的景象之後,才落筆描繪所見抒發所感,我們追隨他的廖廖文字,讀透了,才透過文字能看見詩人眼前的一天一地。
山映斜陽天接水,-----第一個動詞“映”,我認為是作者的高明所在,一般我們習慣於形容影子映在水中或鏡子裡,這裡作者寫“山映斜陽”,必是山頭被斜陽(暮色的陽光)照映出一層有光的色澤,不夠細心的觀察、不秉以熱愛的心情是發現不了描繪不出的。而水天相接的比較常見的景色也因為“山映斜陽”這樣出奇的描寫顯得生動自然。
芳草無情,-----前面一直寫作者親眼所見的實景,再寫下去,讀者也就要對描寫厭煩了,但作者轉而寫道虛句,把芳草擬人化,道之無情,必是作者因由心態而不對萬物都做欣欣向榮的感悟。
更在斜陽外。----徹底由眼中實景轉為意中虛景,而顯而易見的情緒已隱寓其中。
“芳草”歷來是別離主題賴以生髮的意象之一,比如相傳為蔡邕所作的《飲馬長城窟行》寫“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李煜《清平樂》寫“離恨恰如草,更行更遠還生”。埋怨“芳草”無情,正可見作者多情、重情。
黯鄉魂,----一個“黯”字,已經將作者的離鄉愁緒全盤托出,黯字在詩詞中並不多見,如果按照“壞情緒”的品級排列,這也離壞到極點不遠了。
追旅思,-----簡單說出,身在途中,“追”即能立刻窺出追思之中。
夜夜除非,------這首詞中唯一的疊字,增加了詩的韻味,除非略帶的玄惑感,也促使讀者去一窺作者在反問些什麼。好夢留人睡。-------這一句看似簡單明了,但其實並不簡單,與前一句的夜夜緊密相連。
 范仲淹
范仲淹明月樓高休獨倚,----明月一出,已從薄暮寫至月懸中空,一個“休”字,寫出了萬萬不要的強烈文意,孤身一個的境況也不難得知,空中只有一輪明月與高樓上的孤身旅人對照,再聯合前文的開闊景象渲染,更加能夠和作者的處境感同身受。
“明月樓高”一句順承上文:夜間為鄉愁所擾而好夢難成,便想登樓遠眺,以遣愁懷;但明月皎皎,反而使他倍感孤獨與悵惘,於是不由得發出“休獨倚”之嘆。
酒入愁腸,----隨解、常用,記得是范仲淹的句子就好。
化作相思淚。-----試圖借飲酒來消釋胸中之塊壘,但這一遣愁的努力也歸於失敗。所謂借酒澆愁愁更愁,也正如此。
蘇幕遮--周邦彥
燎沈香,消溽暑。鳥雀呼晴,侵曉窺檐語。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
故鄉遙,何日去。家住吳門,久作長安旅。五月漁郎相憶否。小楫輕舟,夢入芙蓉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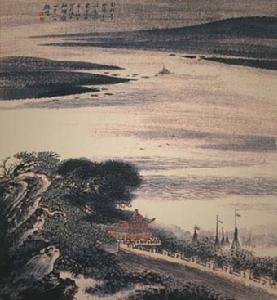 《蘇幕遮》
《蘇幕遮》【作者簡介】
周邦彥(1056~1121) 中國北宋詞人。字美成,號清真居士,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歷官太學正、廬州教授、知漂水縣等。他少年時期個性比較疏散,但相當喜歡讀書,宋神宗時,他寫了一篇《汴都賦》,讚揚新法,徽宗時為徽猷閣待制,提興大晟府。精通音律,曾創作不少新詞調。作品多寫閨情、羈旅,也有詠物之作。格律謹嚴,語言曲麗精雅。長調尤善鋪敘。為後來格律派詞人所宗。舊時詞論稱他為“詞家之冠”。有《清真居士集》,後人改名為《片玉集》。
【注釋】
1.沉香:一種名貴香料,置水中則下沉,故又名沉水香,其香味可辟惡氣。
2.溽暑:潮濕的暑氣。沈約《休沐寄懷》詩:"臨池清溽暑,開幌望高秋。"
3.風荷舉:司空圖《王官二首》詩:"風荷似醉和花舞,沙鳥無情伴客閒。"
4.吳門:古吳縣城亦稱吳門,即今之江蘇蘇州,此處以吳門泛指江南一帶。周邦彥乃浙江錢塘人。
5.長安:原指今西安,唐以前此地久作都城,故後世每借指京都。詞中借指汴京,今河南開封。
6.芙蓉浦:有溪澗可通地荷花塘。唐張宗昌《太平公主山亭侍宴》詩:"折桂芙蓉浦,吹蕭明月灣。"
【譯文】
細焚沉香(名貴香料),來消除夏天悶熱潮濕的暑氣。鳥雀鳴叫呼喚著晴天(舊有鳥鳴可占雨之說),拂曉時分我偷偷聽它們在屋檐下的“言語”。荷葉上初出的陽光曬乾了隔夜的雨,水面清潤圓正,荷葉迎著晨風,每一片都挺出水面。
(看到這風景)我想到遙遠的故鄉,何日才能回去啊?我家本在吳越一帶(今錢塘),長久地客居長安。五月,故鄉的我小時候的夥伴是否在想我,劃著名小船,我的夢中來到了荷花塘(詞中指杭州西湖)。
【賞析一】
此詞由眼前的荷花想到故鄉的荷花。遊子濃濃的思鄉情,向荷花娓娓道來,構思尤為巧妙別致。詞分上下兩片。上片主要描繪荷花姿態,下片由荷花生髮開去,夢回故鄉。
“燎沈香,消溽暑。鳥雀呼晴,侵曉窺檐語”這裡寫的是一個夏日的清晨,詞人點燃了沉香以驅散潮濕悶熱的暑氣。鳥雀在窗外歡呼著,慶祝天氣由雨轉晴。在詞人眼裡,鳥雀仿佛有著人一樣的喜怒哀樂,她們也會“呼”也愛“窺”,如同調皮的孩子一般活波可愛。這幾句描寫看似漫不經心,實際上作者是在為下面寫荷花的美麗做感情上的鋪墊。“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國學大師王國維評:“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先不說神理如何,但是字句的圓潤,就足以流傳千古。至於神理或說神韻,卻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我們不妨把這三句譯成白話:“清晨的陽光投射到荷花的葉子上,昨夜花葉上積的雨珠很快就溜掉了。清澈的水面上,粉紅的荷花在春風中輕輕顫動,一一舉起了晶瑩剔透的綠蓋。遠遠望去,仿佛一群身著紅裳綠裙踏歌起舞的江南女子!”詞人之所以睹荷生情,把荷花寫的如此逼真形象,玲瓏可愛,因為他的故鄉江南就是芙蓉遍地。
“ 故鄉遙,何日去。家住吳門,久作長安旅。”荷花點燃了詞人的思鄉情,下片開頭他就捫心自問,何時才能重歸故里呢,那美麗的吳門,蘇小小居住的地方。“久”字型現了作者對飄泊生活尤其是仕途生活的厭倦,在其它作品中詞人一再以“京華倦客”自稱,可見他早已淡薄功名而魂系故鄉。“五月漁郎相憶否。小楫輕舟,夢入芙蓉浦。”結尾三句,詞人恍惚間飛到了五月的江南,熟悉的漁郎正在河上搖著小船,穿梭於層層疊疊的蓮葉……這時詞人忍不住喊到:打魚的大哥 ,還記得我嗎?我是美成啊!情到深處意轉痴,詞人用一個白日夢結尾,給人留下無限的情思和遐想。
這首詞寫遊子的思鄉情結,寫景寫人寫情寫夢皆語出天然,不加雕飾而風情萬種。思鄉之苦隱藏在清圓的荷葉下,遺忘在五月的江南,漁郎的輕舟上……
【賞析二】
此詞寫異地鄉思。上片為眼前所見之景。夏雨初晴,風荷飄舉,清新宜人。下片由景及情,遙想故鄉五月,風光迷人,小楫輕舟,消失於芙蓉浦中。末句“芙蓉”,與上片“風荷”呼應,點明由此及彼、神思賓士由來,具見經營之妙。
俞陛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葉上”三句,筆力清挺,極體物瀏亮之致。
胡云翼《宋詞選》:周邦彥的詞向以“富艷精工”著稱;這首詞前段描繪雨後風荷的神態,後段寫小楫舟的歸夢,清新淡雅,別具一格。
這首詞,上片寫景,下片抒情,段落極為分明。一起寫靜境,焚香消暑,取心定自然涼之意,或暗示在熱鬧場中服一副清涼劑,兩句寫境靜心也靜。三、四句寫靜中有噪,“鳥雀呼晴”,一“呼”字,極為傳神,暗示昨夜雨,今朝晴。“侵曉窺檐語”,更是鳥雀多情,窺檐而告訴人以新晴之歡,生動而有風致。“葉上”句,清新而又美麗。“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則動態可掬。這三句,實是互動句法,配合得極為巧妙,而又音響動人。是寫清圓的荷葉,葉面上還留存昨夜的雨珠,在朝陽下逐漸地幹了,一陣風來,荷葉兒一團團地舞動起來,這像是電影的鏡頭一樣,有時間性的景致啦。詞句煉一“舉”字,全詞站立了起來。動景如生。這樣,我們再回看一起的“燎沉香,消溽暑”的時間,則該是一天的事,而從“鳥雀呼晴”起,則是晨光初興的景物,然後再從屋邊推到室外,荷塘一片新晴景色。再看首二句,時間該是拖長了,夏日如年,以香消之,寂靜可知,意義豐富而含蓄,為下片久客思鄉伏了一筆。
下片直抒胸懷,語詞如話,不加雕飾。己身旅泊“長安”,實即當時汴京(今開封)。周邦彥本以太學生入都,以獻《汴都賦》為神宗所賞識,進為太學正,但仍無所作為,不免有鄉關之思。“故鄉遙,何日去”點地點時,“家住吳門,久作長安旅”,實為不如歸去之意。緊接“王月漁郎相憶否”,不言己思家鄉友朋,卻寫漁郎是否思念自己,這是從對面深一層寫法。一結兩句,“小楫輕舟,夢入芙蓉浦”,即夢中劃小舟入蓮花塘中了。實以虛構的夢景作結,雖虛而實,變幻莫測。
這首詞構成的境界,確如周濟所說:“上片,若有意,若無意,使人神眩。”(《宋四家詞選》)而周邦彥的心胸,又當如陳世所說:“不必以詞勝,而詞自勝。風致絕佳,亦見先生胸襟恬淡”《雲韶集》。足見周邦彥的詞以典雅著稱,又被推為集大成詞人,其詞作固然精工絕倫,而其思想境界之高超,實尤為其詞作之牢固基礎。
蘇幕遮--梅堯臣
露堤平,煙墅杳。亂碧萋萋,雨後江天曉。獨有庚郎年最少。窣地春袍,嫩色宜相照。
接長亭,迷遠道。堪怨王孫,不記歸期早。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
【作者簡介】
梅堯臣(1002-1060),字聖俞,世稱宛陵先生,北宋詩人。宣州宣城(今屬安徽)人。宣城古稱宛陵,世稱宛陵先生。皇佑三年(1051)賜同進士出身。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早年詩作受西體影響,後詩風轉變,提出與西派針鋒相對的主張。強調《詩經》、《離騷》的傳統,摒棄浮艷空洞的詩風。在藝術上,注重詩歌的形象性、意境含蓄等特點,提倡“平淡”的藝術境界,要求詩寫景形象,意於言外。他的《田家四時》、《田家語》、《汝墳貧女》、《襄城對雪》、《魯山山行》、《晚泊觀雞斗》、《東溪》、《夢後寄歐陽永叔》等詩都體現了這種造語平淡而意在言外的作詩主張。在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中與歐陽修、蘇舜欽齊名,並稱“梅歐”、“蘇梅”。劉克莊在《後村詩話》中稱之為宋詩的“開山祖師”。著有《宛陵先生集》60卷,有《四部叢刊》本。
【譯文】
①墅:田廬、圃墅。 杳:幽暗,深遠,看不到蹤影。
②萋萋:形容草生長茂盛。
③窣地:拂地,拖地。窣:突然,出其不意。
④王孫:貴族公子。這裡指草。多年生,產於深山。
【評解】
雨後天曉,露煙淒迷,芳草如茵,嫩色相照。梅堯臣這首詠草詞,以擬人化手法,
委婉地描繪了春草的形象和特色。
意新語工,為前人所未道者。結尾兩句,意境幽美,極有韻味。這首詞正如他在論
詩中所說的“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最為歐陽修所稱賞。
【賞析】
宋沈義父云:“詠物詞,最忌說出題字。”(《樂府指迷》)這首詠草詞雖不著一“草”字,卻用環境、形象、神態的描繪,將春草寫得形神俱備。詞中,上片以綺麗之筆,突出雨後青草之美;下片以淒迷之調,突出青草有情,卻反落入蒼涼之境。全詞通過上下片的對照,抒發了作者的惜草、惜春的情懷,寄寓了個人的身世之感。全詞形象鮮明突出,意境深遠含蓄,耐人尋味。
上片起首兩句寫長堤上綠草平整、露光閃爍;遠處的別墅如煙綠草掩映下若隱若現。接下來一句總寫芳草萋萋。“雨後江天曉”,是用特定的最佳環境來點染春草的精神,通過雨後萬物澄澈、江天開闊的明媚物象,活畫出濃郁的春意和蓬勃的生機,為下文“少年”的出場作鋪墊。“獨有庾郎年最少”三句,由物及人,由景入意。“庾郎”本指庾信。庾信是南朝梁代文士,使魏被留,被迫仕於北朝。庾信留魏時已經四十二歲,當然不能算“年最少”,但他得名甚早,“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庾開府集序》)。
這裡借指一般離鄉宦遊的才子。“窣地春袍”,指踏上仕途,穿起拂地的青色章服。宋代六、七品服綠,八、九品服青。剛釋褐入仕的年輕官員,一般都是穿青袍。春袍、青袍,實為一物,用這裡主要是形容宦遊少年的英俊風貌。“嫩色宜相照”,指嫩綠的草色與袍色互相輝映,顯得十分相宜。以上,作者描摹出春草的芊綿可愛,用遍地春草映襯出臣游少年的春風得意。
詞的下片轉而抒寫宦遊少年春盡思歸的情懷。過片二句化用李白《菩薩蠻》詞末二句“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之意。接下來兩句,詞人流露出對宦海浮沉的厭倦,用自怨自艾的語調錶達了強烈的歸思。“落盡梨花春又了”,化用李賀《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三月》詩句:“曲水飄香去不歸,梨花落盡成秋苑。”以自然界春色的匆匆歸去,暗示自己仕途上的春天正消逝。結拍兩句渲染了殘春的遲暮景象。
“老”字與上片“嫩”字遙相呼應。於春草的由“嫩”變“老”之中,暗寓傷春之意,而這也正好是詞人嗟老、倦遊心情的深刻寫照。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七云:“梅聖俞歐陽公座,有以林逋詞‘金谷年年,亂生春色準為主’為美者,聖俞因別為《蘇幕遮》一闋云云。歐公擊節賞之。”梅詞與林詞究竟孰優孰劣,讀者諸君自有分解。
【集評】
《能改齋漫錄卷十七》:梅聖俞在歐陽公座,有以林逋草詞“金谷年”年,亂生青
草誰為主”為美者。聖俞因別為《蘇幕遮》一闋,云:
“露堤平云云,歐公擊節賞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