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流傳
李充的文學理論思想集中體現在其《翰林論》中。《隋書·經籍志》載:“《翰林論》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舊唐書·經籍志》載:“《翰林論》二卷李充撰”;《新唐書·藝文志》載:“李充《翰林論》三卷”;《宋史·藝文志》載:“李允《翰林論》三卷”,李允應作李充。《國史經籍志》載:“《翰林論》三卷,李充撰”。從上可見,《翰林論》從成書到梁一段時間內,是一部巨作,有五十四卷之多。從隋到明一直保持在三卷左右,明代以後逐漸亡佚,殘文散佚於類書中。嚴可均據《初學記》和《太平御覽》輯錄八條於《全晉文》,但實際上漏了一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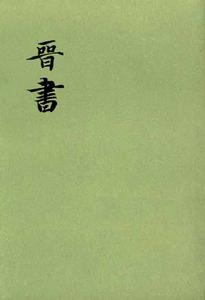 《晉書》
《晉書》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矣。潘安仁之為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容象圖而贊立,宜使辭簡而義正,孔融之贊楊公,亦其義也。表宜以遠大為本,不以華藻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駁不以華藻為先,世以傅長虞每奏駁事,為邦之司直矣。研核名理,而論難生焉,論貴於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成文美矣。在朝辨政而議奏出,宜以遠大為本,陸機議晉斷,亦名其美矣。盟檄發於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誡誥施於弼違。
穆克宏、郭丹《魏晉南北朝文論全編》據胡刻本《文選》李善注,補輯三則:木氏《海賦》,壯則壯矣,然首尾負揭,狀若文章,亦將由未成而然也。(中華書局影印版胡刻本《文選》卷十二);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中華書局影印版胡刻本《文選》卷二十一);楊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劣之義。(中華書局影印版胡刻本《文選》卷四十八)
《太平廣記》卷十三《郭璞》載:“李弘范林明道論(明鈔本林上有翰字),景純善於遙寄,綴文之士,皆同宗之。”周勛初先生認為此處李弘范即李充,《翰林明道論》是《翰林論》的別稱,“景純善於遙寄,綴文之士,皆同宗之”自《翰林論》出。王發國先生在《是“弘范〈翰林〉”,還是“弘度〈翰林〉”》中考證,弘范確有其人,姓李名軌。既然弘范另有其人,那《翰林明道論》是否就是《翰林論》呢?無從考證。王先生還指出,《太平廣記》謂《郭璞》一文出自《神仙傳》,而今本《神仙傳》並無《郭璞》,《神仙傳》有無“李弘范《翰林明道論》”就不得而知了。因此,今暫不把“景純善於遙寄,綴文之士,皆同宗之”列於《翰林論》佚文。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稱:“觀其所取,蓋以沉思翰藻為貴者,故極推孔、陸,而立名曰《翰林》。”交代《翰林》之名由來。此說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王運熙認為《翰林》是李充輯錄的作品總集,《翰林論》是其中的論述部分。《中國文學批評史》稱:“《隋書·經籍志》總集類載:《翰林論》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五十四卷本,疑本名為《翰林》,其書唐初已亡佚。《翰林論》三卷,則是專錄評論之文。二書之區分,猶如摯虞的《文章流別集》和《文章流別論》。”徐公持在《魏晉文學史》中持相同觀點。賈奮然也說:“東晉李充著有《翰林論》是與摯虞《文章流別集》相仿的總集。《隋書·經籍志》總集類載:‘《翰林論》三卷’。注云‘梁五十四卷。’疑原總集稱《翰林》,《翰林論》是其中的論述部分。”此說得到學者的認可,但無從考證。從魏晉南北朝總集編撰之盛以及文體論的發展進程看,這種猜測頗有道理。
思想特點
《翰林論》反映了李充務實重用的文藝思想。從內容來看,《翰林論》所論述的大多是實用文體,且強調“以遠大為本,不以華藻為先”。“遠大”就是重視作品的內容和意義,以實現教化目的。“不以華藻為先”則是與李充“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相一致。“晉李充的《翰林論》也討論了文體的特點和起源問題,併兼舉作品為例。不過就所存佚文來看,涉及詩賦的內容很少,大多限於實用文體。據《晉書·李充傳》,充‘幼好刑名之學’,其論文似乎也偏重於‘貴於允理’,‘不以華藻為先’的論辯文體。”然重視實用不等於輕視文采。從《翰林論》十分推崇孔融、陸機、潘岳、曹植、嵇康等人之文可見看出,李充也十分重視文采,但文采始終要為內容服務,“遠大”才是文章之旨。李充還十分重視詩的教化作用,在評應壉之詩時說“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體現了儒家的教化思想。但《翰林論》也受到名理之學的影響。如“研核名理,而論難生焉,論貴於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成文美矣。”李充認為“論”“難”兩種文體是適應人們研求名理的需要而產生的。名理之學的思想滲入其文體批評論中,體現了時代對文學批評家思想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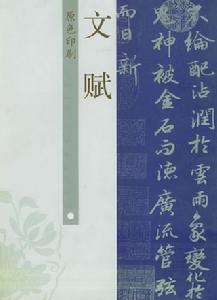 《文賦》
《文賦》《翰林論》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文體劃分更趨細化;舉例概括各文體特徵;繼承並發揚喻體批評。特點之一:文體劃分更趨細化。《翰林論》是文體論在東晉發展的重要表現。中國文體論發端於先秦。《毛詩序》注意到詩的起源:“詩者,志之所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魏晉時期關於文體的論述增多,較為著名者,先是曹丕的《典論·論文》。曹文並不專門論述文體,但對文體已經有相對清晰的概念:“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此文涉及到八種文體,且闡述每種文體的風格。之後是陸機在《文賦》中稱:“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閒雅,說煒曄而譎誑。”《文賦》涉及到的文體有十種。陸機既概括每種文體的風格,又說明風格產生的原因,使人對文體的風格有更加明確的認識。西晉摯虞的《文章流別論》是文體論在西晉發展的里程碑。從《文章流別論》佚文看,其涉及到的文體有:頌、賦、詩、銘、碑、箴、誄等,可能不比《典論·論文》、《文賦》多,但摯虞對文體作更加細緻的劃分,如詩分“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等,且舉例說明:“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文章流別論》還考察文體發展的歷史源流,如“前世為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摯虞開創了對文體的精深研究,故鍾嶸《詩品序》評價說:“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摯虞的論述為後人研究文體淵源提供極大的便利。曹丕、陸機、摯虞的文體論,對文體劃分越來越細,推動文體論的快速發展。李充《翰林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翰林論》亡佚,無法考證其論述的文體到底有多少,但從佚文看,至少有十五:書、議、文、贊、表、駁、論、難、議、奏、盟、檄、誡、誥、詩。其中贊、表、駁、盟、檄、誡、誥等是曹丕、陸機、摯虞等人未提及的,說明李充對文體的劃分又推進一步。《翰林論》體現出文體劃分更加細化的趨勢,為後來總集編撰提供理論依據。
特點之二:簡短概括,舉例說明。《翰林論》對文體的闡述大概是先說明文體的產生:“容象圖而贊立”,“在朝辨政而議奏出”,再以一兩句概括文體風格和寫作規範,最後舉例加以說明,對文體的闡述十分全面。李充的這種論述方式,對劉勰的文體論產生影響。程新煒在《中國古代文體論淵源與〈文心雕龍〉》稱:“李充的《翰林論》多已佚失,留見的文字多是以一、二句簡單的話揭示諸種文體所宜遵循的風格特點與寫作要求,相當於劉勰文體論中的‘敷理以舉統’部分,李充還往往舉出優秀作品示例,相當於劉勰文體論中的‘選文以定篇’部分。”李充關於文體風格的論述也值得注意。曹丕、陸機都對文體風格特點進行概括,李充與之有什麼差別呢?傅剛《論漢魏六朝文體辨析觀念的產生與發展》指出,《翰林論》是通過否定句式對文體加以限定,“與曹丕、陸機正面肯定的表達方式不同,一者是加強了語氣,更能起到警醒的效果,二者更明白地表示了作者主要目的不是談論文體風格,而是通過風格來辨析文體。比如曹丕說:‘詩賦欲麗’,這給讀者造成了作者主旨在於論文體風格的印象,而李充卻反過來說:‘駁不以華藻為先’,作者的意思明顯偏在辨析駁體與以華藻為先的其它文體間的區別之上”。傅先生的這段表述十分準確,既指出《翰林論》的風格特點,也指出其重要意義。
特點之三:喻體批評。魏晉時期崇尚華麗詞藻,因而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是喻體批評,如曹植《王仲宣誄》有:“文若春華,思若湧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陸機《文賦》中有:“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李充將這種喻體批評方式繼承下來,並對後來的《詩品》和《世說新語》產生影響。如李充評潘岳文曰:“潘安仁之為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鍾嶸評潘岳詩就繼承了這種方法:“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世說新語》中的喻體批評更是常見,如評嵇康:“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由此看來,喻體批評是魏晉南北朝時文學批評及人物品評的重要手段,李充的文體論體現了這一趨勢,並在喻體批評發展進程中起承上啟下的作用。
地位影響
作為魏晉時期重要的文體論作品,《翰林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下面逐一闡釋。
梁代鍾嶸《詩品序》稱:“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騭《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鍾嶸在此批評《翰林論》疏略而不切實,且用意只在收錄作品,未曾品評高低,分出等級。雖然鍾嶸對其提出批評,但文學觀念以及品評用語方面卻受到李充的影響。如李充評潘岳:“潘安仁之為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鍾嶸在評潘岳詩時引用此言:“其源出於仲宣。《翰林》嘆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為勝;《翰林》篤論,故嘆陸為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這裡鍾嶸將李充對潘岳的評價完全繼承過來。鍾嶸在評郭璞時說:“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玩。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首。”鍾嶸贊郭璞詩“中興第一”也是參照李充觀點。以上說明鍾嶸的文學觀念以及批評方法,都借鑑了李充《翰林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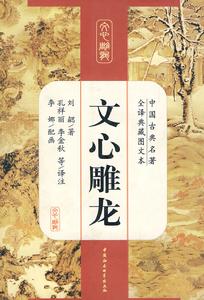 《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李充重視實用文體的觀念,得到《文心雕龍》的繼承。從《翰林論》佚文看,十五種文體中,除“文”、“詩”外,幾乎都可以歸為實用文體之列。從“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矣”來看,李充所說的文並不是“文”“筆”分離後的純文學之“文”,這樣,將文劃入實用文體也未嘗不可。劉勰雖批評“翰林淺而寡要”,但重視實用文體的傳統卻繼承下來,專門設《議對》來討論區分“議”“對”這兩種相似的文體。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心雕龍》中文體的劃分更加精細,沿著李充的道路又向前邁進一步。
李充《翰林論》還對《文選》產生影響。一方面李充與曹丕、陸機、摯虞等人對文體的研究成果,在《文選》中得到繼承和發揚。蕭統將曹丕、陸機、摯虞、李充等人文體論研究成果加以繼承和發揚,並付諸實踐,將其作為《文選》分類的依據。另一方面,李充闡述文體的具體觀點,得到蕭統的繼承。如“戒(誡)”,李充云:“誡誥施於弼違”,蕭統《文選序》曰:“戒出於弼匡”,遵從李充之說。另外,蕭統的“圖像則贊興”也是從李充“容象圖而贊立”而來。衛紹生指出,蕭統的“論則析理精微”是綜合了曹丕、陸機和李充三人的觀點,並在《文選》中把同屬於“析理”的史論之論和論說之論,都劃入論的範疇。
綜上所述,李充《翰林論》是文體論在東晉發展的重要表現,“李充之制《翰林》,褒貶古今,斟酌病利,乃作者之師表。”對後世文學批評和總集編撰產生重要影響。
作者簡介
李充,東晉文學批評家、詩人。字弘度。江夏(治所在今湖北省安陸)人。生卒年不詳。大致與王羲之同時。晉成帝時丞相王導召他為掾。轉記室參軍。又曾任剡縣令、大著作郎,奉命整理典籍。後遷中書侍郎,逝世於任上。
 魏晉士人
魏晉士人李充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曾著《學箴》,以針砭當時人“越禮棄學而希無為之風”。不過他對老莊學說並無貶斥之意。自稱要“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他的文學思想主要見於《翰林論》。李充的詩,以《玉台新詠》所錄《嘲友人》為最有名。其中如“良辰不我俱,中闊似商參。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會罔克從,積思安可任。目想妍麗姿,耳存清媚音。修晝興永念,遙夜獨悲吟”諸句,寫相思之情頗為真切。李充著作據《隋書·經籍志》載有《論語注》10卷、《翰林論》54卷、集22卷。今存詩3首,其中兩首隻有類書所引佚句,逯欽立輯入《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他的辭賦和文,亦多系類書中保存的零星佚文,只有少數幾篇較完整,嚴可均輯入《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