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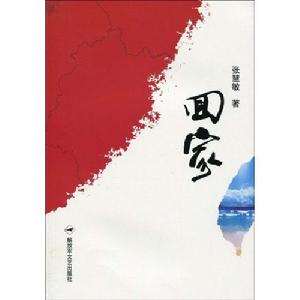 《回家》張慧敏
《回家》張慧敏《回家》以一個1948年冬跟隨國民黨軍隊潰退台灣的老人的一生為線索、第一次以長篇小說的形式講述兩岸風雨60年關係。故事的主人公及他的親人們,一生在革命、政治的波詭雲譎中以難以割捨的親情,和海峽兩岸同宗同根的文化認同情結,再現了半個多世紀以來台灣老兵對家鄉、親人幾近絕望的懷想和“戒嚴令”解除後兩岸的民間往來。其中,1948年國民黨節節失利,最後潰退台灣的整個過程,由於主人公的親歷見聞及作家資料的翔實豐富,讀來極具震撼力。作品一改戰爭只寫焇煙和將帥的運籌帷幄的模式,從細小的邊緣視角審視戰爭的殘酷和無人性。主人公跟隨國民黨軍隊潰逃的這一段是最具文學性的人性拷問。
詳細內容
 張慧敏
張慧敏故事從1947年的山東菏澤講起,主人公的父親高金錫是菏澤城裡的老國民黨員,在一天夜裡,被人突然殺害了。母親認定是高莊惟一的共產黨員、父親的堂弟高金鼎告的密,因此狠心將只有12歲的兒子高秉涵推向了跟隨國民黨軍隊的不歸路。母親原以為兒子可以保命,卻怎么也沒想到這一走就到了台灣,從此音訊全無,生死兩茫茫。一邊是12歲的高秉涵跟隨國民黨軍隊退走台灣,一邊是1949年10月,高秉涵的小姨和兩個姐姐作為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回到了高莊。時代的巨手把玩著芸芸眾生的命運,高金錫的岳父是在日本加入同盟會的老會員、三民主義的信仰者,高金錫入國民黨也是岳父的舉薦,可是小姨宋寶珍和兩個女兒秉潔、秉浩卻作為解放軍從延安歸來。得知父親慘遭殺害的懸案,她們又會作何感想?父親一心想著教育興國,整個身心都撲在教育上,共產黨怎么會殺害他?這是不是國民黨的又一個嫁禍陰謀?高秉涵幾度頻死終於抵達台灣,開始了在台灣的艱難求生。他從火車站小販做起,到考上大學、工作分配時要求到離大陸最近的金門,娶妻生子,一刻也不敢忘記自己山東菏澤的親人,然而兩岸隔絕,音訊渺無。終於在1979年與大陸的親人取得聯繫,那一天,摯愛他的母親卻再也等不到他的訊息,撒手人寰。直到台灣長達38年的戒嚴令解除,台灣人終於可以回大陸探親了。從那以後,高秉涵致力於兩岸親情的聯繫事業,為同鄉們送骨灰罐,為家鄉興資捐助,漫漫回家路得以綿延展開。
高秉涵是一個兩岸關係史的見證人,時代革命和政治的巨大渦流使他和家人不能倖免於外,也因此成就了他和家族的傳奇。父親的慘死使他背負著親人的“血債”踏上流亡之路,可是他卻從來沒有斷過有一天要重回家鄉的念想。中國人熱愛故土,重視鄉土人情,幾千年來積澱成深厚的戀土思鄉的情感,成為中華民族難以拂拭的文化情結。作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所經歷承受的苦難也可以說最為深重。鳳凰涅盤,老樹繁花,正是我們偉大民族生命力的寫照。曾經的苦難不堪回首,但是正視苦難,銘記苦難,苦難就會轉變為民族的財富、民族新的生機活力。高秉涵作為一介平民,身處台灣的政治風雲變幻中,卻時刻難忘與大陸那割捨不斷的血肉親情,當年退走台灣的60萬老兵又哪一個不是如此呢?或是父母妻子、或是兄弟姐妹、或是戀人朋友,就是他們到死都魂牽夢縈、難以放下的心事。這心事也是兩岸同宗同根、血濃於水的民族文化認同情結。
作品特點
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身份認同的基本依據,海峽兩岸在中華文化的認同上基本上是統一的。長篇小說《回家》的推出,及時呼應了大時代里的大政治機遇與挑戰。人們需要返顧那段歷史,回到那段因革命、政治而使親情了斷、天人相隔的歲月,也回到更早更長久的曾經是一家的溫暖回憶。《回家》既形象地折射出海峽兩岸風雨60年的滄桑歷史,也強烈地表達了期望國家統一、人民和平和睦的民意民心,更抒寫了中華民族情感相通、精神相依的文化淵源與親和力。
《回家》的敘事也很有特點。作為一部有真實人物原型的傳記小說,故事的虛構成分相對會少一些,這多少會妨礙小說敘事空間中更多戲劇性衝突的展開。由於小說表現的時間跨度長,眾多人物的性格、命運在紀實的流程里,反而變得不好塑造和把握。作家以超常的結構才能和敘述才華拿出了一部真實感人的作品。深厚的小說語言功力,戰爭場景的逼真再現,故事情節的流暢細膩,主人公性格的成功塑造,使小說的意義不僅僅停留在相關題材中的第一部上。作家關於國民黨軍隊1948年冬至1949年10月的潰退撤離,由於視角是一個12歲男孩的,更生動真實地揭開了人類戰爭描寫中大量鮮為人知的細節。那么多生命如螻蟻一般輕輕覆滅,那么多人承受不了身體和心靈的壓力極限自行了斷,其殘酷和無情直指人性深處。這一部分內容是女作家張慧敏的獨特貢獻。
主人公高秉涵也使我們深思,台海兩岸滄桑60年的風雨經歷從來不曾動搖他對家鄉的嚮往,除了血親、親情,還有什麼更深重的東西吸引著他?而台灣還有多少這樣的高秉涵?《回家》讓我們真切地看到一個民族作為文化的共同體所具有的強大感召力,看到兩岸文化認同的巨大能量與可能性。
作品影響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推出的長篇小說《回家》,以其題材的獨特及文學的功力,引起文藝界的關注,報紙連載,廣播電台連播,中國作家協會與解放軍文藝出版社聯合召開作品研討會,《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等各大媒體分別刊發評論,台灣多家出版商爭購圖書著作權,電視劇改編權最終被湖南廣電集團獲得。
作品評論
作家陳建功說:這部作品看似沒有技巧,但卻是有著很高的技巧,它用一種平實、樸素的語言,講述了以高秉涵為中心的這樣一個人物的命運。其中也用了很多懸念,比如小說一開始寫到關於他父親的死,兩個姐姐的失蹤,都拋出了很多懸念,用平實的語言來記錄這些事情,平實中滲透著非常有內在力量的一種敘事。所以這部小說,我是越看越感到手不釋卷,很難放下,一口氣讀完。作家梁鴻鷹說:文學需要的就是細節的充沛,這本書故事的推進很自然,沒有任何閱讀障礙。讀這本書沒有任何的說教,沒有理念上的東西,踏踏實實地寫作,首先把這個故事講好,我覺得這很好。還有一點,這部小說始終張揚一種美好的東西。高秉涵這一輩子好幾次都走在生命的邊緣,他有很多的委屈,也有很多的不甘,但讀完這個小說,覺得作者把許多美好的東西都呈現給讀者。看得出來作者寫作是在一種極端控制的情況下的一種堅守,讓我們讀後有一種對中華文化強大的認同感。評論家雷達說:看了這部小說,受到感動,被深深地打動。現在的小說,越來越理智了,人們的見識也越來越寬廣,可以說是見怪不驚。所以現在很多的小說,真正出彩的、讓人掉眼淚的不多,但這一部小說我在讀的時候,幾次落下淚水,在目前是很少見的。我們現在的小說技巧越來越好了,但戰爭的氛圍、戰爭的細節、戰爭的真實感還達不到這個水平。說到小說技巧,這部小說中的藝術形象,藝術血肉非常飽滿,這是我的一個突出感覺。評論家孟繁華說:我們看這么多年的這么多作品,包括經典化的幾個作品,都是暴力閱讀,都是血雨腥風,血流成河。這種暴力閱讀也培養了讀者對暴力的欣賞取向。在《回家》裡面我覺得寫得最多的是善和愛,這一點很重要。除了主人公在家庭裡面的善與愛,包括他在顛沛流離的一路上,包括寡婦阿娟對他的關照呵護,讀書的時候那個校長對這個孩子的這種理解和愛,你很難用具體的東西來表達它。小說最華彩的部分,我覺得還是寫高秉涵在台灣的生活經歷。主人公在台灣的生活經歷被寫得一波三折,對台灣風情風貌的描寫我覺得非常精彩。
創作始末
2008年初夏,解放軍出版社副總編輯董保存先生問我願不願意給一家影視公司寫一部台灣老兵題材的電視劇。還是90年代的時候,我寫過一些戰爭題材的中短篇,但卻從來沒有涉獵過台灣老兵題材。一聽到“台灣老兵”幾個字,湧現在心中的情愫比較複雜。這是一個特殊的生命群體,儘管以前對這個群體了解不是太多,但腦海卻瞬間浮現出這樣幾個辭彙——戰爭、死亡、離別、思念、故土、歸根。想到這幾個辭彙基本概括了文學的母體,於是就答應先寫寫試試。拿出影視提綱後,影視公司卻沒了下文。董副總鼓勵我乾脆寫個長篇,免得浪費掉花了兩個多月時間蒐集來的那些素材。就這樣,我開始了《回家》的寫作。但剛寫了幾萬字,就覺得不對勁了,有種兩張皮的感覺。正舉步維艱的時候,我愛人偶然從電視上看到了介紹高秉涵老先生的專題片。當時是個周末的中午,他拉我到電視機旁觀看。就這樣,我知道了高秉涵老先生這個人。採訪過他之後,經過再三考慮,我打算以他的人生大致脈絡來結構這部長篇。
高老先生的人生的確非常傳奇,那么小就離開家鄉和親人,經歷了那么多曲折和磨難能夠生存下來,這不得不說是一種奇蹟。
寫作時,我的確是把這部作品當做小說來寫的,從語言到結構我都是按小說的感覺來把握的。高老先生和其家人的經曆本身就很像是一部精心結構的小說,有著太多的傳奇和感人的細節。儘管這樣,如果完全按照紀實文學的要求來寫這部作品,我覺得會留下許多小說藝術上的遺憾。曾經一度,我想不用真實的人名和地名,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小說,那樣會好處理一些。我和高老先生說了我的想法。他老人家表態說允許我虛構,讓我就當成小說來寫,但請求我保留真實的人名和地名。為了表示對高老先生的尊重,我保留了真實的人名和地名。
出版社知道這一情況後,還特意讓高老先生和菏澤市牡丹區有關單位分別寫了保證書,保證不會因為作品中的虛構部分而引起法律上的糾紛。在作品中,我虛構了十餘個比較重要的輔助性人物,比如朱大傑、韓良明、共產黨的大鬍子團長、台北被國民黨懷疑通共的馬團長、王梅秀、齊美智、李大姐、緬泰邊境的許達輝等等。特別是第三卷,故事基本都是從其他老兵資料那裡移植來的。相信高老先生不會因此而不高興,因為這些故事都是褒獎他的。即便是一些真實發生在高老先生身上的故事,我也是按照藝術規律把事件、時間打碎了再融合、再補充、再推進。我想這是一個文學化和藝術化的過程。
就拿在高老先生的人生經歷中,真實存在的那根繩子來說,事實上高老先生離家帶的那根繩子在南京就在混亂中丟失了。但從小說的技巧上來說,我讓這根繩子一直保留到了小說的最後。至於有的地方交代的過於細緻和具有紀實色彩,我想這是出於對高老先生及其家人的一種尊重吧。這么做儘管流失了一些小說特徵,但我認為是值得的。我還認為不論是紀實文學還是長篇小說小說,其實流淌在語言之下的人物內心的精神世界都是作家人生價值觀和道德觀的一種特有體現。
高老先生的經歷中,最能打動我的應該是人世間的真善美,一個13歲的孩子,在那樣殘酷的環境下能夠生存下來,這個奇蹟的背後閃爍著人性的光芒。書中在很多地方都描寫到這個孩子逢凶化吉、峰迴路轉的奇遇,這是最讓我感動的地方。
至於這部作品最難寫的部分,我認為是對台灣社會的政治和風土人情上的把握,好在大的方面可以查資料,細節上的問題可以諮詢高老先生。
另外一點就是緬泰邊境的那一段。很早就知道有一支流落在在中緬邊境的國軍93師,對那裡的老兵的生活狀態也有一點耳聞,於是想把這一段歷史也融合在作品中。這樣,我就設定了徐達輝這樣一個人物。但是,寫作的時候卻遇到了不小的困難。在大量的資料和熟悉雲南邊防情況的武警邊防朋友的幫助下,還是挺了過來。
說到細節。最初採訪高老先生的時候,打動我的就是一個個的感人細節,比如菏澤老鄉分發菏澤泥土,再比如高老先生離開大陸在廈門海灘登艦過程被李排長一把拉起來。正是發生在高老先生身上的這些真實的細節,引領我走進了歷史的真實,正是在這些細節的啟發下,我又想像、派生出更多的細節。我從來都特別看重作品中的細節,我認為細節是人物內心的真實體現,更是以小見大的最節儉的載體,我還認為細節是閃爍在歲月深處的最不容易被人遺忘的黑珍珠。
細節固然重要,但也有個篩選的問題,如果篩選不當,大概就會給人以“事無巨細”的拖沓感吧。要是覺得我的這部作品還有一些“事無巨細”,正說明我在這方面還有所欠缺,還需要繼續修煉。
我還要提到的一點是流淌在小說字裡行間的一種氛圍。記得,剛動筆不久,有一次見到解放軍藝術學院的朱向前老師。我對他說到了正在寫著的這個小說。朱老師提醒我說,寫作中一定要“淡化意識形態,強化中華傳統”。他還刻意提醒我,不要忽視了“飲食結構”這個問題。朱老師說,一個人離開家鄉,思念家鄉首先是對家鄉獨有食物的思念。這也是我後來在寫作中,反覆出現對菏澤燒餅、耿餅描寫的原因。
作為我個人,我是把這部作品當成是一部長篇小說來寫的。
最後要重申的是,我非常感謝這部小說的人物原型高秉涵老先生。應該說,如果不認識高秉涵老先生我就不可能寫出這樣一部書來,我很感謝高老先生毫無保留的對我講述了他的人生故事。
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這是一種機緣和幸運。
作者簡介
 張慧敏
張慧敏張慧敏,北京武警指揮學院學報編輯部編輯。山東文登人。16歲考入軍校學醫,1993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魯迅文學院第三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學員。1980年就讀於濟南軍醫學校,後歷任濟南軍區一四六醫院護士,解放軍濟南醫學高等專科學校講師。作家。1983年開始發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現任北京武警指揮學院學報編輯部編輯,副教授,上校警銜。著有中短篇小說集《孤旅》,長篇紀實文學《大捷孟良崮》,長篇小說《美麗行旅》。正在創作一部反應武警部隊生活的長篇小說。中篇小說《困馬》獲1992年《解放軍文藝》優秀作品獎,散文集《我們手拉手》獲1997年五個一工程獎,長篇小說《美麗行旅》獲2001年武警文學二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