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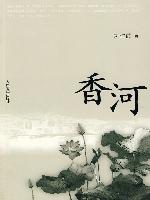 香河
香河這是一條長水,從上游的縣城流出來,一路緩緩的流著、淌著。不曉得轉了多少個彎子,拐了多少個漢子,那般潺潺地流進香河村。再往下,打個陡彎,水流略猴急了一些,泊泊地湧進了一大片盪子。水,湧進盪子之後,便綠了許多,悠然了許多……
這是一個娓娓道來的故事,又是一幅慢慢展開的畫卷。 在蘇北有一條河,叫香河。香河旁有一個村,叫香河村。村裡的村民世世代代勞作在這一方沃土之上……
內容簡介
這是一個娓娓道來的故事,又是一幅慢慢展開的畫卷。 在蘇北有一條河,叫香河。香河旁有一個村,叫香河村。村裡的村民世世代代勞作在這一方沃土之上。 書中的主人公叫柳春雨,作者既講述了他的父輩,也描寫了他的子女。但這一切並不重要,故事既沒有驚濤駭浪,也沒有懸疑驚悚,重要的是這一方沃土,村民們的世俗生活構成了小說的主線,既有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喪、嫁、娶、悲、歡、離、合,也有禮、義、廉、恥、忠、信、恕、仁、孝、悌、貞、節,寫得飽滿,精彩。
隨著作者筆觸的展開,那具有濃郁蘇北風情的河邊小村盡收眼底。村民們活得實在,細緻,有規有矩,有滋有昧,令人嚮往不已。寫小說的,故事只是“形”,要有“意”,“形”才能活起來,如能使讀者得“意”忘“形”,才是高手。讀過《香河》,留在讀者腦海中的,也許只有那一彎緩緩的河水,一處靜靜的村落,一群純樸的村民,還有那別樣的風情、風景、風土、風物。 這是又一部《邊城》嗎?也許是,也許不是。
作者資料
劉仁前,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泰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曾獲全國青年文學獎。汪曾祺文學獎、中國散文年度獎.江蘇省“五個一工程”獎。《安徽文學》獎、泰州市文藝獎等多種獎項。著有小說散文集《瓜棚漫筆》、《眷戀故土》、《香河風情》、《楚水風物》、《屐痕心影》、《蘇中婚俗風情散記》等多部,主編《黑貓叢書》(12冊),著有新聞作品集《流水有痕》,現為泰州日報社副社長一《泰州日報》副總編輯。《香河》為其第一部長篇小說。
藝術特色
好多年前,汪曾祺先生就說過,寫小說就是寫語言。此話有點簡單,也有點深奧。簡單是因為小說不僅僅是語言,還有語言組成的其他的組織,汪曾祺先生當然不會不知這一基本的常識。汪曾祺當然是把深奧的道理用最簡單的方式表達出來了。因為把語言寫好了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些作家寫了一輩子的小說,可能在語言上都沒有過關,不是說他們的語言沒有文采,而是他們的語言沒有貼著人物和事物的本體去寫。
最近讀了劉仁前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香河》,就想起了汪先生的話來。劉仁前的創作多年以來一直師承汪曾祺,20年前就得到過著名作家陳建功的好評,這一次創作的《香河》是他多年生活積累、藝術積累的一次爆發。厚積薄發,讓《香河》這部小說避免了當前長篇小說普遍浮躁、水分過多的流行病,以濃厚的生活積累和濃郁的生活氣息展現了蘇北里下河地區淳樸的民俗風情畫。
《香河》撲面而來的是里下河的特有的地方聲音衝擊波,這聲音大概就是汪曾祺先生所說的“語言”。《香河》寫的是一條河,寫的是一個村,寫的是蘇北里下河的一個生態群落。那些生動的語言和風物仿佛是漂浮在水面上的水浮蓮、水花生,仿佛是那些在蘆葦盪唧唧喳喳的知名和不知名的水鳥一般,“湧進了盪子,便綠許多,悠然了許多。”“香河村,一村七個生產隊,一百三十四戶人家,靠龍巷兩邊住。家前屋後,栽上幾棵楊樹、柳樹,間或,也會有幾棵榆樹、槐樹、苦楝樹。”香河村是里下河平原上的一個非常平凡普通的小村落,那些如楊樹、柳樹、榆樹、槐樹、苦楝樹一樣平常的老百姓在那裡生在那裡死,在那裡耕作,在那裡生活,在那裡苦中作樂(趙本夫語)。無論是生活作風不嚴肅工作卻十分嚴肅的村支書香元,還是為一頭母牛發瘋的光棍漢,無論是不務正業的二流子阿根伙,還是勤勞又執著的二侉子,三奶奶,來娣子,香玉,李鴨子,香河村的男男女女,都活得坦然,生生死死,愛愛怨怨,苦與樂交織在一起,善與惡交織在一起,悲與歡交織一起。是生活的長河,也是人生的浪花。讓我們想起蕭紅的《生死場》,也讓我們想起了沈從文的湘西,這樣一脈人生悲情又有詩意盎然的小說,這樣富有中國老百姓生存哲學意味的文本,雖然不那么刻意為之,但在今天全球化語境中,算得是鮮活的非物質文化的化石。
和小說語言風格相吻合的是小說對很多事物和器物的原生態描寫,顯示了作家對生活的熟悉和技巧的熟稔,小說里有大量的對農事、農具、農活的描寫,這些描寫不只是作為小說的陪襯,而是小說的主體。法國新小說家的代表人物羅伯-格里耶曾強調過小說的“物化”,要求小說家對客觀事物的客觀描畫,也是現實主義的精髓所在。劉仁前的《香河》雖然和新小說派的路數大相逕庭,但對事物本身的器重和精確的把握和呈現說明都是一個優秀的小說家必備的素質。
劉仁前的《香河》寫的是我熟悉的地域文化和語言風物,我的喜愛不免摻雜著鄉情、鄉愁的因素在內,閱讀《香河》其實是我的精神的一次還鄉。在外人看來,這樣一部用高度散文化的小說或許還可以寫的凝鍊些,人物或許更應提煉些,而我欣賞的正是這樣一種自然、原生和散淡。
書評
初讀劉仁前的《香河》,確實給我難以讀畢的感覺。這是因為,這部《香河》簡直不像通常意義上的所謂小說:它雖然也寫了眾多的人物,但卻似乎沒有一個可以被視為真正的人物形象,充其量只是些人物的素描而已;它雖然也安排了一條由柳安然一家三代人的命運構成的主線,但卻似乎僅只限於讓它不時地顯現一下,而沒有使之真正成為一條貫穿始終的紅線;它雖然也講述了許多人物的命運,但卻沒有為讀者提供一些基本的故事情節;此外,它還常常會插入大段大段的關於江蘇蘇中里下河一帶的風物、風俗及風情的描寫與介紹,並且因此使整部小說的敘述節奏變得非常緩慢。總之,對於一般的讀者來說,《香河》的確是一部在題材上很難歸類的作品,它似乎只是以小說元素為主、輔之以散文及隨筆等元素的一部文學性的文字,或者說它似乎只是一個頗有閱歷但又已經超然淡泊的人在對你絮絮叨叨地講述那些存留於他的記憶中的一切的一切。而這當然對讀慣了通常意義上的小說的讀者構成了巨大的閱讀障礙。
然而,慢慢地我的反感減弱了,再慢慢地我感到頗為習慣了,並且逐漸地感到了一種難以言述的情味,到得後來,我便徹底地被這部小說給俘虜了。讀畢全書之後,充滿我內心的只是一種無名的悵觸,而我所能做的便只是掩卷無語,低回良久。我的意思是說,劉仁前的這本《香河》吸引我的並不是通常所謂人物的性格、遭遇、命運等,而是整部作品所流露出來的一種特別的情調。要說《香河》流露出來的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情調,我想也許可以把它表述成“高致的生氣”或者“生氣的高致”。當然也可以把它表述成“俗得雅”或者“雅得俗”。
但是,還是讓我們來看看劉仁前是究竟如何使一本30多萬字的充滿很俗的生氣的《香河》變得雅而有高致的。我想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如前所說,整部《香河》並沒有著力刻畫一個真正的人物形象而只是為讀者提供了許多的人物素描,如柳安然、柳春耕、柳春雨、柳翠雲、三奶奶、二侉子、李鴨子、琴丫頭、楊雪花等,也沒有一條貫穿始終的紅線,只讓柳安然一家三代的命運有如大海里的鯨魚一樣地不時顯露出它身軀的一個局部而已,以及整部小說的敘說不時地會讓大段大段的地方風俗、風情的描寫打斷等,凡此,從一個方面看,的確使《香河》顯得與通常意義上的小說很不相同,或者與通常意義上的小說相比顯得頗為另類。然而這些恰恰應該被認為是《香河》的獨特之處。這些獨特之處的最大作用,主要在於使得《香河》不至於迫使讀者移情於其中並與其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運,而是引導讀者把它當作一個客觀的對象加以審美的欣賞。因此,它儘管也會讓你傷感但不會使你悲痛,它儘管也會讓你歡愉但不會使你狂喜,總之,正像孔子所說的那樣,它使你“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因為,它經由上述種種獨特的處理,和你拉開了一定的距離。這樣,一方面整部小說變得更加真實了——現實所呈現給我們的,除了是些零星的、瑣碎的,並且常常是沒有任何關聯的人物、事情、場景以外,還會是些什麼呢,事實上,《香河》為我們所提供的並不是某個環境中的某幾個人物的獨特命運,而是獨特的年代、獨特的地方的一些底層人物的原質的生存狀態,就結構而言,它不是一部電視劇而更像電視劇開始前的由大量的片斷構成的紛紜交錯、重疊移置的片頭。另一方面,整部小說也因此大大弱化了它的煽情功能而強化了它的審美功能,因為說到底,這裡所謂“原質的生存狀態”畢竟是由作者基於其獨特的審美趣味所經營構造出來的。也許,恰恰因為如此,《香河》才成為了真正的藝術。
其次,作者在《香河》中所採用的敘述主體是非常獨特的,這就是評話藝術中的說話人。凡是讀過中國古代話本小說的讀者,必定都會對作為敘述主體的說話人留有深刻的印象。這位說話人就像西方小說的作為上帝的敘述主體一樣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但是,在以上帝作為敘述主體的西方及中國的類似的小說中,敘述主體常常徹底隱匿,而讓故事自行發展,讓人物自行活動。而在中國古典話本小說中特別是在仁前的這部《香河》中,作為說話人的敘述主體儘管基本上也是隱匿的,但卻始終給讀者一種在場感,即我們始終感到作品中的一切均是由這位說話人講述出來的。舉例來說,在《香河》中,作者很少對人物心理活動進行直接的描寫,而總是像下面這段文字那樣向讀者講述人物的心理活動:“翠雲望著楊雪花的身影從龍巷上消失了,回到家中,心中竟有些傷感起來,這人世間男男女女的事,為什呢就不能順順妥妥,和和美美的呢?自己也不算小了,有人介紹過個部隊當兵的,只是說說,也不曾正式談,更不曾正式見面。不曉得是什呢樣子的命運在等著自己,也不曉的將來花落誰家呢。”至於像“這裡頭有個小插曲”、“有人給柳春雨介紹了”、“眼下,正是棉花田治棉蚜蟲的時機”等表明說話人在場的句子,簡直滿書皆是,無法引錄。正因為如此,讀者與其說是被講述的內容所吸引,到不如說是被說話人的講述本身所吸引。因此,作品便由俗而變雅,由生氣而變得有高致。即便裡面的有關性事的內容,事實上也因此發生了質的變化,即由生理的行為升華為審美的狀態。
第三,作者採用的敘述語言也是很有特色的,而且這一點大概是任何一個讀者很快就能感覺得到的。很難說作者採用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敘述語言,我們只能說它是由現代漢語、民間口語及地方方言土語融煉而成的一種風味特殊的語言。特別是其中的方言土語,的確能傳達出一種難以用現代漢語的詞語加以翻譯的特別的味道。試問,像諸如“關目山”、“熱嘈”、“什呢沙”、“殺殺氣”、“逸事逸當”、“剛嗓”、“波斯獻寶”、“紅白茲湯”、“滑的的”、“風風勺勺”、“鬼出鬼出”等,能否找到與之完全對等的現代漢語的詞語?答案只能是否定的。正因為如此,即正因為用以敘述的語言不是僅僅作為讓內容得以完全展現出來的窗戶而起作用,而是同時更以其自身的存在而使內容被附著了許多特別的風味,因此,整部作品便被處理成為一件審美性的客體,而不是一種純粹的對現實的陳述的文本。
最後第四,但也許是更為重要的是,作者用以講述的語調似乎是不動情的,而是平和的、安詳的和略帶幽默與調侃的。所以能如此的原因,全在於作者實際上是以一個從那些逝去的歲月、人、事、物當中走過來的人的心態去追憶那些歲月、人、事、物等。因此,從前的那份激動已不復存在,存在的只是一種安詳、寧靜及淡泊的傷感。這個傷感,一方面植根於人類的一個普遍的本性,即懷舊,另一方面則基於對現實的某些無奈的不滿。的確,只要人們細加玩味便不難發現,正是因為作者對當今現實生活的那種功利、浮華與奸偽的反感與厭惡,作者才對過去歲月中的那些普通的底層的芸芸大眾們對生活的執著、認真與真誠,表現出無限的渴慕。也正是這種渴慕,使得整個的追憶過程瀰漫著一種難以察覺的傷感。而傷感,在我看來,乃是最難以讓人釋懷的美學品質。
當然,我也知道,肯定不是每一個讀者都能對劉仁前的這部《香河》產生我上面所談到的幾個方面的感受的。由此也帶來這樣一個問題,即對與非蘇中地區的非標準的讀者來說,《香河》的魅力也許會減弱不少。然而,在我看來,一部文學作品只要能真正地贏得一部分讀者,那就是它的成功。畢竟對於一部文學作品來說,其成功與否的根本的標準並不在於它到底能贏得多大的讀者群,而在於它是否具有獨特的美學品質。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可以斷然地說,劉仁前的《香河》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因為它不但有生氣而且也有高致,即它不但很俗而且也很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