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匹克威克外傳》
《匹克威克外傳》作者簡介
 《匹克威克外傳》
《匹克威克外傳》狄更斯曾長期居住在法國、義大利,並曾到美國遊歷。他對美國的觀察極其深刻;美國的虛偽的民主政治、殘酷的監獄、特別是暗無天日的蓄奴制,引起狄更斯極大的憤慨。他說:“我已經失望了,這不是我要來看的共和國,這不是我想像中的共和國。”他的遊記體小說《美國札記》和長篇小說《馬丁·朱什爾維特》都對美國社會的黑暗和醜惡作了有力的揭發。
 《匹克威克外傳》
《匹克威克外傳》查爾斯·狄更斯生活的時代,正是英國資本主義日益發展、資產階級已經取得勝利的時代。但也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隨著資產階級的興起,也就興起了它的對立面即工人階級,而且兩個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也就日益尖銳起來。狄更斯開始寫作的時期正是著名的“憲章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列寧說過:“當英國發生世界上第一次廣泛的、真正民眾性的、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即憲章運動的時候,歐洲大陸發生的革命大都是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而在法國卻爆發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第一次偉大的國內戰爭。”(《列寧選集》第三卷第811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這就是狄更斯生活時代的基本情況。雖然在客觀上偉大的“憲章運動”給了極深刻的影響,推動了他的作品的批判性質的發展,而且在當時也恰恰是“憲章運動”者對狄更斯的價值有正確的認識和高度的評價,認為他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但狄更斯主觀上對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不僅不能理解,而且是反對的。他同情工人,卻不同情工人的革命。他是一個階級調和論者。他幻想可以用道德和教育把那些殘酷的剝削者改造過來,幻想可以依靠好心腸的人的施捨,來消除世界上的貧富懸殊。他揭發了資本主義的罪惡,卻不想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他憎恨金錢對人類靈魂的統治,但是找不到為什麼金錢會變成全能上帝的原因。雖然馬克思就是狄更斯的同時代人,而且馬克思在倫敦住過多年,還領導過英國的工人運動;雖然偉大的《共產黨宣言》在一八四八年已經發表,而且在一八五○年已經出版了英文版,但是狄更斯對這些都一無所知。他始終只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者。也可以說,他不是一個革命者,只是一個改良主義者。所以他的作品,一方面具有深切而有力的批判、揭發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含有不少的消極因素。
雖然如此,由於狄更斯真實地、生動地描繪了十九世紀初葉的英國社會生活,由於他對人民懷著無限的深厚同情,儘管他對資產階級還存在著幻想,致使他的思想和藝術都受了很大限制,但他還是屬於進步傳統的。貫穿在他的一切作品中的基調,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者代表人物、即他心目中的“惡人”的憎恨,和那些處於資本主義壓迫下的普通人和窮苦的勞動者、即他心目中的“善良的人”的同情。他的作品不僅在當時發生了巨大的進步作用,直到現在還為人民所喜愛和珍視。
狄更斯是一位十分關注社會問題的作家,他這第一部長篇小說雖然寫了許多滑稽的冒險故事,不同階層的讀者都贊嘗這部雅俗共賞的小說,甚至一度出現過《匹克威克外傳》熱,但它不是供人消遣的閒書,而是具有豐富而深刻內容的嚴肅文學作品。這部小說所以能暢銷至今,因為它植根於現實生活,書中儘管宣揚善良終歸戰勝邪惡的道德理念,但看不到抽象的說教,作者的道德理念滲透到天才的多姿多彩的藝術世界,使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達到高度的統一。
 《匹克威克外傳》
《匹克威克外傳》狄更斯死於一八七○年六月九日,享年五十八歲。
內容提要
《匹克威克外傳》的情節大體上有四條線索:房東巴德爾太太狀告匹克威克毀棄婚約;山姆·維勒的父親同騙吃喝的偽善牧師史得金斯的紛爭;俱樂部幾位成員的愛情故事;匹克威克和山姆·維勒主僕同流氓金格爾的衝突。
 《匹克威克外傳》
《匹克威克外傳》在匹克威克和他的俱樂部成員一行出遊途中不僅有許多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故事的精彩描述,而且以喜劇的手法對法官、律師、法庭、監獄、議會、選舉等作了深刻的揭露和無情的嘲諷。小說中對於田園生活的描寫帶有理想的浪漫色彩,是作者心想往之的不受封建壓迫和資產階級剝削的人間樂園,反映作者心目中古老的美好的英格蘭;而對於爾虞我詐的城市生活的諷刺和譴責,正表現了作者對當時社會制度弊端的認識和憤懣。
創作手法
作者懷著鮮明的愛憎,運用引人人勝的講故事的寫作技巧和精彩無比的喜劇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不同性格的人物。匹克威克和他的俱樂部成員雖然是有產者,但作者沒有賦予他們本階級的惡習,卻予以平民階層的習性,都循規蹈矩地遵守道德原則。匹克威克在出行途中陷入多重困窘的境地,作品盡力宣染他的天真、幼稚、不懂生活,處處碰壁。匹克威克總是好心腸辦傻事,到處吃虧出洋相,在屢遭挫折的情況下仍保持樂觀開朗的性格,讓人覺得可笑,又逗人喜愛。作者不僅給正面人物都敷上一層喜劇色彩,而且對反面人物和醜惡現象也都採用喜劇的藝術手段,加以誇張、漫畫化,令人看到他們可鄙又可笑,達到尖刻嘲諷和憤怒譴責的藝術效果。小說中凡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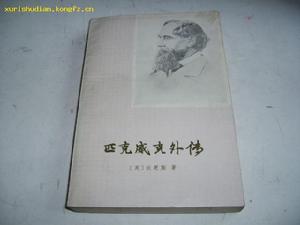 《匹克威克外傳》
《匹克威克外傳》《匹克威克外傳》在英國文學上最主要的貢獻是最早以當代現實生活為創作素材,並把平民當做小說的主人公。小說描寫當時社會生活的各種場景,如街道、廣場、客店、旅館、公寓、別墅、學校、法庭、監獄,肯定當代生活素材的美學價值。人物方面有馬車夫、窮學生、僕人、流氓、獄吏、房東、牧師、紳士、律師、主筆、政客、法官等,幾乎描繪到當時社會上不同階層的人物。匹克威克雖然是位老紳士,但他不請世事、打抱不平、助人為樂,是作者有意把他塑造成仁慈和博愛的典型,客觀上他具有小人物的品格,是平民的化身。匹克威克的僕人山姆·維勒在書中占重要位置。他出身貧苦人家,是在城市下層人民中混出來的,社會大學堂造就他通曉世故,一次次為他的主人解圍,充分表現出機智多謀、勇敢幹練。他們主僕一愚一智,相映成趣,不僅添加許多笑料,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作品增強藝術感染力。
書摘
“我伯父走到萊斯路盡頭的時候,需要穿過一塊很大的荒地,才能走到他回寓所必須走過的一條小街。那時候,在這塊荒地上有一片屬於一個車匠的圍場,這人是和郵局訂了契約,買那些破舊的郵車的;而我伯父很歡喜車子,無論舊的、新的,或者半新的,所以他突然決定離開他走的路,不為別的,只為了從柵欄的縫子裡看看那些郵車:他記得看見了大約一打的車子,被棄置和被拆散了,堆在那裡面。我伯父是那種非常熱情的、容易動感情的人,紳士們;所以,他覺得從柵欄外面不能夠看個清楚,就爬過柵欄,安靜地坐在一根舊車軸上,開始帶著很莊嚴的神情觀察那些郵車。
 《匹克威克外傳》
《匹克威克外傳》“我伯父把頭撐在兩隻手裡,想到多年以前坐在這些舊車子裡飛奔著的忙碌的人們,現在也是沉默而改變了;他想到無數的人,這些破爛腐朽的車子之一,曾經整夜持續了許多年,經歷了所有的氣候,帶給他們所焦急企盼的訊息,熱烈期待的匯款,健康和平安的保證,疾病和死亡的突然的宣告。商人、愛人、妻子、寡婦、母親、國小生、聽見郵差敲門而蹣跚地向門口趕去的嬰孩——他們全都是多么期盼著古舊的郵車來臨呵。而現在他們都上哪裡去了!
 《匹克威克外傳》
《匹克威克外傳》“就算這樣吧。教堂的鐘打了兩點。我伯父醒了,揉揉眼睛,驚訝地跳起身來。”
“鍾一敲兩點,片刻之間,整個這荒涼和寂靜的場所變成了一種最特別的活躍生動的景象。郵車的門安在鉸鏈上,村里又有了,鐵製品像新的一樣,油漆恢復了,燈也點著了,坐墊和大衣放在每個車箱裡,腳夫們在把包裹丟進每一個行李車箱,車掌在收藏著郵包,馬夫們提著一桶桶的水在沖洗那些修補好了的車輛;有許多僕役四處奔忙著把轅軒裝上每一輛車;乘客們來了;旅行箱被遞上去,馬被套上了車;總之,每輛郵車馬上都要出發了。紳士們,我伯父看見這一切把眼睛都睜大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後瞬間他總是時常懷疑他怎么能夠居然又閉下來。
‘喂!’一個聲音說,同時我伯父感覺到有一隻手放在他肩膀上。‘你訂了一張內座。你還是進去吧。’
‘我訂了內座!’我伯父說,轉過頭來。
‘自然囉。’
 《匹克威克外傳》
《匹克威克外傳》‘喂,你進去不進去呀?’先前對我伯父說過話的人說。他打扮得像個郵車車掌,頭上戴了假髮,上衣上有最大的硬袖,一隻手裡提一盞燈,另外一隻手裡是一根很大的大口徑槍,正準備塞進他的小手提箱。‘你就進去嗎,傑克·馬丁?’車掌說,把燈提向我伯父的臉照著。”
‘哈羅!’我伯父說,退了一兩步。‘不用隨便了!’
‘乘客表上這樣寫的呀,’”車掌答。
‘上面沒有寫著“先生”嗎?’”我伯父說——因為他覺得,紳士們,一個不認識的車掌來叫他傑克·馬丁,那是如此放肆,即使郵局知道的話,是絕不會批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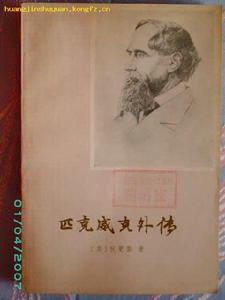 《匹克威克外傳》
《匹克威克外傳》‘付車錢了嗎?’我伯父問。
‘當然付過了,’車掌答。
‘是真的?”我伯父說。‘那么就去——哪部車?’
‘這部,’車掌說。指著一輛老式的愛丁堡倫敦線的郵車,踏腳已經放下了,門開著。且慢——有些別的客人來了。讓他們先進去。’
車掌才說完,我怕父的面前立刻就出現了一位青年紳士,戴著撲粉的假髮,穿一件深藍色的上衣,滾了銀邊,衣據非常飽滿和寬大,裡面襯著硬麻布。那印花布和背心上有‘鐵近和威普斯’的字樣,因此我伯父馬上知道了那所有的料子。他穿了短褲,在他的絲襪和帶著扣子的鞋上面打著一副裹腿;他的手腕那裡打了襞褶,頭上戴著一頂三角帽,身邊掛著一把細長的劍。背心的垂邊拖到大腿的半中間,蝶形領結的頭子拖到腰裡。他莊嚴地高視闊步走到車門旁邊,脫下帽子,伸直手臂把它高舉在頭上,同時把小指翹在空中,像有些裝腔作勢的人端著一杯茶的樣子;然後把兩腳收攏在一起,深深鞠了一個躬,於是伸出了左手。我伯父正打算走上去熱烈地握它,忽然他覺察到這些殷勤根本不是對他獻的,卻是對一位那時剛剛出在踏板前面的青年女子,她穿了古式的深綠色天鵝絨衣服,置了長長的胸衣。她頭上沒有戴軟帽,紳士們,卻用黑色的絲頭巾包著,不過在她預備上馬車的時候回頭瞧了一眼,露出的臉是很美麗,我伯父從來也沒有見過——哪怕是在圖畫裡。她上馬車的時候用一隻手提著衣服;我伯父講這故事的時候老是大罵一聲說,要不是他親眼看見,他決不相信腿和腳會達到如此完美的程度。
“但是,在這漂亮臉孔的這一瞥中,我伯父看出那位小姐對他投射了懇求的眼光,她似乎又恐懼又惶惑。他並且注意到,那戴著打粉假髮的青年人,雖然那些獻殷勤的表示都很漂亮和高貴,卻在她上車的時候牢牢抓住她的手腕,並且立刻跟著進去。一個惡相的戴著棕色短假髮的傢伙,穿著一套梅子色的衣服,帶著一把很大的劍,高統靴子一直穿到屁股下面,他也是他們這一夥;當他在那小姐旁邊坐下的時候,她連忙縮到角落裡去,我伯父就更相信他最初的印象,覺得正在進行什麼黑暗和神秘的勾當,或者用他自己常說的話講,‘什麼地方有隻螺絲鬆了。’真是十分可驚,他那么快就決定了不顧一切危險幫助那位小姐,倘若她需要幫助的話。
‘死和閃電!’當我伯父進了馬車的時候,那位青年紳士手握著佩劍叫。
‘血和雷!’另外一位紳士吼。說著,他就猛然拔出了劍,向我伯父一刺,也不再打任何招呼。我伯父沒有帶武器,但是他很靈巧地從那惡相的紳士頭上抓了他的三角帽,讓劍從帽頂正中戳穿,折起帽邊來,一把緊緊抓住他的劍。
從後面刺他!’惡相的紳士對他的同伴喊,一邊拚命奪劍。
‘我看他最好還是不那樣,’我伯父叫,用威脅的態度顯一顯他一隻鞋子後跟。‘不然我要踢出他的腦漿來,假使他有什麼腦漿的話,要是他沒有腦漿,我就踏破他的腦袋。’這時候我伯父用全部氣力從惡相的紳士手裡把劍奪了下來,乾脆丟出了車窗:那比較年青的紳士看見了,就又吼叫一聲‘死和閃電’!並且把手伸到劍柄上,神情很兇猛,不過他沒有拔劍。也許,紳士們,就像我伯父總是帶著微笑說的,也許他是怕驚嚇了那位小姐吧。
‘喂,紳士們,’我伯父說,逍逍遙遙地坐好,‘在一位女士面前,我不需要什麼死,無論有沒有閃電,我們這一趟旅行也已經有了足夠的血和雷了;因此,如果你們歡喜的話,我們就照安安靜靜的內座乘客們的樣子坐好了——喂,車掌,快把那位紳士的餐刀拾起來。’
我伯父剛說了這句話,車掌就出現在車窗外面了,手裡拿著那紳士的劍。他把劍遞進來的時候,舉起了燈,密切地注視著我伯父的臉:就在這時,借著燈光,我伯父很吃驚地看見一大群郵車車掌擁擠在窗戶外面。每人的眼睛都急切地盯著他。
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片海似的月臉孔、紅身體和急切的眼睛。
‘這真是我遇到過的最奇怪的事,’我的伯父想——‘請允許我把你的帽子奉還吧,先生。’惡相的紳士默默地接了他的三角帽;帶著疑問的神情,看看中間的那個洞;最后庄重地把它戴在他的假髮上,但是那莊重的效果略微受了些損害,因為他這時猛然打了一個噴嚏,把帽子又震落下來。”
‘都妥啦!’拿燈的車掌叫,爬進車尾他的小小的座位。他們出發了。離開車場的時候我伯父從車窗向外望,他看見另外的郵車帶著車夫、車掌、馬匹和全部旅客,在兜著圈子趕草,大概是一小時五里的慢速度。我伯父大為憤慨了,紳士們。作為一個商人,他覺得郵包是不能這樣草率送的,他決定一到倫敦馬上就寫信向郵局提建議。
然而,現在,他的思想放在那位小姐身上,她坐在馬車裡面最遠的一角,臉孔緊緊地裹在頭巾里:穿著深藍色上衣的紳士坐在她對面,穿一套梅子色衣服的另外那位坐在她旁邊:兩人都緊張地看守著她。甚至她把她的頭巾的褶襉弄出聲來,他就聽見那惡相的人用手抓劍的聲音,從另外一個(很黑,所以看不見他的臉)的呼吸聲也聽得出,好像他是那樣大的巨人,要一口吞她掉似的。這事使我伯父越來越激動,他決定不管如何都要把這弄清楚。他對於明亮的眼睛、甜蜜的臉和漂亮的腿和腳有極高的崇拜;總之,他喜歡所有的女人。那是我們家族遺傳,紳士們——我也是如此呢。
我伯父設法去吸引那位女士的注意,或者無論如何要引得那兩位神秘的紳士談起話來。全都徒勞無功;紳士們不願意說話,女士更不敢。他過些時就把頭伸到窗戶外面,喊著問他們為什麼不趕得快些。但是他喊啞了嗓子也沒有誰注意他。他倚在座位上,想那美麗的臉、腳和腿。這倒比較好些;可以消磨時間,而且兔得叫他納悶他是上哪兒去、並且怎么偏偏是他,落到如此古怪的處境。但是不管怎樣,這也並沒有使他太煩惱——我伯父是個了不得地自由自在、無拘無束。什麼都無所謂的人呵,紳士們。
突然,馬車停了。‘哈羅!’我伯父說,‘怎么啦?’
‘這裡下車,’車掌說,放下踏板。
‘這裡!’我伯父叫。
‘這裡,’車掌答。
‘我才不乾,’我伯父說。
‘很好——那么你留在原處不許動,’車掌說。
‘是嘛,’我伯父說。
‘得’,車掌說。
別的乘客們對這段對話很關注,發現我伯父決定不下車,那年輕些的人就從他旁邊擠過去,把那小姐扶下車。這時候,惡相的人在察看著他的三角帽頂上的洞。那青年女士走過去的時候,掉下一隻手套在我伯父手裡,並且輕聲地對他耳語——她的嘴唇這樣貼近他的臉,他的鼻子上都感覺到她的溫暖的呼吸了——簡簡單單兩個字,‘救命!’紳士們,我伯父馬上跳出了馬車,跳得如此猛,使車子又在彈簧上搖起來。
‘啊!你改變了想法,是不是?’車掌看見我伯父站在地上的時候,說。我伯父對車掌看了片刻,猶疑著好不好把他的敞口槍搶過來,對那拿大劍的人臉上開一下,再用槍柄對另外一個當頭打一下,搶了那青年女士趕快逃走。但是轉念一想,他放棄了這個計畫,因為實行起來有點太離奇式了,於是就跟著那兩個神秘的男子:他們把女的看守在他們之間,正走進一所古老的房屋,馬車就停在這房子前面。他們轉進了過道,我伯父也跟了進去。
在我伯父見過的一切荒涼的地方中,這裡是最嚴重的了。看起來它好像曾經是一座很大的娛樂場所;不過屋頂好幾處已經坍下來,樓梯是陡峭的。崎嶇的、髒亂的。他們走進去的一間房,裡面有一隻巨大的火爐,煙囪被煙燻得漆黑;不過現在沒有溫暖的火焰照亮它了。白色的羽毛一般的柴灰仍然鋪在爐底,不過爐子是涼的,而一切都是陰暗的。
‘嗨,’我伯父四面看著的時候說,‘一部郵車用一小時六里半的速度趕路並且在這樣一個洞似的地方無限期地停下來,真是一件極不正當的事情呢,我想。這是要查清楚的;我要寫信給報紙。我伯父說這話用的是特大的聲音,並且持公開的毫無保留的態度,目的是儘可能地引那兩個陌生人和他說話。但是,他們對他根本不注意,只是一面向他狠狠地盯著,一面互相小聲說話。那位小姐是在房間的緊裡頭,她冒險揮了一次手,好像乞求我伯父救助似的。
最後,兩個陌生人走近了一點,很認真地開始談判了。‘你不知道這是私人的房間吧;我想,傢伙?’穿深藍色上衣的人說。‘不,我不知道,傢伙,’我伯父答。‘不過若這就是臨時特地開的私人房間,那我相信公共房間一定是極其舒服的房間了。’說著我伯父就在一把高背椅子上坐下,用兩隻眼睛打量那位紳士;打量得這樣精細,只要根據他的估計,鐵近和威普斯就可以替他做一套印花布衣服,不會大一時,也不會小一時。
‘離開這房間,’那兩人不約而同說,抓住他們的劍。
‘呃?’我伯父說,像是根本不懂他們的意思。
‘離開這房間,否則就要了你的命,’拿著大劍的惡相的人說,同時就拔出劍來在空中舞著。”(第49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