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國史綱》
《中國史綱》作者張蔭麟是著名的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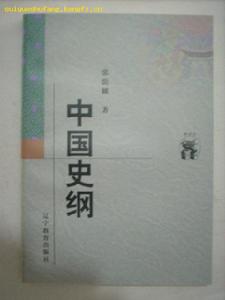 《中國史綱》
《中國史綱》張蔭麟此作,天然去雕飾,絢爛之極歸於平淡,通史之難作即在於此。史學材料本身蕪雜龐繁,沒有足夠的才學與駕馭全局的能力,很容易掉進材料淵博的海洋中,像進了茂密的森林,在那裡摸索著,找不到出路。蔭麟天縱天才,以其深厚的樸學功底,縝密的思維,和傑出的處理材料的能力,把紛繁蕪雜的史料處理得隱而不露。那平實的文字的背後,藏著多少典籍與史料,我們不得而知;讀者讀此書,只覺得它一氣呵成,毫無雕琢堆壘的成分,從中得到無盡的閱讀快感。
《中國史綱》這本書就有著這樣的語言。清晰的敘事,是在作者清晰的掌握歷史的脈絡並銘記於心之後才能達到的,這是功力的體現。嚴謹的態度存在於字裡行間。而那掩不住的熱情,在作者寫思想史時尤為明顯,《墨子》一篇,就是優美而充滿熱情的散文,可以單獨拿出來放到教科書上了。著作不在乎多寡,而在乎作品的質量。著作等身的歷史學家不少,能流傳下來的能有幾部呢?很多能流傳下來的也是僅能當作資料來查一下而已。張蔭麟只這一部足矣。
此書名為通史,實際上到東漢以後便無下文,天妒英才,奪走了蔭麟年輕的生命,蔭麟之亡對於史學界是一重大的損失。今天江蘇文藝出版社重版蔭麟未竟之作,既是對蔭麟史學名作的肯定與重新審視,也是對讀者的一種饗饋。細讀此書,於基本的史學知識之外,還能學到不少治史的方法。國學大師黃侃先生曾說,術由師授,學自己成。讀《中國史綱》這樣傑出的作品,既是養學之勝地,同時更是求術之佳所。
成書經過
張蔭麟(1905-19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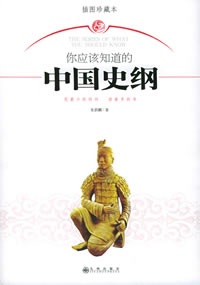 《中國史綱》
《中國史綱》張蔭麟卓特精神、天性聰穎、高屋建瓴外,與其勤奮若癲狂分不開。他每寫一文,精神高度集中,幾晚不睡,直至一氣呵成,然後大睡幾天大吃幾頓,滿屋狼藉亦不顧。
當時張蔭麟寫《中國史綱》是準備給民國作課本的,計畫他寫到唐朝,以後的交給吳晗。可惜只寫到王莽,他就病了。他的好友張其昀追憶:“他是一位飽學之士,能禁其閱書,而不能禁其運思。他念念於史綱之完成,雖在病中仍精思不休,而病勢遂陷入深淵。”
編纂方法
張蔭麟寫《中國史綱》強調從長編入手,
 《中國史綱》
《中國史綱》將所選擇的重要史料系統化,即張先生所說“統貫動的歷史的繁雜”可以有四個範疇:1、因果的範疇;2、發展的範疇:定向的發展、演化的發展、矛盾的發展。
張蔭麟寫《中國史綱》有一整套寫作通史的理論,但他不必把這深奧的理論壓給讀者,只是化在書里了。並且有著那個時代青年特有的對國家民族命運之憂,然而歷史的開闊眼界又給了他一種不同於憤青的信心。書中極少引用古文,往往是作者將古文化了再複述出來,比翻譯又高了一層。民國學者寫作大抵不像現在寫論文,東超西拼加起來。感覺張蔭麟是自己先想好要怎么寫,整篇文章一段一句都已經在胸中了,這才動筆,遇到實在不記得的地方,或涉及時間地點等,才查查資料。編撰通史是最難的工作,蔭麟的體會是:“寫中國通史永遠是一種極大的冒險。”
主要內容
蔭麟《史綱》否定黑格爾以來“目的論”史觀,
 《中國史綱》
《中國史綱》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會》分9節整體勾勒周代社會,從而否定西周奴隸制社會說,認為西周封建乃中國式,是以家族、宗族聚邑為基礎,由部族方邦聯合,進至以宗法制為紐帶的散漫的封建。他進而認為:“周代的社會組織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史的基礎。”
第二章後面直到第七章,遵從這樣的思想:“從這散漫的封建的帝國到漢以後統一的郡縣的帝國,從這階級判分、特權固定的社會到漢以後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較平等的社會,這其間的歷程,是中國社會史的中心問題之一。”用一個“散漫”到“統一”來過渡並描繪了周代後的總貌。他把中國古代史分為三個時代:部族時代、封建時代和統一時代。這種體例與現行的通史體系極為不同。蔭麟認為統一的帝國歷史主要的內容其實是如何作好統一下隨“大”而生出的工作。
張蔭麟挖掘史料的能力非常強。舉個例子,陳烯造反的時候,手下有很多都是商人。漢朝那邊聽到這個情況,就知道可以收買之,於是輕鬆平定了造反。這件事是史有名文的,算不得什麼大事。而張君竟可以將此事與當時的抑商政策(錢不從平民身上出,只能從商人身上出,中產以上商人破產之事便是因此了)聯繫起來,分析了一通漢朝的經濟問題。
又如關於武王伐紂,他沒有採用傳統經書的說法,而是從詩經等材料入手,比如說周飢,伐殷而後得食之類。由此分析這一場戰事的真是背景,以期更加貼近事實。
張蔭麟先生他對夏商周時代的描摹,與其說是朝代的更替,不如說是處於中原不同方位之部族間的爭鬥更為妥帖。在書里花了不小的篇幅敘述了商周的宗教(第9-10頁,第42頁以下)。“商人尚鬼”,乃是一種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最早的宗教形式之一。人之死亡,最早時大約是不能為在世者注意得到的。後來,在世者開始對於人之死亡感到困惑不解,認為人之死乃是去了另一個不為在世者所知的地方,但是死者的力量並未消失,仍然存在,後世的福禍由死者控制。這種心理對於人類早期來說再自然不過,是極為樸素的哲學觀,而不是迷信。這種樸素的哲學觀,反應了早期人類對於時間的意識。
商代的五度盛衰,對後世“未來”觀念的形成意義重大。商人較為穩固,但卻如漂泊於茫茫大海的船,由於大船堅固,船上的人從未考慮過船身某天會遭遇不測。未來對他們來說是不存在的,因為還沒有“未來”這個觀念。只有幾經變革、更替、興衰之後,商王才逐漸意識到今天的治理與未來安寧存在某種“關係”。這種因果聯繫歷經數代變遷被逐漸強化,也成為了後世的記憶。
周朝評價商說:“不知稼穡之艱難,惟耽樂之從”。這是歷史經驗之總結,卻是商人不得不歷經的事實。對前人來說,這種荒廢再正常不過。總結前人經驗,是文明開化過程,是生存本能,在此歷程里,未來觀念漸漸形成。
張在事件的結尾來一句精當的總結,這樣的總結通篇都有。在講敘漢武帝時期“道家學說的全盛及其影響”一節的最後“但道路黃老學說成為大腹賈的附身符時,黃老的勢力就快到末日了”,在總結王莽失敗的原因時引用《新論》的篇幅、指出劉秀所著手的變革都是朝著“鞏固自己和子孫的權位”這種方向……斷想一個沒有經過長期研究、考證的人是無法作出如此結論的。治學但須如此,有自己的方向,有自己的觀點。
《中國史綱》里的王朝的興起,必定有一種強有力的思想流派在支撐,而王朝的更迭,更是預示著一種思想的沒落與不合時宜。書中談到王莽之所以失敗的原因,“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辯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群下,又數陰中不快己者”,作一國之君,有“飾非奪是”之智,但專斷獨行,打擊異己,人是有局限性的,不廣開言論渠道,尋求各種矛盾的相互制橫,當事者必定走向昏聵,王者必定陷入孤立無援;“……欲事事效古而不知……已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很多故事的意義都只在同樣的條件下產生效應,脫離了環境,又會有其他的結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