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王銘銘剽竊事件
王銘銘剽竊事件可是,偏偏是這樣一本“像樣的書”,被一位非人類學專業的年輕人看出了破綻:當時正在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攻讀博士學位的王曉生,2002年1月10日在《社會科學報》發表《北大博導剽竊,叫人如何不失望》(署名“曉聲”),揭露《想像的異邦》第二編《視野》“總共10萬字左右全部抄襲自他自己所翻譯的哈維蘭的《當代人類學》”,“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想像的異邦》書末開列的‘參考文獻’中,王銘銘列舉了120位中外學者的論著,卻沒有列舉哈維蘭的著作。這本由王銘銘自己翻譯,且由王銘銘全篇搬運了10萬字左右的學術名著,遭遇如此的待遇,實在是不公。”王銘銘是從英國獲得博士學位、在北大從事完博士後研究而留校的“海龜”,當時是北大教授、博士生導師,而且還是國家“百千萬工程”入選人、全國高校優秀青年教師。
一石激起千層浪。於是北大教授抄襲再度成為報紙、網路、廣播、電視關注的焦點話題,有嚴厲批評的,有冷靜分析的,也有為王銘銘唱讚歌、鳴不平的,無奇不有。在這些為王銘銘抄襲辯護的人看來,對王教授“體無完膚的攻擊”乃是一個“別有用心的群體”所為;“似乎成了竭斯底里發泄的典型”;乃“居心不良”、“別有用心”、“卑鄙”、“恣意玷污對方的名聲”、“階級仇恨”、“學術鬥爭”、“一棍子打死”、“整人”、“文革”,等等。王教授指導的博士生感到“自己敬愛的老師遭受惡意攻擊”,並說“王老師之所以遭到這樣的惡意攻擊,就在於‘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就在於有人嫉妒他為中國人類學做出的突出貢獻,嫉妒北大人類學在學術界的地位”。王教授教過的本科生則討論如何“向銘銘獻花”。包括清華、北師大在內的10多位教授向北大校長寫信,要求“保護王銘銘”;武漢大學的一位教授把10萬字的抄襲說成是王教授“放棄自己的言說能力而讓一個或許並不比自己高明多少的哈維蘭先生替自己作學術發言”。還有的認為“這樣對待王銘銘過了”,因為“王銘銘在學術上是有貢獻、有創見的,像他這樣處在該學科前沿的人才,中國沒有幾個。費孝通先生年紀大了,精力有限,他名下的一些博士生,平時實際上由王銘銘指導。如果讓王銘銘靠邊站,有些事無人代替。”於是,“為王銘銘辯護”一度成為相當流行的關鍵字。
處理結果
抄襲事件被披露後,北大“有關領導多次找王銘銘教授談話,對其進行嚴肅的批評教育,要求他做出深刻檢討,並通過適當方式向有關方面致歉”。王銘銘本人在《我的檢討與致歉》(2002年1月23日)中表示:“《想像的異邦》……在書中介紹學科研究領域、概念和著名描述性案例的過程中,我確實大量錄入了《當代人類學》一書中的有關內容。當我意識到這事實上已構成對他人著作的抄襲時,我對自己所犯的嚴重錯誤感到震驚,並感到深深的痛悔。在引用他人的論述時,不註明出處,顯然不符合學術活動規範。對這一錯誤,我正在深刻反省,並將終生為鑑。”北大黨委《關於在全校師生中開展師德學風教育的通知》稱:“王銘銘事件在媒體披露以後,不僅在校內,而且在社會上都引起了廣泛關注。這表明社會各界和全國人民對北京大學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也顯示人們對學術腐敗現象的強烈不滿。”北大校發24號檔案(2002年2月5日)《關於停止王銘銘招收博士生的決定》云:“鑒於王銘銘教授錯誤行為的性質,為嚴肅學術紀律,2002年2月4日,學校研究決定,停止王銘銘教授招收博士生。”王銘銘先生現在依然是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的教授,也仍舊是該所的博士生導師(只是暫時停止招生而已)。而且,據《中華讀書報》頭版頭條報導,王教授的書照樣暢銷。
涉嫌剽竊國外名教材的北京大學教授王銘銘已受到嚴肅處理。記者從北京大學獲悉,北大校領導已與王銘銘進行了嚴肅的談話,他本人對此事也有了較深刻的認識。目前,王銘銘的學術職務基本已全部被撤消,其中包括北大民俗學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社會學系學術委員會委員、北大人類學教研室主任等職務。北大社會學系正準備以此作為教材,對全體教師進行關於學術道德的教育。
據了解,揭露剽竊真相的是北京某大學中文系2000級博士研究生,真名為王曉生,專業是研究文藝理論。今年1月10日,《社會科學報》第七版刊登了王曉生以“曉聲”為名寫的稿子《北大博導剽竊,叫人如何不失望》,文章中所指的剽竊者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年輕教授和博士生導師王銘銘。
據王曉生說,王銘銘的書在高校文科生中比較知名。但在看王銘銘的近作《想像的異邦》(1998年出版)時,王曉生髮現有些問題。他聯想到了1987年出版的美國人類學家哈維蘭的《當代人類學》(中譯本)。最終,王曉生髮現,除了個別字的修改或者語氣的改變,《想像的異邦》第二編幾乎與《當代人類學》第四部分、第五部分、第六部分相同,甚至連結構段落順序也沒有改變,大改的只是原書中的一些小標題給去掉了。為了證明問題的嚴重性,王曉生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終於算出,兩本書竟然有10萬字的內容是一模一樣。
《當代人類學》(中譯本)和《想像的異邦》相隔出版的時間有11年,而王銘銘正是此書的翻譯者之一。當年的王銘銘不到30歲,在廈門大學任職。後來王銘銘到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留學,畢業後被北大引進回國,成為北大一名年輕教授。儘管兩本書有如此多的內容相同,王銘銘在《想像的異邦》一書中的序言部分和參考文獻部分沒有一次提到美國作者哈維蘭。這兩本書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事件啟示
這幾年學者抄襲剽竊的事件陸陸續續被抖落出不少,當事人有的挨了處分,有的被撤職,被調離,總之大部分是內部解決了事。而這一次不同,一是由媒體率先曝光,引起了社會的關注,想遮也遮不住了;再就是當事人的身份不同凡響,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優秀青年教師獎獲得者。看著這一長串如雷貫耳的頭銜,不由得人們不驚詫,驚詫之餘,也就產生了一些想法。誠信是立人之本,也是師道之本據《社會科學報》一篇署名“曉聲”的短文揭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北京大學著名青年學者王銘銘所著《想像的異邦》,存在著嚴重的抄襲問題。化名“曉聲”的王曉生是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2001級博士生,王曉生很喜歡人類學,也很仰慕王銘銘的學問,凡是王銘銘寫的書或文章都要找來讀一讀。在上人類學課時,讀到哈維蘭的《當代人類學》,覺得似曾相識,於是找出《想像的異邦》對照一看,發現問題嚴重。王曉生用了一個多月時間,逐字逐句地對照兩本書。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拿著‘文曲星’一個字一個字對照的”。結果全書共32萬餘字,其中有10萬多字幾乎是原封不動地抄自美國人類學家哈維蘭所著的《當代人類學》;更巧的是,《當代人類學》中譯本,正是由王銘銘與別人在1987年翻譯,也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的。翻開那本惹事的《想像的異邦》,我們可以看到一段令人羨慕欽佩的履歷和響亮的學術頭銜:“王銘銘,1962年出生,曾就讀於廈門大學人類學系(1981-1987),1992年獲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社會人類學博士學位,此後在倫敦城市大學、愛丁堡大學、北京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現任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學人類學與民俗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兼秘書長、倫敦城市大學名譽研究員。已出版《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社區的歷程》、《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力》、《山街的記憶》等專著,《當代人類學》、《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等譯著及學術論文40餘篇。” 毫無疑問,王銘銘的學術地位並不是浪得虛名,能在全是人尖子的北大出類拔萃,自然有過人之處。常言道,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只不過這陣風是他自己攪起來的。在人類學界,王銘銘的榮譽和是非幾乎一直是一樣多的。兩年前,復旦大學曹樹基教授就曾在報上撰文,對王銘銘《社區的歷程》一書中存在的粗製濫造和常識錯誤提出批評;王銘銘寫文章回應,二人之間產生爭論。不過,事情很快就過去了。在北大校方眼裡,王銘銘是難得的人才。就像北大4位人類學博士在支持王銘銘的一封公開信中所說的,他“誨人不倦、學識淵博、胸懷寬廣,乃是學生中的楷模”。很快他當上了博士生導師,還獲得教育部第二屆優秀青年教師獎。然而,在學生形容導師的幾個漂亮的形容詞中,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他們漏掉了一個辭彙:“誠實”,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誠信乃是立人之本。做學問要先學會做人。不知道王銘銘教授對他的學生有沒有過這方面的教誨。如果有,那么他就是言不由衷;如果沒有,那他至少不算是個優秀的教師。上過學的人都知道,從國小起,老師就不厭其煩地要求學生獨立思考,不得抄襲同學的作業和試卷。違反這一條紀律的,最輕的處罰是成績以零分計算。無論上學上到什麼階段,無論國內還是國外,抄襲和剽竊都是校紀校規明令禁止的。王銘銘對此不會不知道。知道而又明知故犯,要么是得意忘形,要么是有恃無恐,要么就是壓根兒沒把這當回事兒。有學者說,現在的社會風氣就是如此,急功近利、學風日下,都是學術機制不完善的惡果;學術腐敗的根源在社會,其咎不在學者個人;王銘銘本人也是受害者。這種說法不能成為為其剽竊行為開脫的理由。倘若每個人都以“很多人都如此”為由原諒自己行為的不端,那將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災難。現實中這樣的事情太多了。“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我們幾乎每天都能聽到這耳熟能詳的話語,阿Q 的幽靈一直在中華大地遊蕩。社會道德的長堤就這樣在一點點被侵蝕,被蛀空。人人都在抱怨道德的淪喪,但在板子打向自己屁股的時候卻又希望能夠得到赦免。高校是神聖的學術殿堂,學者們在肩負著文化傳承的歷史使命的同時,也一直扮演著社會道德守護者的角色。他們不僅是知識的載體,也是維繫社會道德的鬥士。“大學教授”在歷年的“社會聲望調查”中依然名列前茅;在青少年的“職業選擇調查”中,“科學家”和“大學教授”也始終位列前幾名。這一切不是靠行政命令和媒體炒作得來的,而是多少代優秀學者身體力行、鞠躬盡瘁的歷史積澱。讓人痛心的是在今天這種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一些知識分子未能經受住利益的誘惑和驅使,一個失去道德約束的學者,縱然學富五車,縱然著作等身,也只能遭到同仁的鄙視。在這一點上,任何為王銘銘辯解的理由都是蒼白無力的。學術剽竊不是學術界的內部問題,它反映的是社會道德問題半年多以前,面對學術界的世風日下,北大召開“樹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識”誓師大會,信誓旦旦地提出“清除贗品拒絕平庸!”副校長何芳川教授在會上義正辭嚴地指出:“如今,學術打假的呼聲,開始不絕於耳。面對負面亂流,凡我北大文科同仁,皆應橫眉冷對、拍案而起。首先,要從‘我’做起,北大人應有勇氣向社會作出莊嚴承諾:清除贗品,拒絕平庸;同時,抱定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精神,以建設優良學風為己任,高舉北大文科精品意識大旗,反亂流,出精品,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刊載此次訊息的《光明文摘》用心良苦地寫道:假如北大真的不負眾望,在拒絕平庸、倡導精品方面,真心誠意,心口如一,以身作則,率先垂範,其功德將善莫大焉。然而,距北京大學不久前召開的一次最大規模的關於文科學術道德的大會僅僅數月,一直受到校方器重的王銘銘就讓北大蒙受了近20年來最大的恥辱。王銘銘的所有學術職務一夜之間被撤銷了,而學術界對此事件的反映卻各不相同。有人甚至認為同學科的學術著作,相互之間的啟發、借鑑是正常的現象,“剽竊”行為難以界定;有的以為王銘銘事件是學術問題,應由學術界內部處理,媒體沒有必要大肆炒作;有的說以王銘銘在人類學界的貢獻和地位,不該被“一棍子打死”,不該對他求全責備。還有人懷疑,這一事件是學術派系之爭的結果,王銘銘是犧牲品。北大的幾位博士居然說:“學術批評應該全面、客觀、平和、公正,執一端而不計其餘的做法是不正常的。”不知道他們是愛師心切,還是讀書讀昏了頭。抄襲剽竊不能算是學術專業領域內的事情,不屬於學術爭論的範疇,而是關乎一個人的學術道德、關乎為人師表的思想品德問題。對抄襲剽竊的揭露和批評,也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學術批評。的確,我們不能因為某人的一個或幾個錯誤而否定他的全部成績,但是,如果這個錯誤已經影響到教師職業的神聖和尊嚴的話,對一位教師來說,那就是不可原諒的了。武漢大學鄧曉芒教授說得好,對待學術抄襲應該像對待盜版一樣,一旦發現就罰個傾家蕩產。北大規定:對有嚴重學術道德問題者,實行一票否決。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學識淵博是一回事,道德品質是另一回事。犯什麼樣的錯誤就必須付出同等的代價,至於以後如何,那要看他今後的表現。王銘銘已經向其抄襲的《當代人類學》的作者哈維蘭道了歉,具體內容不得而知。面對國內媒體,他依然表示“無可奉告”,但承諾“會在適當的時候表態”。但不管王銘銘有何話說,學術剽竊,學術腐敗就像官員貪污受賄一樣要不得,它涉及的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學術界乃至社會的道德問題。處理不力是學術剽竊行為蔓延的罪魁想成為學者,在學術界謀得一席之地,首先要學會的是遵守學術規範。學術規範包括學術道德規範和學術操作規範。學術操作規範是硬槓槓。從文獻檢索到論文寫作,從引文注釋到參考文獻,前輩學者已經創立了整套的規範,照著做就是了。而學術道德規範則是無形的,只能在長期的學習過程中耳濡目染,只能從師長的一言一行中去領會感悟。在諸多學術道德規範中,最敏感的大概就是禁止學術剽竊了。學術剽竊,歷來為學人所不齒。然而近些年來,在學術界屢有發生,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這固然與整個社會風氣惡化有關,恐怕和處理不力也不無關係。為尊者諱,為長者諱,為地方利益諱,結果投鼠忌器,反而助長了這種歪風的蔓延。在我們的教育實踐中,有一種令人擔憂的現象,那就是唯上、唯書;只注重上級評價,只看中考試結果,對個人的思想品質關心甚少。一個教師或學生只要能出成績,能給學校或老師帶來榮譽,就是好的,就會受到種種恩惠和關照。而他們犯的錯誤因為關係到他的成績,關係到領導的面子,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有學者呼籲“以德治學”,也有人苦口婆心地提出“身為學者,以學術為主。就理應在道德操守上率先垂範,起碼也要守住為人為學的底線”。然而,在功名利祿的強烈誘惑面前,“貴在自律”顯得那么的書生氣十足,那么的蒼白無力。王銘銘事件帶給我們的思考太多了。在為一位青年學者惋惜的同時,我們呼籲有關方面加強學術道德的宣傳和教育。幸運的是,黨和政府已經把目光投向了思想道德建設,我們有理由期待社會環境的淨化。事件曝光後,北京大學對王銘銘迅速做出處理,撤銷其包括北大民俗學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社會學系學術委員會委員、北大人類學教研室主任在內的全部行政職務。
爭論焦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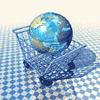 王銘銘剽竊事件
王銘銘剽竊事件對王銘銘的批評和處分到底對不對?此事在各類媒體上成為爭論焦點。
眾說紛紜:同情之聲漸占上風
意味深長的是,此事在各類媒體上被大規模報導和批評之後,近日網上的反應來了個大逆轉:在新浪網、人民網、世紀中國等網站裡,人們對王銘銘事件由原來的群起而批之,變為千姿百態的同情、理解和辯護,對學術硬傷的揭露者,則予以各種猜測和抨擊。以下是網上幾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學生:
我們發覺這些批評越來越不正常,嚴肅的學術批評失去了可能性,代之以上綱上線的誇大和炒作。有的批評,專事挑三揀四,以找語病“硬傷”為能事;有的批評,言詞尖刻,不惜發動人身攻擊;有的批評,空穴來風,對作者引用的著作,幾乎一本沒讀,竟輕言作者“食洋不化”。王老師曾多次表示,沒有必要為這些不具備專業水準的批評申辯。不想,一些人變本加厲,炮製大字報式的文章,肆意進行人身攻擊。而某些傳媒則為了製造轟動效應,推波助瀾,對學術問題指手劃腳、以訛傳訛。我們認為,學術批評應該全面、客觀、平和、公正,執一端而不計其餘的做法是不正常的,尖酸刻薄的言辭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學術批評應該激勵學術創新,應該樹立學術標準的自主和自尊,而不是泄私憤,不是行政干預,更不是無限上綱的大字報。一句話,絕不能用非學術標準評判學術。
——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生:張宏明梁永佳褚建芳楊渝東《致校領導的一封公開信》
同行: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張XX:本來完全可以在一個小圈子內進行,為何要讓所有的人都知道?是不是炒作,已經昭然若揭。現在的問題在於,學術批評畢竟是非常專業的事情,是不是普通民眾有能力作出判斷,我個人對此懷疑。……新聞媒體剛剛披露王銘銘涉嫌抄襲,還沒有等到學術論證,還沒有等到學術委員會的界定,就匆匆地作出處分,是不是有點太快了。北京大學是否堅持了學術自由的傳統?是否堅守了學術規範?是否北大屈服於新聞媒體的壓力?我個人對此表示疑問。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郭於華女士:王銘銘教授涉嫌抄襲哈維蘭著作固然有其個人的原因,也從根本上離不開整個學術評介制度的不完善、數字量化等簡單化管理。但是還有一點不容忽視,在學術研究上非常有天分和素養的王銘銘教授被當作了學術明星,被抬到了很高的位置。實際上王銘銘教授處在那樣的一個位置,不能不試圖最大限度地作出努力來適應整個社會對他的評價。他實際上是無法完成這樣的任務的。某種意義上,他也是一個受害者。 北京某高校研究所青年學者對“學術媒體化”頗有微詞,他說:“經過媒體的一番集中轟炸,使得像王銘銘教授這樣推動學術創新機制、具備創新能力的中青年學者膽戰心驚,噤若寒蟬,誰站出來說句公道話都很可能會招致無盡的攻擊。”
網友:
至於公開道歉,既然陳章良也沒有公開向全社會道歉,憑什麼要王銘銘向全社會道歉?既然大家都做不到,曹教授單單要求王這么做(指曹樹基撰文要求王銘銘向讀者道歉,並公開自檢還有哪些專著曾有抄襲。———記者注),還不過份嗎?……這次批王銘銘,注定是要發生的,這倒不是因為王銘銘確有其事,當然了如果王銘銘沒有這樣的事,那些自認為自己是學者的人們不會認為這次我可是吃準了,要大舉攻擊王銘銘。但是,就是這些“學者”認定了這次的攻擊必然得手,恰恰反映的就是一種醜陋的以學術名義,但事實上是要通過非學術手段打倒對方的行為!
———燕園秋士
現在發表的一些批評文章已經從“吹捧”這個極端走向了“打倒”這另一個極端,很像“文革”做法。那些自我標榜的“學術警察”之所以會盡其大批判之能事來打擊別人,表現出對違反學術規範的學者的刻骨仇恨,而不將學術批評當成是學術的事情來做,是因為他們嫉恨其他學者的成就和社會影響,是因為這些學術警察除了抓人之外,不知道學問需要冷靜地做,更不知道學海無涯。……這樣的情況如果延續下去,就只能導致學術批評的品質變化,使學術批評成為“整人”的手段。
———成真言
當然,也有人士對此持明確看法。剛從香港回來、對此事尚未聽說的著名社會學家李銀河博士聽記者介紹了大致情況之後,說,如果王銘銘的情形的確如王曉生所指出的那樣剽竊了近10萬字,那么別管批評者動機如何,只要事實成立,都沒什麼可辯白的,剽竊就是不對,學術研究決不能淪為不顧起碼的學術規範、單純博取名利的手段。
學術評定機制:問題出在哪裡?
面對轟動的“北大博導涉嫌抄襲事件”,公眾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集體性的庇護傾向?如果說“王銘銘事件”反應的是一種學術評定機制的弊端,那么它的弊端究竟在什麼地方呢?為此,記者採訪了幾位學界中人。
吳寶科:我不清楚評審委員能否看完每部專著
當記者撥通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黨支部書記吳寶科先生的電話,表示關於王銘銘的事要採訪他一下時,吳先生立刻表示不接受採訪。記者趕忙請教他評定教授和博導的標準,吳先生解釋道:一是看“參考分”,它又分為“教學參考分”和“科研參考分”,後者以成果數量計分,作為計分依據的專著卻不一定會被審讀。另外,申請職稱還須走三個步驟:述職、提交成果由評審會審閱、投票。吳先生特別指出,提交的成果一般是申請人代表性的而非他的全部成果。評審會分系、學部、校三級,共有幾十名委員。記者問:“這些評審能保證把每位申請人的著作都看一遍嗎?”吳先生回答:“不清楚。”
何光滬:學術評審會產生得不合理
中國人民大學宗教學系教授何光滬認為,王銘銘涉嫌抄襲事件暴露了我們的學術體制存在已久的問題。每個國家的學術界都會有試圖投機的人,為什麼我們這裡卻會成風呢?首要一點在於,西方有專利制度,保護智慧財產權,它要求一個人在著作里引用他人著作的詞語超過三個以上就必須用引號標示出來,並且對學術著作和通俗著作加以嚴格區分。學術鼓勵原創,重“質”勝於重“量”。
在我們這裡,首先是學術委員會產生得不合理,在多數單位,它的成員是由上面指定的,而西方是由學術同行選舉產生的。我們有些單位的學術委員會往往由退休官員組成,不具備專業上的權威性,工作上無章可循,官本位,學術創造性不被了解和重視,必然會出現人情票、論資排輩、重數不重質等弊端。學術評審總要求在“核心學術刊物”發表文章,而不少核心學術刊物是腐敗的,你給他錢他就給你發文章,真正有價值的文章他們卻可能並不發表。
金雁:量化評定逼使學人無法踏實做學問
中央編譯局研究員、東歐問題專家金雁女士說,王銘銘事件和整個社會的素質下滑有關,學界這種情況太多了,不只是王銘銘一個人,所以會有很多人為他辯護,而這就更可悲。如果是同聲譴責,表明學界還有救。
金雁認為王銘銘事件僅僅是學術評定量化弊端的一個例子而已。現在的科研單位都實行量化的評審制度:每年年底有考核,把科研成果量化成分數,比如在核心刊物發表論文得多少分,發在非核心刊物多少分,電視腳本多少分,出鏡率多少分,專著多少分……分值相加,就可以評定你稱職與否,一年一次,立竿見影,這就要求你必須重視短期效應,把研究快餐化。這樣學者就沒法沉下心來做踏實深入的研究,更不可能“十年磨一劍”出一個大成果了。即便你磨出一部厚重的著作出來,社會也不接受,現在大眾趣味是快餐化、兒童化,什麼讀物都以能否在捷運、廁所閱讀為尺度,那么厚重的著作自然吃不開。
金雁說,現在有的單位“出鏡率”也要計算在成果里,這其實就鼓勵了學者明星化,而學者的真正義務卻是學術研究啊。可如果紮實的研究者的心血之作和一個人出幾次鏡的分數相當,誰還願意耐著寂寞去做學問呢?如果你老是沒有著作,就不會有分,一兩年這樣下去,就會被淘汰出局。於是學術界爭相急功近利,抄外國人,抄自己,只要有好處,就什麼都乾。再過幾年,學術界就會跟娼妓差不多了。可如果你在體制內吃這碗飯,就會把你往這個方向上推。
另外,評職稱就必須要拿課題。首先有些課題的設定就有問題,常常向媚俗化和政治化的方向靠攏;其次課題分配給誰,往往是黑箱操作,得需要搞人際關係才能拿到課題,沒有課題,你的評議就會受到很大影響。另外,許多評審並不懂專業,他們的評定結果在很大程度上自然就有問題。
所以,追究王銘銘個人的事情固然重要,但更應追究的是當前的這種學術評定機制,它是一個大問題,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
北大的反應
 王銘銘剽竊事件
王銘銘剽竊事件北京大學的惱火是可以想像的。2001年4月27日,北京大學召開的“樹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識”大會上,北大副校長何芳川言猶在耳:“北大人應有勇氣向社會作出莊嚴承諾:清除贗品,拒絕平庸。”
北京大學此次對於王銘銘事件的反應出奇地迅速,很快宣布,王銘銘的學術職務基本已全部被撤消,其中包括北大民俗學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社會學系學術委員會委員、北大人類學教研室主任等職務。
此訊息發布出去之後,叫好者認為處理得嚴肅及時,同時也有不少人提出疑問,學術處理應該有規範可循,何以北大因受到傳媒的壓力就匆忙做出決定?
後來,北京大學新聞中心有關官員又稱,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已對此事進行調查。不過,這種說法有些自我矛盾,既然學術委員會還沒有查清王銘銘的錯誤,為什麼處理決定已經做出?
訊息人士說,北京大學對王銘銘的處分其實是在去年11月份而不是在今年1月份做出的。處罰事因應該差不多。在事態被炒大之後,為了面對大眾媒體的質詢,北大統一了口徑。因此,“北大迫於公眾壓力,對王進行懲罰措施”的說法不成立。
對王銘銘的處罰看來還沒有結束,據傳,他的教授職稱和博導資格也有可能不保。
北大清除“學術腐敗”的決心和力度固然可嘉,但北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應付責任。
比如說,對於去年影響很大的那次“樹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識”大會,《史學月刊》編輯部副編審周祥森就曾經毫不客氣地評論,儘管言之鑿鑿,但“北大領導層的講話,浸透於其中的依然是學術的功利性,而且不乏浮躁的氣息”。
周尤其反感的是所謂“春種秋收”理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產品,不是工廠流水線上生產的產品,可以按照一定的標準或模式,保質保量按時完成,甚至大規模批量生產。它必須經過研究者相當的知識儲備、理論醞釀、方法論的創新等,才能生產出來。文科精品的生產尤其如此。4月份種下精品意識,指望幾個月後的秋天就能有‘最前沿的科研收穫’,這不顯然是操之過急嗎?”
郭於華就指出,在學術研究上非常有天分和素養的王銘銘教授被當作了學術明星,被抬到了很高的位置,所以他不得不試圖最大限度地作出努力來適應整個社會對他的評價。
“春種秋收”會不會導致“拔苗助長”?需要反思的大概不止北大一家。
方舟子學術打假記錄
| 時間 | 涉及人員 | 事件 | 時間 | 涉及人員 | 事件 |
| 2000年9月 | 楊池明 | 楊池明事件 | 2004年7月 | 薛涌 | 薛涌事件 |
| 2000年8-9月 | 陳曉寧 | 基因皇后事件 | 2004年10月 | 丁祖詒 | 西安翻譯學院美國排名事件 |
| 2000年11月 | 斯德誼 | 北航抄襲事件 | 2005年 | 夏建統 | 夏建統事件 |
| 2001年11月 | 吳征 | 吳征假文憑事件 | 2005年12月 | 潘知常 | 潘知常事件 |
| 2002年1月 | 王銘銘 | 王銘銘剽竊事件 | 2005年12月 | 丘小慶 | 丘小慶事件 |
| 2003年 | 陳進 | 漢芯造假門 | 2006年1月 | 朱蘇力 | 朱蘇力招生事件 |
| 2003年1月 | 顧冠群 | 顧冠群事件 | 2006年3月 | 魏於全 | 魏於全事件 |
| 2003年5月 | 汪丁丁 | 汪丁丁事件 | 2006年8月 | 肖傳國 | 肖傳國事件 |
| 2003年8月 | 董關鵬 | 董關鵬事件 | 2010年7月 | 唐駿 | 唐駿學位門 |
| 2004年3月 | 朱涵 | 朱涵事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