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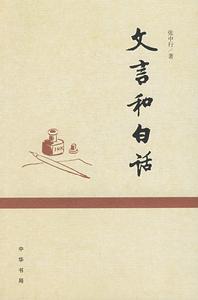 文言白話之爭
文言白話之爭“五四”時期發生的新文學陣營同封建復古派文人之間的一場論爭。
“五四”前後勃興的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和科學兩大旗幟,對以孔孟之道為核心的封建道德和以文言文為工具的封建文學進行了猛烈的批判。當時流行的各種文言舊體文學成為反對的直接目標,其中最主要的是桐城派的古文和文選派的駢體文。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宣布,明代以來擬古派文學家前後七子(見前七子、後七子)和桐城派古文家歸有光、方苞、姚鼐、劉大櫆為文學革命所要反對的“十八妖魔”。錢玄同在1917年7月2日致胡適的信中,更進一步指斥“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的古文,“以不通之典故與肉麻之句調戕賊吾青年”的敝害(《新青年》3卷5期)。當時,“桐城派”的古文和“文選派”的駢體文,不僅成為脫離生活和口語的封建文學的工具,而且在政治生活中也同復辟帝制、祭天尊孔、復古讀經等活動密不可分。因此,新文學運動一開始就招致一班維護舊道德和舊文學的復古守舊派文人的竭力反對,從而釀成激烈的文言白話之爭。
階段
文言白話論爭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
 胡適
胡適第一階段:論爭的醞釀。1917年初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之後不久,自附於“桐城派”的復古文人林紓(林琴南)發表了《論古文之不當廢》進行反對。他只申明古文不當廢除的主張,卻說不出什麼道理,“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1918年初,《新青年》發表傅斯年的《文學革新申義》一文,第一次對“桐城派”古文給以較系統的批評。3月,《新青年》4卷 3期以“文學革命之反響”的標題,刊登了錢玄同、劉半農串演的“雙簧信”。由錢玄同託名王敬軒給《新青年》編者寫信,集中了舊文人反對文學革命的見解,然後劉半農寫《答王敬軒書》加以批駁。劉半農在信中對於“桐城派”、“文選派”的復古論調以及荒謬的古文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揭露和揶揄,特別是對復古派文人林琴南駁得更為著力。反對復古派鬥爭的深入,白話文運動的勝利,使得復古派文人再也耐不住沉默,便起而反抗掙扎了。
第二階段:論爭的高潮。1919年初,復古派文人陳拾遺等出版了維護封建國粹的《文藝叢報》,攻擊白話文運動,說:“今則新體竟尚,吸歐糟而吹美粕,與國粹為大敵,貿然欲推翻之。”林紓在該刊發表了《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一文,鼓吹白話必須以古文為根底,“無古文安有白話”的論調。這樣就拉開了復古派文人向新文化運動進攻的序幕。同年2月,林紓發表小說《荊生》,影射攻擊《新青年》編者,罵反對舊道德提倡白話文是“傷天害理”的“禽獸之言”,幻想有軍閥勢力的“偉丈夫”出來禁壓新文化運動。 3月,他又在《公言報》上發表了《致蔡鶴卿書》,憤憤於白話文運動“必以覆孔孟,鏟倫常為快”,“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接著又發表小說《妖夢》,影射攻擊《新青年》同人。同時,“文選派”古文家劉師培等,創辦《國故》月刊,鼓吹昌明“國粹”而重振“頹綱”,與新文化運動相對抗。北京上海等地報刊也刊登了《新青年》同人被逐出北京的謠言。新文學方面以《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等刊物為陣地,對於復古派掀起的反動逆流進行了激烈的反擊。蔡元培發表了《答林君琴南函》,李大釗發表了《新舊思潮之激戰》,陳獨秀發表了《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林紓的留聲機》,魯迅發表了《〈孔乙己〉篇末附記》、《隨感錄五十七·現在的屠殺者》、《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等文章,對遺老遺少的復古言論和衛道嘴臉,做了徹底的批駁與揭露。魯迅說這些復古派文人想用“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他們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隨感錄五十七·現在的屠殺者》)。到了1919年8月,化名思孟的守舊文人發表《息邪》(一名《北京大學鑄鼎錄》)一文,以為《新青年》同人作傳的形式,對新文化運動及其倡導者進行誣衊和人身攻擊,同樣受到了魯迅、錢玄同、胡適、孫伏園等人的有力駁斥。這場文言白話之爭的勝利促進了白話文的進一步發展,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據“有人估計,這一年(一九一九)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陳獨秀
陳獨秀第三階段:論爭的繼續。1921年以後,新文學運動脫離了一般的新文化運動而獨立,獲得了更迅猛的發展。進步的文學社團和作家對復古的逆流繼續進行鬥爭。這就使得復古派的進攻不得不改換了方式。1922年1月,留洋回國的東南大學教授梅光迪、胡先驌、吳宓創辦《學衡》雜誌,先後發表了《評提倡新文化者》、《論新文化運動》等文章,引述西洋文藝理論為護身符,提出“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口號,反對白話文和新文學,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又一次向新文學運動發起進攻。接著,1925年 7月,北洋軍閥政府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章士釗在北京復刊專登文言的《甲寅》雜誌。章士釗先後在該刊發表《評新文化運動》和《評新文學運動》,重彈提倡“尊孔讀經”和根本否定白話文價值的陳詞濫調,又掀起一股反對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復古主義逆流。“學衡”派和“甲寅”派的復古主張雖然比林紓等人帶有更多的買辦知識分子理論色彩和封建官僚倚恃權勢的特徵,但在文言文已被白話文所代替的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中,畢竟是強弩之末了。進步思想界文學界人士對他們的揭露批判也就充滿了奚落嘲諷的戰鬥色彩。魯迅的《估“學衡”》、《答KS君》、《十四年的“讀經”》,玄珠(沈雁冰)的《四面八方的反對白話聲》,成仿吾《讀章氏〈評新文學運動〉》等,都是在批判“學衡”派“甲寅”派復古逆流鬥爭中寫下的著名文字。魯迅的文章深刻剖析了這些“掊擊新文化而張皇舊學問”的國粹家和復古派們的沒落和可憐。他們“不過以此當作訃聞,公布文言文的氣絕罷了”,即使真的“將有文言白話之爭,我以為也該是爭的終結,而非爭的開頭”。
落幕
其實,在1920及1930年代,關於寫好白話是否需要有文言根底的爭論,發生過不只一次,而且爭論雙方都是現代中國文化界舉足輕重的人物。比如,朱光潛十分欣賞周作人的文體試驗,1926年撰《〈雨天的書〉》,給予大力表彰。
 文言白話之爭
文言白話之爭想做好白語文,讀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現在白話文作者當推胡適之、吳稚暉、周作人、魯迅諸先生,而這幾位先生的白話文都有得力於古文的處所(他們自己也許不承認)。
未見同是新文化運動主將的胡適、周作人對此說發表異議,只有敏感的魯迅不只“不承認”,還將此番言論與復古思潮聯繫起來,稱此乃“新文藝的試行自殺”。在《寫在〈墳〉後面》中,魯迅批評“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詩詞中摘些好看而難懂的字面,作為變戲法的手巾,來裝滿自己的作品”。自認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魯迅因此堅持“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的說法,而且說,這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憤激之辭”。不談思想,單以文章論,魯迅也主張“博採口語”,而不是閱讀古書(《寫在〈墳〉後面》)。
1934年,也就是朱光潛發表《〈雨天的書〉》並受到魯迅嚴厲批評的八年後,章太炎在縱論“白話與文言之關係”時,稱“以此知白話意義不全,有時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白話中藏古語甚多,如國小不通,白話如何能好?”(《白話與文言之關係》)此語同樣招來白話文提倡者的批評,魯迅也對其師之“把他所專長的國小,用得範圍太廣大了”表示不以為然(《名人和名言》)。魯迅等新文化人之所以如此敏感,有文體學方面的考慮,但更主要的,還是基於思想史意義上的反覆古。
隨著時光的流逝,文言白話之爭變得越來越遙遠,以至逐漸被學者和大眾所遺忘。可仔細傾聽,你依然能夠發現不少隱約的回音。只不過這回更多的是梁啓超、朱光潛的意見,而不是胡適或者魯迅的聲音。不見得認定白話文寫得好者,文言文功夫必深;但中學語文教育之注重文言文,卻是不爭的事實。除了文革十年,這一主流意見似乎沒有受到太多的挑戰。一直到去年第五、六期的《粵海風》上,方才有中學是否需要教學文言的爭辯。挑戰者稱,“古代漢語已經失去了工具效應”,而文言文在中學語文教材中“所占篇幅為三分之一”,為了避免“浪費孩子的青春和民族的智力投入”,不如乾脆放棄(摩羅《請文言文退出基礎教育》)。緊接著發表的兩則商榷文章,呼籲“勿做漢語的不肖傳人”者(王曉華《勿做漢語的不肖傳人》),用心良苦,可語調過於悲憤;至於主張“應該退出的是現代漢語文章”(蔣寅《應該退出的是現代漢語文章》),則有點“對著幹”的味道。
貫穿整個二十世紀的“文白之爭”,折射出整箇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波瀾起伏。此類論爭,容易引起研究者的極大興趣,並被迅速納入已經定型的“宏大敘事”中。正因為此話題“關係重大”,人們往往更看好高瞻遠矚者,比如像胡適、魯迅那樣著眼於整個思想文化潮流。至於章太炎、梁啓超、朱光潛之兼顧文字改革、中學教育或文體實驗,則因其稍嫌專業化,而不怎么被社會大眾理解,也不怎么受研究者欣賞。
如何調適中學語文課里的文言與白話,作為一種迫在眉睫的教育實踐,其實是需要認真對待的。相對來說,此類時尚話題,容易引起史家的注意;而我以為,更值得推薦的,當屬梁氏另外兩個容易被忽視的見解。一是強調中學生需要培養欣賞美文的能力,“但中學目的在養成常識,不在養成專門文學家,所以他的國文教材,當以套用文為主而美文為附”。一是主張“學文以學敘事文為最要”,但不應該從小說入手。所謂“有名的史家或敘事文大家,大抵不會做小說;而敘事文的技術,絕非從小說可以學得來”,或許說得過於絕對,但強調敘事文的寫作訓練,主要在於觀察生活與整理資料,而不是馳騁想像力,卻是個值得注意的思路。只要對前幾年中學語文教學的爭辯略有了解,或者對目前散文寫作之趨向於虛構有所反省,當能明白我為何關注梁啓超的這兩段話。
斗換星移,物是人非,八十年前的老古董,不可能成為今人前進的路標;但作為晚清重要的思想家與文體家,梁啓超的思考,還是值得我們認真品味。只是有一點必須提醒:討論任公先生後期的文體意識與教育觀念,必須將《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1922)、《要籍解題及其讀法》(1923)、《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1923)等,以及其在各大學的諸多講演考慮在內,方能有比較通達的見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