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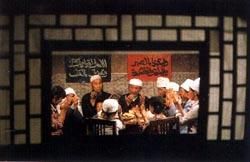 回藥
回藥回醫學是中國傳統醫學與阿拉伯-伊斯蘭醫學“東西合璧”的產物。當歐洲其他各國尚未脫離神學統治之時,阿拉伯人開始發展科學文化。他們開辦大學、建立圖書館,培養了大批人才,阿拉伯文化達到較高水平,在所有科目中,醫學是最主要的,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回藥歷史
隨著阿拉伯人與鄰國的交往,鄰國文化隨之在阿拉伯諸國滲透,並互相補益,醫學上也是如此。伊斯蘭教復興者穆罕默德曾說過:“學問遠在中國,亦當求之”。中阿於公元651年正式友好往來,醫藥方面的交往也興於此時。因此許多阿拉伯學者,特別是一些哲學家不斷總結自己民族的醫療實踐經驗,同時還將其他國家的醫學著作譯成阿文。如格夫退葉在《哲學家傳記》一書中提到:“巴斯拉醫生馬西爾朱衛是哈里發奧馬·阿不杜·阿齊茲時代以色列學者,其真名叫馬西爾·吉斯,精通醫學,在奧馬爾時主持翻譯愛赫蘭·格斯的醫學著作,成書於哈里發穆爾時代,他的另兩部著作是《食物的力量及益損》和《草藥的功能及益損》”。在哈里發奧馬爾時代(公元717年至719年)還請精明醫生充當教育和醫學顧問。倭瑪亞王朝的另一個哈里發哈立德·葉其德是第一個將希臘文天文學、醫學、化學等專著譯成阿拉伯文的人,由於其哲學、文學修養高深,貢獻卓著,被阿拉伯後世學者稱為賢哲。不言而喻,隨文化交流,醫學理論的相互補益滲透現象在後世阿拉伯醫著中不乏其例,這與中國中醫藥著作的《海藥本草》《千金要方》《本草綱目》等記載阿拉伯醫藥同屬一理,都是歷史事實。
早在公元7世紀,阿拉伯一伊斯蘭醫學曾居世界醫學的先進行列,並對西方現代醫學有巨大影響。到中世紀,阿拉伯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醫學家阿維森納的足跡遍及伊拉克、波斯、亞塞拜然、巴基斯坦大片土地。他一生大膽實踐,潛心鑽研,廣徵博求,於公元980至1037年著成熔古希臘醫學、印度醫學、中國醫學、阿拉伯醫學與哲學於一爐的巨著——《醫典》,成為現代醫學和阿拉伯醫學的奠基人。中世紀阿拉伯醫學著作繁多,不少已散失,包括《醫典》在內,流傳至今尚有400多種。
由於阿拉伯醫學廣泛吸收希臘醫學、羅馬醫學、印度醫學(包括中國醫學的脈學在內)的精髓,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醫學體系。其理論核心是“四大物質學說”、“四津學說”。到公元12世紀,伊朗著名醫家拉齊斯的醫學巨著《綜合醫學》10卷和阿巴薩德·達維亞的《綜合百科全書》問世,更加豐富了阿拉伯醫學的治療學內容。是時阿拉伯醫學已成為有理論有豐富經驗的古代醫學。
中國回回醫學的發展,相伴於中阿醫藥交流。中阿醫藥交流歷史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到西漢。當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後,中國與西域之交流日益頻繁,據史料記載張騫曾到達大宛(即今之中亞費爾乾納)、大月氏(即今之阿富汗北部)、大夏(即今之阿姆河南)、康居(即今之中亞撒馬爾罕)等國,並從大月氏經安息(即今之伊朗)直抵大秦(即今之羅馬)。張騫的副使曾達身毒國(即今之印度北、盂加拉、巴基斯坦一帶)及??賓(即今之克什米爾及巴基斯坦北部),經此路輸入中國的物品中有不少藥物,據范行準先生統計:礦物藥如石硫黃、密陀僧等凡18種,植物藥如木香、豆蔻等凡58種,動物藥羚羊角及龍涎等凡16種,總計92種。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阿拉伯地區的藥物。這些藥物均被當時漢醫吸收和套用。
雖然早在西漢時期張騫、甘英先後通使西域,但阿拉伯與中國的正式友好往來則始於唐代,醫藥方面也興於此時。
公元651年,第三任哈里發歐斯曼使節於8月25日到達中國長安,進見唐皇,搭起了中阿友誼的橋樑。自此以後阿拉伯等穆斯林主要沿水旱兩路往來於中阿之間,水路由波斯灣到馬爾納灣。經盂加拉灣抵馬六甲海峽至我國南海達廣州、泉州、杭州,再轉至長安;陸路則經波斯、阿富汗到新疆天山南北,最後達唐都長安。比較而言,穆斯林經水路達中國的時間要比陸路早100年。從唐永徽二年到唐貞元十五年的148年中,阿拉伯遣唐使多達36次。當時唐人稱阿拉伯人為大食(Taz或Tazih的譯音)人。唐安史之亂,大食應中國之請求,派精兵支援唐王朝,後一些阿拉伯人即定居中國。據史料記載,在安史之亂到長安有更多大食人,其中大部分長期居住在“西市”一帶,從事“回回”奇香異藥經營。由於盛唐五代時期,阿拉伯與中國的關係最深的是商業貿易,醫藥方面則是香藥進口,有時一處經營香藥珠寶者甚至達一二十萬人,單香藥貿易有時竟達千斤之多,如此大大豐富了中藥品種。到唐末五代時,最負盛名的回回醫藥家李珣,人稱李波斯。他著有一本獨具風格的藥學著作《海藥本草》,顧名思義,該書之所以用“海藥”命名,是因其所收錄的藥物多來自海外。該書為總結唐末時南方藥物與海外藥物臨床套用的本草學著作,有較高的文獻學價值。另外還有鄭虔的《胡本草》及非醫藥學書籍《西陽雜俎》等也記載了許多外來藥物,包括阿拉伯藥物。
在唐代不僅有香藥輸入中國,與之同時一些醫療技術也傳入中國,如在《千金翼方·養性》中所記載的“悖散湯”(又名牛乳補虛破氣方),本為波斯、大秦醫方,曾在朝野間廣為流傳,對治療氣痢、一切氣病、健運脾胃其效甚佳。從唐代開始,回回先民對香藥推廣套用頗多貢獻,如用香藥防治疾病、薰洗衣物、化妝美容、調味食品、祛邪防腐等。同時中國穆斯林研究介紹了大量阿拉伯世界文化成就如數學、天文曆法等,而中國的造紙術、針灸學、脈學、煉丹術、臨床科學經驗也源源不斷地輸入阿拉伯國家,特別是造紙術輾轉外傳,給歐洲中世紀文明以很大促進。因此早期的回回先民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大貢獻,尤其在未有空間傳播科技的時代,堪稱豐功偉績。
宋代,中國與西域的陸路交通不如海路發達,在東南沿海一帶如廣州、泉州、杭州、揚州等地集居了大量的大食人,其中不乏香藥巨商與醫家,且人數日增。由於海上交通頻繁,宋皇特命在廣州、杭州、泉州等沿海地設“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貿易及對外文化交流。載入史冊的有福建蒲氏家族。《宋會要稿·蕃夷七》記載的蒲壽庚,也是宋代著名香藥富商。《蒲氏家譜》有“家居西板”,“世秉清真教,天下蒲氏皆一脈”之記載,蒲氏家族興盛於宋元,衰落於明清,世襲經商大食香藥。
宋代的中阿海外貿易較唐代有很大的發展,貿易品種由唐代的珍寶犀牙為主、香藥為輔,漸變為以香藥貿易為主。宋太平興國七年,宋太祖曾下詔令對海外香藥香料放通行的有37種,其銷路較廣的是有醫療作用的香藥如丁香、木香、龍腦香、乳香、草豆蔻、沉香、檀香、龍涎香、蘇合香油等。由於大量香藥的引進,從而大大豐富了中醫方藥及治療方法。宋代醫方較唐代醫方在香藥的套用或組方上有明顯變化,就《太平聖惠方》而言,僅卷48“諸心痛門”以香藥命名的醫方有:沉香散3首、沉香丸1首、木香散6首、木香丸6首、丁香丸1首;《聖濟總錄》卷56“心痛門”以香藥命名的醫方有木香煮散、木香湯、豆蔻湯、丁香湯、沉香散等31方次,計套用香藥8種。《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是宋代政府和劑局的成藥配本,書中以香藥命名的醫方不下30餘種,其中有不少名方,眾所周知的蘇合香丸、至寶丹、牛黃清心丸等便是。蘇合香丸中15味藥就有13味是進口藥,至今蘇合香丸對於中風所致的神志不清、牙關緊閉、半身不遂等重症有明顯療效。其間,大食醫家及學者功不可沒。
宋代在社會上廣用香料、香藥薰衣、焚香、啖香之際,禮尚往來亦常以香藥作為饋贈佳品,用香藥配製的藥茶甚至一度成為社會生活中的時尚。皇權貴族之間也視藥茶為饋贈佳品。民間百姓們不僅用香藥治病,而且也用於消毒。泉州有香料文獻記載:“蕃藥能治冷氣,醫學多用之……,泉人每歲家無貧富,皆燃之如燔柴”。現代研究,燃燒香料,對於防止傳染病傳播和擴散有一定作用。這種習俗,自古至今,不僅在回民中間流行,在閩南地區其他民族中也同樣流行。
元代一統天下,將國內民族分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及南人。穆斯林則是色目人中的主要分子,他們往往與蒙古人享受同等待遇,無論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都優於漢人,同時在元代“回回”一名開始代替“大食人”,被人們認為信仰伊斯蘭教者的名稱。如此則為阿拉伯醫藥的廣泛深入傳播與興盛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礎,且元人統一中國之後,繼續奉行南宋時的海外貿易政策,推行少數民族醫藥共存的方針,回回醫藥在此得以興旺發達。
元初,在元朝政府中設有相應的醫藥機構。元世祖即位後效法漢制在建立太醫院之後,於至元七年(公元1273年)改回回愛薛所立京師醫藥院為廣惠司。據《元史·百官志》說:“廣惠司秩正三品,掌修制御用回回藥物及和劑,以療諸宿衛士及在京孤寒者”。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1年)先後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藥物院”;至治二年隸廣惠司,定置達魯花赤一員,大使二員,副使一員。
金元之際,西域技術之士,醫家之流多入仕於元,如愛薛、答里麻等。
由於元代統治者對阿拉伯藥物高度重視,元代阿拉伯人在當時政府中的醫藥機構里占極大勢力、廣惠司是回回醫家的大本營。
另外還有一些祖籍西域,生於中國,精通漢、回醫藥的學者,如元末著名學者丁鶴年,為虔誠的伊斯蘭教徒,工儒學,通奧義,精詩律,是一位善兼醫術的人。又如元末明初杭州的穆斯林大商人鄂施曼乃的子孫曾設立豪華的私人醫院,取名“鄂施曼尼雅”,聘有回回醫生從職。陶宗儀《南村輟耕錄》所記,不乏不知姓名的回回醫官為百姓治病的事例。
金元之際醫學文化領域學術活躍,百家爭鳴,中醫界出現了金元四大學派,回回醫藥文化此時也發展到鼎盛時期,湧現了與回回藥物院有關的、集阿拉伯醫藥學與中國傳統醫學為一體,具有中國回回特色的醫藥大型綜合性醫著《回回藥方》等專著。
回藥著作
下面介紹回回醫學中的重要醫著,其中三部問世於元代。
《回回藥方》(以下簡稱《藥方》)。中國回族醫藥學大型綜合性典籍,未著撰人,紅格明抄本,原書36卷,殘存4卷,現藏於北京圖書館。全文基本上用漢文記述,並夾雜不少阿拉伯、波斯藥物名稱術語的原文和音譯辭彙。現殘存卷為:目錄卷之下、卷12、卷30、卷34。目錄卷下包括卷19至36據目錄可見,卷19為咳嗽門,包括眾嗽、濕嗽、喘嗽、嗽血、嗽痰、肺經腫嗽、說治咳嗽等類。卷20為胸膈凝聚、胸膈熱促、胸弱、胸疼痛、胸奄濁、胸冷濕、胸中生瘡、開胸膈等類。卷21為腸風肚腹門,包括腸風、腸中生瘡、腸中生蟲等。卷22為瀉痢門,包括論、方及瀉從遍身來的、胃經泄瀉、腸經泄瀉等類。卷23為嘔吐門、痞證門、秘門、勞瘵門、補益門;嘔吐門包括嘔吐、吐瀉、泄瀉、止吐、止瀉等類;痞證門包括痞證類;秘門包括臟腑不通類、能通小水類;勞瘵門包括勞熱、勞蟲、勞嗽等類;補益門包括補益類。卷24為眾熱門、眾冷門。眾熱門包括一切熱類;眾冷門包括胸膈冷類、胃經冷、一切冷等類。卷25為眾氣門、眾血門、時氣斑疹門、瘧疾門。眾氣門包括眾氣、氣不依常度、氣喘急等類;眾血門包括治吐血、能吐血、下血、止血等類;時氣斑疹門包括時氣、斑疹等類;瘧疾門包括瘧疾類。卷26為身體門,包括身體肥瘦、身體疼痛、癍痕花繡、治體氣、治生虱、手足等類。卷27為黃病門、蠱症門、積聚門,黃病門包括黃類,蠱症門包括蠱症等類;積聚門包括積聚類。卷28為腳氣門、脫肛痔漏門、谷通門。腳氣門包括身體疼痛腳氣、熱腫腳氣、冷腫腳氣、寒濕腳氣、一切腳氣等類;脫肛痔漏門包括痔瘡、腸風痔漏、痔風、脫肛等類;谷通門包括谷通等類。卷29為雜症門,包括論16條,方189首。卷30為雜症門,載方307首。卷31為婦人眾疾門、小兒眾疾門。婦人眾疾門包括婦人身內動靜、乳上症候、懷孕動靜、子宮症候、眾疾等類;小兒眾疾門包括小兒眾疾類。卷32為眾瘡腫腫毒門。包括腫毒、癧瘡、惡瘡等,卷33為眾瘡腫毒門、疥癬門。眾瘡腫毒門包括疥瘡、甜瘡、疳瘡、癩瘡、臭瘡等類。疥癬門包括疥瘡、癬瘡、一切疥癬等類。卷34金瘡門、折傷門、針灸門、湯火所傷門、棒瘡門、治人齒所傷門。金瘡門包括刀箭所傷、取箭頭刺簽等類;折傷門包括傷損、接骨、骨脫出等類;針灸門包括灸各種症候類;湯火所傷門包括湯火所傷類;棒瘡門包括棒打傷類;治人齒所傷門包括治人齒咬傷類。卷35為眾蟲獸傷門、眾毒門、辟蟲門。眾蟲獸所傷門包括眾蟲獸傷類;眾毒門包括論及說眾毒物、辨驗何等毒物所傷、解服藥毒、解眾蟲獸所傷等類;辟蟲門包括辟眾蟲、辟惡物等類。卷36為修合藥餌門、修合諸般馬準門、眾香湯煎門、活物治病門、眾花果菜治病門。修合藥餌門包括論及製藥法,相合藥法、比量用藥、說造良方。藥性期度、藥餌分兩等類;修合諸般馬準門包括論及方87首(均已分見各門);眾香湯煎門包括湯藥類;活物治病門包括活物治病類;眾花果菜治病門包括眾果物類、眾菜類、眾花物等類。
從上述部分藥目錄所涉及的病種門類可以看出,《藥方》是一部包括內、外、婦、兒、骨傷、皮膚等科,內容豐富的中國回族醫學方書。從現存3卷所載方劑看,全書所載可能達,6000~7000首之多。其系統性、綜合性不亞於中醫古籍《外台秘要》。
《藥方》以敘方為主,方論結合,回回藥物與傳統中藥並用。據統計《藥方》殘卷常用藥259種,明顯屬於海藥並註明中文名稱者有61種;沿用阿拉伯藥名,目前尚不知何藥者52種,合計海藥為113種,占殘卷全部用藥的43.6%。其他146種則為傳統中藥,其中也包括已經華化的海藥在內。從《藥方》中所載方劑來看,無明顯君、臣、佐、使之配伍。據研究,《藥方》不僅與阿拉伯醫學有根深的淵源關係,而且突出特色,東西合壁。在藥物劑型的運用方面,既有中國式的丸、散、膏、湯,又保存有阿拉伯式的芳香揮發藥、滴鼻劑、露酒劑、油劑,糖漿劑;有些醫方的臨床套用如菖蒲煎劑治療中風等,又是借鑑了中國傳統醫學經驗並和回回醫藥相結合的一種用法。《藥方》有它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反映了成書時代中國回醫對疾病認識在理論上已較成熟,這種理論既保存有阿拉伯醫學的特徵,也有中國傳統醫學的成份。
《藥方》內容之廣,涉及臨床多科,同時在治療方法上也較豐富,對有些疾病則採用內外並治。當然《藥方》的治法中除了阿拉伯醫學的治方經驗外,其中也不乏傳統中醫的治療方法以及民間驗方。值得一提的是許多方法特別是一些外治法及其對骨傷科的論治具備了時代的先進性。如《藥方》中對頭部外傷的診斷,是根據組織損傷程度劃分的,並分別使用不同的方法治療。對外傷腫脹不退,且並發全身症狀者,主張作“十字”切開,排膿引流。對顱骨下膿腫,採用鑽孔鋸開的開顱方法等,在今天看來尚且合理。
《藥方》“折傷門”、“針灸門”之論述較全面。“折傷門”基本上包括了古今骨科的內容,包括了軟組織損傷、骨傷及關節脫臼,並從理論上闡述了這些損傷的原因、發生機制、診斷和治療方法,對一些合併症也作了相應的介紹。從而反映了14世紀時期中國骨傷科診療水平發展成就。在今天看來,“折傷門”中許多內容仍有臨床實用價值。“針灸門”實為專論灸而罕論針,所論灸法有三種情況,即艾灸、藥灸、烙灸,以烙灸法所占篇幅最長,尤為詳述,其方法為阿拉伯醫學的燒烙法。在書中烙灸法的適應症被分為16等,涉及範圍很廣,包括了內科、外科、眼科、傷科、皮膚等多種疾病,其病因多與體內惡液有關,具體方法是採用多種器械、燒烙皮膚,令其破損、潰爛、流膿,而不能早用生肌收口之藥,必令其膿外流,則體內之惡液因之排出,然後施用生肌收口的藥,使之平復。《藥方》中灸法雖然以烙灸為主體,也確實帶有明顯的阿拉伯醫學特色,但中醫特有的艾灸法在書中出現及烙灸法中出現針灸穴位,這說明《藥方》的灸法體現了共同的醫學特色。
《海藥本草》。作者為唐末五代時的李珣。祖籍波斯,又名李波斯,善詩。曾幾代定居長安西市一帶,以賣藥為生,《海藥本草》收藥124種,大多數來自波斯等地及南海諸地區,因此為回回醫藥根基的一部分,對中醫學的發展也曾有過作用。有醫學專家指出,在唐末五代時在民族醫藥史上有突出貢獻的書籍首推《海藥本草》。它還補充了《神農本草》《名醫別錄》《唐本草》《食療本草》《本草拾遺》等不足,且糾正了前著的一些錯記,豐富了中國藥物學,是回回醫學的重要基礎與典籍。
《飲膳正要》。本書是我國第一部營養學專著,成書於元代天曆三年(公元1330年)。作者忽思慧(又作和斯輝),史書無載。從本書序文和進書表來看,是元仁宗時的宮廷飲膳太醫,舊說是蒙古族醫家。這部書初刊後,明清兩代多次翻刻,但因屢遭兵災,已散佚不多。書中配方多以羊肉為主料,“聚珍異撰”第一方馬思答吉湯,《本草綱目·菜部》蒔蘿條附馬思答吉註:“元時飲膳用之,雲極香料也。不知何況,故附之。”書中多引用回回豆子、回回蔥、回回青、回回小油。許多食品冠以“胡”字,如胡蔥、胡麻、胡椒、胡荽等。以胡蔥為例,《本草綱目》指出:“元人《飲膳正要》作回回蔥,似言自胡地,故曰胡蔥耳”。《洛陽伽蘭記·城南》記:“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可見大量配方是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和國家飲食療法所用。將《飲膳正要》推論為“兼通蒙漢醫學”的太醫所撰,看來根據不足。
《瑞竹堂經驗方》(下稱《瑞竹堂方》)。原著在明代中葉後國內已失傳,但書中許多內容則散見於國內外許多醫藥文獻,其原序兩則及清明兩代若干輯佚和抄本,分別在中國和日本有關部門和私家珍藏,作者及成書年代國內外專家爭論不一,清乾隆年間修纂的《四庫全書》曾將明代《永樂大典》中本書散在內容搜采編輯為5卷24門。集得內、外、婦、兒、眼、齒、調補、美容等科效方170餘首。當時“計亡闕已十之五六”,中國中醫研究院現藏有清代《抄本瑞竹堂經驗方》及仿明刻日刊本《瑞竹堂經驗方》,有的專家認為本書作者肯定是回回醫家,其名為沙圖穆蘇·薩謙齋,官至元朝御史兼太守。其成書年代不晚於泰定三年(公元1327年),陳垣先生在其名著《勵耕書屋叢刊·元西域人華化考》中早已經將本書作者考證為“華化”了的回回。
清代《抄本瑞竹堂經驗方》現亡闕者多,但明刻日刊本可能近《瑞竹堂方》原帙。此日刊本按明刻分15卷,每卷1門,集方300餘首,即諸風門、心氣痛門、疝氣門、積滯門、痰飲門、喘嗽門、滋補門、瀉痢門、頭面口眼門、耳鼻門、發口門、咽喉門、雜治門、瘡腫門、婦女門、兒門。該書用香藥較多,書中記載的懸吊水桶淋浴式是回族自古以來獨特的衛生傳統習慣,另有治急氣疼方、治惡瘡方、治疔瘡方在其方名上標有“海上方”等字樣,還有的驗方特彆強調忌馬、驢、豬肉等。
《回回藥方》簡介
《回回藥方》(以下簡稱《藥方》)。中國回族醫藥學大型綜合性典籍,未著撰人,紅格明抄本,原書36卷,殘存4卷,現藏於北京圖書館。
《藥方》以敘方為主,方論結合,回回藥物與傳統中藥並用。
據統計《藥方》殘卷常用藥259種,明顯屬於海藥並註明中文名稱者有61種;沿用阿拉伯藥名,目前尚不知何藥者52種,合計海藥為113種,占殘卷全部用藥的43.6%。其他146種則為傳統中藥,其中也包括已經華化的海藥在內。
從《藥方》中所載方劑來看,無明顯君、臣、佐、使之配伍。據研究,《藥方》不僅與阿拉伯醫學有根深的淵源關係,而且突出特色,東西合壁。在藥物劑型的運用方面,既有中國式的丸、散、膏、湯,又保存有阿拉伯式的芳香揮發藥、滴鼻劑、露酒劑、油劑,糖漿劑;有些醫方的臨床套用如菖蒲煎劑治療中風等,又是借鑑了中國傳統醫學經驗並和回回醫藥相結合的一種用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