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風·園有桃》
《魏風·園有桃》原文
園有桃,其實之餚。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魏風·園有桃》
《魏風·園有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心之憂矣,有誰知之!
有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棗,其實之食。
心之憂矣,聊以行國。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心之憂矣,有誰知之!
有誰知之!蓋亦勿思!
譯文
果園裡面長著桃,果實可以作佳肴。
我的心中多憂傷,又唱歌來又誦謠。
不理解我心的人,說我書生太狂傲。
 《魏風·園有桃》
《魏風·園有桃》莫非他們說得對,你該說些什麼好?
我的心中多憂傷,我的憂傷誰知道。
我的憂傷誰知道,何不丟開不去想。
果園裡面有酸棗,果實可以作吃食。
我的心中多憂傷,國中週遊且消愁。
不理解我心的人,說我書生不知足。
莫非他們說得對,你該說些什麼好?
我的心中多憂傷,我的憂傷誰知道。
我的憂傷誰知道,何不丟開莫煩惱。
注釋
1、之:猶“是”。《集傳》:“餚,食也。”食桃和下章的食棘似是安於田園,不慕富貴的表示。
2、我:是詩人自稱。謠:行歌。《毛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
 《魏風·園有桃》
《魏風·園有桃》3、不我知者:唐石經作“不我知”,一本作“不知我者”。下章同。
4、士:旁人謂歌者。《通釋》:“我士,即詩人自謂也。”
5、彼人:指“不我知者”。《鄭箋》:“彼人,謂君也。”
6、子:歌者自謂。其(姬jī):語助詞。《集傳》:“其,語詞。”
7、“彼人”二句詩人自問道:那人說得對么,你自己以為怎樣呢?
8、蓋:同“盍(河hé)”,就是何不。亦:語助詞。這句是詩人自解之詞,言不如丟開別想。
9、棘:酸棗。
10、行國:周行國中。這二句言心憂無法排遣,只得出門浪遊。
11、罔極:無常。《集傳》:“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已見《衛風·氓》篇。
主題
因不被理解而生感慨,由感慨而作歌詩,《魏風·園有桃》正是在表白自己的清正高潔,抒發不平和鬱悶,這是書生們常有的心態和做法。這種心態和做法容易理解。不容易理解的是,世間何以難於尋求到理解?人們有時看重的僅僅就是理解,為什麼就尋覓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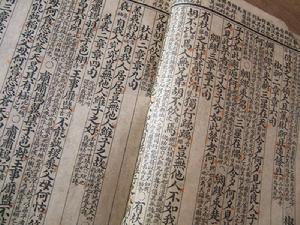 《魏風·園有桃》
《魏風·園有桃》其實,理解難覓也很容易埋解。人們各自從各自的立場去看問題,各自關注各自的利益,難得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更不用說為他人排憂消愁。“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這話道出了世間人人各自為陣、各自設防的心態。我們很難說這種心態是好是壞。說它好吧,它卻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和冷淡,使人與人如同陌生的異鄉人,沒有溫情和人情味,更沒有同情和理解。說它不好吧,它又可以避免人言可畏的麻煩和流言蜚語的軟刀子,保護自己不受到傷害,不落入他人的陷井。
真正困難的是,既想得到同情和理解,又想避免他人的陷害和非難。這種兩全其美的境界很難達到。
在一個人人為自己忙碌奔波的陌生的世界上,企圖尋求別人的理解,完全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讀書人知書識禮,比一般人懂得更多,如果連這點道理都悟不透,也該算作一個不大不小的悲劇。
鑑賞
這首詩語言極明白,表現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對詩人“憂”什麼,時人為何不能理解他的“憂”,反認為他驕傲、反常?難以找到確切答案。同時他自稱“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實際並不確定,《詩經》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個,僅毛傳、鄭箋就有多種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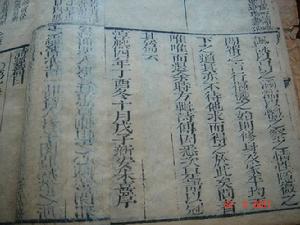 《魏風·園有桃》
《魏風·園有桃》本詩兩章復沓,前半六句只有八個字不同;後半六句則完全重複。兩章首二句以所見園中桃樹、棗樹起興,詩人有感於它們所結的果實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飽腹,而自己卻無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貢獻出來,做一個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詩人心中的鬱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著說“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他無法解脫心中憂悶,只得放聲高歌,聊以自慰。《毛詩序》說:“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位正是因為歌之不足以瀉憂,決定“聊以行國”,離開他生活的這個城市,到別處走一走,看一看。這只是為了排憂,還是想另謀出路,我們無法測知。但從詩的五六句看,他“行國”是要換一換目前這個不愉快的生活環境,則是可以肯定的。詩云:“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罔極)。”詩人的心態似乎是“眾人皆醉我獨醒”。因為他的思想,他的憂慮,特別是他的行為,國人無法理解,因此不免誤解,把他有時高歌,有時行游的放浪行動,視為“驕”,視為“罔極”,即反常。詩人感到非常委屈,他為無法表白自己的心跡而無可奈何,所以七、八兩句問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們說得對嗎?你說我該怎么辦呢?這兩句實際是自問自答,展現了他的內心無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後四句:“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詩人本以有識之士自居,自信所思慮與所作為是正確的,因而悲傷的只是世無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說“其誰知之”,表現了他深深的孤獨感。他的期望值並不高,只是要求時人“理解”罷了,然而這一丁點的希望,在當時來說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來自慰自解。全詩給人以“欲說還休”的感覺,風格沉鬱頓挫。陳繼揆《詩經臆補》認為:“是篇一氣六折。自己心事,全在一‘憂’字。喚醒群迷,全在一‘思’字。至其所憂之事,所思之故,則俱在筆墨之外,托興之中。”
這首詩以四言為主,雜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參差,確如姚際恆所說:“詩如行文。”(《詩經通論》)押韻位置兩章詩相同,前半六句韻腳在一、二、四、六句末;後半六句換韻,韻腳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並且十、十一兩句重複,哀思綿延,確有“長歌當哭”的味道。
《詩經》簡介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約五百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詩”,有目無辭,不計在內),所以又稱《詩三百》。匯集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詩歌總集,與《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合稱為五經。古者《詩》三百餘篇,及於孔子,去其重……”(《史記·孔子世家》),據傳為孔子編定。“最初稱《詩》,被漢代儒者奉為經典,乃稱《詩經》,也稱《詩三百》。他開創了中國古代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的優秀傳統。《詩經》里的內容,就其原來性質而言,是歌曲的歌詞。《墨子·公孟》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意謂《詩》三百餘篇,均可誦詠、用樂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記·孔子世家》又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些說法雖或尚可探究,但《詩經》在古代與音樂和舞蹈關係密切,是無疑的。
 詩經
詩經《詩經》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十分豐富,它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經濟,祭祀典禮,戰爭徭役,定都建國,燕饗歡聚,狩獵耕耘,採摘漁牧,君王貴族,將軍大夫,君子淑女,農夫商賈,思婦棄婦,遊子隱逸,初戀思慕,閨怨春情,幽期密會,洞房花燭,迎親送葬,懷人悼亡,草木魚蟲,飛禽走獸,鶯啼馬鳴,風蕭雨晦,波光山影,火山地震,祈禱祝願,占卦圓夢等等,其信息量之大,文獻價值之高,令人驚嘆。可以說,一部《詩經》立體地再現了生存環境、事態人情,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多方位、多角度的反映,其內容在世界古代詩歌作品中是獨一無二的,遠比印度的《吠陀》與基督教《聖經》中的詩篇要廣泛得多。它的主題已不限於宗教性的,或僅僅表達一種虔誠的感情,它也不像荷馬史詩只談論戰爭與冒險,它歌唱的是人的生活,人的感情,用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的詩說:“卑俗的山歌俚曲,現今日常熟悉的事情,天然的悲苦和傷逝,過去有過,以後還會有。”(選自《孤獨的割麥女》)在如此自然,如此樸素,如此親切地表現普通人民的心聲和感情方面,很少有別的詩集堪與《詩經》相提並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