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資料
《糖史》的寫作始於1981年,最終完成於1998年。全書共分三編:第一編為國內編;第二編為國際編;第三編為結束語。約83萬餘字。這部近百萬字的《糖史》,展示了古代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東南亞,以及歐、美、非三洲和這些地區文化交流的歷史畫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使季羨林在學術高峰上留下獨具特色的足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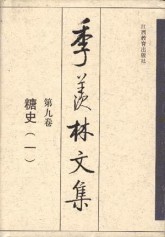 《糖史》
《糖史》書名:《季羨林文集》第九卷:糖史
作者:季羨林
頁數:539
SS號:10853693
封面頁
書名頁
著作權頁
前言頁
本書目錄
《糖史》自序
第一編 國內編
《糖史》(一)自序
引言
第一章飴?餳餹
第三章石蜜
第四章蔗糖的製造在中國始於何時
第五章唐代的甘蔗種植和製糖術(618--907年)
附關於唐代製糖法的一點小考證
第六章宋代的甘蔗種植和製糖霜術(遼金附)(960--1279 年)
第七章元代的甘蔗種植和沙糖製造(1206--1368年)
第八章明代的甘蔗種植和沙糖製造(1368--1644年)
第九章白糖問題
第十章清代的甘蔗種植和製糖術(1616--1911年)
附錄一清代糖史部分資料索引[楊寶霖]編
附錄頁 ...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從糖這種人人日常所用而又微不足道的東西的發展中,向世人揭示出一部十分具體、生動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作者用數年時間,翻閱了自周秦以來浩如煙海的中外群籍,從“糖”字的演變到甘蔗種植、製糖業的發展,引用了大量例證,用以說明:文化交流而使科技得以發展,人類必須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才能不斷進步,這是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之一。
《糖史》用大量事實考證出一千多年來糖和製糖術在世界交流的軌跡。《糖史》證明是印度最早製造出了紫砂糖,傳到中國。後來,中國提高了製糖術,將紫砂糖淨化為白糖,又返銷印度。到了明末,中國人製造出來的糖,顏色純白,接近今天的白糖,是當時世界上品質最好的糖,遠銷世界各國。由於季羨林《糖史》的問世,糖,這種最常見的食品,它的製造、發展、交流、流通的歷史便大白於天下。中國人對糖的製造、提高、傳播曾經作出過重大貢獻,也成為不爭的事實。但《糖史》並非一部純科學著作,它的主要價值在於,通過考證一千多年糖和製糖術在世界交流的軌跡,讓我們了解到人類的文化交流史的一個重要方面。
寫作背景
 季羨林先生
季羨林先生早在20世紀30年代,季羨林在德國學習梵文時就已經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在歐美許多語言中,"糖"這個詞,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ere,俄文是caxap,其他語言也大同小異,不僅形式相仿,發音也相似,而且這些單詞都屬於外來語,來自同一個梵文字sarkara。這一現象說明歐美地區原本是沒有糖的,這一日用食品的原產地是印度。當時他並沒有想到寫《糖史》。真正讓他萌生寫一部《糖史》的念頭,則是在他得到了一張敦煌佛經殘卷之後。一個偶然的機會,伯希和從敦煌藏經洞拿走了正面寫著佛經,背面寫著印度造糖法的一張殘卷。幾經周折,這張殘卷被季羨林得到了。敦煌殘卷多為佛經,像這樣有關科技的殘卷可謂鳳毛麟角,乃無價之寶。但對季羨林來說,這更是一個學術上難啃的硬核桃。要知道,從伯希和算起,已經有數不清的中外學者試圖想啃開這個硬核桃,卻都沒有成功。最終,季羨林這個耄耋之年的老人啃開了這個核桃。它講的是印度的甘蔗種類;造糖法與糖的種類;造煞割令(石蜜)法;沙糖與煞割令的區別;甘蔗釀酒;甘蔗種植法等。接著,文章又從這張敦煌卷子提供的線索,通過大量的考證,最後得出結論:中國早就知道甘蔗,而且甘蔗製糖技術也早就有所發展,但不如印度制的糖好。於是,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遣使者到印度去學習製糖技術,取得經驗回來後,中國造的糖“色味愈西域遠甚”,意思就是在顏色和口味方面遠遠超過了印度。這本是常見的現象,中國古語說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指的就是這種現象。
由“糖”的傳播而出現的文化交流現象,使季羨林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感到這是一個極有意義的研究題目,因為從糖的傳播過程中,不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交流的軌跡,而且沿此道路探索下去,還可以尋找到人類文化交流的軌跡。這就是季羨林研究“糖史”的發軔和濫觴。
此後,季羨林就開始注意蒐集有關“糖”傳播的資料,並且陸續寫了多篇有關“糖史”的文章,如《蔗糖製造在中國始於何時》(1981年)、《古代印度砂糖的製造和使用》(1983年)、《歐、美、非三洲甘蔗種植和砂糖製造》(l987年)、《cīnī問題──中印文化交流的一個例證》(1987年)、《唐太宗與摩揭陀──唐代印度製糖術傳入中國的問題》(1987年)、《再談cīnī》(l994年)等。1993年和1994年兩年,如前文所述,季羨林天天跑圖書館,集中精力查閱中國古籍及國外有關資料,把其中有關“糖”的資料挑選出來,再進行分析研究,最後撰寫出了這部長達七十多萬字的《糖史》。
季羨林嘔心瀝血,冒著失明的危險寫成的《糖史》一經出版,便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因為這部書規模宏大,內容翔實,寫作中採用最嚴格的考證方法,"言必有據,無徵不信",讀之必定受益匪淺。雖然前人也寫過《糖史》,但真正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來寫《糖史》的,唯季羨林一人而已。
寫作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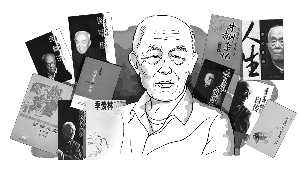 季羨林先生白描和他發表的主要作品。新京報漫畫/趙斌
季羨林先生白描和他發表的主要作品。新京報漫畫/趙斌季羨林寫《糖史》需要蒐集大量的資料,引用別人的著作甚至觀點,不可避免。引他人的著作和觀點,必須註明出處,這是起碼的學術道德,季羨林決不敢有違。可是,季羨林所需的資料都在古書中,這些書現在尚未輸入電腦。他只能採用最原始,最笨,可又決不可避免的辦法,這就是找出原書,一行行,一句句地讀下去,像砂里淘金一樣,搜尋有用的材料。為了寫《糖史》,他用了兩年時間,天天跑北大圖書館,查《四庫全書》,硬是把一部《二十四史》翻了一遍,詳細摘引出其中的寶貴資料。《糖史》雖不是一部純粹的科技史,但是它仍然是一部在最嚴格意義上講的科學著作。這是因為季羨林在寫作中採用了最嚴格的考證方法,“言必有據,無徵不信”。季羨林為了求真,在浩如煙海的中外書籍中,爬羅剔抉,像大海撈針一樣地尋找證據。僅在《國內篇》中,他選來使用的資料,其出處就包括:正史、雜史、辭書、類書、科技書、農書、煉糖專著、本草和醫書,還包括僧傳及音義在內的佛典、敦煌卷子、方誌、筆記、中外遊記、地理著作、私人日記、各種雜著,還包括梵文、巴利文及英德等西文著作。閱讀量之大是難以想像的。季羨林寫道:“我拼搏了將近兩年,我沒做過詳細統計,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書,但估計恐怕要有幾十萬頁。”“幾十萬頁”是一個什麼概念呢?以今天出版的漢文書來說,一本四十萬字的書,大約五百頁左右,即使以讀了二十萬頁計算,季羨林為了寫《糖史》,在將近兩年中,也讀了四十萬字一本的著作在四百本以上。實際的閱讀量當然只會超過這個數字,而不會更少。他在回憶這段工作時寫道:
“我曾經從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除了禮拜天休息外,每天來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圖書館,風雨無阻,寒暑不輟。我面對汪洋浩瀚的《四庫全書》和插架盈樓的書山書海,枯坐在那裡,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攝氏度的酷暑,揮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時候偶爾碰到一條有用的資料,便欣喜如獲至寶。但有時候也枯坐上半個上午,把白內障尚不嚴重的雙眼累得個“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卻找不到一條有用的材料,嗒然拖著疲憊的雙腿,返回家來。經過了兩年的苦練,我煉就一雙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頁,而遺漏率卻小到幾乎沒有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