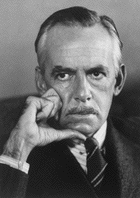作品簡介
《毛猿》(1922)是尤金·奧尼爾最令人感興趣的劇作之一,不分幕,共8場。在關於這齣戲的評論中,研究者常從象徵主義的某些概念出發,探討劇本所蘊含的人類生存價值及意義的主題,即“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如何解決的問題。奧尼爾本人在獲諾貝爾文學獎受獎演說辭中亦強調瑞典戲劇大師斯特林堡對其戲劇創作的影響:“……對於我來說,像尼采在哲學王國一樣,他將繼續是我們的精神導師……”然而,通過對主角揚克的悲劇命運分析,不難發現揚克的“瘋癲”與米歇爾,福柯觀念里的“瘋癲”竟有異曲同工之妙。藉助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對“瘋癲”的理解,《毛猿》可以理解為是一出探索瘋癲的悲劇,這場悲劇實質上彰顯了揚克完成由沉迷於“原始驕傲和過分自我”到追求真實與自由的心路歷程。然而。揚克個人的努力在整個社會機制面前顯得蒼白無力,即使是企圖與獸類進行溝通的美好願望最終也化為泡影,成為20世紀初又一幕美國悲劇。
奧尼爾和福柯的相通性
奧尼爾和福柯生活在不同的時代和國度,但他們都從悲觀哲學家尼采那裡得到了幾乎相同的思想觀念,形成了對悲劇的相同視點。只不過一個體現在戲劇創作里,一個表述在哲學著述中。
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劇作家之一,奧尼爾的思想較為複雜,受到希臘悲劇意識、尼采悲觀哲學以及東方道教的影響。在諸種影響因素中,尼采悲觀哲學無疑起著決定性作用。奧尼爾對尼采的接受,其直接原因與奧尼爾的成長經歷有關。而且,尼采和奧尼爾對信仰的轉變經驗也有不少相似之處。
1888年奧尼爾出生在一個篤信天主教的愛爾蘭家庭,7歲至13歲在天主教學校度過。奧尼爾是一個不幸的孩子,他從小目睹母親深受毒品戕害,祈求上帝幫助卻無濟於事,十幾歲時父母和大哥相繼離開人世。目睹人間悲劇,奧尼爾傷痛不已。他開始憎恨天主教教義的欺騙與偽善,懷疑是否存在萬能的上帝。最終,親人的離去和宗教的迷失讓奧尼爾喪失了歸屬感,陷入了巨大的困惑和悲痛之中。
1907年,奧尼爾放棄天主教已有5年,他思想困惑、對前途感到迷惘,這時尼采的哲學思想進入了他的生命。尼采的思想對奧尼爾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奧尼爾稱《查拉斯圖拉如是說》對他思想的影響“超過以前他讀過的任何一本書”。此後幾年,奧尼爾的境遇每況愈下,他不僅真切體驗到了死亡的威脅,同時對人生的理解也更加深刻。早先接觸的希臘悲劇和尼釆“上帝死了”的觀念在年輕的奧尼爾身上潛移默化,終於形成了奧尼爾獨特的現代嚴肅悲劇意識。
無獨有偶,從20世紀50年代直至80年代,尼采的思想對福柯的影響幾乎貫其一生。在學生時代,福柯就解讀過尼釆,並把尼采奉為精神導師。按照福柯的說法,1953年在他去義大利度假期間閱讀尼采的《不合時宜的思考》,促使他對周圍的一切進行重新思考和認識。他說:“尼采是一種啟示,我以巨大的熱情研讀了他,並與我的生活實現了決裂——我有一種上了圈套的感覺。透過尼采,我變得對生活中的一切都感到陌生了。”深受尼采《悲劇的誕生》的影響,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明確地闡釋了自己的觀點,認為自文藝復興以來,有關瘋癲的悲劇因素因屈從於古典時代理性主義的排斥和道德的批判,在人們的視野中消失殆盡了。這點和尼采對希臘悲劇與哲學的理性化之間關係的看法極其相似。
尼採在分析希臘藝術精神時,發現希臘文化中有理性和非理性兩種對立因素。酒神狄奧尼索斯(Dionysus)不畏一切羈絆,衝破所有禁忌,象徵著主觀和非理性,代表人性中曠達、放蕩、狂醉和灑脫的一面,揭示了人的本性是在痛苦的刺激下去對抗痛苦所表現出的張揚個性意志的生命力量;而日神阿波羅(Apollo)是客觀、理性的代表,象徵光明、克制。狄奧尼索斯精神構成的那個醉狂的世界是尼采所欣賞的。尼采首先批判的是自希臘開始的理性主義傳統,認為蘇格拉底辯證法用理性主義使生活變得消極、被動。福柯在拷問瘋癲的命運時,把矛頭直逼視瘋癲為非理性的哲學基礎,即笛卡兒理性主義,因為笛卡兒在其著作《第一沉思錄》中把瘋癲從理性領域直接驅除出去了。在《瘋癲與文明》中,福柯結合歷史的連續性和哲學的深刻性,驗證了心理學和精神病學在18世紀末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可能性,精闢地闡述了古典時期禁閉體制的衰落和瘋人院的誕生,暴露了以“瘋癲”為表征對象的非理性在理性統治時代的種種遭遇,試圖改變人們長期以來把瘋癲當作理性對立面存在的看法。福柯認為,瘋癲是各種社會關係的產物,不是一種獨立的生物學存在。瘋癲只存在於社會中,它“不是自然現象,而是文明的產物。瘋癲史即迫害史”。福柯並不否定“瘋癲”作為一種精神或行為現象的客觀性,也不否定人類社會中的確存在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瘋子或愚人。但他更堅定地認為,把瘋癲看作一種生理意義的精神病只會導致瘋子被當成“非人”(l’inhumain)看待,但實質上瘋人的靈魂可能並不瘋。
儘管奧尼爾宣稱他自己是個“哲學上的無政府主義者”,藉此說明他在哲學思想上否認某一主義的絕對權威,但在20世紀初期理性面臨巨大挑戰、信仰出現危機時,奧尼爾和福柯在尼采精神的指引下,傾其一生探索生命意義。關注入的生存狀態,探究人類的生存意義。正如奧尼爾所說,“今天的劇作家應該挖掘當代病的根源,即老上帝的死亡,以及科學和物質主義無力提供一個新的上帝,以滿足人們身上殘留的原始宗教本能——尋找生命的意義,用來安慰死亡恐懼的本能。”
揚克的瘋癲表征
奧尼爾的《毛猿》在以下四個方面與福柯的“瘋癲”觀點形成映照。
瘋子與水。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描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醫生針對瘋癲的諸多療法,其中有“浸泡法”和“突襲浴”,因為水是“簡單原始”的液體,也是自然界中“最純淨”的事物之一。回歸水之清澈可達淨化意識的功效,而人在這種透明的液體之中,重返無邪天真。這裡有一點很重要,即水的淨化或治療作用是針對瘋癲患者而言的。《毛猿》的敘述對水的功能也持相同的看法。第六場,揚克故意在街上搗亂被警察抓進監獄以後,由於難以遏制的憤怒使他把監獄裡的鐵柵欄扳彎得像一根單簧管。警察被嚇住了,喊道:“只有一個瘋子才有那么大的力氣!”“打開水龍頭!加足壓力!然後便聽見衝擊揚克牢房的水聲。顯然,警察對揚克的做法跟醫生對瘋子的療法幾乎一樣。警察想通過水的衝擊制止揚克的“野蠻”行為。在第四場中,忙碌一天的燒火工人都用肥皂和水擦洗身體和臉,唯獨揚克無動於衷。大伙兒喊揚克去洗澡,否則煤灰會粘在身上,然後滲進皮膚里,把身上弄得斑斑點點的就像一頭豹子,這表明,骯髒是與獸類相聯繫的,而水是淨化骯髒獸性的有效手段,是人與獸之間的分界線;否則,沒有水的清洗和淨化,人與獸的差別就很少,人的理性屬性就會消失,沒有理性的人很容易被當作瘋子對待。
瘋子與監獄。據福柯看來,理性的社會主體力量為了消除、馴化異己力量,必然要設定一個強有力的消解之地。歷史上,監獄作為一個政治機構的產生正是順應了這樣的要求,《瘋癲與文明》記載和描述了歐洲監獄,較為詳細地敘述了古典時期瘋人被當作野獸關起來的遭遇。1620年德國漢堡設立了第一個監獄(Zuchthaus),並於1622年出台了相當詳盡的規章制度。關在這種機構里的囚徒都必須工作,但他們會得到其所創造價值的四分之一的報酬。因此,禁閉的壓迫功能不再僅僅是禁閉不工作的人,而且還包括給被禁閉者提供工作,如紡紗、織布、磨麵或當鐵匠。這樣不僅為社會提供了廉價勞動力,還發揮了防範騷擾和起義的社會保護作用,以有利於民族的發展。後來,被禁閉者的處境進一步惡化,到了18世紀,瘋癲被戴上了野獸的面孔,“瘋人一獸”的類比開始盛行,那些被鐵鏈拴在囚室的人似乎等同於被狂暴本性攫住的野獸。純粹的獸性羈越了道德界限,狂暴的人們像狗一樣被拴起來,保衛人員通過鐵柵欄給被囚者遞食品和睡覺用的稻草。救護院看起來就像是一座關猛獸用的、由一個個獸籠組成的“動物園”。終於,代表理性的社會主體力量把被命名為瘋癲的人群歸於精神病患者、罪犯以及懶漢、乞丐等所謂異己力量的行列,瘋癲者被當作野獸關進了監獄,並在監獄裡受盡屈辱和酷刑。通過研讀劇本,我們不難發現,在《毛猿》中,揚克與各種“監獄”意象如影隨形。
揚克的出場是在波瀾壯闊的海上,一艘相當豪華的郵輪里,揚克的生存空間卻是監獄似的燒火房:“……被白色鋼鐵禁錮的、一條船腹中的一種壓縮的空間。一排排的鋪位和支撐它們的立柱相互交叉,像一隻籠子的鋼鐵結構,天花板壓在人們的頭上,他們不能站直……關在籠子裡是一個野獸的瘋狂而憤怒的掙扎與反抗……”這裡的“籠子”意象不僅有監獄的含義,而且還直接將裡面的人與獸類聯繫起來,與後面那個大猩猩所呆的籠子形成呼應。事實上,劇本從身體敘述的角度,表明揚克和其他燒火工人的身體長相與正常人的身體形態是不相同的。他們長相猶如舊石器時代中期尼安德特人,長臂,力大無窮,背部佝僂。揚克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比其餘的人更健壯、更兇猛、更好鬥也更自信。他們躁動不安,沒有神聖的理想,更沒有崇高的德行,有的僅是蠻力和粗俗不堪的語言,在上層人的眼裡,他們形同獸類和愚人。雖然這艘郵輪外表豪華,但內部如同一座監獄。船腹里黑煙滾滾、灰塵瀰漫、暗無天日的工作環境和被關禁閉的囚徒的生活環境實質上相差無幾。前艙燒火艙就是一個大籠子,關押著夜以繼日幹活的工人們。燒火工人們呆在燒火艙里,如同呆在地獄般的監獄裡。這種監獄意象還延伸到國際產業工人協會總部所在地。在那裡,狹窄的街道被黑色的建築物包圍,就像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籠子般的監獄。因此,揚克的掙扎無非是從前艙的鐵籠子,走進關人的監獄籠子,最後死在動物園裡關獸的籠子。監獄無所不在,揚克的命運只是從這個監獄走到另外一個。
瘋子與被展示。根據《瘋癲與文明》,在歐洲一些國家,展示瘋子是一個非常古老的風俗。在德國,瘋人成了被觀看的對象,專門為瘋人修建的塔裝上柵窗,人們可以看到鎖在裡面的瘋人。在收容院關閉後,這種風俗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幾乎成為巴黎和倫敦的一種特色制度。據一份1815年提交國會下院的報告說,伯利恆醫院在每個星期日展覽精神病人,入場費用是一便士,每年有九萬六千參觀者,這種奇怪的展覽竟帶來高達近四百英鎊的收入。在法國,迄大革命為止,參觀瘋子一直是巴黎波希米亞區資產階級的周末娛樂項目之一。米拉波(Mirabeau)在《一個英國人的遊記》中報導,比塞特爾的瘋人像“奇獸”一樣被展示給願意付一里亞的“大傻瓜”看。有些管理員竟然因善於使瘋人表演舞蹈和雜技而遠近聞名!《毛猿》第二場,貴族小姐米爾德麗德想獲得一種不同於她生活的上流社會的特別體驗,前去骯髒不堪的燒火艙。這位米爾德麗德小姐的父親是一家大型鋼鐵公司的總經理,也是揚克所在的那個輪船公司的董事長。米爾德麗德對自己的社會身份感到滿意和驕傲,並認為自己有絕對的權利和自由來燒火艙觀看“另一半人”是怎樣工作和生活的。米爾德麗德的這種動機和行為與展示瘋子、參觀瘋子的行為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她就是參觀者,那些無辜的燒火工人們就是困在“籠子”里被展示的“瘋子”。揚克他們這些像“瘋子”一樣的半獸人沒有發聲的權利,只能緘默。試想,如果揚克如願地進入大猩猩的籠子裡面,他肯定會成為一個最具吸引眼球的展示對象,只是劇作家出於人道的考慮,讓他以死亡的形式結束了悲劇人生。對人而言,死亡比當成“奇獸”展示更具人道意義。
瘋子與自戀。福柯把瘋癲形象歸納為四種:浪漫化的瘋癲,狂妄自大的瘋癲,正義懲罰的瘋癲,以及絕望情慾的瘋癲。揚克屬於第二種。在揚克眼裡,頭等艙里那些有錢人只不過是臭皮囊。他總認為自己力氣大,郵輪的轉動、前行離不開他的份,“……使它發熱的是我!使它發出吼聲的是我!使它轉動的是我!不錯,沒有我一切都要停頓……我是原動力……我是結尾!我是開頭!我開動了什麼東西,世界就轉動了!”揚克的豪言壯語實質是上帝式的語言。根據《聖經》,上帝不僅創造萬物,還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詩篇》中說;“主掌權者為王……他奠定了塵寰,大地就不得動搖!”(93:1)“(約書亞)向神禱告說:‘讓太陽停在基甸,讓月亮停在亞雅!’太陽果然停住,月亮也不轉動……”(《約書亞書》10:12~14)亞里士多德把支配天體的神靈(God)看作“不動的推動者(theunmovedmover)”。由此可見,天體的運轉是由神靈決定的。揚克作為下層勞動工人,竟自詡為世界的原動力,具有上帝一樣的能量和權力,這無非是一種狂妄和盲目自戀的表現。然而,揚克如此自戀與他的生存環境密不可分,狂妄是他在這似監獄、如地獄般的環境生存下來的唯一動力,自戀也許是他不自暴自棄,對生活始終抱有美好期待的最後砝碼。但米爾德麗德的出現徹底粉碎了揚克的自戀。當她在底艙見到坦胸露背滿身煤黑正在工作的揚克時,頓時被嚇得癱瘓了,發出一聲窒息的喊叫“這個骯髒的畜生”,隨即暈了過去。米爾德麗德這極具侮辱性的尖叫把可憐的揚克僅有的那點自尊和自戀打擊得蕩然無存。也許這種赤裸裸的揭露過於殘忍,他驚呆了,嘴張開,變成了“化石”,驚慌失措,不知道該怎么辦才好。米爾德麗德喚醒了自戀狂妄的揚克,但同時也讓他悲哀地意識到,原來自己在他人的視線里不過是畜生和野獸,是可以隨意地被窺視和展示、辱罵和愚弄的毛猿!揚克的瘋癲是在遭到理性強勢話語的鎮壓和排擠後,甜蜜的自戀頃刻間崩塌的結果。
瘋與非瘋之間
1947年2月,巴黎一所小劇院上演了一部較為轟動的舞台劇,名叫“與阿多之間的討論”。這是演員阿多從一所精神病院出來不久。在告別舞台12年後的首次演出,事先沒有人知道他將在當晚演出什麼。他向觀眾逼真地再現了自己這9年來在精神病院忍受的痛苦與折磨,特別是不下60次被迫進行的電擊治療。他給觀眾留下了這樣的遺憾和反抗,“如果這個世界沒有醫生,是不會有病人的……再沒有什麼能像精神病院那樣把人溫柔地拖進死亡了。”9年的身心折磨令阿多對這種打著“慈善”幌子的邪惡機構恨之入骨,他以自身經歷揭露了精神病院的偽善和不人道。
阿多的話和經歷令人深思,至少在精神病院,瘋與非瘋之間沒有絕對界線。在隱喻層面上,精神病院這個社會組織可以被看成一個大精神病院,那裡的醫生就是社會的主體勢力,病人則是弱小的異己力量。也許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福柯認為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造就了各種各樣的瘋態。由此,我們也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揚克既是瘋的又是非瘋的,他的瘋與非瘋是社會利益關係作用下的產物。
福柯認為,瘋癲與激情相剋相生,瘋癲的人往往充滿激情,他們無以排遣內心的苦悶,常表現得歇斯底里和躁動不安,這種強烈的情緒導致了瘋癲更頑固的存在。但是,導致這種瘋癲激情的根源並非一般病理學層面的疾病,而很大程度上源於來自對立利益階層的壓抑、打擊,正常的生命激情和能力得不到釋放,就以一種非常規的方式表現出來。有研究表明,生命激情是一種“健康和力量”,對於個人的命運具有激勵、推動和喚醒作用。但是,生命激情在瘋癲者身上以非常態的精神狀態和行為方式表現出來,瘋癲者通過直白的言行或健壯的身體顯示出野性未羈的力量。誇張的語言和肢體姿勢恰恰暗示了他們的夢想,張揚了那些不被承認的自由。
生命激情還表現為對理想化生存狀態的嚮往,當這種嚮往無法實現時,追求者就以戲仿方式表現出來。常人以為是瘋人之舉,而在行為發生者看來卻再正常不過了。揚克對“沉思者”的戲仿便是十分典型的例子。勞累了一天,工友們吆喝揚克去洗澡,揚克回答道:“夥計們,別管我。你們沒有看見我在思考嗎?”揚克不經意的回答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揚克在他那像毛猿、像獸人的外表下,軀體裡還活躍著一個靈魂。奧尼爾在劇中屢次提及揚克默默地坐下,擺出一副《沉思者》的姿態。《沉思者》是19世紀法國著名雕塑家羅丹的作品,是他《地獄之門》群像中的一座塑像。西方文化歷來褒沉思者,貶感官者,認為沉思行為可以讓人接近真理、甚至基督教的上帝。柏拉圖認為理想的國君應該是一個沉思的哲學家。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新教詩人認為通過對自然的沉思,人可以接近和領悟上帝的神聖真理。揚克身處社會下層,卻幻想上層社會沉思者的階級地位,以不自覺的身體姿勢扮演沉思者,實為一種戲仿行為,常人看來就屬一種瘋人行為。
社會主體勢力操控著話語權力,下層階級則無話語權。根據病理學原理,做為社會唯一具有說話能力的人,必須有傾訴的對象,否則就會生病。燒火工人來自美國、德國、法國、義大利、愛爾蘭等不同的國家,揚克只是其中的一員。他們經常一邊放任酗酒,一邊在大聲嚎叫、咒罵,混亂的聲音震耳欲聾,酒精的麻醉無法宣洩積壓在心中的鬱悶和憤懣。揚克對大猩猩的訴說和親近的瘋癲之舉,實為他毫無傾訴對象的表現。揚克試圖改變自身生存狀態的努力全盤失敗後,無法向社會上層控訴,也沒有工友可以交流,走投無路之下,他來到動物園,向大猩猩訴說衷情:“你又怎么會不懂得我的意思呢?難道我們不都是同一個俱樂部、毛猿俱樂部的會員嗎……我也是在籠子裡——比你更糟——真的——一副可憐相——因為你還有機會衝出去——可是我呢?”面對大猩猩,揚克要把滿腔的憤慨和悲哀發泄出來。揚克哀嘆自己是人類中的“毛猿”,在工作的船艙中沒有自由和尊嚴,掙扎出來後到了社會上想有所作為,沒想到還是被嘲笑、排斥,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自己還不如一隻被關在動物園的猩猩。“你可以坐在那兒,夢想過去,綠樹林呀。叢林呀……可是我呢——我沒有過去可想,也沒有未來,只有現在——而那又不頂事……我在天地中間,想把它們分開,卻又從兩方面受盡了夾縫罪。”揚克內心被接二連三的失敗與恥辱折磨著,他已經深感自己力量的微不足道,掙扎、反抗都是徒勞的,只能在這地獄般的世界中倍受痛苦的煎熬。最後揚克企圖打開鐵籠,想和猩猩握手,卻被猩猩拚命一摟,肋骨折斷。幾個月前,揚克還激情高呼“見鬼!法律!……見鬼!政府!……見鬼!上帝!”但此時,揚克意識到人類不理解自己,動物也不可能理解自己,對生命的徹底絕望代替了以往的瘋狂激情與自信情結:“上帝,我該從哪裡開始呦?又到哪裡才合適呦?”揚克在生命的盡頭把最後的希望寄託於上帝。尼采認為,只有弱者、頹廢者、馴服者才會懷念上帝,需要上帝的憐憫和眷顧。揚克無疑是個弱者,上帝在看不見的地方觀望著,並沒有向揚克施與同情的甘霖。
據福柯看來,人類社會並不存在一個瘋子群體,而只存在著各種瘋態。當人與現實之間的距離加大時,便會產生一些模糊的或騷動的遐想,將自己所缺少的各種品質或權力賦予自己。人類不應該歧視、排斥、打擊、迫害他們,或剝奪他們做人的權利和尊嚴。瘋癲並不可怕,因為“這個世界上有多少種性格、野心和必然產生的幻覺,不可窮盡的瘋癲就有多少種面孔。”揚克就是在對自身的依戀中,通過自己的錯覺而造成瘋癲。尼採在《悲劇的誕生》中相當肯定地說“瘋狂也許未必是蛻變、衰敗、沒落文化的徵兆吧?也許有一種健康的精神病。”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所謂的文明即是在打擊與排擠異類中確定自身,標榜自我的。中世紀時期麻風病患者被流放,古典時期瘋癲者被囚禁,在現代文明和理性面前瘋癲者依舊無法逃脫被扼殺的命運。
揚克是現代工業文明的犧牲品。他的瘋癲映射了一個被看作是社會異己力量的社會底層人企圖追求真實的人性的心路歷程,而他的死表征了現代人面臨的災難和困境。通過揚克,奧尼爾傳達了他對深陷物慾橫流的工業社會中的普通勞動者的關注和思考。揚克是工業文明、鋼鐵機器的受害者,在他那看似瘋癲的言行背後卻隱藏著一個有一定思想緯度的下層人。他由盲目自戀到痛苦、發瘋、甚至到最後瀕臨絕望,他的瘋癲源自對自身處境逐漸清醒的認識,想有所改變卻無能為力。道出了事實卻被那些“木偶”一樣的人恥笑為瘋子後的無奈。揚克這樣的瘋癲者不是暴露了某種“生理機制”,而是揭露了社會的某種病理生成機制。社會強勢力量竭力壓抑人性中潛藏著的原始力量和激情,而這種原始力量和激情是對自由的渴望、對人際交流的嚮往和對回歸人性的期盼。這些都是人的正常需求,但在涉及社會各種關係的利益機器的運作下,卻以一種非正常的瘋癲方式表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那些背負各種罪名的瘋癲者是無辜的。
作者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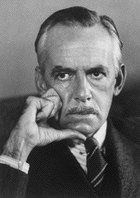 奧尼爾
奧尼爾尤其·奧尼爾(EugeneO'Neill,1888-1953)美國劇作家。生於紐約一個演員家庭,幼年隨父親劇團走南闖北,漂泊無定。中學畢業後,考入普林斯頓大學,後因酗酒鬧事被開除學籍。在此後的冒險生活中,他曾到宏都拉斯淘過金,在非洲和南美當過水手,做過演員、導演、新聞記者、小職員等。1912年患肺結核住院期間,研讀了自古希臘以來的戲劇經典作品,並開始戲劇創作,此後成為專業劇作家。 奧尼爾是位多產作家,一生創作獨幕劇21部,多幕劇28部。其中優秀劇作有:《東航卡迪夫》(1914)、《加勒比斯之月》(1917)、《天邊外》(1918)、《安娜·克利斯蒂》(1920)、《瓊斯皇》(1920)、《毛猿》(1921)、《榆樹下的欲望》(1924)、《奇異的插曲》(1927)、《啊、荒野》(1923)、《無窮的歲月》(1933)、《送冰人來了》(1939)等。奧尼爾生前三次獲普利茲獎。作家自認為並得到公認的最好作品是《長夜漫漫路迢迢》。這部帶有自傳性的劇作,按作家生前聲明,在他死後的1956年首次在瑞典上演,並又一次獲得普利茲獎。
國內外戲劇書籍盤點(一)
| 戲劇,指以語言、動作、舞蹈、音樂、木偶等形式達到敘事目的的舞台表演藝術的總稱。文學上的戲劇概念是指為戲劇表演所創作的腳本,即劇本。戲劇的表演形式多種多樣,常見的包括話劇、歌劇、舞劇、音樂劇、木偶戲等。本任務主要盤點國內外著名的戲劇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