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
簡介
曹丕納袁熙之妻甄氏為妻。操哭袁紹。盡免河北居民一年租賦。自領冀州牧。
許攸傲激許褚被殺。而後褚見曹操,操責之,厚葬攸。又訪冀賢士,得崔琰。
袁譚被曹洪殺死。曹操得南皮,“安撫百姓”。王修哭袁譚,操稱其為“忠臣”。
幽軍馬降操。操荀攸詐降計破並。操又從郭嘉計,遠征沙漠,得柳城。郭嘉遺書定遼東。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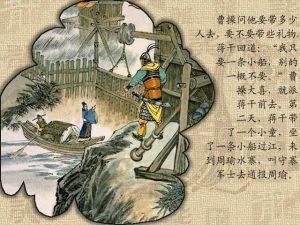 《三國演義》第三十三回
《三國演義》第三十三回卻說曹丕見二婦人啼哭,拔劍欲斬之。忽見紅光滿目,遂按劍而問曰:“汝何人也?”一婦人告曰:“妾乃袁將軍之妻劉氏也。”丕曰:“此女何人?”劉氏曰:“此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因熙出鎮幽州,甄氏不肯遠行,故留於此。”丕拖此女近前,見披髮垢而。丕以衫袖拭其面而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也。願保汝家。汝勿憂慮。”道按劍坐於堂上。
卻說曹操統領眾將入冀州城,將入城門,許攸縱馬近前,以鞭指城門而呼操曰:“阿瞞,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門?”操大笑。眾將聞言,俱懷不平。操至紹府門下,問曰:“誰曾入此門來?”守將對曰:“世子在內。”操喚出責之。劉氏出拜曰:“非世子不能保全妾家,願獻甄氏為世子執箕帚。”操教喚出甄氏拜於前。操視之曰:“真吾兒婦也?”遂令曹丕納之。
操既定冀州,親往袁紹墓下設祭,再拜而哭甚哀,顧謂眾官曰:“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本初問吾曰:‘若事不輯,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喪,吾不能不為流涕也!”眾皆嘆息。操以金帛糧米賜紹妻劉氏。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一面寫表申朝;操自領冀州牧。
一日,許褚走馬入東門,正迎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怒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攸罵曰:“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劍殺攸,提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殺之矣。”操曰:“子遠與吾舊交,故相戲耳,何故殺之!”深責許褚,令厚葬許攸。乃令人遍訪冀州賢士。冀民曰:“騎都尉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數曾獻計於袁紹,紹不從,因此託疾在家。”操即召琰為本州別駕從事,而謂曰:“昨按本州戶籍,總計三十萬眾,可謂大州。”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相爭,冀民暴骨原野,丞相不急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先計校戶籍,豈本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聞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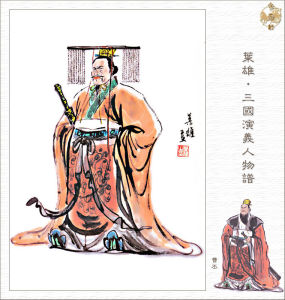 曹丕
曹丕操已定冀州,使人探袁譚訊息。時譚引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袁尚敗走中山,乃統軍攻之。尚無心戰鬥,徑奔幽州投袁熙。譚盡降其眾,欲復圖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書絕其婚,自統大軍征之,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軍來,遣人求救於劉表。表請玄德商議。玄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袁氏兄弟不久必為操擒,救之無益;況操常有窺荊襄之意,我只養兵自守,未可妄動。”表曰:“然則何以謝之?”玄德曰:“可作書與袁氏兄弟,以和解為名,婉詞謝之。”表然其言,先遣人以書遺譚。書略曰:“君子違難,不適仇國。日前聞君屈膝降曹,則是忘先人之仇,棄手足之誼,而遺同盟之恥矣。若冀州不弟,當降心相從。待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高義耶?”又與袁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計曲直,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得表書,知表無發兵之意,又自料不能敵操,遂棄平原,走保南皮。
曹操追至南皮,時天氣寒肅,河道盡凍,糧船不能行動。操令本處百姓敲冰拽船,百姓聞令而逃。操大怒,欲捕斬之。百姓聞得,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軍士擒獲。”百姓皆垂淚而去。
袁譚引兵出城,與曹軍相敵。兩陣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吾厚待汝,汝何生異心?”譚曰:“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賴吾妻子,反說我有異心耶!”操大怒,使徐晃出馬。譚使彭安接戰。兩馬相交,不數合,晃斬彭安於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皮。操遣軍四面圍住。譚著慌,使辛評見操約降。操曰:“袁譚小子,反覆無常,吾難準信。汝弟辛毗,吾已重用,汝亦留此可也。”評曰:“丞相差矣。某聞主貴臣榮,主憂臣辱。某久事袁氏,豈可背之!”操知其不可留,乃遣回。評回見譚,言操不準投降。譚叱曰:“汝弟現事曹操,汝懷二心耶?”評聞言,氣滿填胸,昏絕於地。譚令扶出,須臾而死。譚亦悔之。郭圖謂譚曰:“來日盡驅百姓當先,以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譚從其言。
當夜盡驅南皮百姓,皆執刀槍聽令。次日平明,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遍地。操見未獲全勝,棄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被殺者無數。曹洪奮威突陣,正迎袁譚,舉刀亂砍,譚竟被曹洪殺於陣中,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中。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下城壕,人馬俱陷。操引兵入南皮,安撫百姓。忽有一彪軍來到,乃袁熙部將焦觸、張南也。操自引軍迎之。二將倒戈卸甲,特來投降。操封為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為平北將軍。下令將袁譚首級號令,敢有哭者斬。頭掛北門外。一人布冠衰衣,哭於頭下。左右拿來見操。操問之,乃青州別駕王修也,因諫袁譚被逐,今知譚死,故來哭之。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知之。”操曰:“汝不怕死耶?”修曰:“我生受其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若得收葬譚屍,受戮無恨。”操曰:“河北義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用,則吾安敢正眼覷此地哉!”遂命收葬譚屍,禮修為上賓,以為司金中郎將。因問之曰:“今袁尚已投袁熙,取之當用何策?”修不答。操曰:“忠臣也。”問郭嘉,嘉曰:“可使袁氏降將焦觸、張南等自攻之。”操用其言,隨差焦觸、張南、呂曠、呂翔、馬延、張顗,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一面使李典、樂進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幹。且說袁尚、袁熙知曹兵將至,料難迎敵,乃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投烏桓去了。幽州刺史烏桓觸,聚幽州眾官,歃血為盟,共議背袁向曹之事。烏桓觸先言曰:“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投降,有不遵令者斬。”依次歃血,循至別駕韓珩。珩乃擲劍於地,大呼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主敗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操,吾不為也!”眾皆失色。烏桓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韓珩既有志如此,聽其自便。”推珩而出。烏桓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徑來降操。操大喜,加為鎮北將軍。
忽探馬來報:“樂進、李典、張燕攻打并州,高幹守住壺關口,不能下。”操自勒兵前往。三將接著,說乾拒關難擊。操集眾將共議破乾之計。荀攸曰:“若破乾,須用詐降計方可。”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呂曠等引軍數十,直抵關下,叫曰:“吾等原系袁氏舊將,不得已而降曹。曹操為人詭譎,薄待吾等;吾今還扶舊主。可疾開關相納。”高幹未信,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二將卸甲棄馬而入,謂乾曰:“曹軍新到,可乘其軍心未定,今夜劫寨。某等願當先。”於喜從其言,是夜教二呂當先,引萬餘軍前去。將至曹寨,背後喊聲大震,伏兵四起。高幹知是中計,急回壺關城,樂進、李典已奪了關、高幹奪路走脫,往投單于。操領兵拒住關口,使人追襲高幹。乾到單于界,正迎北番左賢王。乾下馬拜伏於地,言曹操吞併疆土,今欲犯王子地面,萬乞救援,同力克復,以保北方。左賢王曰:“吾與曹操無仇,豈有侵我土地?汝欲使我結怨於曹氏耶!”叱退高幹。乾尋思無路,只得去投劉表。行至上洛,被都尉王琰所殺,將頭解送曹操。曹封琰為列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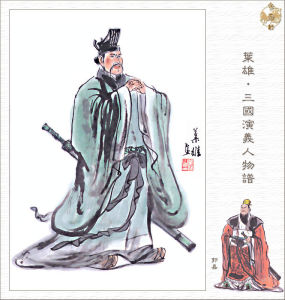 郭嘉
郭嘉并州既定,操商議西擊烏桓。曹洪等曰:“袁熙、袁尚兵敗將亡,勢窮力盡,遠投沙漠;我今引兵西擊,倘劉備、劉表乘虛襲許都,我救應不及,為禍不淺矣:請回師勿進為上。”郭嘉曰:“諸公所言錯矣。主公雖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邊遠,必不設備;乘其無備,卒然擊之,必可破也。且袁紹與烏桓有恩,而尚與熙兄弟猶存,不可不除。劉表坐談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操曰:“奉孝之言極是。”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望前進發。但見黃沙漠漠,狂風四起;道路崎嶇,人馬難行。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嘉。嘉此時不伏水土,臥病車上。操泣曰:“因我欲平沙漠,使公遠涉艱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嘉曰:“某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一。”操曰:“吾見北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但須得識徑路者為引導耳。”
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嚮導官以引路。人薦袁紹舊將田疇深知此境,操召而問之。疇曰:“此道秋夏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楫,最難行動。不如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柳城,掩其不備:蹋頓可一戰而擒也。”操從其言,封田疇為靖北將軍,作嚮導官,為前驅;張遼為次;操自押後:倍道輕騎而進。
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正遇袁熙、袁尚會合蹋頓等數萬騎前來。張遼飛報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蹋頓兵無隊伍,參差不整。操謂張遼曰:“敵兵不整,便可擊之。”乃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奮力急攻,蹋頓大亂。遼拍馬斬蹋頓於馬下,餘眾皆降。袁熙、袁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去了。操收軍入柳城,封田疇為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涕泣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蒙厚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寨以邀賞祿哉!死不敢受侯爵。”操義之,乃拜疇為議郎。操撫慰單于人等,收得駿馬萬匹,即日回兵。時天氣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糧,殺馬為食,鑿地三四十丈,方得水。操回至易州,重賞先曾諫者;因謂眾將曰:“孤前者乘危遠征,僥倖成功。雖得勝,天所佑也,不可以為法。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
操到易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在公廨。操往祭之,大哭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回顧眾官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惟奉孝最少,吾欲托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之書呈上曰:“郭公臨亡,親筆書此,囑曰:丞相若從書中所言,遼東事定矣。”操拆書視之,點頭嗟嘆。諸人皆不知其意。次日,夏侯惇引眾人稟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賓服。今袁熙、袁尚又往投之,必為後患。不如乘其未動,速往征之,遼東可得也。”操笑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之後,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諸將皆不肯信。卻說袁熙、袁尚引數千騎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本襄平人,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也。當日知袁熙、袁尚來投,遂聚本部屬官商議此事。公孫恭曰:“袁紹在日,常有吞遼東之心;今袁熙,袁尚兵敗將亡,無處依棲,來此相投,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後必相圖。不如賺入城中殺之,獻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我。”康曰:“只怕曹操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使為我助。”恭曰:“可使人探聽。如曹兵來攻,則留二袁;如其不動,則殺二袁,送與曹公。”康從之,使人去探訊息。卻說袁熙、袁尚至遼東,二人密議曰:“遼東軍兵數萬,足可與曹操爭衡。今暫投之,後當殺公孫康而奪其地,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北也。”商議已定,乃入見公孫康。康留於館驛,只推有病,不即相見。不一日,細作回報:“曹公兵屯易州,並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大喜,乃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使二袁入。相見禮畢,命坐。時天氣嚴寒,尚見床榻上無裀褥,謂康曰:“願鋪坐席。”康瞋目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席之有!尚大驚。康叱曰:“左右何不下手!”刀斧手擁出,就坐席上砍下二人之頭,用木匣盛貯,使人送到易州,來見曹操。時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惇、張遼入稟曰:“如不下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待二袁首級至,即便回兵。”眾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級至,眾皆大驚。使者呈上書信。操大笑曰:“不出奉孝之料!”重賞來使,封公孫康為襄平侯、左將軍。眾官問曰:“何為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出郭嘉書以示之。書略曰:“今聞袁熙、袁尚往投遼東,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二袁往投必疑。若以兵擊之,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眾皆踴躍稱善。操引眾官復設祭於郭嘉靈前。亡年三十八歲,從征十有一年,多立奇勳。後人有詩讚曰:“天生郭奉孝,豪傑冠群英:腹內藏經史,胸中隱甲兵;運謀如范蠡,決策似陳平。可惜身先喪,中原梁棟傾。”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安葬。
程昱等請曰:“北方既定,今還許都,可早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久矣。諸君所言,正合吾意。”是夜宿於冀州城東角樓上,憑欄仰觀天文。時荀攸在側,操指曰:“南方旺氣燦然,恐未可圖也。”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正看間,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寶於地下”。操下樓令人隨光掘之。正是:星文方向南中指,金寶鏇從北地生。
不知所得何物,且聽下文分解。
賞析
三國演義雖以三國為名,但實際上三國直到孫權稱帝才正式形成,那已經是公元229年的事了,在演義中談到此事時已經是九十八回,幾近結束了,假若以曹丕篡位,東漢滅亡來作為三國形成的標誌,也要到八十回,而以劉備得漢中並進為漢中王為分界點也是七十三回的故事,所以我們常說的三國演義,大半部分說的是東漢末年的故事。
自然,稱之為三國演義自然有其道理,我們大凡說故事,需要說前因後果,而這三國演義,不單說三國,而更是說劉曹孫三家是如何創立三國的故事,我們看演義第一回,以黃巾起義為開端,先引出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再曹操登台,到了第二回,江東孫家的奠基人孫堅也開始亮相,這並非無的放矢,而是作者蓄意為之,所以我們可知,三國演義實際上說的那就是三國英雄人物的故事。
如此一來,對三國演義便有了兩種劃分辦法,一種以三國的創建來劃分,所謂前三國是群雄並起的時代,以曹操擊敗袁家為一標準,而中三國可視為劉曹孫三分天下的那段故事,後三國則是三國建立後到西晉一統天下,也是全章結束,中三國和後三國的劃分正如上文所言,或以曹丕篡漢或以劉備進為漢中王為標誌比較合適。
而另一種方式則是以英雄人物為劃分標準,三國演義的主角是誰?並非劉關張,也非曹操,更不用說孫權了,而是諸葛亮是也。三國之中,作者對諸葛亮給予厚愛,對其事跡美化和描寫無人可及,即便是同樣受到推崇的關羽也不能相提並論。演義一百二十回中近半是為說那諸葛孔明的忠誠才智,三國演義的第一主角以諸葛亮莫屬,所以以人物來劃分,中三國是以劉備知諸葛亮之名到五丈原武侯身亡這段成一故事,而後三國則可被視為諸葛亮身後的英雄故事,那時早期的英雄已經大都逝去,我們稱之為後三國英雄時代也不為過。
因此,我將前三國時代的結尾便選在這第三十三回上,一來以第一種劃分方式來說,這回便是曹操徹底擊敗袁家勢力,鞏固北方之時,二來以第二種劃分方式來說,其實之後第三十四回到第三十七回,都是為劉備請諸葛亮出山做的鋪墊而已,諸葛亮不見其人,但是其聲卻一點一點滲入劉備之心。而前三十三回則是純粹的沒有諸葛亮的前三國時代,因此,我便將前三十三回定為前三國時代。
那前三國時代是個什麼樣的時代呢?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個時代是個亂世時代,原本相對安定的東漢王朝已經失去了自己的權威,皇帝變得虛有其表,那些原本朝廷的官僚們與地方勢力結合起來,割據一方,並為著人口,地盤,財富進行了大大小小的戰爭,即便是相對穩定的荊州益州也面臨著與江東漢中的對峙,更別提這場戰爭的重災區兗青徐豫各州了,神州大地,烽火四起。十餘年中群雄爭鬥。終於由曹操將北方大致一統。前三國講述的便是此時群雄爭霸的故事。前三國之中,雖說在部分細節上做了改動,添加了部分虛構情節,比如關羽的過五關斬六將之事,但是相比較中三國為了諸葛亮而做的改動相比,前三國的演義還算是大致符合歷史,其中主要以曹操統一北方為主線,描寫了中原戰場的情況,其中間或談到關中和江東的局勢,為之後的三國鼎立埋下伏筆。
對於演義來說,歷史只是一個大舞台而已,更重要的是在舞台上所展現的英雄人物,和中三國時代的諸葛亮的一枝獨秀不同,前三國時代並沒有局限於一兩個英雄人物,而著重的是展現一個眾生相。其中以曹操,關羽,劉備,張飛,呂布等人較為突出。
在整部三國演義中,趙雲,關羽,諸葛亮是作者最為偏愛的角色,而在前三國時代,諸葛亮還沒出現,趙雲則表現的機會不多,只是在界橋一戰嶄露頭角,而後長時期沒有他的篇章,只是通過劉備暗自的擔憂來側面表現趙雲的能力,但是趙雲真正大顯身手的時刻還是在之後的演義之中。惟有關羽在前三國時代便奠定了自己的形象,在之後的華容道水淹七軍只是為了添磚加瓦而已。所以我們先說說關羽形象的奠定。
關羽第一次亮相是在第一回中,關羽一上場的第一句話便是:
“快斟酒來吃,我待趕入城去投軍。”
這不單是和劉備張飛兩人的志願相合而引出桃園結義,也是初次表現關羽對國之忠,而後再以劉備的角度看關羽相貌:
“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重棗,唇若塗脂;丹鳳眼,臥蠶眉,相貌堂堂,威風凜凜。”
又在攀談中道出關羽來歷:
“吾姓關,名羽,字長生,後改雲長,河東解良人也。因本處勢豪倚勢凌人,被吾殺了,逃難江湖,五六年矣。今聞此處招軍破賊,特來應募。”
短短几十字便現出一個不畏豪強的好漢形象來。對關羽來說,之後滅黃巾只是牛刀小試,真正的亮相則是那溫酒斬華雄,先以俞涉潘鳳的死來表現華雄之能,再以關羽出場,那句“其酒尚溫”將關羽之威風展露無疑。
這之後關羽便沒有太多的大場面,只是如十四回借劉備之口說“吾早晚欲與爾議事,”來體現關羽之智,或二十回關羽要斬曹操來表現關羽之忠了。
但是這些小事終比不上一次大場面,就象趙雲之七進七出,張飛之長坂橋。而關羽終於得到了機會,而且一次便是兩次,第一次是斬顏良文丑,顏良文丑可非華雄可比,顏良擊敗徐晃,文丑射中張遼,兩人是一等一的大將,而關羽卻能斬之,如此一來,關羽這一流武將的身份再也跑不掉了。而第二次則便是那次出名的歸劉備。
關羽之歸,如同諸葛亮之亮相一樣,是個大工程,先是二十五回,關羽兵敗在土山定三約降曹操為之後的歸定下基調,再以曹操連番的重賞試探和關羽的對應表現關羽對劉備之忠義。其中以對張遼的問答,與劉備的回信,及對曹操的留書最為體現關羽之忠義,
再之後就是那出名的過五關斬六將,千里尋兄,終於將關羽這個忠義角色完全表現出來,之後的只是鞏固而已。
相對關羽來說,張飛則是扮演了傳統演義中的莽將角色,就好象水滸中的李逵,說岳中的牛皋,說唐中的程咬金,這種角色往往是一種調和劑,鹵莽而又不失純真,比較而言,說唐中的程咬金和說岳中的牛皋更多的帶有一種喜劇色彩,而水滸中的李逵比較純真,而在原來的評書中,張飛也確實帶有很多的喜劇元素,不過在演義中,喜劇元素漸漸被淡化,鹵莽的一面更多表現出來,如在第一回中,便安排張飛與劉備那突然的相遇:
隨後一人厲聲言曰:“大丈夫不與國家出力,何故長嘆?”
這般的問話和隨後的同舉大事之言假若放在劉備和關羽身上,都顯得不協調,而在鹵莽的張飛身上,則是那般的合身,而作者在之後更是加強這種感覺,比如因受輕視要殺董卓,鞭打督郵,醉酒失徐州,古城初見關羽卻要斬殺之,這些或是虛構或是真實的故事都將一個鹵莽但是又疾惡如仇的三將軍形象表現出來。而對於張飛的武勇,比較關羽那么多的斬殺大將戰例來說,張飛則少的多,主要通過與呂布的幾次交鋒,關羽在曹操面前對張飛武藝的讚頌,來表現張飛之勇,而這樣的描寫也達到了極好的效果,等到長坂橋上張飛三聲喝退百萬曹軍,讀者也並不覺得突然,反而認為理所當然,只有猛張飛而非其他任何人能做到這個效果,這便是之前對張飛的描寫成功之處。
至於呂布,我在第十九章一文中便已經說過,呂布是演義中常見的那般武藝天下第一帶有傳奇性的英雄角色,每本演義都需要這樣一個天下無敵而又有戲劇性衝突的英雄來點燃氣氛,三國演義也不例外,雖然說選擇呂布作為這個角色有呂布在歷史上行為的關係,但是將其塑造成天下第一則有刻意的成分,如著名的三英戰呂布便是如此,原本三國志平話中不單有張飛單騎戰勝了呂布這一說,而且還有呂布被董卓眾將擒住才歸降的說法。但是在三國演義中,這些都被祛除了,呂布成為真正的天下第一。但是演義中天下第一的角色結局往往是悲慘的,大都是早死的命,而且這些角色往往不是貪財好色就是頭腦簡單,呂布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了。或許其中也包含著作書的文人對這些只知恃武之人的蔑視吧。
此外,袁紹的昏庸剛愎,袁術的妒賢嫉能,孫策英勇而又急燥的性格,在演義中也有相當出色的描寫,即便是陳宮,田豐,沮授,審配,王允,郭嘉這些次要人物,我們也能從演義寥寥幾筆的描寫體會出其中的個人魅力來。
自然,在諸葛亮之前,關羽之外,演義中最主要的兩個人物還是曹操和劉備,而兩人卻是完全不同的對立面。
對於曹操,羅貫中可以說表現的相當的出色,曹操第一次出場是在平黃巾中,那時的介紹只是將史書上的原話抄下而已,真正的作者創作在於第四回中,在王允召開的宴會之上,眾人皆哭,卻只有曹操大笑,充分顯示了曹操的與眾不同,而曹操獻刀更是精彩,我們且看演義中。先是曹操入內,說:“馬羸行遲耳。”,引得董卓將呂布遣出尋馬。再是曹操暗忖:“此賊合死!”,但因多疑,不敢輕動,等到董卓面朝內坐,曹操終於擎刀在手,卻被董卓發現,而此時曹操借獻刀之名逃過一劫,隨後當機立斷,乘馬逃離。這段描寫展現了曹操多疑,但是又多智果斷的性格特徵,這點在同一回與陳宮結伴而行殺呂伯奢一家又顯現了一次,並以曹操那句“寧可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為其做了總結。再如十七回,攻打袁術糧食要用盡時,先令倉官用小斛,再斬倉官之頭,安軍心。三十回見許攸來投奔,一方面喜出望外,跣足相迎,一方面卻不肯告之真情,其軍糧從一年,半年,到一月,還是不肯說實話,最終還需許攸道破才罷。
曹操的性格不單如此,他對人才的重視在演義中也有詳盡的描寫,且不提對典韋和郭嘉的哭祭,對關羽的愛才,就以第三十三回與崔琰的對話就可見一斑,曹操稱冀州人口眾多,真是大州,沒想遭到崔琰一番搶白,稱其“冀民暴骨原野,丞相不急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先計校戶籍,豈本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這樣的搶白曹操的反應卻是改容謝之,待為上賓,實在是人所不能及的地方。(不過日後崔琰還是被曹操殺死。)
應該說曹操的性格相當複雜,集機智多疑,豁達果斷,尊賢愛才,又畏人知心,明理,殘忍好殺,多才多藝為一體。清朝詩人趙翼對明太祖朱元璋的評價是:“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以我來看,這個評價用於曹操身上也很適當。
演義對曹操性格的描寫十分成功,這是貫穿整個演義而並非局限於前三國之中,或許可稱曹操是演義中除諸葛亮之外塑造最成功的人物,這一來是因為曹操這樣的性格很容易出彩,二來曹營之中是以曹操為主體,其他文臣武將都是次要角色,這樣不會分散曹操的戲分。三來也是因為曹操的事跡有大量的記載,而演義最大限度的採用了這點,所以我們稱演義中的曹操和史書上的曹操是很相近的。
相對曹操而言,劉備的塑造演義某種程度上就比較失敗,劉備早期的事跡比較少,這樣供演義發揮的空間就大了許多,但是演義在這點上做的並不好,一方面為了表現劉備的仁,搞出一些虛構情節,比如劉安殺妻,之後的摔阿斗,但是這些情節的效果並不好;另一方面為了顯示諸葛亮和關羽之能,將大量劉備所擁有的功績轉嫁到諸葛亮而關羽身上,這點倒是十分的有趣,因為諸葛亮和關羽這兩個演義主角在劉備陣營的關係,最大的演義受害者成為了劉備,自己的功績幾乎都被剝奪,差點就成為一個只會哭鼻子和問軍師怎么辦的角色了,反倒是與諸葛亮站在對立面的曹操,卻因禍得福,因為自己的陣營中沒有刻意要加強的角色,所以也沒人為他分擔那些本就屬於他的功績了。演義如此安排,但是歷史上的劉備卻並非這樣,而演義中又大量採用了歷史記載,如此一來,導致劉備的角色非常的彆扭,與曹操相比,演義中的劉備就不是真實的劉備。演義中對劉備這個主君的塑造並不算很成功。比較而言,演義中劉備更象關張的兄長,諸葛亮的知音,而不是一個馳騁沙場的主公。(關於劉備與曹操的角色,日後再專門尋一章敘述之)
總而言之,前三國時代是一個群雄並起的時代,各種各樣的角色在有限的篇幅中展現著自己,不過這一切總會結束,三國演義將迎來真正的主角,而那些還在演義注視範圍內的角色依舊將發揮著自己的光熱,新的角色也將陸續到來,真正的三國就要來臨了。
回評
毛宗崗批語
袁尚母劉氏之妒,其酷烈也甚矣。乃城破之後,不能死節,而獻甄氏於曹丕,以圖苟全,又何其無烈性至此乎!可見婦之貞者必不妒,婦之妒者必不貞。呂氏為項羽所得而不死,所以有人彘之刑;飛燕曾事射鳥兒,所以多殺皇嗣;武曌有聚麀之恥,所以弒王后、殺蕭妃:豈非妒婦之明驗哉?
袁譚不得娶曹操之女,曹丕反得娶袁紹之婦,是曹操失一婿而得一婦,袁紹失一婦而又失一婦也。曹操之女未嫁而已寡,猶當悼其死婿;袁熙之妻未寡而再嫁,毋乃負其生夫乎!婚可絕,婿可易,曹操不妨舍譚求後婿;婿可續,兒不可續,劉氏亦將認丕為繼兒乎?紹妾毀既死之容,熙妻何不毀欲生之面?為紹妻者,妒及於既死之夫;為熙母者,何不念及於未死之子?總只因兄弟之變,遂引出夫婦之變、母子之變、翁婿之變、姑媳之變。君子讀書至此,蓋深有感於骨肉之間矣。
沮授不屈,審配亦不屈。同一不屈也,而沮授則一於事袁,審配則知有袁尚而不知有袁譚,審配不如沮授多矣。許攸降操,王修亦降操。同一降也,而許攸則助曹謀袁,王修則不忍助曹謀袁,王修賢於許攸遠矣。是不可以無辨。
殺許攸者,曹操也,非許褚也。許攸數侮曹操,操欲殺攸久矣。欲自殺之,而恐有殺故人、殺功臣之名,特假手於許褚耳。昔顛頡焚僖負羈之家,而重耳殺顛頡以旬于軍;今許褚殺攸而操曾不之罪,故曰非許褚殺之,而曹操殺之也。曹操資許攸之力以得冀州,劉備資法正之力以得西川。而法正恃功而橫,未聞見殺於關、張;許攸恃功而驕,遂乃見殺於許褚。君子以是知劉備之厚而曹操之薄。
王修和解二袁之言,是真語、激語、熟語。劉表和解二袁之言,是假語、緩語、冷語。然則劉表不過自解其不發兵之故,而在二袁聽之,則當以表之言為良言也。董卓嘗和解袁紹與公孫瓚矣,曹操嘗和解劉備與呂布矣。仇敵相爭,猶可暫時和解,況兄弟耶?而二袁不能聽,悲夫!
曹操有時而仁,有時而暴。免百姓秋租,仁矣;而使百姓敲冰拽船,何其暴也。不殺逃民而縱之,仁矣;又戒令勿為君士所獲,仍不禁軍之殺民,何其暴也。其暴處多是真,其仁處多是假。蓋曹操待冀州之民,與其待袁紹無以異耳。殺其子,奪其婦,取其地,而乃哭其墓;然則其哭也,真為慈悲乎,假為慈悲乎?奸雄之奸,非復常人意量所及。
“急之則合,緩之則爭”,此郭嘉所以策冀州者也;其策遼東亦猶是矣。曹操進軍攻北,而譚與尚相和;及其回兵向南,而譚與尚遂相鬥。觀譚之與尚,而熙、尚之與公孫康,豈異此哉!但操之於譚則兩之,於熙、尚與康則一存而一滅之;於冀州則待其亂而我滅之,於遼東則聽其自滅而更不煩我滅之:此則微有不同者爾。
李贄總評
老瞞易州賞諫,真帝王之策也。如以成敗論事,便同小兒,老瞞豈觀場者哉?固知若是丈夫,決不從人啼笑也。
史官以郭奉孝為若在,可西無蜀、東無吳也。此亦童子之言。當時奉孝死,智過奉孝者尚多,何卒三分也?固知隆中之言,非一時之言,彼己冷眼窺之久矣。
鍾敬伯總評
老瞞賞諫恍惚帝王故事,果出真心,固是丈夫所為;然賞之可也,賞必易州,正其奸也,豈真開言路者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