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簡介
操築銅雀台於漳河之上,領兵回許都,養精蓄銳,分兵屯田。
蔡瑁與其姊蔡夫人獻計劉表欲謀玄德。劉表讓玄德往新野駐紮。
劉備不同意劉表廢長立幼,蔡夫人和蔡瑁欲害劉備。劉備乘的盧馬出襄陽西門,躍過檀溪而逃。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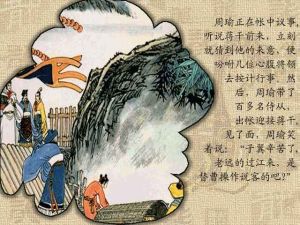 《三國演義》第三十四回
《三國演義》第三十四回卻說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夢玉雀入懷而生舜。今得銅雀,亦吉祥之兆也。”操大喜,遂命作高台以慶之。乃即日破土斷木,燒瓦磨磚,築銅雀台於漳河之上。約計一年而工畢。少子曹植進曰:“若建層台,必立三座:中間高者,名為銅雀;左邊一座,名為玉龍;右邊一座,名為金鳳。更作兩條飛橋,橫空而上,乃為壯觀。”操曰:“吾兒所言甚善。他日台成,足可娛吾老矣!”原來曹操有五子,惟植性敏慧,善文章,曹操平日最愛之。於是留曹植與曹丕在鄴郡造台,使張燕守北寨。操將所得袁紹之兵,共五六十萬,班師回許都。大封功臣;又表贈郭嘉為貞侯,養其子奕於府中。復聚眾謀士商議,欲南征劉表。荀彧曰:“大軍方北征而回,未可復動。且待半年,養精蓄銳,劉表、孫權可一鼓而下也。”操從之,遂分兵屯田,以候調用。
卻說玄德自到荊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正相聚飲酒,忽報降將張武、陳孫在江夏擄掠人民,共謀造反。表驚曰:“二賊又反,為禍不小!”玄德曰:“不須兄長憂慮,備請往討之。”表大喜,即點三萬軍,與玄德前去。玄德領命即行,不一日,來到江夏。張武、陳孫引兵來迎。玄德與關、張、趙雲出馬在門旗下,望見張武所騎之馬,極其雄駿。玄德曰:“此必千里馬也。”言未畢,趙雲挺槍而出,徑沖彼陣。張武縱馬來迎,不三合,被趙雲一槍刺落馬下,隨手扯住轡頭,牽馬回陣。陳孫見了,隨趕來奪。張飛大喝一聲,挺矛直出,將陳孫刺死。眾皆潰散。玄德招安餘黨,平復江夏諸縣,班師而回。表出郭迎接入城,設宴慶功。酒至半酣,表曰:“吾弟如此雄才,荊州有倚賴也。但憂南越不時來寇,張魯、孫權皆足為慮。”玄德曰:“弟有三將,足可委用:使張飛巡南越之境;雲長拒固子城,以鎮張魯;趙雲拒三江,以當孫權。何足慮哉?”表喜,欲從其言。
蔡瑁告其姊蔡夫人曰:“劉備遣三將居外,而自居荊州,久必為患。”蔡夫人乃夜對劉表曰:“我聞荊州人多與劉備往來,不可不防之。今容其居住城中,無益,不若遣使他往。”表曰:“玄德仁人也。”蔡氏曰:“只恐他人不似汝心。”表沉吟不答。次日出城,見玄德所乘之馬極駿,問之,知是張武之馬,表稱讚不已。玄德遂將此馬送與劉表。表大喜,騎回城中。蒯越見而問之。表曰:“此玄德所送也。”越曰:“昔先兄蒯良,最善相馬;越亦頗曉。此馬眼下有淚槽,額邊生白點,名為的盧,騎則妨主。張武為此馬而亡。主公不可乘之。”表聽其言。次日請玄德飲宴,因言曰:“昨承惠良馬,深感厚意。但賢弟不時征進,可以用之。敬當送還。”玄德起謝。表又曰:“賢弟久居此間,恐廢武事。襄陽屬邑新野縣,頗有錢糧。弟可引本部軍馬於本縣屯紥,何如?”玄德領諾。次日,謝別劉表,引本部軍馬逕往新野。
方出城門,只見一人在馬前長揖曰:“公所騎馬,不可乘也。”玄德視之,乃荊州幕賓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玄德忙下馬問之。籍曰:“昨聞蒯異度對劉荊州云:此馬名的盧,乘則妨主。因此還公。公豈可復乘之?”玄德曰:“深感先生見愛。但凡人死生有命,豈馬所能妨哉!”籍服其高見,自此常與玄德往來。玄德自到新野,軍民皆喜,政治一新。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生劉禪。是夜有白鶴一隻,飛來縣衙屋上,高鳴四十餘聲,望西飛去。臨分娩時,異香滿室。甘夫人嘗夜夢仰吞北斗,因而懷孕,故乳名阿斗。此時曹操正統兵北征。玄德乃往荊州,說劉表曰:“今曹操悉兵北征,許昌空虛,若以荊襄之眾,乘間襲之,大事可就也。”表曰:“吾坐據九郡足矣,豈可別圖?”玄德默然。表邀入後堂飲酒。酒至半酣,表忽然長嘆。玄德曰:“兄長何故長嘆?”表曰:“吾有心事,未易明言。”玄德再欲問時,蔡夫人出立屏後。劉表乃垂頭不語。須臾席散,玄德自歸新野。至是年冬,聞曹操自柳城回,玄德甚嘆表之不用其言。忽一日,劉表遣使至,請玄德赴荊州相會。玄德隨使而往。劉表接著,敘禮畢,請入後堂飲宴;因謂玄德曰:“近聞曹操提兵回許都,勢日強盛,必有吞併荊襄之心。昔日悔不聽賢弟之言,失此好機會。”玄德曰:“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機會豈有盡乎?若能應之於後,未足為恨也。”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酒酣,表忽潸然淚下。玄德問其故。表曰:“吾有心事,前者欲訴與賢弟,未得其便。”玄德曰:“兄長有何難決之事?倘有用弟之處,弟雖死不辭。”表曰:“前妻陳氏所生長子琦,為人雖賢,而柔懦不足立事;後妻蔡氏所生少子瓊,頗聰明。吾欲廢長立幼,恐礙於禮法;欲立長子,爭奈蔡氏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亂:因此委決不下。”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若憂蔡氏權重,可徐徐削之,不可溺愛而立少子也。”表默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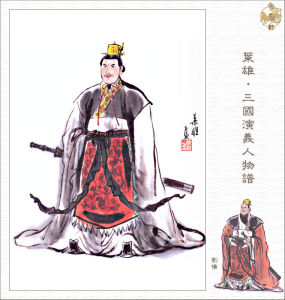 劉備
劉備原來蔡夫人素疑玄德,凡遇玄德與表敘論,必來竊聽。是時正在屏風后,聞玄德此言,心甚恨之。玄德自知語失,遂起身如廁。因見己身髀肉復生,亦不覺潸然流涕。少頃復入席。表見玄德有淚容,怪問之。玄德長嘆曰:“備往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散;分久不騎,髀里肉生。日月磋跎,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表曰:“吾聞賢弟在許昌,與曹操青梅煮酒,共論英雄;賢弟盡舉當世名士,操皆不許,而獨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以曹操之權力,猶不敢居吾弟之先,何慮功業不建乎?”玄德乘著酒興,失口答曰:“備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輩,誠不足慮也。”表聞言默然。玄德自知語失,托醉而起,歸館舍安歇。後人有詩讚玄德曰:“曹公屈指從頭數:天下英雄獨使君。髀肉復生猶感嘆,爭教寰字不三分?”
卻說劉表聞玄德語,口雖不言,心懷不足,別了玄德,退入內宅。蔡夫人曰:“適間我於屏後聽得劉備之言,甚輕覷人,足見其有吞併荊州之意。今若不除,必為後患。”表不答,但搖頭而已。蔡氏乃密召蔡瑁入,商議能事。瑁曰:“請先就館舍殺之,然後告知主公。”蔡氏然其言。瑁出,便連夜點軍。
卻說玄德在館舍中秉燭而坐,三更以後,方欲就寢。忽一人叩門而入,視之乃伊籍也:原來伊籍探知蔡瑁欲害玄德,特夤夜來報。當下伊籍將蔡瑁之謀,報知玄德,催促玄德速速起身。玄德曰:“未辭景升,如何便去?”籍曰:“公若辭,必遭蔡瑁之害矣。”玄德乃謝別伊籍,急喚從者,一齊上馬,不待天明,星夜奔回新野。比及蔡瑁領軍到館舍時,玄德已去遠矣。瑁悔恨無及,乃寫詩一首於壁間,逕入見表曰:“劉備有反叛之意,題反詩於壁上,不辭而去矣。”表不信,親詣館舍觀之,果有詩四句。詩曰:“數年徒守困,空對舊山川。龍豈池中物,乘雷欲上天!”劉表見詩大怒,拔劍言曰:“誓殺此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曰:“吾與玄德相處許多時,不曾見他作詩。此必外人離間之計也。”遂回步入館舍,用劍尖削去此詩,棄劍上馬。蔡瑁請曰:“軍士已點齊,可就往新野擒劉備。”表曰:“未可造次,容徐圖之。”蔡瑁見表持疑不決,乃暗與蔡夫人商議:即日大會眾官於襄陽,就彼處謀之。次日,瑁稟表曰:“近年豐熟,合聚眾官於襄陽,以示撫勸之意。請主公一行。”表曰:“吾近日氣疾作,實不能行。可令二子為主待客。”瑁曰:“公子年幼,恐失於禮節。”表曰:“可往新野請玄德待客。”瑁暗喜正中其計,便差人請玄德赴襄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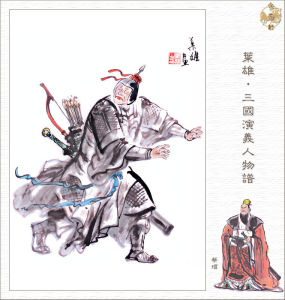 蔡瑁
蔡瑁卻說玄德奔回新野,自知失言取禍,未對眾人言之。忽使者至,請赴襄陽。孫乾曰:“昨見主公匆匆而回,意甚不樂。愚意度之,在荊州必有事故。今忽請赴會,不可輕往。”玄德方將前項事訴與諸人。雲長曰:“兄自疑心語失。劉荊州並無嗔責之意。外人之言,未可輕信。襄陽離此不遠,若不去,則荊州反生疑矣。”玄德曰:“雲長之言是也。”張飛曰:“筵無好筵,會無好會,不如休去。”趙雲曰:“某將馬步軍三百人同往,可保主公無事。”玄德曰:“如此甚好。”
遂與趙雲即日赴襄陽。蔡瑁出郭迎接,意甚謙謹。隨後劉琦、劉琮二子,引一班文武官僚出迎。玄德見二公子俱在,並不疑忌。是日請玄德於館舍暫歇。趙雲引三百軍圍繞保護。雲披甲掛劍,行坐不離左右。劉琦告玄德曰:“父親氣疾作,不能行動,特請叔父待客,撫勸各處守收之官。”玄德曰:“吾本不敢當此;既有兄命,不敢不從。”次日,人報九郡四十二州官員,俱已到齊。蔡瑁預請蒯越計議曰:“劉備世之梟雄,久留於此,後必為害,可就今日除之。”越曰:“恐失士民之望。”瑁曰:“吾已密領劉荊州言語在此。”越曰:“既如此,可預作準備。”瑁曰:“東門峴山大路,已使吾弟蔡和引軍守把;南門外已使蔡中守把;北門外已使蔡勛守把。止有西門不必守把:前有檀溪阻隔,雖有數萬之眾,不易過也。”越曰:“吾見趙雲行坐不離玄德,恐難下手。”瑁曰:“吾伏五百軍在城內準備。”越曰:“可使文聘、王威二人另設一席於外廳,以待武將。先請住趙雲,然後可行事。”瑁從其言。
當日殺牛宰馬,大張筵席。玄德乘的盧馬至州衙,命牽入後園拴系。眾官皆至堂中。玄德主席,二公子兩邊分坐,其餘各依次而坐。趙雲帶劍立於玄德之側。文聘、王威入請趙雲赴席。雲推辭不去。玄德令雲就席,雲勉強應命而出。蔡瑁在外收拾得鐵桶相似,將玄德帶來三百軍,都遣歸館舍,只待半酣,號起下手。酒至三巡,伊籍起把盞,至玄德前,以目視玄德,低聲謂曰:“請更衣,”玄德會意,即起如廁,伊籍把盞畢,疾入後園,接著玄德,附耳報曰:“蔡瑁設計害君,城外東、南、北三處,皆有軍馬守把。惟西門可走,公宜速逃!”玄德大驚,急解的盧馬,開後園門牽出,飛身上馬,不顧從者,匹馬望西門而走。門吏問之,玄德不答,加鞭而出。門吏當之不住,飛報蔡瑁。瑁即上馬,引五百軍隨後追趕。
卻說玄德撞出西門,行無數里,前有大溪,攔住去路,那檀溪闊數丈,水通襄江,其波甚緊。玄德到溪邊,見不可渡,勒馬再回,遙望城西塵頭大起,追兵將至。玄德曰:“今番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頭看時,追兵已近。玄德著慌,縱馬下溪。行不數步,馬前蹄忽陷,浸濕衣袍。玄德乃加鞭大呼曰:“的盧,的盧!今日妨吾!言畢,那馬忽從水中涌身而起,一躍三丈,飛上西岸。玄德如從雲霧中起。後來蘇學士有古風一篇,單詠躍馬檀溪事。詩曰:“老去花殘春日暮,宦遊偶至檀溪路;停驂遙望獨徘徊,眼前零落飄紅絮。暗想鹹陽火德衰,龍爭虎鬥交相持;襄陽會上王孫飲,坐中玄德身將危。逃生獨出西門道,背後追兵復將到;一川煙水漲檀溪,急叱征騎往前跳。馬蹄蹄碎青玻璃,天風響處金鞭揮。耳畔但聞千騎走,波中忽見雙龍飛。西川獨霸真英主,坐下龍駒兩相遇。檀溪溪水自東流,龍駒英主今何處!臨流三嘆心欲酸,斜陽寂寂照空山;三分鼎足渾如夢,蹤跡空留在世間。”玄德躍過溪西,顧望東岸。蔡瑁已引軍趕到溪邊,大叫:“使君何故逃席而去?”玄德曰:“吾與汝無仇,何故欲相害?”瑁曰:“吾並無此心。使君休聽人言。”玄德見瑁手將拈弓取箭,乃急撥馬望西南而去。瑁謂左右曰:“是何神助也?”方欲收軍回城,只見西門內趙雲引三百軍趕來。正是:躍去龍駒能救主,追來虎將欲誅仇。
未知蔡瑁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賞析
本章劉表請劉備赴宴,談得一事,便是兩子劉琦劉琮的問題,和袁紹一樣,劉表也想廢長立幼,而又猶豫不決,為何呢?演義中說限於禮法,什麼樣的禮法呢?就是傳統的嫡長子繼承制。一般認為,這是周公所創,長期以來已經被世人所接受了,這主要是為了防止諸子為了繼承權而發生糾葛,減少繼承成本的一種制度,可以說,這種制度是相當有效的,不單是皇室,而且也是被世人所公認的原則。而袁紹和劉表都違反了這一原則,之後頗被人拿出來作為反面典型批判的,比如曹操在立世子時遲疑不決,賈詡一句:“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便讓曹操立了曹丕。
不過呢,理論上應該是由嫡長子繼承,但是實際操作上卻並非如此。
其一:所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長子呢,有時就意味著比其他兒子要死的那么早一點,當然喔,按正常來說,皇帝父親也會比長子先走,但是往往就有幾位皇帝壽命長的驚人,一般在平常人家裡,有個老壽星是件好事,但是在皇家就未必是好事了,至少對於太子來說就是如此,這一方面要提防著下面的弟弟盯著自己的皇位眼紅,搞出什麼事來,另一方面要想這皇帝父親哪天才會住進早就準備好的陵墓去,想來這不合孝道的事老天也不開心,所以白髮老皇帝送黑髮太子的事並不新鮮,有時還一連送一兩個,明太祖梁武帝就不說了,就說這三國孫權吧,長子孫登就在他前頭去了。(說起孫權,他也差點造成袁紹劉表一樣的錯誤,就是偏愛四子孫霸,冷落三子也是被立為太子的孫和,造成兩子相爭的局面,不過他心夠狠,我兩個都不要了,廢了孫和,殺死孫霸,立孫亮為太子。)這種是看誰活的長,這就是衛生健康的重要性了,在古代叫天命,怪不得誰,是最文雅的一種非長子繼承的原因。
其二,雖然有嫡長子繼承制,所謂“立長不立賢”,但是實際上頗多時候立賢占了上風的,這裡的“賢”大家千萬不要認為是真正的賢,實際上“賢”就是皇帝所認可,所喜歡的就是“賢”,皇帝不喜歡的就是“愚”了,(當然,象晉惠帝那樣明顯的愚也是少見了。)就拿袁紹和劉表兩個土皇帝來說,他們認為袁尚和劉琮是比較聰明,比較“賢”,但是並沒有任何證據來證明這點。這樣的唯賢標準只能導致各子為了爭奪那個“賢”而明爭暗鬥,爭政績,爭武略,爭文采,爭相貌,有時連再下一代也可以拿出來爭爭。(證明自己生育能力沒有缺陷嘛!)這還算比較正常點,不正常點就賄賂皇帝身邊比較寵信的妃子宦官大臣為自己說好話也是常見的事,至於拉幫結黨,最後爭到刀兵相間,連皇帝父親也牽扯進去的也不希奇。袁尚和袁譚不就最後動刀到槍了嘛,曹丕得了皇位也想煎煎弟弟曹植呢。不過最著名的兩個例子還是隋煬帝楊廣和唐太宗李世民啦,隋煬帝楊廣認真表現,把父親隋文帝和母親獨孤皇后迷的一怔一怔的,硬是把長子楊勇廢了立了楊廣為太子,正是所謂的兵不血刃啊。而唐太宗李世民就有些火暴了,玄武門之變幹掉一個哥哥一個弟弟,父親也嚇的退位,是武力的代表。
其三,嫡長子繼承制其中有個“嫡”字,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牽扯到之前說起的妻妾的區別了,皇家之中也是一樣的,正宮皇后地位在一般妃子之上,更別提那些宮女了,所以皇后生的兒子那是被視為嫡出的,而其他妃子宮女所生的就是庶出,那些庶出的兒子別說是長子,就算比嫡出的長十幾年,那還是庶出的,論不到他繼位,這所謂就是“子憑母貴”了。但是事物也常常變化,比如皇后生不出兒子,要么不生,要生都是丫頭片子,那庶出的身價就大漲了,這也算正常情況,有時皇后乾脆去一般妃子那領養一個,算做自己生的。而另一種情況就是,皇后生了兒子,還被立為太子了,可幾年之後皇后死了,皇帝父親另有新歡,皇后換了人,而且新皇后還為太子生了個小弟弟,那隨著這個小弟弟的出生,那老太子的地位就危險了,這太子再怎么親還有親生兒子親嗎?此時新皇后使出百般解數來勸說皇帝,這枕頭風一動,皇帝說不定就動心了。那劉表就是中了此種招數。一代雄主漢武帝本人也非嫡長子,而是母親王美人運作得當,使其擠走栗姬和其子太子劉榮,一個做了皇后,一個做了太子。(還有一例,三國之後的晉惠帝,其太子便被賈皇后陷害,當然這有晉惠帝腦子痴呆的因素在裡面。)
其四,繼承制度里,還有一個關鍵的一條就是“立長”,這不單是指皇子,也包括了皇弟等族內親戚在內,所謂國無長君不穩定,尤其是在立國初期等特定因素下,就算有嫡長子在,但是為了國家穩定,有時還是選擇皇帝的其他年長族人,最典型的便是皇弟繼承皇位。最典型例子莫過於宋太宗了,宋太祖趙匡胤有子,但是為了國家穩定著想,還是由其弟趙匡義繼承皇位。(當然,這種事比較另類,宋太宗上台一事也疑點多多,一般來說有自己的兒子大都是自己兒子繼位,沒兒子才會在族中選擇。)
還有一種情況比較特殊,非常少見,就是這父親的位置都是兒子搶來的,比如唐睿宗能夠復位,功勞可說全靠其三子李隆基之力,唐睿宗雖然有嫡長子李成器,但是還是立李隆基為太子。(李成器也頗為識趣,主動要求放棄太子之位。)不過這種情況比較少見罷了。當然,劉邦那種開國皇帝立自己的父輩為太上皇的就不能算進去了,那否則就多了去了。
這以上說的是有子繼承的時候,那些沒兒子繼承的就不在討論範圍內了,其實嫡長子繼承制度在真實的實施中少之又少,而且大都集中在皇朝穩定的中期,而大多數皇朝在前三代往往就不是嫡長子一房來繼承皇位了。我們下面便舉例來看。
元清等少數民族政權一開始本就沒有嫡長子繼承的制度,(元朝在早期蒙古時代到是有幼子繼承制的說法,但是仔細看來還是誰的拳頭大誰就做皇帝,忽必烈建立元朝後也沒見有改進,至於清朝嘛,正式建立清這個國號的皇太極就不是長子,康熙到是立過太子,後來廢了立,立了廢,乾脆改成我們所常知道秘密立儲制度,在皇帝死之前誰也不知道下一任是誰,太子都沒,更不用說什麼嫡長子繼承制了。)他們就不用說了,我們就說漢族皇朝。
先看秦朝,秦始皇到是想要長子扶蘇繼承來著,但是被胡亥奪位,可說嫡長子繼承制一開始就沒個好頭。
第二代漢朝,劉邦又想立幼子來著,但是總算被制止了,但是好景不長,長子漢惠帝和其母呂后死後,(漢惠帝沒有兒子,一般認為那個太子是呂后指使人假冒的),周勃立了劉邦的另外一個兒子劉恆為帝,到這一代已經不是長房了。而且我們還要注意到一點,漢文帝又被稱為漢太宗,我們注意下,日後看到唐太宗,宋太宗,明太宗(明成祖原本是明太宗,後來被明世宗改為明成祖)這個太宗稱號就知道了,他們都不是正宗的第一代皇帝嫡長子那一房的,
東漢,第二代漢明帝劉莊就不是光武帝劉秀的長子,而是第四子。(劉莊這個太子位置比較曲折,他的生母陰麗華是劉秀的結髮妻子,但是劉秀在河北時又娶了郭聖通為妻,這是一個政治婚姻,等到了建武二年要立皇后了,他本來想立陰麗華為皇后,但是陰麗華推辭,最終郭聖通被立為皇后,而郭聖通的兒子劉疆也被立為太子,等到了建武十七年,劉秀把郭聖通廢了,重新立陰麗華為皇后,而到了建武十九年,原來的太子劉疆要辭職……劉秀同意了,結果劉莊成為太子,這也是一種子憑母貴吧。)
三國蜀漢只傳二代不說,東吳在上文說了,嫡長子孫登早死了,而魏文帝曹丕(曹操沒有稱帝,我們不算進去。)嫡長子曹叡繼承皇位,但是曹叡沒有子嗣,之後少帝曹芳是養子,這長房在第三代也斷了。
晉朝,晉武帝長子就是那個白痴皇帝晉惠帝,他的太子被賈后害死了,之後繼任的晉懷帝是晉武帝的兒子,不用說,長房一脈也斷了。
南北朝亂的一團糟,那就不用說了。隋朝我們上面說過,隋煬帝擺了父親一道,把皇位騙過來了。
唐朝嘛,唐高祖李淵到是想長子李建成繼位來著,但是李世民功勞太大,兩人爭位,鬧出了我們所知的玄武門之變,李世民唐太宗這個廟號掛在那,大家也早該明白了,其實說起唐朝,諸子爭位爭的最可怕,兄弟相殘常見,子殺父也不是沒有,這種情況下,想讓嫡長子繼承只怕也不容易。
五代太短,宋朝我們上文說過,太宗是皇弟即位,而且還沒把皇位還給侄子,直到到南宋高宗無後乾脆就把太祖一脈的後人收為養子,後人便是宋孝宗,不過那是多年以後的事了。
至於明朝嘛,明太祖朱元璋到是挺信奉嫡長子繼承的,長子朱標死後乾脆立長孫朱允炆繼承,就是後來的建文帝,但是也就是在這第三代上,被明成祖或者說明太宗將位奪了過去。
所以說,這嫡長子繼承制終究還只是理論而已,而要把理論變成現實,要有很長的一段路走。
回評
毛宗崗批語
管仲之有三歸,或雲是台,或雲是女。以今度之,意者管仲喜得三歸之女,而即以此名其台,未可知也。然則是台亦是女,非有兩三歸也。若銅雀之二橋則不然:曹植所欲建者,玉龍、金鳳所接之二橋;曹操所欲得者,乃孫策、周瑜所娶之二喬。橋之與喬,則有辨矣。
此回以雀始,以馬終。有曹操得雀,卻遠引舜母夢雀;有舜母夢雀,卻便有禪母夢斗。又因銅雀生出金鳳,又因金鳳生出玉龍。前有鳳與龍,後有鶴與馬。將有的盧之躍,先有白鶴之鳴。至於張武喪馬、趙雲奪馬、劉備送馬、劉表還馬、蒯越相馬、伊籍諫馬,種種波瀾,無不層折入妙,此文中佳境。
前回百忙中忽敘曹丕生時之異,此回百忙中忽敘劉禪生時之祥,皆為後日稱帝張本也。然敘曹丕於入冀州之時,是追敘已往;此敘劉禪於屯新野之日,是現敘目前,又是一樣筆敘法。
袁紹昵後妻,劉表亦昵後妻;袁紹愛幼子,劉表亦愛幼子;袁紹優柔不斷,劉表亦優柔不斷;二人性情何其相似至於如此之甚也!一則以家世自矜,大而無當;一則以虛名自愛,文而無用:雖冑美三公,名高八俊,亦何益哉!然劉表亦有過於袁紹者:紹以逢紀之譖而殺田豐,表不以蔡瑁之譖而殺玄德;畢竟聲望中人,猶較勝於閥閱中人。
曹操攻冀州之時,備不勤表襲許都;至操擊烏桓之時,備乃勤表襲許都:其故何也?從冀州回救許都也近,近則不可襲;從烏桓回救許都也遠,遠則可襲:勢不同也。且有不救袁譚以示怯於前,操必輕表而不設備;乘其不備而襲之,此所謂始如處女,後若脫兔,真兵家之妙算也。劉表不用備言,失此機會,可勝嘆哉!
蔡夫人從屏風后竊聽,大是怕人,玄德襄陽赴會,幾乎喪命,皆此一聽所致。不獨景升害怕,玄德亦當害怕;不獨玄德害怕,即讀者至此亦為之寒心咋舌也。今日懼內之家,多有此風。凡賓客至堂中敘話者,切宜仔細,不可妄言,恐驚動屏風后竊聽之人,不是耍處。
天下怕老婆之人,未有不緣於愛老婆者也。愛極生怕,怕則不敢,愛則不忍。不忍與不敢之心合,而於是妻之旨不可違,妻之鋒不可犯,而妻黨之權遂牢固而不可破矣。雖然,今天下豈少劉景升哉!笑景升者復為景升,吾正恐景升笑人耳。
光武過滹沱之馬,安行水上;昭烈過檀溪之馬,幾陷水中。李世民過澗之馬,卻有三跪;劉玄德過溪之馬,只是一躍。金太祖混同江之馬,按轡而行;劉先主檀溪之馬,超越而過。宋高宗渡江之馬,死馬當活馬騎;漢昭烈過溪之馬,劣馬作神馬用。讀書至此,真千古奇觀。
范增欲殺沛公,而項羽不忍;蔡瑁欲殺玄德,而劉表不忍。然鴻門之宴,項羽在,故范增不能為政;襄陽之宴,劉表不在,則蔡瑁為政:由此言之,襄陽一會,其更險於鴻門哉!
李贄總評
的盧妨主,其言甚驗。畢竟劉表是主,救玄德而去,非妨劉表而何?余之註腳的盧者如此,聊發讀者一笑而已。
但看蔡夫人及其弟蔡瑁,乃見婦人,小人得陰氣偏多,偏與君於為難也。吁!人亦徒為婦人,徒為小人耳,何妨於君子乎哉!何妨於君子乎哉!
鍾敬伯總評
人言的盧妨主,余觀玄德英主檀溪逃難,此馬一躍三丈,飛上西岸,的盧不啻千里龍駒,能救主耳,誰雲妨主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