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
救壽春於詮死節 取長城伯約鏖兵
簡介
諸葛誕戰敗而亡,吳將降魏者多,敗兵放回。
姜維又欲伐魏,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一篇,勸阻姜維,維不聽。
姜維先大勝,後被鄧氏父子與關中兵三面夾擊;又傳東吳兵敗,姜維只得退兵。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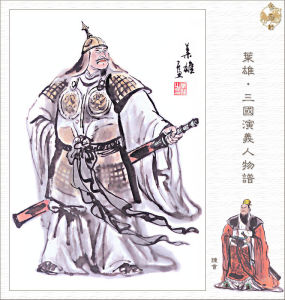 鍾會
鍾會卻說司馬昭聞諸葛誕會合吳兵前來決戰,乃召散騎長史裴秀、黃門侍郎鍾會,商議破敵之策。鍾會曰:“吳兵之助諸葛誕,實為利也;以利誘之,則必勝矣。”昭從其言,遂令石苞、州泰先引兩軍於石頭城埋伏,王基、陳騫領精兵在後,卻令偏將成倅引兵數萬先去誘敵;又令陳俊引車仗牛馬驢騾,裝載賞軍之物,四面聚集於陣中,如敵來則棄之。
是日,諸葛誕令吳將朱異在左,文欽在右,見魏陣中人馬不整,誕乃大驅士馬徑進。成倅退走,誕驅兵掩殺,見牛馬驢騾,遍滿郊野;南兵爭取,無心戀戰。忽然一聲炮響,兩路兵殺來:左有石苞,右有州泰,誕大驚,急欲退時,王基、陳騫精兵殺到。誕兵大敗。司馬昭又引兵接應。誕引敗兵奔入壽春,閉門堅守。昭令兵四面圍困,並力攻城。
時吳兵退屯安豐,魏主車駕駐於項城。鍾會曰:“今諸葛誕雖敗,壽春城中糧草尚多,更有吳兵屯安豐以為掎角之勢;今吾兵四面攻圍,彼緩則堅守,急則死戰;吳兵或乘勢夾攻:吾軍無益。不如三面攻之,留南門大路,容賊自走;走而擊之,可全勝也。吳兵遠來,糧必不繼;我引輕騎抄在其後,可不戰而自破矣。”昭撫會背曰:“君真吾之子房也!”遂令王基撤退南門之兵。卻說吳兵屯於安豐,孫綝喚朱異責之曰:“量一壽春城不能救,安可併吞中原?如再不勝必斬!”朱異乃回本寨商議。於詮曰:“今壽春南門不圍,某願領一軍從南門入去,助諸葛誕守城。將軍與魏兵挑戰,我卻從城中殺出:兩路夾攻,魏兵可破矣。”異然其言。於是全懌、全端、文欽等,皆願入城。遂同於詮引兵一萬,從南門而入城。魏兵不得將令,未敢輕敵,任吳兵入城,乃報知司馬昭。昭曰:“此欲與朱異內外夾攻,以破我軍也。”乃召王基、陳騫分付曰:“汝可引五千兵截斷朱異來路,從背後擊之。”二人領命而去。朱異正引兵來,忽背後喊聲大震:左有王基,右有陳騫,兩路軍殺來。吳兵大敗。朱異回見孫綝,綝大怒曰:“累敗之將,要汝何用!”叱武士推出斬之。又責全端子全禕曰:“若退不得魏兵,汝父子休來見我!”於是孫綝自回建業去了。
鍾會與昭曰:“今孫綝退去,外無救兵,城可圍矣。”昭從之,遂催軍攻圍。全禕引兵欲入壽春,見魏兵勢大,尋思進退無路,遂降司馬昭。昭加禕為偏將軍。禕感昭恩德,乃修家書與父全端,叔全懌,言孫綝不仁,不若降魏,將書射入城中。懌得禕書,遂與端引數千人開門出降。諸葛誕在城中憂悶,謀士蔣班、焦彝進言曰:“城中糧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吳、楚之眾,與魏兵決一死戰。”誕大怒曰:“吾欲守,汝欲戰,莫非有異心乎!再言必斬!”二人仰天長嘆曰:“誕將亡矣!我等不如早降,免至一死!”是夜二更時分,蔣、焦二人逾城降魏,司馬昭重用之。因此城中雖有敢戰之士,不敢言戰。誕在城中,見魏兵四下築起土城以防淮水,只望水泛,衝倒土城,驅兵擊之。不想自秋至冬,並無霖雨,淮水不泛。城中看看糧盡,文欽在小城內與二子堅守,見軍士漸漸餓倒,只得來告誕曰:“糧皆盡絕,軍士餓損,不如將北方之兵盡放出城,以省其食。”誕大怒曰:“汝教我盡去北軍,欲謀我耶?”叱左右推出斬之。文鴦、文虎見父被殺,各拔短刀,立殺數十人,飛身上城,一躍而下,越壕赴魏寨投降。司馬昭恨文鴦昔日單騎退兵之仇,欲斬之。鍾會諫曰:“罪在文欽,今文欽已亡,二子勢窮來歸,若殺降將,是堅城內人之心也。”昭從之,遂召文鴦、文虎入帳,用好言撫慰,賜駿馬錦衣,加為偏將軍,封關內侯。二子拜謝,上馬繞城大叫曰:“我二人蒙大將軍赦罪賜爵,汝等何不早降!”城內人聞言,皆計議曰:“文鴦乃司馬氏仇人,尚且重用,何況我等乎?”於是皆欲投降。諸葛誕聞之大怒,日夜自來巡城。以殺為威。
鍾會知城中人心已變,乃入帳告昭曰:“可乘此時攻城矣。”昭大喜,遂激三軍,四面雲集,一齊攻打。守將曾宣獻了北門,放魏兵入城。誕知魏兵已入;慌引麾下數百人,自城中小路突出;至吊橋邊,正撞著胡奮,手起刀落,斬誕於馬下,數百人皆被縛。王基引兵殺到西門,正遇吳將於詮。基大喝曰:“何不早降!”詮大怒曰:“受命而出,為人救難,既不能救,又降他人,義所不為也!”乃擲盔於地,大呼曰:“人生在世,得死於戰場者,幸耳!”急揮刀死戰三十餘合,人困馬乏,為亂軍所殺。後人有詩讚曰:“司馬當年圍壽春,降兵無數拜車塵。東吳雖有英雄士,誰及於詮肯殺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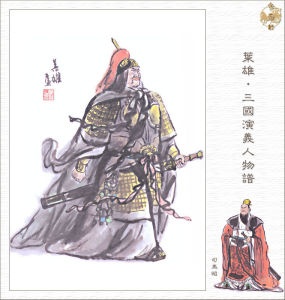 司馬昭
司馬昭司馬昭入壽春,將諸葛誕老小盡皆梟首,滅其三族。武士將所擒諸葛誕部卒數百人縛至。昭曰:“汝等降否?”眾皆大叫曰:“願與諸葛公同死,決不降汝!”昭大怒,叱武士盡縛於城外,逐一問曰:“降者免死。”並無一人言降。直殺至盡,終無一人降者。昭深加嘆息不已,令皆埋之。後人有詩讚曰:“忠臣矢志不偷生,諸葛公休帳下兵,《薤露》歌聲應未斷,遺蹤直欲繼田橫!”
卻說吳兵大半降魏,裴秀告司馬昭曰:“吳兵老小,盡在東南江、淮之地,今若留之,久必為變;不如坑之。”鍾會曰:“不然。古之用兵者,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若盡坑之,是不仁也。不如放歸江南,以顯中國之寬大。”昭曰:“此妙論也。”遂將吳兵盡皆放歸本國。唐咨因懼孫綝,不敢回國,亦來降魏。昭皆重用,令分布三河之地。淮南已平。正欲退兵,忽報西蜀姜維引兵來取長城,邀截糧草。昭大驚,慌與多官計議退兵之策。時蜀漢延熙二十年,改為景耀元年。姜維在漢中,選川將兩員,每日操練人馬:一是蔣舒,一是傅僉。二人頗有膽勇,維甚愛之。忽報淮南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東吳孫綝助之,昭大起兩都之兵,將魏太后並魏主一同出征去了。維大喜曰:“吾今番大事濟矣!”遂表奏後主,願興兵伐魏。中散大夫譙周聽知,嘆曰:“近來朝廷溺於酒色,信任中貴黃皓,不理國事,只圖歡樂;伯約累欲征伐,不恤軍士:國將危矣!”乃作《仇國論》一篇,寄與姜維。維拆封視之。論曰:“或問:古往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曰:處大國無患者,恆多慢;處小國有憂者,恆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恤眾,以弱斃強。此其術也。或曰:曩者楚強漢弱,約分鴻溝,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句踐之事乎?曰:商、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當此之時,雖有漢祖,安能仗劍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傑並爭。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不幸遇難,雖有智者,不能謀之矣。”姜維看畢,大怒曰:“此腐儒之論也!”擲之於地,遂提川兵來取中原。乃問傅僉曰:“以公度之,可出何地?”僉曰:“魏屯糧草,皆在長城;今可逕取駱谷,度沈嶺,直到長城,先燒糧草,然後直取秦川,則中原指日可得矣。”維曰:“公之見與吾計暗合也。”即提兵逕取駱谷,度沈嶺,望長城而來。
卻說長城鎮守將軍司馬望,乃司馬昭之族兄也。城內糧草甚多,人馬卻少。望聽知蜀兵到,急與王真、李鵬二將,引兵離城二十里下寨。次日,蜀兵來到,望引二將出陣。姜維出馬,指望而言曰:“今司馬昭遷主于軍中,必有李傕、郭汜之意也,吾今奉朝廷明命,前來問罪,汝當早降。若還愚迷,全家誅戮!”望大聲而答曰:“汝等無禮,數犯上國,如不早退,令汝片甲不歸!”言未畢,望背後王真挺槍出馬,蜀陣中傅僉出迎。戰不十合,僉賣個破綻,王真便挺槍來刺;傅僉閃過,活捉真於馬上,便回本陣。李鵬大怒,縱馬輪刀來救。僉故意放慢,等李鵬將近,努力擲真於地,暗掣四楞鐵簡在手;鵬趕上舉刀待砍,傅僉偷身回顧,向李鵬面門只一簡,打得眼珠迸出,死於馬下。王真被蜀軍亂槍刺死。姜維驅兵大進。司馬望棄寨入城,閉門不出。維下令曰:“軍士今夜且歇一宿,以養銳氣。來日須要入城。”次日平明,蜀兵爭先大進,一擁至城下,用火箭火炮打入城中。城上草屋一派燒著,魏兵自亂。維又令人取乾柴堆滿城下,一齊放火,烈焰沖天。城已將陷,魏兵在城內嚎啕痛哭,聲聞四野。
正攻打之間,忽然背後喊聲大震。維勒馬回看,只見魏兵鼓譟搖旗,浩浩而來。維遂令後隊為前隊,自立於門旗下候之。只見魏陣中一小將,全裝慣帶,挺槍縱馬而出,約年二十餘歲,面如傅粉,唇似抹朱,厲聲大叫曰:“認得鄧將軍否!”維自思曰:“此必是鄧艾矣。”挺槍縱馬來迎。二人抖擻精神,戰到三四十合,不分勝負。那小將軍槍法無半點放閒。維心中自思:“不用此計,安得勝乎?”便撥馬望左邊山路中而走。那小將驟馬追來,維掛住了鋼槍,暗取雕弓羽箭射之。那小將眼乖,早已見了,弓弦響處,把身望前一倒,放過羽箭。維回頭看時,小將已到,挺槍來刺;維一閃,那槍從肋傍邊過,被維挾住。那小將棄槍,望本陣而走。維嗟嘆曰:“可惜!可惜!”再撥馬趕來。追至陣門前,一將提刀而出曰:“姜維匹夫,勿趕吾兒!鄧艾在此!”維大驚。原來小將乃艾之子鄧忠也。維暗暗稱奇;欲戰鄧艾,又恐馬乏,乃虛指艾曰:“吾今日識汝父子也。各且收兵,來日決戰。”艾見戰場不利,亦勒馬應曰:“既如此,各自收兵,暗算者非丈夫也。”於是兩軍皆退。鄧艾據渭水下寨,姜維跨兩山安營。艾見了蜀兵地理,乃作書於司馬望曰:“我等切不可戰,只宜固守。待關中兵至時,蜀兵糧草皆盡,三面攻之,無不勝也。今遣長子鄧忠相助守城。”一面差人於司馬昭處求救。
卻說姜維令人於艾寨中下戰書,約來日大戰,艾佯應之。次日五更,維令三軍造飯,平明布陣等候。艾營中偃旗息鼓,卻如無人之狀。維至晚方回。次日又令人下戰書,責以失期之罪。艾以酒食待使,答曰:“微軀小疾,有誤相持,明日會戰。”次日,維又引兵來,艾仍前不出。如此五六番。傅僉謂維曰:“此必有謀也,宜防之。”維曰:“此必捱關中兵到,三面擊我耳。吾今令人持書與東吳孫綝,使併力攻之。”忽探馬報說:“司馬昭攻打壽春,殺了諸葛誕,吳兵皆降。昭班師回洛陽。便欲引兵來救長城。”維大驚曰:“今番伐魏,又成畫餅矣,不如且回。”正是:已嘆四番難奏績,又嗟五度未成功。
未知如何退兵,且看下文分解。
賞析
三國之中哪一個家族最強,有一個說法是諸葛家族,確實也有道理,諸葛亮在蜀漢一代名相,諸葛恪在東吳也一度權傾朝野,這兩人是叔侄兩,諸葛恪的弟弟還一度過繼給諸葛亮。而本回演義說到的諸葛誕其實和諸葛亮諸葛恪也算是一族的,雖然沒那么近的血緣,但是也是諸葛豐之後,他沒有諸葛亮諸葛恪那樣的權力,但是權力也算不得小,在曹魏也做到了征東大將軍,統領揚州一帶,封疆大吏。諸葛家族在三國都擁有如此的權力,考慮到當時天下三分,諸葛家族確實不凡。
只是諸葛家族的結局不是很好,諸葛恪被孫峻所殺,在東吳的諸葛謹家族都被屠盡,過繼給諸葛亮的諸葛喬之子諸葛攀又重新回到諸葛謹一族。諸葛亮一系大家應該比較清晰,諸葛亮之子諸葛瞻和長子諸葛尚戰死,諸葛瞻次子諸葛京遷移到河東,在東晉為官,至於諸葛誕,三族被夷,不過送到東吳的人質諸葛靚活了下來,後來東吳被滅,諸葛靚東躲西藏,後來還是被司馬炎找到,司馬炎與其是好友,赦免了他。其後人諸葛恢在東晉時為官。
這樣看來諸葛家族都算不得什麼好的,在東吳曹魏的兩家都被自己所在朝廷滅族,諸葛亮這一家雖然不算滅族,但是亡國也算不得好。而且真要說三國那大家族的話,還應該是那三家,劉曹孫,這三大皇族自然是毫無疑問的大家族,自然,最後的勝利者不用說還是司馬家了。
確實,自古以來,說到大家族,那些能夠最終稱帝建業的才都是真正的大家族。那些原本就以家族為核心從而問鼎江山的自不用說,如魏國之曹家,晉朝司馬家,唐朝李家,那些少數民族政權更不用說,都是以家族為核心的,以一己之身成就霸業如劉邦朱元璋等人在其建立皇朝幾代後也建立了龐大的家族。我們常說封建王朝一家一姓治天下,這說的不是那皇帝一人,而是包括了整個皇族。
為什麼要以家族治理天下,這是因為個人力量的限制,而古代社會,以血緣為基礎的家族力量組織力和凝聚力最強,所以不得不利用家族的力量來控制。不單中國如此,西方也是如此。就說古羅馬吧,在共和國時期其實就是少數幾個家族共同統治的時期,我們假如去看那些古羅馬的名人傳記,就會常看到一句,我是某某家族的某某,我們家族是某某的英雄的子孫等等,到了後來,這不單沒有減少,反而更加誇張,中世紀的貴族追求血統,以家族為耀,這點和中國沒有什麼區別,或者說,整個世界都是如此。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家族,是古代的重要力量,在農業或者遊牧這種古代社會,無論是生產還是作戰,都要求著人多就是力量,個體難以生存,人類往往尋求集體的生存模式,而在集體生存中,結親等方式將個體聯絡在一起,而這種血緣或者婚姻為紐帶的家族最能適應古代社會的要求,東西方的家族制度正是迎合了古代社會這種要求,將其完善化,而在此基礎之上,再度形成帝王制度。等到現代社會,家庭的力量日漸淡化,原先的那種大家族越來越少見,不單個人的家庭獨立出來,個人在工業化大協作的背景之下也漸漸可以獨立在家庭之外,家族這種組織模式被新的組織模式取代,在這種情況之下,古代宗法制度瓦解,古代社會也隨之瓦解。
當然,取代這只是說說,實際上家族的力量只能說比古代弱小,而新興了許多新的組織模式,但是家族還是依然存在,只是沒有往日那般強大罷了。
那一個家族是如何形成的呢?當然,生育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並不是有了生育和有了姓氏就可以了結的,尤其是那些被世人公認的大家族,是要有一定條件才行的,我們這裡就說說那些名聲顯赫的大家族形成的基本要求。
其一:始祖:這是肯定要的,當然,有說法,人類的祖先都是一個猴子,這個問題且不說是不是一個猴子,便就是一個,那時候誰知道這猴子姓啥?所以到文字產生前,這始祖沒辦法找。要找,只能從文字出現後開始早,最老牌的家族那不用說了,不是神仙就是英雄。炎黃子孫那就不說了,我們都是一個疙瘩里出來的沒辦法分,但是堯舜禹三代就產生各自的後人了,比如袁術稱帝時就說自己家這個袁是出自陳,而這個陳呢,是舜的子孫,這圈子繞的夠大的,不管怎么說吧,總是套到了舜老的頭上。再比如說匈奴吧,太史公老人家就說他們是夏後氏之苗裔,把圈子套到了大禹的頭上。反正吧,總是要從當年幾位神話也好,傳說也好,歷史也好,那幾位英雄人物的頭上套一個。這點其他國家也不例外,埃及法老就硬說自己是神的子孫,西方嘛,傳說中那些早期英雄都是半神,也就神的兒子,稍微近一點的就是半神的兒子,再近點的就是英雄的兒子,也就是神的孫子或者曾孫一類。總之一句話,都喜歡和早期大牌結親。
當然,這些傳說中的人太多了,比如我是炎黃子孫,你也是啊,那不好分,尤其是顯赫家族,按這樣分和一般家族肯定也是一樣的,怎么能顯出身份,那既然老祖宗是共同的,我們就找近一點的,這裡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當初改名的時候,打個比方,我原來是姓黃的,後來分家出來我改姓趙了,那我的子孫也全部改姓,那我就是趙家的始祖。(當然,這不是說趙家是從黃家分出來的,只是比方而已,其實姬姓後來改成其他姓的數量相當多。)但是,這也有問題,一來也有原來不同姓的後來改成一個姓撞車的事件發生,這點就顯出始祖的重要性了,但是另一點始祖也沒辦法解決啊,就是歷史一長,就算改姓分支也多了,這支分支和那支分支差別也很大,這個問題我們放在下面說,我們再說另一種情況:就是之前家道中落或者肯定沒中落的機會,一直就很窮,那始祖不可考,當然,也有些人隨便找了同姓的就認祖宗了,比如唐朝李家就找了老子當祖宗,還有就是象朱元璋這樣的,自己雙親早亡,還都是窮光蛋,怎么找始祖去,於是乾脆就把能想到哪代就哪代,實際上是自己當了始祖了。再好象劉邦也是一樣,劉姓當時有幾個分支,劉邦自己也不知道屬於哪個,所以現在實際上大多數把劉邦當作始祖了。當然劉邦朱元璋之上還有幾代是可考的,但是誰也不會記得那幾位是誰,這就涉及第二個要求。
其二:顯赫之身份:我們前面說劉邦和朱元璋實際上被當作了始祖,當然按規矩不是這樣的,但是考慮到他們的身份和對之後自己姓氏的影響,稱之為始祖並不委過,沒有這兩位,就沒有劉邦一系劉家和朱元璋一系的朱家的顯赫家史了。
因為一個家族興起,貢獻者除了當年起家族之姓的那位始祖外,便就是為家族立大功勞的人,所謂光大門楣,就是這個意思,能不能成為大家族,不看始祖,而看那位光大門楣的。當然也有幾位是當初連姓都沒的那是兩者的身份一肩挑了。這種大功勞是什麼呢?自然是身份,比如當了皇帝了,那是多大的功勞啊,皇族子弟的身份地位可不是一般的貴族可比的,尤其是皇族就意味著可以做一國之君,其他家族再顯赫也就是臣子而已。當然,這皇帝也沒幾個姓做過,多數還是做臣子的,這做臣子的也要等級,象東晉時期士族勢力為什麼這么清高強盛,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當時的幾個家族可以與皇帝平起平坐了,王家不用說了,王與馬,共天下嘛,雖然沒做皇帝,這和皇帝也差不多。有這樣的地位自然可以傲視其他家族了。謝家淝水一戰定東晉江山,其地位也與王家差不多。這些名門望族,是要靠權力,地位威望來撐門面的,一旦失去了這些,隨著時間的推移,身份也會下降了。
其三:歷史,儘管有身份,但是若是維持不下去,也稱不得名門,算不上望族,只能算暴發戶而已,一世而盛,一世而衰,人們更只會說這個是失敗者,連暴發戶都算不上了。要成為名門望族,一定要有相當長的顯赫歷史,不是有句話嗎?叫“富不過三代”,這是說保持富裕的難度,權力也一樣,權力變遷十分之快,今日你為一國之首,明日你的子孫就可能成為階下囚。但是當你度過了權力的高危期,比如維持三代以上的興盛或者平穩,比如形容袁紹家族的四世三公吧。那就證明著你們家族長期以來掌握了極大的權力,這時你的家族就已經成為了名門望族。這需要著歷史的沉澱了。王導當初覺得自己的家族勢力很大了,就和諸葛誕的後人諸葛恢開玩笑,說“人言王葛,不言葛王”,其言下之意,王家比諸葛家地位高了,但是被諸葛恢回了一句“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拋開兩人開玩笑的角度不說,諸葛恢說的也不錯,王導一系的王家單純從歷史上也遠不能和諸葛家比,不說漢代時期,(當然,兩家在漢代都算不得超級豪門)王家真正起家的王祥出仕時諸葛家族正在三國扮演主角呢,魏晉的另一個太原王家也遠比王導這一系威風得多。不客氣的說,王導這一家能在東晉興起,和八王之亂時期老牌家族死光大有干係。諸葛家族比王家早了幾年,自然有資格看王家不起,那其他家族也是一樣的,看權位,看歷史,名門需要歷史和權位為自己增添光彩。也和那些新興的家族保持距離。李唐這個家族也算是顯赫了吧,結果照樣被崔家那些老牌士族看不起。
其實,便是這些老牌世家,也熬不過時間的磨練,那些世家大族們,其實也就是最多幾百年而已。便沒有日後的戰亂,這些世族也會因為自身的腐敗墮落而消亡,由其他家族取而代之。便如皇朝更替一樣,世間沒有不落的太陽,自然也不會有永興不落的家族。
回評
毛宗崗批語
諸葛恪之進兵於新城,魏無釁之可窺;若孫綝之進兵於壽春,則乘魏之釁而動矣。毋丘儉之討司馬昭,猶懼吳之襲其後;若諸葛誕之討司馬昭,則吳且為之援矣。綝之事易於恪,誕之事易於儉,而迄無成功者,是綝之才不如恪,誕之才亦不如儉也。然吳有不降賊之將,則於詮一人為忠臣;魏有不降賊之兵,則諸葛誕數百人皆義士。君子謂吳之一人,可以愧吳之眾人;而誕之數百人,愈以重誕之一人云。
“威克厥愛”,為將之道固然,而用法太嚴,御人太酷,又必敗之理也。朱異不殺,則吳將不至離心;文欽不誅,則魏將不至解體。讀書至此,可為嚴酷之戒。
曹操築土城於潼關之西,地高而無水患;司馬昭築土城於淮水之南,地卑而有水患。無水患,則城難墮;有水患,則城易墮也。而天雨不降,淮水不發。與壽春相拒數月,而曾不得上方谷一日之雨;以淮河之勢,而曾不及鐵籠山一井之漲溢。此實天意,豈人事哉!此譙周《仇國論》之所作也。
譙周《仇國論》,不過以成敗利鈍為言耳。其不作於武侯伐魏之時,而作於姜維伐魏之時者,蓋武侯“非所逆睹”一語,已足以破之矣。使人盡明哲,孰竭愚忠?使人盡知天,孰盡人事?故後世人臣有報國之志者,願讀《出師表》,不願讀《仇國論》。
聞魏之釁而起,聞吳之敗而止,此姜維五伐中原之師,所以一出而即返。前於三伐、四伐之時,魏軍中早有一鄧艾為之設謀,為之畫策,而維與艾尚未識面;直至此回,而又先見其子,後見其父。及既見之後,而又略戰而退,未及大決雌雄。其事之紆徐,文之曲折如此。讀書至此,又樂得而觀其後矣。
李贄總評
諸葛公休,又一諸葛恪也,何諸葛之多人也,想為孔明拔盡秀氣耶?一笑一笑。
讀演義至此,惟有打頓而已,何也?只因前面都已說過,不過改換姓名重疊敷演雲耳,真可厭也l此其所以為《三國志演義》耳。一笑,一笑。
鍾敬伯總評
後主此時病已在腹心,伯約累欲遠征,恢復中原,忠義使之也。然天命已去,人力無如之何,吾於伯約何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