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劉亮程
劉亮程個人影響
 劉亮程
劉亮程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於1998年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後,引起了新疆文壇的熱切關注,多位評論家先後撰文對其創作進行研討。接著,1999年10月,在國內文學界享有盛譽的《天涯》雜誌的頭題位置刊發了“劉亮程散文專輯”,並配發了李銳、李陀、方方、南帆、蔣子丹等著名評論家、作家的推薦文章。一時間,國內文學界為之譁然。湖北《今日名流》雜誌隨即對劉亮程做了長篇專訪;中央電視台“讀書時間”以“劉亮程和他的村莊”為題對其作了專訪;《書評周刊》、《作家文摘》、《新華文摘》、《江南》等報刊也紛紛轉載刊發劉亮程的散文及評論文章;在新疆壓庫1年多的數千冊劉亮程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也在一個月里被訂購一空。2001年4月獲得“第二屆馮牧文學獎”文學新人獎。被譽20世紀最後的文學景觀。
作品目錄
《一個人的村莊》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12-20ISBN:9787210096085
《在新疆》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12-20ISBN:9787210096115
《虛土》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12-20ISBN:9787210096399
《一片葉子下生活》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5-5ISBN:9787020125159
《在新疆》春風文藝出版社2012-2-1ISBN:9787531341222
《劉亮程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2011-7-1ISBN:9787530659335
《遙遠的村莊:劉亮程散文精讀》(劉亮程原著,黃榮華編注)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1-1ISBN:9787309062090
《鑿空》作家出版社2010-4-1ISBN:9787506352864
《劉亮程散文(下)——博格達文學叢書》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9-1ISBN:9787228128358
《劉亮程散文(上)——博格達文學叢書》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9-1ISBN:9787228128341
《風把人刮歪》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8-09ISBN:9787537139878
《遙遠的村莊》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8ISBN:9787309062090
《遙遠的村莊:劉亮程散文精讀》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8-1ISBN:9787309062090
《杏花龜茲》(與張國領合作編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12-1ISBN:9787228112425
《曬曬黃沙梁的太陽》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7-04-24ISBN:7537121036
《驢車上的龜茲》春風文藝出版社2007-01-01ISBN:9787531331490
《一個人的村莊》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1-1ISBN:9787531329329
《虛土》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1-1ISBN:9787531329503
《天邊塵土》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10-28ISBN:9787221070494
《庫車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1-1ISBN:9787543449794
《風中的院門》山東文藝出版社2002-10-01ISBN:9787532920297
《站在黃沙梁邊上》山東文藝出版社2002-10-01ISBN:9787532920297
《正午田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8-1ISBN:9787222032590
《一個人的村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4-1ISBN:9787228046478
獲得榮譽
2001年2月獲“第二屆馮牧文學獎”文學新人獎。
2014年3月《新疆無傳奇》獲得“2013年度華文最佳散文獎。
2014年8月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散文雜文獎。
2015年6月獲“第十六屆百花文學獎”散文獎。
人物評價
 劉亮程
劉亮程真是很少讀到這么樸素、沉靜而又博大、豐富的文字了。我真是很驚訝作者是怎么在黃沙滾滾的曠野里,同時獲得里對生命和語言如此深刻的體驗。在這片垃圾遍地、精神腐敗、互相複製的沙漠上,談到農民劉亮程的這組散文,真有來到綠洲的喜悅和安慰。——李銳
劉亮程的才能在於,他好像能把文字放到一條清亮透明的小河裡淘洗一番,洗得每個字都乾乾淨淨,但洗淨鉛華的文字里又有一種厚重。捧在手裡掂一掂,每個字都重得好像要脫手。——李陀
身邊小事皆可入文,村中動靜皆可成詩,散文中透出的那種從容優雅的自信,是多少現代人已經久違了、陌生了、熬長了黑夜搔短了白頭也找不回的才華。這當然是一種哲學,是發現的哲學,是悲懷和樂世的哲學,是生命體大徹大悟頂天立地的哲學。——蔣子丹
作品簡介
擺在我面前的是劉亮程的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劉亮程不同於其他作家所寫農村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他不是站在一邊以“體驗生活”的作家的身份來寫,而是寫他自己的村莊,他眼中的、心中的、生於斯長於斯、亦必葬於斯的這一方土地。這就是《一個人的村莊》之命題和立意所在吧。
 劉亮程
劉亮程“我在草中睡著,我的身體成了眾多小蟲子的溫暖穴巢。”在《與蟲共眠》中,你會體會到村莊中人與蟲子的那種感情。“一年一年地聽著蟲鳴,使我感到小蟲子的永恆。而我,還在世上苦度著最後十幾個春秋。面朝黃土,沒有叫聲。”這樣的釋懷,便是“鄉村哲學”的一種了。
寫人的篇章就更深刻了。《寒風吹徹》寫的是西部村莊的寒冷。“一野的寒風吹著我一個人,好像寒冷把其他一切都收拾掉了,現在全部地對付我。”劉亮程的散文中充滿這類詩一樣的語言,他是一位從詩轉向散文的作家,因此,哲學思維能與詩性智慧相交織,形成他散文中特有的深厚與詩美素質。在這篇作品中,寫到他曾將一位老人領回家中,以爐火溫暖了他。但第二天還是發現那位老人已凍死在路邊的荒野中。“落在一個人一生中的雪,我們不能全部都看見。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獨地過冬。我們幫不了誰。我的這一爐火,對這個寒冷一生的人來說,顯然微不足道。他的寒冷太巨大。”“我知道這一時刻之外,我其餘的歲月,我的親人們的歲月,遠在屋外的大雪中被寒風吹徹。”
劉亮程曾獲第二屆馮牧文學新人獎,在獲獎評語中有言:“他的語言素淡、明澈,充滿欣悅感和表達事物的微妙肌理,展現了漢語獨特的純真和瑰麗。”這當然是對的,然而同時我感到“欣悅感”之外,還有一種悟透人生的深邃與悲涼,而這後者,是尤為感人的。
作品解讀
劉亮程的意義
平心而論,讀劉亮程《城市牛哞》,內心深處所受到的震撼是無以言表的。作為散文界的一個異類人物,劉亮程以其對“人畜共居”的鄉村生活的獨特思考以及詩意化的藝術表達,給了讀者全新的“陌生化”的審美體驗。馮牧文學獎評審會對其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有如下的評價:“劉亮程的寫作賡續著中國悠久燦爛的散文傳統。他單純而豐饒的生命體驗來自村莊和田野,以中國農民在蒼茫大地上的生死哀榮,莊嚴地揭示了民族生活中素樸的真理,在對日常歲月的詩意感悟中通向‘人的本來’。他的語言素淡、明澈,充滿欣悅感和表達事物的微妙肌理,展現了漢語所獨具的純真與瑰麗。”應該說,這種充滿學理的評價是恰如其分的,並非如他人所認為的是過譽之詞。
劉亮程散文作品的數量並不很多,筆者在對所能尋覓到的劉亮程的所有散文作品的反覆閱讀的過程中,逐漸形成這樣一個粗淺的體會:劉亮程散文的出場意義,不僅僅是一種對鄉村生活的人道解讀之後所呈現出的素樸清新的美學個性,而是以其獨到的鄉村生活的心靈體驗,以一種滿蘊詩意的文化銳角、心靈思考的形而上的高度以及散文與詩歌在深層次的精神層面上的溝通與榫合,從而真正實現了散文文本對激情的渴望與審美的回歸的本質要求。這無疑是對90年代貌似繁榮、實為平庸的機械複製式的散文創作的總體現狀,實現了一次強勁的反撥。在經歷了80年代中後期“小女人散文”對現實生活尋常瑣事的世俗甜膩表現的虛妄,以及“文化大散文”濫觴於“審智”的沉重而失卻散文本體“詩性”意義的描述的所引發的心靈孤寂之後,劉亮程散文適時地填補了人們閱讀視野的單一與蒼白,並以一種寂寞而又遼遠的聲音喚醒了我們業已沉睡已久的心靈。
《城市牛哞》是劉亮程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中的重頭作品,也是在不同的讀者在解讀的過程中歧見紛出的作品。有論者認為劉亮程是“萬物有靈論者”,“信奉佛家悲憫萬物的世界觀”,也有論者認為是“對城市文明的詛咒”和“對城市工業化的厭惡”等等。筆者認為,其實這些觀點都侷促於認識的單一層面,是過多的流連於散文文本表現內容的道德評判後產生的偏狹認識。作家所希冀獲得的,並非是都市與鄉村、讚美與批評等傳統的二元對立,而是以一種高貴而又包容的生存俯瞰,表達對人間不平與歷史蹂躪的深切關注,進而表達對一切生命尊嚴的維護與精神自由的強烈渴望。而這一切也正好是尋常人在世俗生活的庸碌與無奈中常常乏失的內涵,因此顯得彌足珍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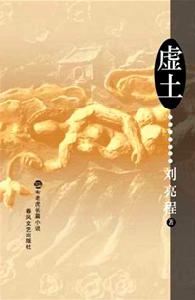 劉亮程
劉亮程接下來的幾段文字是本篇中最動人心魄的。作家自述有一次在街上看到從鄉下運來的一卡車牛,“並排橫站在車廂里,像一群沒買到坐票的乘客,東張西望,目光天真而好奇。”擬人化的對牛之情態的描摹,伴隨了主體的想像,“雜糅了悲劇與黑色幽默式的喜劇”,表達了“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生命歷程、一種因天真無知而愈顯悲壯的集體命運。”(於君《散文講稿》,群言出版社2003年1月版)惟其如此,當聽到“熟悉的一聲牛哞”,看見“一車牛的眼睛齊刷刷盯住了我”,感覺到牛認出我的農民身份,而且似乎聽到了它們對自己的“議論”的時候,作家驚竦之餘“羞愧得抬起頭”的情感才顯得尤為的沉痛與真誠。作家由此感慨萬千:“牛隻是作為肉和皮子被運進城裡。一頭牛從宰殺到骨肉被分食,這段時間體現了一個城市的胃口和消化速度。早晨還活蹦亂跳的一頭牛,中午已擺上市民的餐桌,進入腸胃轉化成熱量與情慾。”一頭牛見證了一個城市世俗意義上的日常生活,也揭開了城市文明的背後所隱藏著的殘酷的現實本質,這與“人畜共居的村莊”中“不是人跟著牲口走便是牲口跟著人走”的和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更令人心悸的是下面的一段超越現實層面的想像文字:
牛會不會在屠刀搭在脖子上時還做著這樣的美夢呢?我是從裝滿牛的車廂里跳出來的那一個。是沖斷韁繩跑掉的那一個。是掙脫屠刀昂著鮮紅的血脖子遠走他鄉的那一個。
林賢治先生在《九十年代最後一位散文家》一文中曾有如下一段感性評價:“這是狂哞,是撕心裂肺的聲音。驚恐、憤怒、決絕,整個文壇聽不到這種聲音。沒有一個來自鄉土的作家,能夠如此看待自己的出身、處境和命運。”這確實是一種沉痛至極而衝口而出的血淚文字,牛的命運具有了縱深感的象徵的意味,而人與牛之間的角色互換與思考,將人的命運與牛的命運被神奇地疊化在一起,從而將牛的命運的悲劇象徵意義擴展到了一個更為遼遠的世界。這種由“對象”到“主體”的之間角色互置及人性理解,顯然已經超越了佛家“悲憫”的層次,人作為萬物靈長的中心性與優越性也隨之消失得無影無蹤,其所觀照的是牛的命運的背後所隱藏著的人的命運的悲劇性,牛的命運也象徵著人的命運,而不甘於淪為牛的命運的奮力抗爭,不正是體現了崇尚獨立與自由天性的一種絕好的真實寫照!接下來的一段文字是激情跌宕之後的餘緒飛揚:當許多次的看到“比人高大有力的牛”,“不掙扎”、“不逃跑”,“被人輕輕鬆鬆地宰掉”,作家由衷地從心靈深處發出呼喊:
我在心裡一次次替它們逃跑,用我的兩隻腳,用我遠不如牛的那點力氣,替千千萬萬頭牛在逃啊逃,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最終逃進城市,躲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讓他們再認不出來。我儘量裝得跟人似的,跟一個城裡人似的說話,做事和走路。但我知道我和他們是兩種動物。我沉默無語,偶爾在城市的喧囂中發出一兩聲沉沉牛哞,驚動周圍的人。他們驚異地注視著我,說我發出了天才的聲音。我默默地接受著這種讚譽,只有我知道這種聲音曾經遍布大地,太普通、太平凡了。只是發出這種聲音的喉管被人一個個割斷了。多少偉大的生命被人們當食物吞噬。人們用太多太珍貴的東西餵了肚子。渾厚無比的牛哞在他們的腸胃裡翻個滾,變作一個咯或一個屁被排掉——工業城市對所有珍貴事物的處理方式無不類似於此。
 劉亮程
劉亮程無庸置疑,鄉村文明與城市文明之間的對立以及對這種對立的複雜理解,一直是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中國當代文學所表現的重要話題之一。例如賈平凹、劉震雲、張煒等農裔作家,就在鄉村文明與現代文明之間的評判與取捨上陷入兩難的境地。賈平凹前期的作品就明顯地表達出對封閉落後、甚至是愚昧麻木的鄉村傳統道德的批判,表現出走出鄉村封閉禁錮的“覺醒者”的姿態,但在後期的作品中,作家開始逐步走出單一性地認同現代文明的時期,對鄉村文明的依戀情感與現代文明的理性認識的糾纏,從而使其陷入情與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深刻矛盾而不能自拔。發表於90年代後期的長篇小說《懷念狼》,更是表達出對人類現實社會的一種悲觀與絕望。作家將希望寄托在狼的世界之中,希望原始的野性生命能夠改造現實社會,而最終的狼的滅絕,也意味著人類原始生命力的萎縮與衰竭。而人的狼化(獸性化),則象徵著作家對現代文明的拒絕和對前景的一種擔憂與恐懼。
而對劉亮程而言,其筆下的鄉村始終是一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世界,基於這樣的一種認識,便對牛以及同樣具有鄉村身份的“我”進入城市之後將遭遇的命運抱有深深的警惕,一方面固然有對城市生活的功利需要而展開的對鄉村和諧境界的蹂躪與破壞感到痛惜,另一方面則在心靈深處固守著對鄉村淨土的依戀而保持著一種可貴的心境。如果說賈平凹等所發出的是充滿痛苦與絕望情愫的鄉村輓曲,表現出的是一種即將面臨歷史淘汰的鄉村文化的哀怨,因而在試圖實現文化回歸認同的同時滿蘊著徹骨的無奈的話,劉亮程則是在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守望著精神的家園,這個家園有著人與自然萬物各適其所、相依為命的和諧,每個生命的存在都是一個奇異的景觀,都有一部紛繁的心靈歷史,都保持著卓然獨立的堅韌,因而也不能為外部世界的蠻橫所輕易改變。因為“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樹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蟲的鳴叫也是人的鳴叫。”(劉亮程《剩下的事情》)
惟其如此,作家為即將遭到屠戮命運的牛“在心裡一次次替它們逃跑”的聯想、發出“太普通、太平凡了”的“沉沉牛哞”的喉管“被人們一個個割斷”的感慨以及對吞噬“偉大生命”的工業城市生活方式的指責才顯得如此的振聾發聵,在痛徹心肺的情感抒寫的背後,尋找與追懷一種“鮮活如我們古老的血液”、“永遠不舊的東西。”
故鄉的意義,在劉亮程的心中,始終有兩層含義:一是生存之地,二是精神居所。作家曾如此說過:“故鄉對中國漢民族來說具有特殊意義。我們沒有宗教,故鄉便成為心靈最後的歸宿。”而對其後來相處的城市,作家也曾如此認為:“與鄉村相比,城市生活不易被心靈收藏。一件事物要進入心靈,需要足夠長的時間。”作家無意要將鄉村與城市作絕然的對立,因為“城市與鄉村沒有實質性的區別”,兩者之間真正區別在於“城市不斷產生新東西,不斷出現,不斷消失,一些東西還沒來得及留意它便永遠消失了”,“但人的心靈卻總是懷想那些漸漸遠去的、已經消失的事物。”這不是單純的戀舊,而是有感於城市生活方式的功利需要對所存在的事物的自然生命過程的漠視與無情剝奪,而在鄉村,每一個生命都有其賴以生長、存在的自然過程,因而作家才能對“大概要用五年時間,長滿被人剷平踩瓷實的院子”的“自然”的“草”產生獨特的心儀,以及對“帶給土地的將是永久的刺痛”的“ 一根扎進土地的鋼筋”的人為性的引發擯棄的情感。
由此我們也不難理解文末作家坐在街心花園的一堆牛糞上的幽幽思索,與生長在城市的同行相比,“我唯一的養分便是這些牛糞”,“我也會在適當的時候邀請我的朋友到一堆牛糞上來坐坐”,因為“飽食了現代激素”的他們,缺乏的就是這種“人類最本原的底肥”,而“沒這種底肥的人如無本之木,是結不出大碩果的。” 劉亮程散文作品的魅力也正在於此,其對所見現象的感悟顯然已經超越了物象本身的層面,進而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學意義的層面。作家沉溺於感激自然賦予自己乃至人類的那一份渾厚的血脈傳承,用心靈去審視、拷問這種傳承過程中的種種撕裂現象,其所追求的並非是規避現實的烏有之鄉,因而也並非是消極的逃遁,而是對人類精神家園的守望與捍衛。
劉亮程所具有的獨特意義或許正在於此。
我所知道的劉亮程
採訪劉亮程,我是約了他很長時間,我的聽眾您別誤會,不是劉亮程拒絕,而是他一直待在鄉下,我們沒法見面。終於見到他的時候,他又準備第二天飛北京了。出於時間的安排,我和他約在他的住處附近。
在南湖小區門口,當一個約40歲出頭的男子向我走來時,我知道他就是劉亮程了。我注意劉亮程,是因為第二屆馮牧文學獎的頒獎,在一長串名單中,突然跳出了他的名字,也許是因為他是咱們新疆本土的作家,這讓我對他有了更想了解的欲望。於是我留心起他的文字和有他名字的文章,不留心不覺得,一留心竟一陣感慨:原來文壇上有多位知名作家、學者推崇劉亮程的散文--李銳說:真是很少讀到這么樸素、沉靜而又博大豐富的文字了;韓少功說:我多年來想寫的一種文字,被劉亮程寫出來了;林賢治說:關於鄉土的散文,……集中於寫一種哲學,一種心理文化,劉亮程是獨步的;甚至徐懷中也不惜筆墨:你可以列舉出你更為喜愛的多少位散文作家,可是你舉不出有哪一位和劉亮程相仿佛……
或許還有很多推崇的評價,但那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張輝覺得應該把這位自稱"農民"的作家介紹給更多讀者和聽眾。
 劉亮程
劉亮程他就是劉亮程,一個放過牛,種過地,上過幾年國中,當過10多年農機管理員,此後進烏魯木齊城打工,現為《中國西部文學》編輯的40歲新疆漢。要說經歷,其實他和他的村莊人沒什麼兩樣。只是他們都沒去寫作,而劉亮程後來中斷了這種生活,跑到別處,選擇了寫作。
劉亮程的寫作始於詩歌。八十年代,正是文學如火如荼的好時候,只是在鄉村,可看的書極少,不過這並不影響一個有所希望、有些夢想的年輕人。他找到一本《楚辭集注》,喜歡得不得了,儘管那時還只是一知半解,可屈原的文字和屈原的精神就這樣影響了他以後的創作。他寫詩,一寫十多年。他的詩也是寫一個村莊,不過比之他散文中的村莊,詩歌中的村莊只是一個意象,有些飄忽、有些游移,暗含著年輕人的情緒。這些詩後來結集為《另一隻眼睛》和《曬曬黃沙梁的太陽》。
和那些同樣也寫農村,但只是偶爾路過村莊,看到幾個生活場景就激動不已,大肆抒懷的人不同,劉亮程在僻遠荒涼的黃沙梁看到的是一大段歲月。他說,真正認識一個村莊很不容易,你得長久地、一生一世地潛伏在一個村莊裡,全神貫注留心它的一草一物一事。這樣到你快老的時候,才能勉強知道最基本的一點點。
如今進入了城市的劉亮程沒有與鄉村隔斷,他仍時不時地回去一次,看看家人,看看脫落的牆皮、蓬生的院草……關注著他寫作的朋友們,都期待著他能保持他這一份對生活的獨特感悟,期待著他能真正走進"一個人的村莊"。
採訪劉亮程的時候,我發現他的語速一直不是很快,一邊思考一邊說話,他一句一句地說,就像是完成一件件不太簡單的事情,在作家都忍不住去做秀的年代裡,劉亮程的矜持讓我看到了一個農民的風骨,他勤勤懇懇地建造著精神家園,尋找著人類靈魂的遠地。當所有的話都說完了,他忽然夾雜著反問:“你們文學星河”這檔節目的聽眾,經常給你們投稿,你會採用哪些文章?”呵,他好象真象個記者一樣。
採訪結束的時候,劉亮程說61路車直接就可以到電台,我不必打的的。當61路車緩緩開動的時候,他還站在車站,我看見採訪中很少露出笑容的他,在安靜的、卻舒展的對我微笑。後來,我聽中央電視台的一個朋友說,他們也採訪過劉亮程,總體感覺他是個沉默如金的人。想想我們之間的對話,我對他多了幾分感激,還有幾分親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