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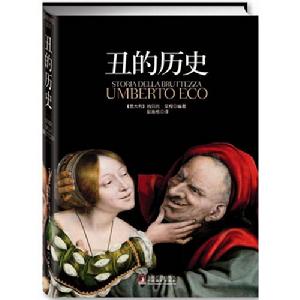 《醜的歷史》
《醜的歷史》本書講述醜是什麼?醜只是美的反面嗎?醜的範疇有哪些?繼全球驚艷的《美的歷史》之後,博學大師艾柯再推本書,以豐富的圖文資料與獨特的見解深度剖析世人對“醜”的成見,顛覆傳統審美觀,形成一部異彩紛呈的審醜觀念史。他親自保證:“《醜》比《美》更精彩。”
寫作背景
繼讓全球驚艷的《美的歷史》之後,博學大師安柏托·艾可寫出“醜”,而且他親自保證,一定比“美”更精彩。
每個世紀,哲學家和藝術家都提出“美”的定義,藉他們述作之助,我們能夠建構一部審美觀念史。“醜”則異於是。大多時候,醜被界定為美的相反,但幾乎不曾有誰針對醜寫一部專論,醜淪落為邊緣作品順帶一提的東西。因此,美的歷史可以援引範圍很廣的理論文獻(我們由此推出一個特定時代的品味),醜的歷史則必須在關於人或事物的視覺、文字刻畫裡窮搜數據。
不過,醜的歷史和美的歷史還是有些共同特徵。首先,我們只能假定一般人的品味在某些方面和他們同時代的藝術家相同。假設一位來自外層空間的訪客走進一所當代藝術的畫廊,又設使他看見畢卡索畫的女子臉孔,並且聽到其它觀賞者形容其為“美麗”,他可能誤以為,在日常生活里,我們這時代的人認為畢卡索畫的那些女子臉孔美麗,秀色可餐。
但是,這位訪客看一場時裝秀或環球小姐選美,目睹那裡讚美其它類型的美,可能就要修正他的見解。很不幸,我們回顧久遠以前的時代,無法做到這一點,無論談美還是談醜,我們都無此參考,因為那些時代留給我們的只有藝術品。
醜的歷史和美的歷史另外一項共同特徵是,我們討論這兩種價值的故事,勢必得局限於西方文明。在上古文明和所謂原始民族方面,我們有出土藝術品,但我們沒有理論文字來告訴我這些藝術品本來的用意是要引起審美的喜悅、對神聖事物的畏怖,還是歡欣。
作者
作者安伯托·艾可(UmbertoEco)生於1932年,義大利人。他是享譽國際的知名作家,也是記號語言學權威、知名的哲學家、歷史學家、文學評論家和美學家。現居米蘭,執教於波隆納大學。著名的4部著作為《玫瑰的名字》(Ilnomedellarosa)、《傅科擺》(IlpendolodiFoucault)、《昨日之島》(L'isoladelgiornoprima)、《波多里諾》(Baudolino)、《美的歷史》(Storiadellabellezza)等。
文化內涵
美的對立為醜,然而審美與審醜皆有共性,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翁貝托·艾柯寫《美的歷史》後,再作《醜的歷史》,在書前《導論》里說:“每個世紀都有哲學家和藝術家提出‘美’的定義……但幾乎不曾有誰針對醜寫一部專論。因此,美的歷史可以援引範圍很廣的理論文獻(我們由此推導出一個特定時代的品味),醜的歷史則必須在關於人或事物的視覺圖像與文字材料里窮搜線索。”羅森克蘭茨在1853年寫過《醜的美學》,艾柯稱其為“第一部也是最完備的”醜著。
艾柯在《醜的歷史》認為美與醜的審視標準隨歷史時期或文化之不同而變化,說:“一個時代認為合乎比例的東西,另一個時代卻不認為它合乎比例。在比例這件事上,一位中世紀哲學家會想到哥特大教堂的層次和形式,一位文藝復興理論家會想到依照黃金分割來建構的16世紀殿堂。文藝復興時代的人認為大教堂的比例是野蠻的,他們以‘哥德式’一詞來形容,就說明了一切。”這意思是美與醜並無定論,觀念亦會隨時代或社會發展而起變化。一個著名的例子便是巴黎艾菲爾鐵塔,“艾菲爾1889年為巴黎的世界博覽會完成鐵塔之前,1887年的《時代報》(LeTemps)刊出一封署名者包括作家小仲馬和莫泊桑等的信:‘我等作家、畫家、雕刻家、建築家,珍愛巴黎仍然完好之美者,在此盡我等全副力量與滿腔義憤,為法國人民被低估的品味、為受威脅的法國藝術與歷史請命,抗議在我國首都的心臟興建無用且醜怪的艾菲爾塔,富於常識與正義精神的不滿的大眾早已為此塔取一諢名:巴別塔。’抗議信怒斥這巨大的‘工廠煙囪’將會像一塊墨漬渲染開來,‘可恨的鐵柱子’的可恨陰影將籠罩巴黎。”這段話里最有趣的是信的措辭,寫這封信的人皆是知識賢達和社會名流,倘若我們的知識分子有這般勇氣敢於大聲疾呼直抒己見,大概老北京城不至損毀到今天這副模樣。
關於醜有許多可談的話題,書中第十四章《媚俗》一節曰:“醜也是一種社會現象。‘上層’階級的人向來認為‘下層’階級的品味討厭或可笑。我們當然可以說,經濟因素在這類歧視里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也就是說,雅致常常和昂貴的布料、顏色及珠寶相連。”大多藝術品雖出自工匠之手,卻由上流社會所推動,皇室和貴族成為藝術品最好的維護者,而每當有底層暴動和騷亂,都會使藝術品受到損毀。然而藝術常被政治和宗教所支配,使其成為時代政治的符號,艾柯稱此為“媚俗”,比我們狹義的媚俗更多出政治因素。“媚俗也一直被用來形容希特勒、墨索里尼政權下那些歌功頌德,要全民歡迎的藝術。”另有一些稱作“好東西,壞品味”的,如古鎮開發成旅遊景點,將舊時代的東西拆除掉再建設新古董,倒是符合“壞品味”的標準了。
談美易令人愉快,但要把醜說得不讓人反感,實非易事。《前衛運動與醜的勝利》一章里說:“心理學家榮格在1932年撰文討論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認為今天的醜是即將到來的巨變的徵兆和症候。意思是說,明天被當作偉大藝術來欣賞的作品,在今天可能被認為倒人胃口:新事物來臨時,品味往往還跟不上。”這為我們當代藝術提供了理論依據,因此當代藝術展上經常見到以醜為美的作品,或怪誕、褻瀆的自我表現,很是有點賭明天的心理,似乎天才也要靠運氣,古今皆然。[2]
編輯推薦
中央編譯出版社“圖文館”書系,精挑世界一流學者,細選高品位作品。該書系編排精緻、印裝精美,旨在“讓書成為最精美的禮物”,已出版的《時間的故事》《醜的歷史》《美的歷史》《色彩的性格》《聖經的歷史》《人類與宗教》《閱讀的女人》《書店風景》《有生之年非看不可的1001部電影》《閱讀的女人危險》《寫作的女人危險》等圖文書廣受歡迎。2010年將陸續推出《錢的歷史》《這是什麼意思?》《女人與珍珠》《零ZERRO》《圓與方》等書。[3]
媒體評論
尋找醜真是樂事一件,因為醜比美更精彩有趣。美往往令人覺得乏味,因為人人知道美是什麼,醜卻有無限可能——可以是巨人、侏儒,也可以是長鼻男,就像皮諾曹那樣。——翁貝托·艾柯
艾柯為《美的歷史》撰寫的這部姊妹篇既是對視覺的衝擊,也是對思維的挑釁。艾柯嘗試把醜作為歷史和文化批評的一部分做進一步的分析,呼應上一次的尋美之旅。……這種兼收並蓄的研究別具一格,必將吸引文化和藝術史學者以及一般讀者對這個頗受冷落的主題產生興趣。——《出版商周刊》
美可能吸引人,但醜更有趣——這正是艾柯這本迷人的大書呈現給讀者的。……百科全書式的引文、生動炫目的插圖……在這些歡笑、色情、噁心或恐怖形態的背後,你將很難接受它們有醜的一面。——《紐約時報》
大多數藝術書值得看看,或許,在咖啡桌邊即可。這部無法言喻、令人發狂的書卻是要讀的。——《細節》雜誌
《醜的歷史》為休閒讀者提供了大量信息,也為那些希望深入探討這個課題的人指引了門徑。——《選擇》雜誌
2010年值得推薦的40部好書
| 讀書,當然要讀好書,新書。本期任務讓我們走進本年度值得推薦的40部好書中去吸取養料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