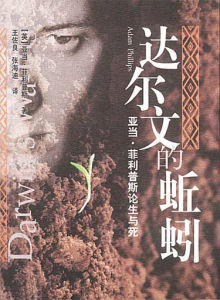 達爾文的蚯蚓
達爾文的蚯蚓作者:英.亞當·菲利普斯
譯者:王佐良張海迪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年7月
ISBN:750632604
頁數:161
裝幀:平裝
開本:大32開
版次:1
目錄
我們的終極目的是什麼——譯者的對話序言
達爾文為蚯蚓正名
弗洛伊德之死
結束語
內容提要
所有的人都感到震驚,這個世界上居然有太多的苦難,好像我們真的相信苦難本來能夠少一點,或者應當少一點的。的確,當我們在談論公正和科學進步這樣的話題時,其實也是這樣說,有些苦難是可以避免的。作者採用了一種獨特的視角,他借用了達爾文和弗洛伊德這兩個人,通過對他們的論述,來談自己的生死觀,很有意思。書評
約翰·凱吉講了一件事,說他去聽一個朋友的音樂會。朋友是一位作曲家,他在音樂會節目單的註解中寫道,希望自己的音樂能多少消弭一點這個世界上的苦難。音樂會結束後,他問凱吉對音樂會有什麼想法,凱吉回答說:“我喜歡你的音樂,可我討厭那張節目單。”“你不覺得這個世界上的苦難實在太多了嗎”朋友問,他顯然是被激怒了。“不。”凱吉回答,“我認為不多不少。”所有的人都感到震驚,這個世界上居然有太多的苦難,好像我們真的相信苦難本來能夠少一點,或者應當少一點的。的確,當我們在談論公正和科學進步這樣的話題時,其實也是在說,有些苦難是可以避免的。我們應該相信,有人能介入我們的苦難之中,使晴況有顯著的改觀。如果世界上有太多的苦難是不可迴避的事實,那將會引起宗教信仰的喪失。試想,一個容忍人間有這么多的苦難,這樣踐踏他的子民的上帝,還值得崇拜嗎?現在提出這種疑問可能會造成絕望情緒。可是,在一個世俗的世界上,我們除了責備自己,怪罪自然,還能說誰呢?宗教上的絕望情緒會導致政治上的絕望。上帝已經不再拯救我們了,政治進程也不能充分地保護、甚至都不能代表我們最珍視的人和事了,全球資本主義使民主顯得幼稚,而仍然得勢的宗教都懷有原教旨主義的意圖。
以一種嚴肅地對待經濟學、因此也嚴肅地對待剝削的政治觀點來看,凱吉講的事讓人感到恐懼。它似乎暴露了貌似灑脫的禪宗的麻木不仁和冷酷無情。凱吉作為一個有強迫癖的人,在對他的朋友使用休克療法。有些人相信一種常常被他們稱為自然或者本性的東西(這個詞:nature通常是小寫的),例如達爾文和弗洛伊德及其追隨者,他們都認為這個世界上的苦難不多也不少,即使實際上也確實多了一點。達爾文和弗洛伊德這兩位作家都被苦難這個詞的各種概念所困擾,認為沒有一個活的生命個體能夠承免這些苦難,因此,他們告訴我們,要活著,就要把理智丟在一邊,就要忍受某些不可躲避的壓力,就不能迴避不可避免的衝突。他們兩人似乎都要我們相信,政治制度可以減輕苦難,卻決不可能極大地減少苦難。他們要在自然里生存(除此以外我們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就要求我們更現實地承認政治的局限性,只能利用政治來改善我們的境遇。表面上,他們對政治活動不無懷疑,認為有些東西是政治所無法改變的,
和平主張政治體制的安排應基於這種認識。他們著作的批評者們都認為,這兩人的著作——不管它們還是別的什麼一其實都是另一種手段的政治。達爾文和弗洛伊德還常常是他們自己著作的評論者,不公開地用自已的語彙來評論自己的著作。每當他們告誡我們不要有危險的烏托邦式(或者救贖的)幻想時,實際上卻是在推薦他們自己偏愛的世界圖景。在關於人的本性的描述中,他們總想讓人相信,那都是可以實現的。
……
書摘
單個的人,就像物種的一個成員,她的去向是模糊不清的(不可預知的),也不是特殊的。但是作為繼續虛構未來的一張請帖,悲痛還不足以成為原因。當達爾文和弗洛伊德越來越多地發現過去的力量時,發現當今不斷地被過去超越時,他們也認識到一個簡單的事實:過去影響著一切,卻並不支配什麼。那種所謂關於過去的知識既不預言也不保證我們對未來的認知。未來不是由過去引起的,而僅僅是由過去告知的。荒謬的是,他們新發現的死亡的終極性是和這個開放的終結性相一致的。我們行將死去,這個事實僅僅說明我們就要死去,而沒有說到未來。一旦我們的死對任何其他人、對上帝、對眾神、對自然本身都無關緊要,而僅僅與我們自己有關,死亡對於我們就是另一回事了;一旦沒有任何東西(或任何人)俯瞰著死亡,死亡就開始變成另一種樣子。我們應當看到,達爾文和弗洛伊德為我們創造了新的死亡,他們不得不使死亡和一種世俗的語言有關。這反過來使得未來成為欲望的一種新的目標。達爾文遺產的一部分讓人驚奇的是,我們可以為自己認領已經無可挽回地失去的東西。化石記錄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化石的殘存物暗示著某種已經無法恢復的消失。換句話說,達爾文在其寫作生涯初期寫的這四篇論文中,在那篇著名的論述珊瑚形成的論文裡就已經“第一次透露出他對進化的信仰”,在這裡已經潛伏著被壓抑的精神危機。有他自己特徵的經驗主義觀察把他推向了一個讓人極反感的問題,一個在政治上和神學上都引起分裂的問題。當然,他從沒有直截了當地提出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真的認為瞬息是不可挽回的,那我們該如何生活?他轉向蚯蚓正是為了尋找有可能被稱為精神營養的東西:尋找撫慰,尋找激勵,甚至還為了尋找歡樂,華滋華斯認為快樂是自然最大的恩惠。
“泥土表面的一層,通常叫做腐殖土,它的形成,”達爾文在他的論文《論腐殖土的形成》一文開頭寫道,“有許多困難的問題需要充分地理解,可它們顯然被忽視了。”困難的問題被忽視是因為它們是看不見的,達爾文用了忽視(overlooking)這個詞的兩層意思:看得過度使眼睛失明。達爾文像弗洛伊德一樣,總是認為他所能看見的事物和現象都是一種隱伏的過程的產物(在這裡,這個隱伏的過程的產物字面上指的是泥土的表層)。而這一過程需要進一步的證明來重構。之所以會有地面,是因為在地表下正發生某種過程,而看得見的是這個故事的結尾。
張海迪作品
| 張海迪,1955年9月生於濟南,漢族,哲學碩士,中共黨員,山東省作家協會創作室一級作家,九屆、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