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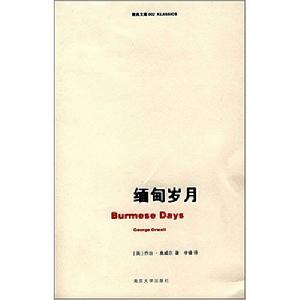
作者: [英]喬治·奧威爾
出版: 南京大學出版社
定價: 20元
ISBN: 9787305051609
出版日期: 2007-08
內容介紹
這部生動真實、引人回味的小說講述了一幫英國人的故事。在大英殖民統治日薄西山之際的緬甸,他們相聚在歐洲人俱樂部,整日飲酒,以排遣內心那無法言說的寂寞。其中有一位約翰·弗洛里,他內心柔弱,深知英國統治毫無意義可言,可又缺乏足夠的堅毅,不敢為自己的印度朋友維拉斯瓦米醫生爭取進入白人俱樂部的資格。而沒有會員資格以及由此帶來的聲譽保護自己,醫生所擁有的一切,將會毀於一名地方治安官無恥捏造的誹謗之辭。弗洛里無意中愛上一個新來的英國女孩兒,令事態更趨複雜。他必須有勇氣作出正確的舉動,不止為了朋友,也為了自己的良心。
作者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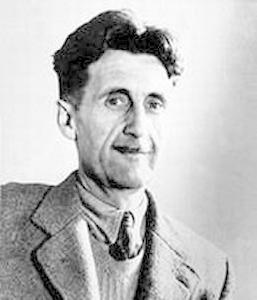 喬治·奧威爾
喬治·奧威爾喬治·奧威爾(1903—1950)曾擔任駐緬英國皇家警察,為支持共和政府而參加西班牙內戰,在二戰期間參與地方志願軍,並為英國廣播公司撰寫文章。他著有大量小說和散文作品,代表作有《動物農莊》、《一九八四》、《向加泰羅尼亞致敬》等。
李鋒,山東青島人,先後於山東大學英語系和南京大學英語系攻讀碩士、博士學位,主要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和西方文藝批評。代表作品有《非理性的光輝,瘋癲中的詩意》、《一個特立獨行的奧威爾》等,譯著有《聖經的敘事藝術》、《世紀末的維也納》、《巨匠與傑作》。
譯序
作為殖民地,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英屬印度地區(包括現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以其異域的景致和情調、同西方迥然不同的文化習俗,給英國作家提供了一個極為理想的創作背景。於是我們看到,在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批判聲中,在現代主義技法實驗的大潮中,一些作家同時也將眼光瞄向了這片奇異的南亞土地,並創作出大量優秀的作品。
然而單就長篇小說而言,在這些數量龐大、題材繁博的作品當中,真正稱得上佳作的,恐怕除了吉卜林的《吉姆》(Kim)和福斯特的《印度之行》(Passage to India)以外,就當屬奧威爾的這部《緬甸歲月》了。我曾長期懷疑,這是由於自己對英國文學史見識淺薄所致的個人見解,後來在批評家勞倫斯•布朗德(Laurence Brander)的著述里看到了類似的評價,他認定《緬甸歲月》比之《吉姆》和《印度之行》差距尚大,但定要排個第三出來的話,還真是難有與之匹敵的。再翻到著作權頁一看,此書1954年便已出版,看來我的見識淺薄的確不假,而《緬甸歲月》的“探花”地位倒也不是一己之見。
奧威爾同印度有著極深的因緣,他的父親長期供職於印度政府的鴉片部,而他本人就出生在印度比哈爾邦的莫蒂哈里,次年隨母親回國,公學畢業後,雖學業尚好,但未像其他伊頓生那樣去牛津劍橋深造,而是重返亞洲,在緬甸做了五年(1922-1927)的警察。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亞洲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英國與緬甸民族關係最為糟糕的時期,於是,奧威爾也就親歷了諸多的民族隔閡,衝突,甚至殺戮,以及由此給雙方所帶來的難以擺脫的精神苦痛。奧威爾自認是大英帝國殖民機器上的一個部件,自然感受到難以承受的道德罪責。所以,如同當年的霍桑寫作《紅字》(The Scarlet Letter)是意在給自己的清教徒先祖贖罪一樣,奧威爾寫《緬甸歲月》時,亦是感受到內心中有一股“我必須為之贖罪的龐大重負”,因此必須通過文學創作的方式,來獲取內心的安寧和平靜。
《緬甸歲月》的故事有兩條主線,有點類似中國評書中“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講述方式。一條線索是主人公弗洛里同伊莉莎白的感情糾葛,另一條是緬甸治安官吳波金與印度醫生維拉斯瓦米為爭奪進入歐洲人俱樂部的席位而展開的明爭暗鬥。最後兩條線索合二為一,一切終見分曉。這當中的懸念設定和情節鋪陳,倒也扣人心弦,不過真正讓人擊節讚嘆的,是作者在描物狀景中對聲音和色彩的熟練把握,讀來仿佛真的置身熱帶叢林的光影世界。
奧威爾對東方有著很深的興趣,在《緬甸歲月》里,他借主人公弗洛里之口,表達了對緬甸的自然風光、傳統習俗、宗教信仰的痴迷,同時夾雜著對這個陌生又熟悉的國度那種愛恨交織的複雜情感。同《印度之行》一樣,這部小說涉及到不同種族之間的緊張關係,言語間也透出對殖民統治的種種不滿。但不同的是,《緬甸歲月》中的土著似乎更像是背景化的陪襯,而作者真正關注的,還是歐洲人自身在這個第二祖國的生存狀態,從而生髮出該書的真正主題——孤獨。
奧威爾的小說儘管取材廣泛、形式多變,但卻有一個依稀可辨的模式,就是幾乎每部小說里都有一個性格內斂、精神孤寂的靈魂被置於故事中心,而他們渴望與人溝通、追尋生命價值的動機,也就構成了整個故事的張力,推動情節向前發展,從《牧師的女兒》中的多蘿西,到《一九八四》中的溫斯頓,大抵如此。
而就本書而言,孤獨具有兩個層面的指涉,一方面,歐洲人出於對土著居民的鄙視,不肯與之交往,而是封閉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整天在俱樂部打牌飲酒、閒談漫扯,生活死一般的沉寂和無聊,處處透出陳腐的味道;另一方面,弗洛里又是這個孤獨群體中的一個異類,雖然他也曾沉淪過,甚至不時地酗酒和狎妓,但是對自己個人乃至整個大英帝國的墮落,卻能感到道義上的羞恥,而對身邊這些同胞的矯揉造作、無知自大,也嫌惡不已。正由於他對美好的生活依舊保有一顆企盼的心,巴望能有個人來分享自己的感受,去除心中的落寞和孤寂,所以才對初來緬甸的英國女孩兒伊莉莎白充滿了遐想和期待。
陷入愛情的人總是難免會昏聵與盲目,在隱約覺出伊莉莎白的學養淺薄和圖慕虛榮之後,弗洛里仍舊幻想通過自己的思想來影響和改變她,直至將其變成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愛人。人們經常說:把一個相貌美麗、頭腦蠢笨的女人變得聰明起來,總比把一個相貌醜陋、頭腦聰明的女人變得美麗起來來得容易。這本是男人之間調侃的戲言,當不得真的。一個人,尤其是二十出頭的女孩子,假若愛上了浮華,又痛恨學問,其實是斷難改變的。尤其像伊莉莎白這種出身不高、受過窮苦的女孩,對財富、階級、種族的成見更加根深蒂固,她可能會比富家小姐還要百倍地熱愛地位和權力,也百倍地痛恨學問和貧窮。弗洛里錯就錯在把對方一味地理想化,陷於其中,不肯自拔,到最後只落得個飲彈自絕的下場。
因此從表面上看,弗洛里是兩個土著官員權力爭鬥的犧牲品——吳波金眼見弗洛里支持維拉斯瓦米醫生,妨礙自己的權力之路,便設計令他在大眾面前出醜,導致其含羞自殺——實則卻是死在了對人的錯誤判斷上。他把人生的希望寄託到一個根本不可能理解自己、同自己有著完全不同追求的女人身上,指望對方能幫助自己驅走可怖的孤獨感,而幻滅之時,孤寂猶在,除了死,也實在別無出路。
其實,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這樣一個人物抱有這樣的思想,其死幾乎是必然的。這很有些自然主義的味道,奧威爾本人在後來憶及寫《緬甸歲月》的初衷時也說過:“我當時想要撰寫宏大的自然主義小說,帶有悲慘的結局。”換言之,弗洛里的交手對象,也是這部小說的另一個主角,並非伊莉莎白或者吳波金,也不是英國的殖民統治,而是命運自身。敢與命運抗爭,幾乎注定一死,但雖死猶榮,就像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明知自己推到山頂的巨石還是要滾下來,卻依然堅持不懈。正如加繆所言:“那向著極頂奮力前進的過程本身即足以填充一個人的內心,我們可以構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當然,弗洛里的形象遠不如西西弗斯高大,他自憐自哀、膽小懦弱,是個可愛又可恨、可憐又可鄙的“反英雄人物”(antihero),然而這並不影響整個故事的悲壯之美。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界定,真正的悲劇是指一個平凡人,沒有特別做好事,也沒有故意做壞事,卻因為命運的擺布,而陷入一種極慘的情況傅佩榮,《哲學與人生》,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年,第76頁。,而這正是對弗洛里的境遇的貼切寫照。
既是悲劇,在觀眾/讀者心中所激起的,無非就是憐憫和恐懼兩種心緒,不過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寫過,即使是在宏大的記事和嚴正的說理後面,也永遠躲藏著一個諧趣的奧威爾,尤其是描寫起惡棍形象來,他簡直有著揮之不去的興味。本書亦不例外,開篇介紹吳波金的幾段文字,可謂生動傳神,甚至被認為是印度題材的英國文學中最富幽默感的篇章。Brander, Laurence. George Orwell. London, New York, Toronto: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1956. p79.
作為奧威爾的首部小說,《緬甸歲月》在語言駕馭和人物塑造上尚有一些不足之處,有些技巧上的處理方式,一直延續到以後的多部作品中,並因之屢受指摘。在這裡,我不願多去贅述這些觀點,對於看熱鬧的讀者,這純屬破壞興味,而對於看門道的,又有越俎代庖之嫌,還不如留給大家自行審視。
另外需要說的是,很多人都認為奧威爾的隨筆要遠勝他的小說,這不好籠統論定,但無可否認的是,他的許多小品文,無論是文筆之凝練,還是語詞之幽默,確是英語文學中值得反覆誦讀甚至效法的精品之作。對於喜愛奧威爾的讀者,我建議在閱讀這本小說的同時,不妨將他的兩個名篇《絞刑》(A Hanging)和《獵象記》(Shooting an Elephant)找來讀讀,尤其是後者,形象地描畫出作為統治者的英國人,實則卻受到緬甸人無形支配的那種無助與無奈,此中的諷喻,同《緬甸歲月》實在是有暗合之處。
從當初翻譯聖經敘事研究開始,也算有了幾部譯作,而奧威爾亦是我這幾年專門研究的對象,這次翻譯《緬甸歲月》,算是一次鍛鍊筆功和加深研究相結合的過程。原作中有一些法語和拉丁語的表達,幸有友人相助才得以化解,然而亦有大量印緬地區的方言俚語,時至今日,有的甚至在其本地也不多用,譯者藉助網路和一些相關的參考書籍,通過詳查和推斷,基本確定箇中含義,但仍有個別詞句不夠精當,還望方家指正。
以上所言,一則是為了記錄自己翻譯此書的些許感受,再則算作導讀,把一些相關的背景信息提供出來。當然,對於很多讀者而言,這些文字或許純屬多餘,他們不需知曉過於明細的歷史背景,更懶得去理會文本閱讀過程中的種種專業視角和方法,而只是想圖個樂子,那就索性拋開那些 ism(主義)和 ology(學說)的束縛,直接進入這個熱帶叢林的國度吧!在這個世界裡,有爾虞我詐的爭鬥,有扣人心弦的捕獵,有奇麗壯闊的景致,還有通俗文學中似乎永不可缺的複雜的愛情糾葛。我始終不解的是,一向執守自見、恥於迎合市場的奧威爾,何以在自己的這部小說處女作中,將這些今天看來非常商業化的元素拿捏得如此嫻熟和到位。
易中天教授在品三國時曾給小說下過一個極有趣的定義——“可以躺在床上看的東西”,也就是說,要“好看”,這有點像一些通俗雜誌上的諧談,出自講壇之上似有不夠嚴肅之嫌,但卻從某個方面道出了小說不同於其他敘事作品的基本特徵。時而見到有人批評易先生讀解文史的方式有些流俗,其中包括他平實的措辭,照此觀之,瓦爾特•本雅明那句“書和女人都可以帶上床”的著名論斷簡直可說是淫俗了,但它在隱喻之間卻點出了書的趣味性,也實在比其他的諸多說法來得貼切。按這個標準說來,我覺得《緬甸歲月》至少是好看的,即使未必真把它帶到床上,但一樣可以領受到其中的閱讀快感。
內容選錄
吳波金是緬甸北部凱奧克他達的地方治安官,此時正坐在自家的陽台上。剛剛八點半,可由於是四月份,而且空氣非常悶熱,恐怕正午時間會又長又憋悶。偶有微風拂過,吹動著掛在屋檐上的蘭花,感覺倒也有些清涼。在蘭花遠處,能看到一棵棕櫚樹那灰頭土臉的彎曲樹幹,然後就是耀眼的深藍色天空。空中盤鏇著幾隻禿鷹,翅膀一動不動,高得讓人目眩。
眼睛眨都不眨的吳波金,活像一尊大的瓷像,正凝視著刺眼的陽光。他五十歲了,非常的胖,以致多年來,要是沒有人攙著,就無法從椅子上站起來,可他胖得很勻稱,甚至可說是美觀,這是因為緬甸人不像白人那樣下垂和腫脹,而是均衡的肥胖,像是脹大的果子。他的臉盤很大,黃黃的,沒什麼皺紋,眼睛呈黃褐色。他的腳又短又厚,足弓得很厲害,腳趾頭都一般長,沒有穿鞋,光禿禿的頭上也沒戴帽子,身上裹著那種鮮艷的阿拉卡尼斯羅衣羅衣為緬甸民族服裝,裹於下半身,類似筒裙。——譯者注,上面帶著綠色和絳紅色的格子,是緬甸人的日常衣著。他一邊從漆盒中拿著檳榔吃,一邊回想著過去的時光。
之前的人生倒也算是志得圓滿了。吳波金最早的記憶是在八十年代,可謂揮之不去,當時他還是個衣不遮體、大腹便便的小孩,望著英軍雄赳赳地進駐曼德勒。這一隊隊身高馬大、專吃牛肉的人臉色通紅,身穿紅色戎裝,肩上扛著長長的步槍,腳上的靴子落地有聲,也不乏節奏。他還記得自己當初對此有多么恐懼,瞧了幾分鐘後,他慌張地撒腿跑了。在其幼稚的內心裡,他已然斷定,自己的人根本不能和這個近乎巨人的種族相比。要同英國人站到一處、依附他們的勢力,尚且還是個孩子的他,就已經將此當作了自己的最大抱負。 十七歲時,他曾謀求過一個政府職位,但並未如願,由於身無分文又沒有朋友,他只好在縱橫交錯的曼德勒集市幹了三年活兒,幫米商辦事,不時也偷雞摸狗。到二十歲的時候,由於走運,他敲詐別人得手,有了整整四百盧比,便立即去了仰光,一路買通關係謀了個辦事員的位置。這份活兒雖說薪水不高,但頗有油水。那時候有一幫辦事員,通過不斷挪用政府儲備品而贏取私利,波金(他當時只叫波金,“吳”這個敬稱是後來加上的)自然也喜好此道。不過他才華過人,不可能在區區一個小辦事員的位置上終此一生,偷那點兒可憐的小錢。有一天,他發現政府由於缺乏低級官員,正準備從辦事員中選拔一些人上任。再過一個禮拜,訊息就會公之於眾,可吳波金有一個本事,那就是他總能夠提前一周比別人探聽到訊息。他感到機會來臨,趁自己的同夥尚未警覺就把他們全都指控了。於是大多數人被捕入獄,而吳波金卻被提拔為鎮區助理幹事,作為對他奉公辦事的表彰。自此之後,他平步青雲,如今五十六歲的他已經成了地方治安官,而且很可能進一步得到提拔,當上代理副警長,同英國人平起平坐甚至凌駕於他們之上。
書評
不知道為什麼,至今不見翻譯出版奧威爾的文集。所以只好陸續地零星購買散裝的奧威爾了。新近買到的是小說《緬甸歲月》,它來自奧威爾到緬甸當5年警察的經歷。《緬甸歲月》是奧威爾的首部小說,就是那種“矛盾感”、“孤獨感”的產物。作為殖民地,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的英屬印度地區(包括現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以其異域的景致情調、與西方迥然不同的文化習俗,提供了創作的理想背景。在《緬甸歲月》里,奧威爾講述了一幫英國人的故事。“在大英殖民統治日薄西山之際的緬甸,他們相聚在歐洲人俱樂部,整日飲酒,以排遣內心那無法言說的寂寞”。《緬甸歲月》的故事有兩條主線:一是主人公弗洛里同伊莉莎白的感情糾葛;二是緬甸治安官吳波金與印度醫生維拉斯瓦米為爭奪進入歐洲人俱樂部的席位而展開的明爭暗鬥,最後兩條線索合二為一。小說的故事既重要又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核心思想—孤獨與救贖,那恰是歐洲人身在“第二祖國”的生存狀態和作者的思想狀態。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英國與緬甸民族關係最為糟糕的時期,奧威爾也就親歷了諸多的民族隔閡、衝突、甚至殺戮,看見了雙方難以擺脫的精神苦痛。奧威爾自認是大英帝國殖民機器上的一個零件,感受到內心的“我必須為之贖罪的龐大重負”,於是通過文學創作的方式,來獲取內心的安寧和平靜。
人類文明的進步早已是浩浩蕩蕩。可是,在一些地方,在一些角落裡,“野蠻人”照樣瀟灑地存在,那些民主、自由、人道、博愛、公正、平等、法治等等人類的普世價值,總得不到兌現。奧威爾轉向寫作之後,開始了清除自己內在野蠻人一面的漫長過程。他的代表作當然就是《動物莊園》和《1984》。作為一位先知,奧威爾在《1984》這部預言小說中,描繪了一幅未來社會在極權統治下的恐怖景象,對專制統治的譴責達到了小說的極至。
寫《緬甸歲月》,奧威爾如果不是回憶,而是像《1984》那樣寫未來,那會是怎樣的情景呢?就在奧威爾逝世前兩年的1948年,緬甸於1月4日宣告脫離大英國協而獨立,這個奧威爾恐怕不難想到;但他能想得到2007年的秋天,一位日本攝影記者在緬甸仰光遊行示威現場採訪時被子彈擊中而身亡嗎?他能想到緬甸爆發這樣大規模的反政府活動、在仰光有數萬名僧侶和市民舉行示威遊行時的那種堅定嗎?他能想得到許多人已死於緬甸軍政府的槍口下嗎?他能想得199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者翁山蘇姬已被軟禁長達15年嗎?
“我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抗議!”翁山蘇姬是緬甸民主運動的旗幟,她是領導緬甸獨立的民族英雄昂山將軍的女兒,父親在她兩歲時遇刺身亡,那時距離緬甸宣布獨立僅僅只有半年時光。作為緬甸全國民主聯盟總書記的翁山蘇姬,容貌極為美麗,被稱為“最美的女政治家”,甚至有人稱她為“亞洲第一美女”,深受緬甸民眾愛戴。但是,在威權統治的環境裡,翁山蘇姬的命運只能是“被禁”,儘管是所謂的“軟禁”。
人類前進的腳步,總是那么艱難,文明的推動力,不一定能輕易戰勝愚昧的阻擋力。專制的統治,就是一種反文明的愚昧。西方的殖民主義,帶來的是一種國與國之間的主僕關係;東方的專制主義,帶來的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主僕關係。而這種主僕關係,成了一種深入到社會肌理、人文血液里的因子。在《緬甸歲月》里,通過具體人物的故事情景,對那種“仆”對“主”的“懇求”,有纖毫畢現的描寫,比如“她已伸出雙臂抱住他的腳踝,居然吻起了他的鞋子”……家庭里個人對個人的“統治”,社會上群體對群體的統治、國際上國家對國家的統治,不是殖民就是治民。而一個人從“仆性”到“奴性”,只有一步之遙。
專制者對專制者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專制政體對專制政體也有著天然的親近感。“人猿相揖別”之後,不過幾千寒熱;可常常是“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所以“流遍了,郊原血”。人類文明進步的代價,總是慘重的,因為威權者看起來“獨孤”,卻依然活得強悍而瀟灑。公眾忽然發現,面對威權依然那么無力;後來一些媒體關注緬甸,焦點變成了日本記者長井健司槍彈中的犧牲。長井健司死了,翁山蘇姬依然被軟禁。奧威爾的《緬甸歲月》畢竟是懷想過去的,那么,誰能寫下預言未來的《緬甸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