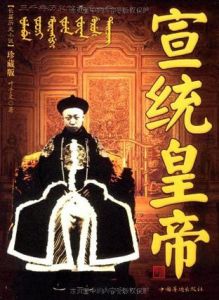簡介
如果我們把溥儀的前半生簡單地敘述一遍,那么就不如讓讀者去翻看《我的前半生》了;事實上,人們對溥儀一生的事跡是比較熟悉的。鑒於此,本書把重點放在對溥儀性格形成的原因的揭示上,從而對溥儀生活的社會作了全方位的立體的再現。本書對特務、太監等人物的私生活作了細緻的描寫,對一些政治人物欺世盜名、竊國篡權的種種卑鄙、奸詐的權術和伎倆作了生動具體的再現,相信讀者會以批判的眼光看待這種種醜惡,從中看出所有醜惡及罪孽的根源在封建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上。
小說中對皇后去世的描寫:
人們對太后的逝去並沒有顯示悲哀,除溥儀一人而外,宮內宮外的滿清遺老道少,倒是保有著自舊曆年年前時所滋長的喜悅,這種喜悅歡樂的氣氛隨隆裕太后的死而一天比一天濃烈。雖然滿清的遺臣們在太后靈櫃前乾嚎,雖然太監們發出種種陰陽怪氣的哭聲,可是人們總是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和歡樂。
太后是在她的萬壽節的第七天去世的。當天,孫文和黎元洪副總統就發來了唁電,那些王公舊臣一片歡喜。內務府馬上以“大清皇帝暨王公大臣”的名義復黎元洪的唁電,
電文如下:
“副總統哀悼大行皇后仙馭升邏,情詞懇摯,並蒙飭屬依製成禮,遣員致吊,足征優待之隆,不勝感紉之至。”
最為動人的是袁世凱,他自己黑紗纏臂,又通令全國下半旗誌哀一天,文武官員服喪二十七天,報喪的電文均由國務院代發。
2月28日,全體國務員前往宮內致祭,宮內外車轎雲集。靈樞前,國務員們採用了新式的志衷方法,隨著號令,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齊齊刷刷,煞是好看。
袁世凱大總統對宮廷的關心更是無微不至,他致書“大清醇親王”請晉封晉妃的尊號,清內務府和王公道臣們不敢怠慢,忙恭上尊號,曰“端康皇貴妃”。這樣,後宮又有了新主子。
3月19日即陰曆2月12日,太和殿舉行了國民哀悼大會,主祭的總代表是參議院議長吳景濂。
陰曆初二日是隆裕釋服的日子,軍界舉行了全國陸軍哀悼大清隆裕太后大會,領銜的是段棋瑞將軍。
辮帥張勛通電全國,稱隆裕大後之喪為“國喪”,電文曰:“……食毛踐土,莫非王臣……我國大總統及政府諸公皆清朝二百餘年之臣子,即新黨人物有崛起草莽,其祖若父亦皆受祿於朝。”
滿族王公大臣賞穿孝服百日;漢人中,陸潤庫、徐世昌、陳寶琛、袁勵雄,也賞穿了孝服。特別令人興奮的是,徐世昌太傅是從青島趕來的,在太后的退位詔頒布後,他就寓居青島,而今專程前來奔喪,而他,又是袁總統至交密友心腹,更是北洋元老,如今特來奔喪,怎能不令清臣王公們興奮?
可是也有讓人氣惱的事兒,做過軍機首席,內閣總理大臣的慶親王奕劻,寓居天津租界,卻屢召不來。
“什麼玩藝兒?”
“還是人嗎?”
“這種無君無父,不仁不義之徒,還該活在世上!”
連北京街頭的普通百姓也在罵著奕劻。
光緒皇帝的崇陵是在他死後才在梁格莊修建的,並不是像以前的皇帝一樣在生前已經建陵,在清儀建位時,基礎工程尚未及半。當時從京漢鐵路高碑店車站起,修建了一條支路,經淶水縣、易水城,直達梁格莊,光緒皇帝的樣宮即由北京用專車“奉移”到梁格莊行宮內“暫安”。1908年12月,光緒的靈樞奉移至梁格莊行宮,暫安殿的近旁設立了王大臣六班公所,凡現任各部院的王大臣和八旗都統都要輪流值班,守護梓宮,每日朝奠。暫安殿內由清內務府包衣旗人負責,門外由泰寧鎮的綠營白晝巡邏,夜間走籌。
隆裕太后死後不久,崇陵地宮也剛好建成,還好舉行光緒帝及隆裕太后的奉安合葬,兩宮一起奉安是自古未有的,而奉安是在皇帝退位後舉行的,更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
但是奉安盛況空前,隨之而來的是清朝王公遺臣的喜悅歡樂達到了頂點。
奉安經過的路面都鋪上了黃土。隆裕太后的靈車也到了梁格莊。
4月3日是兩宮梓宮的奉移之期,全體國務員及滿蒙王公大臣都來向光緒帝和隆裕行最後的大禮。滿蒙王公及妃子們在溥儀的帶領行跪拜禮,國務大臣及一些政府地方官員和軍界代表則在靈前三鞠躬。這些人由趙秉鈞率領,趙秉鈞脫下大禮服,挽上了清朝的素旗褂。
突然,正在伏地痛哭的兩位老人起來走到一位西裝革履的紳士前,一位老人上前欠身為禮,道:“敢問先生是哪一國人?叫甚么名字?”
那位西裝革履的紳士道:“節庵,你莫惡作劇呀。”
“什麼東西!”這位老頭勃然扳起面孔,“你若是革命黨,就不應該來;若是大清朝的官,就應該穿起孝服來。你這個無恥的東西,虧你老著臉站在這片乾淨土地上。你帶信給奕劻那個老東西,最好莫再活在這個世界上。”
另一位老頭附和道:“問得好。”他指著那西裝革履的人道,“就是,這是個什麼東西。”
先前的那個老頭又罵了起來:“你忘了你是孫治經的兒子?你做過大清的官,你今天穿著這身衣服來行這樣的禮,來見先帝先後,你、你、你有廉恥嗎!你是個什麼東西。”
被罵的人面如土色,結結巴巴的道:“好得好,不錯,不錯,我不是東西……我不是東西。”
人們都圍攏起來,“西裝”恨不得有個地縫能鑽進去。
喧嚷的聲音傳到博儀的耳朵里,博儀正要尋問,陳寶琛師傅笑道:“皇上,這是好事,是梁鼎芬和勞乃宣在罵孫寶琦。”
接著陳寶琛介紹了孫寶琦是奕劻的親家,是故山東巡撫,辛亥時曾鬧過獨立投降孫文的。對這些小皇帝並沒有什麼大興趣,可當陳師傅介紹了梁鼎芬的事跡後,博儀激動不已.
光緒梓宮在暫安殿期間,梁鼎芬經常哭臨樣宮前,跪地不起;他每日朝奠,風雨無阻。建陵工程竣工後,梁鼎芬見陵園無樹,既不美觀,又關風水,便設法在這裡栽樹。他先派人在北京定購了三百隻陶瓷酒瓶,然後就率領十幾個人往崇陵的“寶城”上將所有的酒瓶都裝滿了潔白的雪,塞好瓶口,封上紅紙簽,上書“崇陵雪水”四字,再運回北京他們住所,寫了一份告啟,說明崇陵栽樹的理由。隨後他就每天攜著從人,用人力車載著雪水瓶,按著道路的遠近和預定拜訪的先後,到各親貴和遺臣家一一拜訪。到達某一府第後,先報名片並送雪水一瓶為禮,隨即開門見山對主人說明崇陵理宜栽樹,勸他們拿出幾個錢購買樹苗,並將捐啟遞與對方,寫明捐款數目。這些人的捐款如與其身份職位相稱,他就含笑而別;不然,他就立刻用激烈的語氣數落對方,讓他難堪。倘若至某府第拜訪某君沒有謀面,即留言於某日某時再來拜訪。這樣,梁鼎芬終於在崇陵上
栽了樹。
“真忠臣也!”溥儀讚嘆道。
“老臣一定將皇上的讚譽轉告梁鼎芬。”陳寶琛道。
跪拜鞠躬致奠後,辭靈奉安。奉安盛況不遜以前。
先用六十四人槓小請將梓宮抬至行宮前大道上,換升大槓,謂獨龍槓,由128人扛。此時,輥輬輅杖,傘亭旌旛等全副鑾駕,已由鑾輿衛準備整齊,待命發動。太寧鎮綠營馬隊在最先頭開道,一部禁衛軍及憲兵沿路警戒。鑾輿衛所屬的鑾駕範圍內,最前是32人抬的紅漆四方木架,中間裝置一根紅漆旗桿,上面掛著直幅下垂、黃帛金龍、紅火焰、上系銅鈴的一架旛桿。旛桿後面,有木製采漆的斧鉞棍、熊虎常旗。其後是一班滿洲執事,執大門一對、小旂旒八根,形式相同,俱用紅漆桿挑著直幅黃帛、金龍、紅邊的“驅路”。其次是大轎和小轎。隨後是采綢扎的影亭,跟著一柄黃緞繡花傘。下面金鼓樂器和笙管笛蕭樂器各一班。再次是身穿孝衣的二排人,手托木盤,盤內放著檀香爐,燃著檀香,分左右二班,發出嗚嗚哇哇的哀聲。另有一班身穿孝衣的人沿路向天空和路上撒紙錢,所過的路上都鋪得滿滿的。隨後就是由禁衛軍步隊所組成的儀仗隊,官長抱刀,士兵荷槍上刺刀。這一方陣的後面,便是和尚方陣、道士方陣、尼姑方陣、道姑方陣、喇嘛方陣,相連一里左右;他們都穿著本教的法衣,手執法器,不斷地吹奏念經。再後就是由皇帝溥儀率領的執拂恭送的王大臣了。王公大臣一律穿著青布袍褂、青布靴子,戴著去掉頂翎的秋帽。槓後一隊人全身行獵裝束,另有一些車輛和備差員工人等。
奉安隊伍直達崇陵牌樓門。隨即換了六十四人槓,抬至地宮門外,按梓宮安放於特備的車上,隨著“響尺”有節奏的響聲,靈車升堂人殿,移上了石床。之後,欽天監指揮槓夫將梓宮按山向奉安於石床中央的“金井”上面。隨後同樣將隆裕太后的梓宮奉安於梓宮左傍齊頭微低一些的位置。合了葬,奉安禮成,即布置殉葬事宜。人們把石桌、供器、萬年燈,冊寶以及帝後生前用過的衣被、文玩、金銀器皿以及佛經、香料、金玉等貴重鎮壓品等等運至地宮,布置妥當後,恭送人員先後退出地宮。
就要關閉石門了,突然,一個老頭一瘸一拐地往地宮衝去。人們正駭異無措之時,有人叫道:
“梁大人要殉葬,梁大人要殉葬!”
人們明白過來,這是梁鼎芬要隨先帝而去,主事人便急命梁的親隨忙把梁鼎芬背出地宮。
四道石門砰然落下。
博儀剛回到京城,卻意外地接到袁世凱大總統的報告——
大清皇帝陛下:
中華民國大總統謹致書大清皇帝陛下:前於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大清隆裕皇太后懿旨,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政體,命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合滿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大中華民國。鏇經國民公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受任以來,兩穩於茲,深虞險越。今幸內亂已平,大局安定,於中華民國二年十月六日經國民公舉為正式大總統。國權實行統一,友邦皆已承認,於是年十月十日受任。凡我五族人民皆有進於文明,躋於太平之希望。此皆仰荷大清隆裕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為公、唐虞揖讓之盛軌,乃克臻此。我五族人民感戴茲德,如日月之照臨,山河之涵育,久而彌昭,遠而彌摯。維有董督國民,事新治亂,恪守優待條件,使民國鞏固,五族協和,庶有以慰大清隆裕皇太后在天之靈。用特報告,並祝萬福。
大中華民國二年十月十九日 袁世凱
在養心殿里內務府大臣世續讀完袁世凱的報告,道:“我曾問過袁弟,我說:‘你別忘了本啊!’他說:‘大哥,你放心,我是大清的。’從這報告來看,他沒忘本啊。”
瑾皇太妃說:“我們原先是不是看錯了袁世凱?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載濤道:“袁世凱是不是曹操?”
世續道:“項城當年和徐世昌、馮國庫、段棋瑞說過,對民軍只可智取,不可力敵,徐、馮、段這才答應辦共和國。也許這是智取?”
不知是誰在人堆里說道:“我早說過,那個優待條件里的‘辭位’的‘辭”字有意思。為什麼不用退位、遜位,袁宮保單寫成個辭位呢?‘辭’者,暫別之意也。”
另一位說:“大總統常說‘辦共和’辦的怎樣。既然是‘辦’,就是試行的意思。”
載濤道:“鐵良也從日本回來了,日本人也願意為我們恢復祖業出力,不過,我對日本人,不是太放心。”
“鐵良回來了!”人們齊聲地在養心殿里小聲地重複著。
聽了這些,小溥儀不是太懂,鐵良回來了為什麼會在這些人中間引起震動,他更是不甚明了。但有一點他是非常明白的:這些人都是為了他,為了他的地位,為了他權威。
世續又道:“咱們想想看,項城的‘政非舊不舉,人非舊不用’是啥意思?他的‘優容前清耆舊’是啥意思?他親自打電報邀請大清老臣來北京委以重任是什麼意思?這都說明項城要還政於清。”
博倫是國務員,是袁世凱身邊的紅人,他見世續——袁世凱的義兄——滔滔說個不停,不願落後,也道:“前些天,咱大清的東三省總督趙爾類應大總統邀請之京,做參政,又做清史館館長,袁世凱對他說:‘此日所為,皆所以維護皇室,曾商之於世續,謀欲卸肩。世續言無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忍辱負重,蹈此濁流。”
袁世凱給博儀的報告迅速傳開。勞乃宣便寫了《共和正解》、《續共和正解》、《君主民主平議》三篇文章,並把它們印刷成冊,發行各處。勞乃宣把這小冊子送給徐世昌兩套,托徐世昌把其中的一套轉呈袁世凱。袁世凱見上面寫道:“項城之心實未嘗忘大清”,“實有不可告人之苦心也”。又寫道:“轉圓之法,唯有還政於清室,定國名為‘中華國’,以‘共和’紀年,大清皇帝封項城為王爵,世襲罔替,所以報項城之勳勞,亦以保項城之身家也。”
袁世凱測覽了一下小冊子,搖頭大笑:“唉呀,真有這樣的讀書人,可愛,可愛!”
王公舊成可是笑逐顏開,情不自禁。皇宮裡,人人歡喜,都以為皇上很快就會復辟,很快就會日月重光。王爺載灃、皇叔載濤等往養心殿來的次數越來越多,王公們到養心殿覲見皇上和太妃的人也越來越多。就連太監宮女們也是個個喜上眉梢。
宮中最高興的人是張謙和,隆裕大後殯天后,張蘭德便攜億萬家財到天津租界去過逍遙日子去了,這宮中的權威,也就數張謙和最高,若皇帝復辟,身為萬歲爺宮中的總管、萬歲爺的啟蒙罕達,其地位之尊崇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張謙和的臉上總是掛著笑,有時在睡夢中,還能把自己笑醒。他瞅皇上的時候,能盯著看一個時辰都不眨眼,目光中溢滿了快意。
博儀當然也萬分高興,自從人宮,他從沒有見宮裡人這樣快樂過--從沒有見宮裡人因自己、因他皇上受到大總統的尊寵而這樣快樂過。
參考資料:
http://bbs.cn.yahoo.com/message/read_-JUMyJUExJUQ0JUEz_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