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
闞澤密獻詐降書 龐統巧授連環計
簡介
東吳參謀闞澤獻詐降書。
二蔡使人密告黃蓋受刑之事,操不疑澤,令還東吳。
操對甘寧、黃蓋之降持疑,蔣乾願往東吳探聽虛實。
龐統受周瑜之命隨蔣乾見操,獻連環計後回東吳。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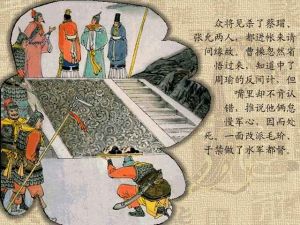 《三國演義》第四十七回
《三國演義》第四十七回卻說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好學,與人傭工,嘗借人書來看,看過一遍,更不遺忘;口才辨給,少有膽氣。孫權召為參謀,與黃蓋最相善。蓋知其能言有膽,故欲使獻詐降書。澤欣然應諾曰:“大丈夫處世,不能立功建業,不幾與草木同腐乎!公既捐軀報主,澤又何惜微生!”黃蓋滾下床來,拜而謝之。澤曰:“事不可緩,即可便行。”蓋曰:“書已修下了。”澤領了書,只就當夜扮作漁翁,駕小舟,望北岸而行。
是夜寒星滿天。三更時候,早到曹軍水寨。巡江軍士拿住,連夜報知曹操。操曰:“莫非是奸細么?”軍士曰:“只一漁翁,自稱是東吳參謀闞澤,有機密事來見。”操便教引將入來。軍士引闞澤至,只見帳上燈燭輝煌,曹操憑几危坐,問曰:“汝既是東吳參謀,來此何乾?”澤曰:“人言曹丞相求賢若渴,今觀此問,甚不相合。黃公覆,汝又錯尋思了也!”操曰:“吾與東吳旦夕交兵,汝私行到此,如何不問?”澤曰:“黃公覆乃東吳三世舊臣,今被周瑜於眾將之前,無端毒打,不勝忿恨。因欲投降丞相,為報仇之計,特謀之於我。我與公覆,情同骨肉,徑來為獻密書。未知丞相肯容納否?”操曰:“書在何處?”闞澤取書呈上。
操拆書,就燈下觀看。書略曰:“蓋受孫氏厚恩,本不當懷二心。然以今日事勢論之:用江東六郡之卒,當中國百萬之師,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吳將吏,無有智愚,皆知其不可。周瑜小子,偏懷淺戇,自負其能,輒欲以卵敵石;兼之擅作威福,無罪受刑,有功不賞。蓋系舊臣,無端為所摧辱,心實恨之!伏聞丞相誠心待物,虛懷納士,蓋願率眾歸降,以圖建功雪恥。糧草軍仗,隨船獻納。泣血拜白,萬勿見疑。”曹操於几案上翻覆將書看了十餘次,忽然拍案張目大怒曰:“黃蓋用苦肉計,令汝下詐降書,就中取事,卻敢來戲侮我耶!”便教左右推出斬之。左右將闞澤簇下。澤面不改容,仰天大笑。操教牽回,叱曰:“吾已識破奸計,汝何故哂笑?”澤曰:“吾不笑你。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操曰:“何不識人?”澤曰:“殺便殺,何必多問!”操曰:“吾自幼熟讀兵書,深知奸偽之道。汝這條計,只好瞞別人,如何瞞得我!”澤曰:“你且說書中那件事是奸計?”操曰:“我說出你那破綻,教你死而無怨:你既是真心獻書投降,如何不明約幾時?你今有何理說?”闞澤聽罷,大笑曰:“虧汝不惶恐,敢自誇熟讀兵書!還不及早收兵回去!倘若交戰,必被周瑜擒矣!無學之輩!可惜吾屈死汝手!”操曰:“何謂我無學?”澤曰:“汝不識機謀,不明道理,豈非無學?”操曰:“你且說我那幾般不是處?”澤曰:“汝無待賢之禮,吾何必言!但有死而已。”操曰:“汝若說得有理,我自然敬服。”澤曰:“豈不聞‘背主作竊’,不可定期?倘今約定日期,急切下不得手,這裡反來接應,事必泄漏。但可覷便而行,豈可預期相訂乎?汝不明此理,欲屈殺好人,真無學之輩也!”操聞言,改容下席而謝曰:“某見事不明,誤犯尊威,幸勿掛懷。”澤曰:“吾與黃公覆,傾心投降,如嬰兒之望父母,豈有詐乎!”操大喜曰:“若二人能建大功,他日受爵,必在諸人之上。”澤曰:“某等非為爵祿而來,實應天順人耳。”操取酒待之。
少頃,有人入帳,於操耳邊私語。操曰:“將書來看。”其人以密書呈上。操觀之,顏色頗喜。闞澤暗思:“此必蔡中、蔡和來報黃蓋受刑訊息,操故喜我投降之事為真實也。”操曰:“煩先生再回江東,與黃公覆約定,先通訊息過江,吾以兵接應。”澤曰:“某已離江東,不可復還。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操曰:“若他人去,事恐泄漏。”澤再三推辭;良久,乃曰:“若去則不敢久停,便當行矣。”操賜以金帛,澤不受。辭別出營,再駕扁舟,重回江東,來見黃蓋,細說前事。蓋曰:“非公能辯,則蓋徒受苦矣。”澤曰;“吾今去甘寧寨中,探蔡中、蔡和訊息。”蓋曰:“甚善。”澤至寧寨,寧接入,澤曰:“將軍昨為救黃公覆,被周公瑾所辱,吾甚不平。”寧笑而不答。正話間,蔡和、蔡中至。澤以目送甘寧,寧會意,乃曰:“周公瑾只自恃其能,全不以我等為念。我今被辱,羞見江左諸人!”說罷,咬牙切齒,拍案大叫。澤乃虛與寧耳邊低語。寧低頭不言,長嘆數聲。蔡和、蔡中見寧、澤皆有反意,以言挑之曰:“將軍何故煩惱?先生有何不平?”澤曰:“吾等腹中之苦,汝豈知耶!”蔡和曰:“莫非欲背吳投曹耶?”闞澤失色,甘寧拔劍而起曰:“吾事已為窺破,不可不殺之以滅口!”蔡和、蔡中慌曰:“二公勿憂。吾亦當以心腹之事相告。”寧曰:“可速言之!”蔡和曰:“吾二人乃曹公使來詐降者。二公若有歸順之心,吾當引進。”寧曰:“汝言果真?”二人齊聲曰;“安敢相欺!”寧佯喜曰;“若如此,是天賜其便也!”二蔡曰:“黃公覆與將軍被辱之事,吾已報知丞相矣。”澤曰:“吾已為黃公覆獻書丞相,今特來見興霸,相約同降耳。”寧曰:“大丈夫既遇明主,自當傾心相投。”於是四人共飲,同論心事。二蔡即時寫書,密報曹操,說“甘寧與某同為內應。”闞澤另自修書,遣人密報曹操,書中具言:黃蓋欲來,未得其便;但看船頭插青牙旗而來者,即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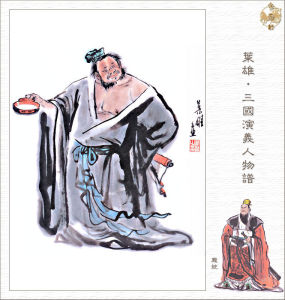 龐統
龐統卻說曹操連得二書,心中疑惑不定,聚眾謀士商議曰:“江左甘寧,被周瑜所辱,願為內應;黃蓋受責,令闞澤來納降:俱未可深信。誰敢直入周瑜寨中,探聽實信?”蔣乾進曰:“某前日空往東吳,未得成功,深懷慚愧。今願捨身再往,務得實信,回報丞相。”操大喜,即時令蔣幹上船。乾駕小舟,逕到江南水寨邊,便使人傳報。周瑜聽得乾又到,大喜曰:“吾之成功,只在此人身上!”遂囑付魯肅:“請龐士元來,為我如此如此。”原來襄陽龐統,字士元,因避亂寓居江東,魯肅曾薦之於周瑜。統未及往見,瑜先使肅問計於統曰:“破曹當用何策?”統密謂肅曰:“欲破曹兵,須用火攻;但大江面上,一船著火,余船四散;除非獻‘連環計’,教他釘作一處,然後功可成也。”肅以告瑜,瑜深服其論,因謂肅曰:“為我行此計者,非龐士元不可。”肅曰:“只怕曹操奸猾,如何去得?”周瑜沉吟未決。正尋思沒個機會,忽報蔣乾又來。瑜大喜,一面分付龐統用計;一面坐於帳上,使人請乾。
乾見不來接,心中疑慮,教把船於僻靜岸口纜系,乃入寨見周瑜。瑜作色曰:“子翼何故欺吾太甚?”蔣乾笑曰:“吾想與你乃舊日弟兄,特來吐心腹事,何言相欺也?”瑜曰:“汝要說我降,除非海枯石爛!前番吾念舊日交情,請你痛飲一醉,留你共榻;你卻盜吾私書,不辭而去,歸報曹操,殺了蔡瑁、張允,致使吾事不成。今日無故又來,必不懷好意!吾不看舊日之情,一刀兩段!本待送你過去,爭奈吾一二日間,便要破曹賊;待留你在軍中,又必有泄漏。”便教左右:“送子翼往西山庵中歇息。待吾破了曹操,那時渡你過江未遲。”蔣乾再欲開言,周瑜已入帳後去了。
左右取馬與蔣乾乘坐,送到西山背後小庵歇息,撥兩個軍人伏侍。乾在庵內,心中憂悶,寢食不安。是夜星露滿天,獨步出庵後,只聽得讀書之聲。信步尋去,見山岩畔有草屋數椽,內射燈光。乾往窺之,只見一人掛劍燈前,誦孫、吳兵書。乾思:“此必異人也。”叩戶請見。其人開門出迎,儀表非俗。乾問姓名,答曰:“姓龐,名統,字士元。”乾曰:“莫非鳳雛先生否?”統曰:“然也。”乾喜曰:“久聞大名,今何僻居此地?”答曰:“周瑜自恃才高,不能容物,吾故隱居於此。公乃何人?”乾曰:“吾蔣乾也。”統乃邀入草庵,共坐談心。乾曰:“以公之才,何往不利?如肯歸曹,幹當引進。”統曰:“吾亦欲離江東久矣。公既有引進之心,即今便當一行。如遲則周瑜聞之,必將見害。”於是與乾連夜下山,至江邊尋著原來船隻,飛棹投江北。
既至操寨,乾先入見,備述前事。操聞鳳雛先生來,親自出帳迎入,分賓主坐定,問曰:“周瑜年幼,恃才欺眾,不用良謀。操久聞先生大名,今得惠顧,乞不吝教誨。”統曰:“某素聞丞相用兵有法,今願一睹軍容。”操教備馬,先邀統同觀旱寨。統與操並馬登高而望。統曰:“傍山依林,前後顧盼,出入有門,進退曲折,雖孫、吳再生,穰苴復出,亦不過此矣。”操曰:“先生勿得過譽,尚望指教。”於是又與同觀水寨。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皆有艨艟戰艦,列為城郭,中藏小船,往來有巷,起伏有序,統笑曰:“丞相用兵如此,名不虛傳!”因指江南而言曰:“周郎,周郎!剋期必亡!”操大喜。回寨,請入帳中,置酒共飲,同說兵機。統高談雄辯,應答如流。操深敬服,殷勤相待。統佯醉曰:“敢問軍中有良醫否?”操問何用。統曰:“水軍多疾,須用良醫治之。”時操軍因不服水土,俱生嘔吐之疾,多有死者,操正慮此事;忽聞統言,如何不問?統曰:“丞相教練水軍之法甚妙,但可惜不全。”操再三請問。統曰:“某有一策,使大小水軍,並無疾病,安穩成功。”操大喜,請問妙策。統曰:“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風浪不息;北兵不慣乘舟,受此顛播,便生疾病。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或三十為一排,或五十為一排,首尾用鐵環連鎖,上鋪闊板,休言人可渡,馬亦可走矣,乘此而行,任他風浪潮水上下,復何懼哉?”曹操下席而謝曰:“非先生良謀,安能破東吳耶!”統曰:“愚淺之見,丞相自裁之。”操即時傳令,喚軍中鐵匠,連夜打造連環大釘,鎖住船隻。諸軍聞之,俱各喜悅。後人有詩曰:“赤壁鏖兵用火攻,運籌決策盡皆同。若非龐統連環計,公瑾安能立大功?”
龐統又謂操曰:“某觀江左豪傑,多有怨周瑜者;某憑三寸舌,為丞相說之,使皆來降。周瑜孤立無援,必為丞相所擒。瑜既破,則劉備無所用矣。”操曰:“先生果能成大功,操請奏聞天子,封為三公之列。”統曰:“某非為富貴,但欲救萬民耳。丞相渡江,慎勿殺害。”操曰:“吾替天行道,安忍殺戮人民!”統拜求榜文,以安宗族。操曰:“先生家屬,現居何處?”統曰:“只在江邊。若得此榜,可保全矣。”操命寫榜僉押付統。統拜謝曰:“別後可速進兵,休待周郎知覺。”操然之。統拜別,至江邊,正欲下船,忽見岸上一人,道袍竹冠,一把扯住統曰:“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闞澤下詐降書,你又來獻連環計:只恐燒不盡絕!你們把出這等毒手來,只好瞞曹操,也須瞞我不得!”諕得龐統魂飛魄散。正是:莫道東南能制勝,誰雲西北獨無人?
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賞析
本回演義是連環三計的最後一出連環計,龐統獻計將船隻連為一體,便為的就是將那曹軍一網打盡,然而曹操之所以接納此計,則確實有他的緣故。
史實上赤壁雖如龐統獻上連環計,但是正如演義中所言的一般,曹操率領的北軍不習水戰,在船隻上受顛簸之苦,曹操還是將大小船隻連為一體,最終被周瑜燒了精光。不過演義本回因那連環計而提及的一事對曹軍的影響只怕比周瑜火燒曹船也不虞多讓。便是:“時操軍因不服水土,俱生嘔吐之疾,多有死者。”也正是因為如此,演義中曹操才接納龐統的連環計,而在史書上這個因素則大大加強。
《三國志.武帝紀》的記載在談到赤壁戰敗的原因中稱:“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將赤壁戰敗主要歸咎于軍中沾染上的疾病。
《三國志.先主傳》的記載中稱:“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除了火燒赤壁外,也同樣也提及了曹操軍中沾染上的疾病。
《三國志.吳主傳》的記載中稱:“瑜、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也談到了曹軍沾染的疾病一事。
《三國志.周瑜傳》的記載除了因周瑜主要策劃火燒赤壁一事對火燒一事談的比較具體外,也談到了曹軍沾染疾病一事,“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併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而且在周瑜在江東政權討論是否與曹操作戰時也談到了疾病對曹軍的影響:“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閒,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
也就是說,三國志中各方在談到赤壁一戰的時候,都不忘提到疾病對曹軍的影響一事,可見當時曹軍所染的疾病對赤壁曹軍戰敗影響甚大。那赤壁曹軍到底得的什麼病呢?
若真是如演義中所說,是由於北軍不習慣水戰,暈船而導致的上吐下瀉,而斷不然影響如此巨大,北軍並不都在船上,何況哪有暈船在下了船之後還不好的,所以更可能是一場流行性疾病,對於疾病的種類,已經有很多文章做過敘述,大致認為是血吸蟲病,瘧疾,斑疹傷寒等幾種疾病。在下並非是專業醫生,對疾病也沒有研究,對這些疾病也不熟悉,只能從歷史角度上分析一下這場疾病的特點。
曹軍得病在周瑜的戰前分析中便已經預料到,可見他對北軍會得病是有預見性的,那怎么才可能有如此的預見性呢?可能性有二:
1.江南盛行的一種流行病,北方沒有,而南方人包括荊州和江東兵有了抵抗能力,但是以北方人為主的曹軍初來乍到,原先在征討荊州時影響還不明顯,尚可擊敗劉備軍,但是到了後期則受到極大影響,如此導致戰鬥力大弱,敗於劉備周瑜聯軍之手,上面提到的那幾種病都有可能,而江東也確實很可能有這樣的流行性疾病,如孫策斬殺的于吉在江東便是以符水治病使得吳人眾多歸附,一般來說,治療流行病往往能得到極高的名聲,因為治療的是同一種病,那使用的藥方單一,很符合符水所用,而且流行病危害廣,治療成功救治的人多,影響大,所以很可能于吉治療的便是這類江東的流行性疾病。此外,醫聖張仲景在長沙做太守時長沙一帶也爆發過大規模的流行病,這也很可能是流行於江南一帶的地方性流行病。
但是這個可能性也有一些疑問,假如真有江東流行性疾病的話,則應該不分貴賤,一視同仁才對,然而卻不見在赤壁一戰有曹操的哪一位重臣死亡,而同樣是流行性疾病,在建安22年爆發的大瘟疫中,建安七子中王粲,陳琳,劉楨,應訰四人死於此次瘟疫,假若說真是極強的流行性疾病,則曹操主要將領謀士幾乎一個都沒染病,全死的是下面士兵,則這個病也太過勢利了些,當然,曹操重臣待遇比士兵好,負擔比士兵小,(一些將領的抵抗力或許也比較強,不過那些文臣則未必比一般的士兵好了。)防護醫療措施比士兵嚴密都是他們不生病的原因之一,但是和曹軍全面的大疾比起來,這個生病的幾率太小了些。
2.可能就是一般性的水土不服而已,雖然說感染上當地的傳染病也可以說是一種水土不服,但是一般性的水土不服就只是指不習慣於當地的飲食生活習慣而已,許多人在來到一個與原本地區相差甚大的地區後對於當地的飲食,生活,氣候會有極大的反應,當反差越大時這種情況就越明顯,這是遠征軍隊通常會遇到的問題,(尤其是古代遠征軍不可能象現代軍隊一樣依賴後方的補給,只能就地取食,影響更大了。)尤其在氣候上最為明顯,北方冬天寒冷,空氣乾燥,南方夏天炎熱,空氣潮濕,這對於不同環境的人來說都是大敵,這還是指一般意義上的南北而言,假如算上北方草原和南方叢林地區,那差別就更大了,中國對北方草原遊牧民族如匈奴突厥和南部的南詔,安南政權的遠征,往往相當數量的士兵損失在不適應當地的水土之上。這也是很少出現類似蒙古遠征那種情況的原因之一。(氣候對於戰爭影響最大的例子莫過於拿破崙和希特勒對俄國遠征時嚴寒的打擊了。)一般的早期帝國中心區域都建立在相同的氣候環境帶之下,如中國中原地區,再慢慢的逐步擴張,如北方攻打南方往往先要奪取與南方環境相近的幾個地區,以這些地區為據點,一步步的蠶食,比如奪取荊州後對於江東則占有優勢,則不單是因為荊州在江東上游的關係,也是因為荊州氣候水土環境比較北方而言,接近於江東,不至於有強烈的水土不服現象,同樣的,對西疆用兵則要依賴於關中雍涼地區,對東北的用兵則要立足於遼東,假如所依賴的地區人口稀少,那則要大力遷徙人口或者等待其休養生息恢復,這都是要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自然,假如征討雙方實力差距太大,如諸葛亮征南中,或者得到當地人的支持或者當地抵抗力量沒有核心,如清朝對南明弘光政權的攻打,則可以快速的控制該地區,但是之後的統治尤其是地方性統治還是要依賴於當地人,如諸葛亮對南中的處理,所謂的南人治南,北人治北,都是這個道理,自然這並非是水土不服一言可以解決的了。
所以以北方士兵為主的曹軍可能就是因為單純的水土不服而導致戰鬥力下降,而荊州兵影響小得多,但是剛剛新近歸附,並不賣力,這導致與劉備周瑜聯軍對抗時屢屢失利,不得不敗退而回,而這種水土不服在回到北方後就自然好了,而假如是流行性疾病的話,曹軍的實力必然大損,即便在回到北方後也不能痊癒,但是從日後的情況下,曹操的實力並沒有大幅度下降的表現。而且這也能解釋曹操主要將領和謀士大都沒有染病,因為他們的待遇遠遠高於一般的士兵,對水土不服的抵抗力自然也大大加強了。(假如是這樣的話,曹軍只要休養段時間便可以適應,那從速擊敗曹操則顯得相當重要。)
但是這種可能性也有很大問題,北方征討南方,南方征討北方都是很常見的,雖然都有水土不服的現象,也有影響至整個戰局的。但是發生的幾率畢竟不大,象赤壁一般的情況應該屬於特殊例子,而且三國志中的記載曹軍死者眾多,一般的水土不服很難達到這樣的情況,更象是一種流行性疾病了。
赤壁之戰很可能是當地流行性疾病和水土不服的混合品種吧,具體曹軍到底得了什麼病,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漢末時期確實發生過許多場大瘟疫。
漢末人口銳減,一般人大都歸咎於漢末三國的戰火,但是憑心而論,現在將戰爭的危害拔的很高往往是因為眾人對戰爭的厭惡,實際上與戰爭比較起來,饑荒和大規模的流行性疾病才是更可怕的,二戰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死亡人數據說在5500萬到6000萬,也有說死傷加起來近2億的說法,而當年的黑死病據說死了2500萬,別看人比二戰死的少,但是因黑死病死亡使得歐洲人口減少三分之一,比率要大得多。1918年流感則是死亡人數在2000萬到5000萬,超過一戰死亡人數。美洲幾千萬印第安人在天花的入侵之下幾乎滅絕則是相當出名的例子了。(不過也是萬幸,假若美洲有一種流行病是舊大陸沒有的,而舊大陸只怕不比印第安人好到哪裡去。)
而漢末之所以人口銳減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和漢末連續爆發大瘟疫有關,如上文提到的建安22年的大瘟疫使得建安七子中的四人死亡。醫聖張仲景在這段時間族人因傷寒致死的便有十分之七,可見當時瘟疫之猖獗,太平道五斗米道等宗教組織的流行便與漢末的這場大瘟疫大有干係。(凡有人類無法控制的大災禍時,人類便常常救助於神靈等虛無縹緲的東西,日後佛教的盛行也是得益於五胡亂華後南北連續的戰亂災害的關係。太平道五斗米道很可能掌握了某些可以控制瘟疫的藥物,以符水等方式治療並拉攏信徒。)
而三國頻發的戰爭則進一步觸發了瘟疫,戰場,屍體,流民就不說了,軍隊本身就是最容易導致瘟疫的部分,軍隊都是集體生活,相互接觸多,傳染快,且軍隊流動性強,比一般的人容易接觸疾病,雖然軍人的體質往往比一般人好,軍隊又有組織性,利於處置流行病,但是一旦得病,爆發起來也是相當快的。之前有一章談到官渡人數曹操為何這么少的時候,其中很可能也有漢末瘟疫導致軍隊人數減少的關係,赤壁則更是一大突出例子了。
所謂大災必有大聖出現,瘟疫的流行也使得張仲景,華佗等名醫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尤其是張仲景,因為族人多死於傷寒,立志於對傷寒的研究,寫成《傷寒雜病論》等書,乃是中醫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代大師,後世稱之為“醫聖”,這或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回評
毛宗崗批語
欺庸人易,欺奸雄難。黃蓋受杖,猶可不死於杖;闞澤獻書,宜其必死於書。而卒能不死而成功者,以得說奸雄之法也。說奸雄之法與說英雄之法,皆不當用順,而當用逆。英雄所自負者義耳,張遼之說關公,妙在責其輕死之非義;奸雄所自負者智耳,闞澤之說曹操,妙在笑其料事之不明:所謂用逆而不用順者也。若使遼而甘言卑說,則公之拒愈峻;若使澤而伏地陳乞,則澤之死愈速矣。
前回寫甘寧,此回寫闞澤。而極寫闞澤,必先極寫曹操;不寫曹操之奸,不顯闞澤之巧。若彼不知為苦肉計而欺之不難,惟彼既知為苦肉計而欺之之為難也。彼不知為詐降書而中之不足奇,惟彼既知為詐降書而我終能中之之為奇也。計雖巧,而無行計之人則亦拙;計雖庸,而有行計之人則不庸耳。
蔡和、蔡中之詐降,兩人同來者也;黃、闞二人之詐降,妙在一來而一未來。二蔡之詐降,竟以身來而不必先以書來者也;黃蓋之詐降,妙在身不來而書來。二蔡之詐降,來而不返者也;闞澤之詐降,妙在速返,又妙在初時不肯復返,而次後乃欲速返,一似速返則得返,不速返則不得返者。一般是降,卻有幾樣降法;一般是詐,卻有幾樣詐法。愈出愈幻,非復讀者意計之所及。
文章之妙,有各不相照者:二蔡現在,而黃蓋之降書,初不煩二蔡為通;闞澤渡江,而二蔡之報信,不即使闞澤為奇。文章之妙,又有各不相照而暗暗相照者:黃蓋但以其謀告闞澤〔而闞澤〕獻降書之後,比然添出一甘寧;闞澤未以其謀告甘寧,而甘寧欺二蔡之言,有如關會乎闞澤。寫來真是變幻可喜。
御戰船之法,有彼方連而我利其斷者,有彼方斷而我利其連者。黃祖之舟,以大索相連,沖之不能入,甘寧以刀斷之,而艨艟遂橫,此則利其斷也;曹操之舟,散而不聚,燒之不能盡,龐統以環連之,而火攻始便,此則利其連也。兵法變化無常,孫臏以減灶勝,而虞詡又以增灶勝,隨機而應,豈可執一論哉!
連環計一見於王允,再見於龐統。前之環虛名也,後之環實事也。王允以貂蟬雙鎖董、呂二人,如環之互動相連,故名連環耳。每見近日演<連環記>者,乃作呂布以玉連環贈與貂蟬,此又是傳奇平空妝點出來,豈連環命名之意乎?若龐統則不然,實實以鐵環連鎖操船,與取名連環者不同。前以貂蟬為環,止有一環;後以鐵環為環,乃有無數連環。前虛後實,前少後多,各極其妙。
北兵多病,而龐統以連環之方治之,此藥毋乃太毒乎!雖然,賣毒藥者不獨一龐統也,黃蓋、闞澤皆是也。蓋之藥甚苦,澤之藥甚甘,統之藥甚辣,合苦者、甘者、辣者金成一劑毒藥;然後周郎煎之以火,孔明扇之以風:而八十三萬大軍,遂無一人有起色矣。
李贄總評
黃蓋、闞澤、龐統,大是用得。蓋劃策不難,全在人能行之,如苦肉、連環二計,誰不知之?若無黃蓋、闞澤、龐統,便成畫柄(餅)矣。我故曰:劃策不難,但行之難得其人耳。誠得其人,無不行之策也。
老瞞雖奸,其如諸君子誠篤不欺何,畢竟奸不敵誠也。
鍾敬伯總評
妙策必待人成,當時苦肉計行,若無連環繼之,縱用一火攻,亦未盡絕也。老瞞雖奸,士元弄之掌股。可見黃蓋有硬骨,闞澤有油嘴,龐統更有毒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