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目
曹操倉亭破本初 玄德荊州依劉表
簡介
袁紹悔不聽田豐之言,致此敗;卻又忌殺田豐。
操引得勝之兵陳列河上,受到土人歡迎。操號令三軍勿要擾民。
操從程昱“十面埋伏”之計,誘袁紹至河上,背水死戰大敗袁軍於倉亭。
操因劉備犯許都,提大兵往汝南迎劉備。
穰山一仗,備勝操敗;但接著操轉敗為勝。
劉備至漢江,從孫乾計歸荊州劉表,劉表迎劉備入荊州。
紹不聽謀士深溝高壘之計,往拒操兵。
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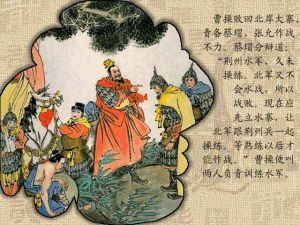 《三國演義》第三十一回
《三國演義》第三十一回卻說曹操乘袁紹之敗,整頓軍馬,迤邐追襲。袁紹幅巾單衣,引八百餘騎,奔至黎陽北岸,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前事訴與義渠。義渠乃招諭離散之眾,眾聞紹在,又皆蟻聚。軍勢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於帳中聞遠遠有哭聲,遂私往聽之。卻是敗軍相聚,訴說喪兄失弟,棄伴亡親之苦,各各捶胸大哭,皆曰:“若聽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禍!”紹大悔曰:“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見之耶!”次日,上馬正行間,逢紀引軍來接。紹對逢紀曰:“吾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逢紀因譖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料!”袁紹大怒曰:“豎儒怎敢笑我!我必殺之!”遂命使者齎寶劍先往冀州獄中殺田豐。
卻說田豐在獄中。一日,獄吏來見豐曰:“與別駕賀喜!”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大敗而回,君必見重矣。”豐笑曰:“吾今死矣!”獄吏問曰:“人皆為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外寬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矣。”獄吏未信。忽使者齎劍至,傳袁紹命,欲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豐曰:“吾固知必死也。”獄吏皆流淚。豐曰:“大丈夫生於天地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乃自刎於獄中。後人有詩曰:“昨朝沮授軍中失,今日田豐獄內亡。河北棟樑皆折斷,本初焉不喪家邦!”田豐既死,聞者皆為嘆惜。
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立後嗣。紹所生三子長子袁譚字顯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奕,出守幽州;三子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出,生得形貌俊偉,紹甚之,因此留在身邊。自官渡兵敗之後,劉氏勸立尚為後嗣,紹乃與審配、逢紀、辛評、郭圖四人商議、原來審、逢二人,向輔袁尚;辛、郭二人,向輔袁譚;四人各為其主。當下袁紹謂四人曰:“今外患未息,內事不可不早定,吾將議立後嗣:長子譚,為人性剛好殺;次子熙,為人柔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公等之意若何?”郭圖曰:“三子之中,譚為長,今又居外;主公若廢長立幼,此亂萌也。今軍威稍挫,敵兵壓境,豈可復使父子兄弟自相爭亂耶?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立嗣之事,毋容多議。”袁紹躊躇未決。忽報袁熙引兵六萬,自幽州來;袁譚引兵五萬,自青州來;外甥高幹亦引兵五萬,自并州來:各至冀州助戰。紹喜,再整人馬來戰曹操。時操引得勝之兵,陳列於河上,有土人簞食壺漿以迎之。操見父老數人,鬚髮盡白,乃命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丈多少年紀?”答曰:“皆近百歲矣。”操曰:“吾軍士驚擾汝鄉,吾甚不安。”父老曰:“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人殷馗善曉天文,夜宿於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於乾象,正照此間。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今以年計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斂於民,民皆怨之。丞相興仁義之兵,弔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眾,正應當時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何敢當老丈所言?”遂取酒食絹帛賜老人而遣之。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於是軍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前至倉亭下寨。操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兩軍相對,各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紹亦引三子一甥及文官武將出到陣前。操曰:“本初計窮力盡,何尚不思投降?直待刀臨項上,悔無及矣!”紹大怒,回顧眾將曰:“誰敢出馬?”袁尚欲於父前逞能,便舞雙刀,飛馬出陣,來往賓士。操指問眾將曰:“此何人?”有識者答曰:“此袁紹三子袁尚也。”言未畢,一將挺槍早出。操視之,乃徐晃部將史渙也。兩騎相交,不三合,尚撥馬刺斜而走。史渙趕來,袁尚拈弓搭箭,翻身背射,正中史渙左目,墜馬而死。袁紹見子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擁將過來,混戰大殺一場,各鳴金收軍還寨。
 袁紹
袁紹操與諸將商議破紹之策。程昱獻十面埋伏之計,勸操退軍於河上,伏兵十隊,誘紹追至河上,“我軍無退路,必將死戰,可勝紹矣。”操然其計。左右各分五隊。左:一隊夏侯惇,二隊張遼,三隊李典,四隊樂進,五隊夏侯淵;右:一隊曹洪,二隊張郃,三隊徐晃,四隊于禁,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為先鋒。次日,十隊先進,埋伏左右已定。至半夜,操令許褚引兵前進,偽作劫寨之勢。袁紹五寨人馬,一齊俱起。許褚回軍便走。袁紹引軍趕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軍無去路,操大呼曰:“前無去路,諸軍何不死戰?”眾軍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當先,力斬十數將。袁軍大亂。袁紹退軍急回,背後曹軍趕來。正行間:一聲鼓響,左邊夏侯淵,右邊高覽,兩軍衝出。袁紹聚三子一甥,死沖血路奔走。又行不到十里,左邊樂進,右邊于禁殺出,殺得袁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又行不到數里,左邊李典,右邊徐晃,兩軍截殺一陣。袁紹父子膽喪心驚,奔入舊寨。令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左邊張遼,右邊張郃,徑來沖寨。紹慌上馬,前奔倉亭。人馬睏乏,欲待歇息,後面曹操大軍趕來,袁紹捨命而走。正行之間,右邊曹洪,左邊夏侯惇,擋住去路。紹大呼曰:“若不決死戰,必為所擒矣!”奮力衝突,得脫重圍。袁熙、高幹皆被箭傷。軍馬死亡殆盡。紹抱三子痛哭一場,不覺昏倒。眾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嘆曰:“吾自歷戰數十場,不意今日狼狽至此!此天喪吾也!汝等各回本州,誓與曹賊一決雌雄!”便教辛評、郭圖火急隨袁譚前往青州整頓,恐曹操犯境;令袁熙仍回幽州,高幹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袁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令尚與審配、逢紀暫掌軍事。卻說曹操自倉亭大勝,重賞三軍;令人探察冀州虛實。細作回報:“紹臥病在床。袁尚、審配緊守城池。袁譚,袁熙、高幹皆回本州。”眾皆勸操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又有機謀,未可急拔。現今禾稼在田,恐廢民業,姑待秋成後取之未晚。”正議間,忽荀彧有書到,報說:“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龔都數萬之眾。聞丞相提軍出征河北,乃令劉辟守汝南,備親自引兵乘虛來攻許昌。丞相可速回軍御之。”操大驚,留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兵往汝南來迎劉備。卻說玄德與關、張、趙雲等,引兵欲襲許都。行近穰山地面,正遇曹兵殺來,玄德便於穰山下寨,軍分三隊:雲長屯兵於東南角上,張飛屯兵於西南角上,玄德與趙雲於正南立寨。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打話。玄德出馬於門旗下。操以鞭指罵曰:“吾待汝為上賓,汝何背義忘恩?”玄德曰:“汝託名漢相,實為國賊!吾乃漢室宗親,奉天子密詔,來討反賊!”遂於馬上朗誦衣帶詔。操大怒,教許褚出戰。玄德背後趙雲挺槍出馬。二將相交三十合,不分勝負。忽然喊聲大震,東南角上,雲長衝突而來;西南角上,張飛引軍衝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曹軍遠來疲睏,不能抵當,大敗而走。玄德得勝回營。
次日,又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再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玄德愈疑。忽報龔都運糧至,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救。忽又報夏侯□引軍抄背後逕取汝南,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前後受敵,無所歸矣!”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不一日,飛馬來報夏侯惇已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雲長現今被圍。玄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龔都,也被圍住了。玄德急欲回兵,又恐操兵後襲。忽報寨外許褚搦戰。玄德不敢出戰,候至天黑,教軍士飽餐,步軍先起,馬軍後隨,寨中虛傳更點。玄德等離寨約行數里,轉過土山,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曰:“休教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玄德慌尋走路。趙雲曰:“主公勿憂,但跟某來。”趙雲挺槍躍馬,殺開條路,玄德掣雙股劍後隨。正戰間。許褚追至,與趙雲力戰。背後于禁、李典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而走。聽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深山僻路,單馬逃生。
捱到天明,側首一彪軍衝出。玄德大驚,視之,乃劉辟引敗軍千餘騎,護送玄德家小前來;孫乾。簡雍,糜芳亦至,訴說:“夏侯惇軍勢甚銳,因此棄城而走。曹兵趕來,幸得雲長擋住,因此得脫。”玄德曰:“不知雲長今在何處?”劉辟曰:“將軍且行,卻再理會。”行到數里,一棒鼓響,前面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是張郃,大叫:“劉備快下馬受降!”玄德方欲退後,只見山頭上紅旗磨動,一軍從山塢內擁出,為首大將,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耶!事勢至此,不如就死!”欲拔劍自刎,劉辟急止之曰:“容某死戰,奪路救君。”言訖,便來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於馬下。
玄德正慌,方欲自戰,高覽後軍忽然自亂,一將沖陣而來,槍起處,高覽翻身落馬。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雲縱馬挺槍,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張郃。郃與雲戰三十餘合,撥馬敗走。雲乘勢衝殺,卻被郃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正奪路間,只見雲長、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相攻,殺退張郃。各出隘口,占住山險下寨。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原來張飛去救龔都,龔都已被夏侯淵所殺;飛奮力殺退夏侯淵,迤邐趕去,卻被樂進引軍圍住。雲長路逢敗軍,尋蹤而去,殺退樂進,與飛同回見玄德。
人報曹軍大隊趕來,玄德教孫乾等保護老小先行。玄德與關、張、趙雲在後,且戰且走。操見玄德去遠,收軍不趕。玄德敗軍不滿一千,狼狽而奔。前至一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玄德權且安營。土人知是玄德,奉獻羊酒,乃聚飲於沙灘之上。玄德嘆曰:“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備之命窘,累及諸君。今日身無立錐,誠恐有誤諸君。君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眾皆掩面而哭。雲長曰:“兄言差矣。昔日高祖與項羽爭天下,數敗於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四百年基業。勝負兵家之常,何可自隳其志!”孫乾曰:“成敗有時,不可喪志。此離荊州不遠。劉景升坐鎮九郡,兵強糧足,更且與公皆漢室宗親,何不往投之?”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某願先往說之,使景升出境而迎莊公”玄德大喜,便令孫乾星夜往荊州。到郡入見劉表,禮畢,劉表問曰:“公從玄德,何故至此?”乾曰:“劉使君天下英雄,雖兵微將寡,而志欲匡扶社稷。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死報之。明公與使君,同為漢室之胄;今使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乾僭言曰:不可背親而向疏。荊州劉將軍禮賢下士,士歸之如水之投東,何況同宗乎?因此使君特使乾先來拜白。惟明公命之。”表大喜曰:“玄德,吾弟也。久欲相會而不可得。今肯惠顧,實為幸甚!”蔡瑁譖曰:“不可。劉備先從呂布,後事曹操,近投袁紹,皆不克終,足可見其為人。今若納之,曹操必加兵於我,枉動干戈。不如斬孫乾之首,以獻曹操,操必重待主公也。”孫乾正色曰:“乾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忠心為國,非曹操、袁紹、呂布等比。前此相從,不得已也。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誼切同宗,故千里相投。爾何獻讒而妒賢如此耶?”劉表聞言,乃叱蔡瑁曰:“吾主意已定,汝勿多言。”蔡瑁慚恨而出,劉表遂命孫乾先往報玄德,一面親自出郭三十里迎接。玄德見表,執禮甚恭。表亦相待甚厚。玄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表遂與玄德等同入荊州,分撥院宅居住。卻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荊州投奔劉表,便欲引兵攻之。程昱曰:“袁紹未除,而遽攻荊襄,倘袁紹從北而起,勝負未可知矣。不如還兵許都,養軍蓄銳,待來年春暖,然後引兵先破袁紹,後取荊襄:南北之利,一舉可收也。”操然其言,遂提兵回許都。至建安七年,春正月,操復商議興兵。先差夏侯惇、滿寵鎮守汝南,以拒劉表;留曹仁、荀彧守許都:親統大軍前赴官渡屯紥。且說袁紹自舊歲感冒吐血症候,今方稍愈,商議欲攻許都。審配諫曰:“舊歲官渡,倉亭之敗,軍心未振;尚當深溝高壘,以養軍民之力。”正議間,忽報曹操進兵官渡,來攻冀州。紹曰:“若候兵臨城下,將至壕邊,然後拒敵,事已遲矣。吾當自領大軍出迎。”袁尚曰:“父親病體未痊,不可遠征。兒願提兵前去迎敵。”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袁譚,幽州取袁熙,并州取高幹:四路同破曹操。正是:才向汝南鳴戰鼓,又從冀北動征鼙。
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賞析
官渡之戰我們只能稱之為決定性的轉折,而不能稱為決定性的戰役,因為官渡袁紹雖敗,但是依舊保留了相當雄厚的實力,曹操只是扭轉了之前被動的局勢而已,由被動防禦轉為主動進攻,但離徹底擊潰袁紹還差的很遠,掃平袁家勢力吞併四州那是建安十二年的事了,離建安五年的官渡之戰有七年之久。
官渡雖勝,但是曹操也到了極限,糧草依舊不足,後方劉備在汝南再起,在第二年乘官渡大勝餘勇在倉亭擊敗袁紹後,便回軍擊敗劉備,劉備不得不投奔劉表,這就是本章的劇情了。
這一章有一句話挺有意思,是劉備與曹操在戰前叫陣的時候說的。
“汝託名漢相,實為國賊!吾乃漢室宗親,奉天子密詔,來討反賊!”
這以後被周瑜也說了一次,在孫權問周瑜戰和之事時,周瑜便說:“操雖託名漢相,實為漢賊。”
不過嘛,周瑜或許真說過這句話,但是劉備八成是沒說過,為什麼呢,因為曹操在建安六年還沒當丞相呢。曹操在建安十三年,也就是袁尚等人被殺,袁家勢力被徹底殲滅的第二年,才正式當上丞相,而且在之前,連丞相一職都沒。不過這點在演義里已經被忽略了,在第十四回曹操迎獻帝那章便許褚便稱曹操為丞相,可就在同一章,演義還說到操自封為大將軍武平侯(史上起初也確實如此,不過後來袁紹不高興,曹操便把大將軍稱號送給袁紹,自己領司空一職),這才幾個字,就把丞相一職送給曹操了。
這一來是小說行文方便,你想那讀者誰知道東漢時期的大將軍是幹嗎的,但是都知道這丞相是管實權的,曹大將軍或者曹司空這一說出來,這讀者誰知道是幹嗎的,可曹丞相這名號一說,大家都明白,所以作者便將曹操當丞相的時間提前了。二來也是因為曹操雖然沒有丞相的稱號,但是卻掌握著丞相的權力,稱之為相到也不為過。不過我們讀史可不能忽略這點,在建安十三年前丞相這一職業在全中國地區都沒有,你在那時說曹丞相是沒人明白的。
宰相這一職業的歷史變遷與遭遇,前人已有無數著作,在下也有寫過《痛並快樂的宰相們》,在此便不多說了,只著重說說三國演義這段時期的情況。
我們常說三國,但其實三國演義在曹丕篡位之前,各方勢力除了袁術這位被讖緯害了的偽帝外,其他勢力都是尊奉漢帝,便是以東漢為正統,沒人自封一國稱帝,在獻帝退位之前,我們說的都是東漢年間,所以關羽曹操這些三國演義的主角們,雖然三國的建立有他們的一分力,但是他們都是漢臣。所以曹操這個丞相,便要從漢朝的制度說起。
我們知秦始皇設立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職,協助皇帝處理政事,這三職極其重要,其中以丞相最有實權,對皇權產生,所以西漢後期便開始不設丞相一職,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的官號也改稱為司徒司空司馬(司馬後來改稱太尉),這便是所謂的三公,位高而無權,到了東漢。漢光武帝乃是中興漢朝的名君,他為了加強皇權,也並沒有設立丞相這一職位(所以說丞相這一職位並不是到了朱元璋才廢棄的,實際上很多朝代便沒有丞相這一職位,)而代以三公,三公也是擺設,尚書台這個皇帝秘書處才是重要的。
所以東漢一直沒有丞相,而掌握權力的要點是掌握尚書台,所以在曹操迎獻帝後他想得到什麼職位呢?
大將軍!這是東漢末年名義上的最高職務,外戚掌權時常常占有這個位置行使丞相的權力,在三公之上,百官之首啊,但是曹操得到這個位置沒多久,袁紹不滿了,曹操不想得罪袁紹,便讓位給袁紹,自己做了司空。所以在袁紹死之前,真正的百官之首還是袁紹而不是曹操。但是曹操掌握了一個法寶,便是錄尚書事。
我們說過東漢時期尚書台最為重要,曹操錄尚書事,實際上就得到了如同丞相甚至皇帝一般的權力,同時,曹操的首席謀士荀彧任職侍中,守尚書令,在曹操離開許都時,便是荀彧掌握朝中大權。(荀彧掌握了如此大的權力,曹操對其也頗有忌憚,所以在曹操受九錫一事上受到荀彧反對時,曹操便藉故將其遣出許都,荀彧不久便死。)
不過即便曹操掌握了如此大的權力,但是還是不方便,尚書台畢竟在法理上還只是皇帝的秘書處啊,所以在他掃平北方,解決了袁家的殘餘勢力之後,重新設立了丞相一職,並自己做上了其職,這樣一來,他將名義上和實際上的權力終於合而為一,也就是這時,我們認為曹操成為了東漢的獨裁者。
為什麼丞相一職這么重要呢?因為丞相這一職位可以說實際上掌握著比皇帝還要大的權力,丞相是可以開府的,就是自己設立一套班子,所謂相府十三曹,這裡的曹是部門的意思,十三曹就是十三個政府部門,這些政府部門就象日後的工部吏部等六部,掌管著全國的種種方面,而皇帝名義上可以掌握所有的權力,但是實際上常設能參與政事的班子就是尚書而已。(這也是日後尚書權重的緣故。)遠遠不及丞相的班子完善,這樣就意味著法理上丞相完全可以拋開同僚甚至皇帝,在自己的府內解決所有政務,所謂政出其門也,而曹操看中的就是這點。
曹操任職丞相時設立東曹西曹法曹,將原來在尚書的權力轉移到丞相之下,後來乾脆將尚書變為丞相的屬官,另外利用中領軍四征將軍的設立,將軍權也劃歸之下,如此一來丞相便將全國的權力都統一在自己手中,曹操屬下的官員才是掌握實權的的官員。所謂的三公和皇帝則是一個空架子而已。曹操這樣做,不單是將皇帝架空,而且等於是在法理上把東漢自光武帝以來的政治制度做了一個大大的改變,為的便是能夠獨裁,從這點上來說,說曹操是漢賊一點沒錯,因為在曹操的丞相光環之下,漢帝的光環是顯得那么的暗淡無光,漢朝已經從姓劉轉為姓曹了。
不過有趣的是,曹操之子曹丕篡漢後因為丞相的巨大權力馬上將其廢除,後來偶爾設立也是作為榮譽稱號品位而已,到是蜀漢和東吳政權設立了丞相一職,尤其是蜀漢的諸葛亮,在擔任丞相時錄尚書事,其權不亞於曹操。當然,這位漢相則是另外的故事了。
回評
毛宗崗批語
前陳琳檄中未及衣帶詔一事,以爾時董承謀未泄,故詔未宣布爾。及官渡之戰,袁紹聲言曰:“吾奉衣帶詔討賊!”此語差強人意,不勞陳琳再作檄文一篇矣。然猶未誦此詔于軍前也。至玄德在軍前將此詔朗誦一番,尤為痛快。《易》曰:“孚號有厲。”玄德有焉。大義所在,豈可以成敗論之耶!
蘇老泉讀書至此而嘆曰:此孟德、本初之所以興亡乎!孟德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吾者,乃萬全之策也。”遂賞諫者,曰:“後勿難言。”本初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田豐。為明主謀而忠,其言雖不驗而見褒;為庸主謀而忠,其言雖已驗而見罪。何其不同如此哉!玄德勢小,曹操不敢小覷之;本初勢大,曹操偏能小覷之。然徐州之役,八面埋伏,是小題大做,固不敢小視玄德也;倉亭之戰,十面埋伏,是大題大做,亦不敢小視本初也。獅子搏兔搏象,皆用全力,曹操可謂能兵矣。
劉備之於曹操,初與之為交而後與之為仇者也。劉備之於袁紹,初與之為敵而後托之為援者也。劉備之於呂布,初與之為敵而後與之為交,既與之為交而又與之為敵者也。劉備之於孫權,初托之為援而後與之為敵,既與之為敵而終托之為援者也。在徐州則先為主而後為客,在西川則先為客而後為主。惟其於劉表可謂始終如一,惜表之不足與有為耳。
劉備與諸將聚飲沙灘之時,惜眾人,遣眾人,正所以留眾人也;亦如舅犯從重耳歸晉國之時,辭公子,別公子,正所以要公子也。遣之而其心愈堅,辭之而其心愈固。一是患難方深,一是安樂將至;一是以君懟臣,一是以臣結主。雖是兩樣局面,卻是一樣方法。
此回有伏筆,有補筆,有轉筆,有換筆。如袁氏譚、尚相爭尚在後面,而在郭圖口中先伏一筆;劉備投托孫權尚隔數卷,而在孫乾口中先伏一筆;檀溪躍馬逃難亦在後文,而於蔡瑁口中先伏一筆:此伏筆之法也。黃星垂象本桓帝時事,而於此方補一筆;袁紹愛幼子已見前回,尚未說明何人,而於此方補一筆;袁譚守青州已見前文,若袁熙、高幹之守幽、並,未經敘明,而於此方補一筆:此補筆之法也。袁紹兵敗心灰,正議後嗣,忽因二子一甥來助,復與曹操相持,是忽轉一筆;操欲乘勢攻紹,忽因秋成在即,又因劉備來襲,回救許昌,是忽轉一筆;劉備既投荊州,曹操欲攻劉表,忽因程昱之諫,置表而圖紹,又忽轉一筆:此轉筆之法也。倉亭之戰,曹操設計,袁紹中計,前後詳敘兩番,至汝南之襲,但敘劉備中計,不敘曹操設計,前隱後現,又換一樣筆法;袁紹授劍,田豐伏劍,劉備投表,劉表接備,皆詳敘兩邊,至劉備之敗,則用實寫,龔都之死,卻用虛寫,又換一樣筆法:此換筆之法也。諸如此類,妙不可言。
李贄總評
孟德雖國賊,猶然知民為邦本不害禾稼。固知興王定霸者,即假仁仗義,亦須以民為念,方於得些少事業。何故今之為民父毋、代天子稱牧民者,止知有妻子,不知有百姓也?卒之男盜女娼也,又何尤焉!
孫乾對劉表之言,字字沁入肺腑,安有不從之理?乾可謂言語之士矣。
鍾敬伯總評
民為邦本,孟德國賊,猶能知之,不害禾稼,況興王定霸者乎?故日:“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孫乾未見劉表,先與玄德日:“乾一往,景升必出境迎。”及見,果然。孫乾不獨能言,亦可謂有膽、有識、有力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