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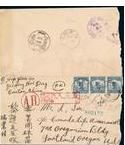 興寄
興寄“興寄”也稱“寄興”。如沈德潛評阮籍詩:“興寄無端”(《古詩源》卷六),陳廷焯評賀方回詞:“寄興無端”(《白雨齋詞話》);胡應麟既以“寄興無盡”評《青青河畔草》(《詩藪》內編卷二),又用“興寄無存”評《柏梁詩》(同上卷三)。元稹論詩評詩則多用“寄興”,如評“沈、宋之不存寄興”,說自己的詩“稍有寄興”等(均見《敘詩寄樂天書》)。所謂“寄”,就是寄託。鍾嶸《詩品》評張華的詩“興托不奇”,也就是“興寄”平常的意思。“興寄”可稱為“寄興”,“興托”也可稱為“托興”,《詩人玉屑》中就有“托興”一條。此外,如“諷興”、“托喻”等,也是相近的意思。
“興”的含意古來雖有種種不同解說,但如“觸物起情”、“借物興情”、“托物寓情”等,大多不能離開“物”的作用,這個“物”,就指事物的形象,所以,“興”和“象”是有著必然聯繫的,古代詩人對“興”的重視,正因為詩人抒情言志必須通過一定的形象。如《詩經》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劉熙載舉以為例說:“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過曰春往冬來耳,有何意味?”(《藝概•詩概》)僅僅說“春往冬來”,的確毫無詩味,甚至不成其為詩。運用“興寄”的托物寓情則不只是為了有詩意詩味,還在發揮詩的更大作用。古代詩詞,篇幅短小的甚多,怎樣才能使有限的篇幅,容納豐富而深厚的內容?主要就靠“興寄”。《詩人玉屑•諷興》中舉到王安石一詩為例:“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余。想因君出守,暫得免苞苴。”此詩乃“送呂望之赴臨江”,因其出守臨江,使黃雀敢於遠飛而無遭捕殺之慮,這確能說明很多問題。所以《玉屑》析云:“詩才二十字耳,崇仁愛,抑奔競,皆具焉。何以多為!能行此言,則虐生類以飽口腹,刻疲民以肥權勢者寡矣。”這裡有歌頌,有批判,確是思深意廣。
這種“寄興”之妙,就是充分發揮了形象的作用。鍾嶸《詩品》釋“興”為:“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這話發展成古代詩話中的名言:“言有盡而意無窮。”其實,能發揮“有餘”或“無窮”作用的主要是形象,所以,“深得文理”的劉勰在《物色》篇提出:“物色盡而情有餘。”“物色”就是事物的形象,上舉王待就是借“黃雀”這個形象而“情有餘”的。古人常講意在言外,也就是藉助形象而產生的象外之意。如《六一詩話》引梅聖俞所舉詩例“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詩人並不直言旅途的愁苦,但他們描繪的形象不僅表明了愁苦,且生動地再現了途中早早晚晚的愁苦之狀,它比直言愁苦更為感人。這種可貴的經驗,古人曾做過許多總結。如李東陽《麓堂詩活》所說:所謂比與興者,皆托物寓情而為之者也。蓋正言直述,則易於窮
盡,而難於感發。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寫,反覆諷詠,以俟人之自得;
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爽飛動,手舞足蹈而不自覺。
這段話可以作為本文的小結,它具體說明了:“興寄”的特點和作用。直質的 陳述,只能是言盡意止,沒有感人的力量。必須把感情寄寓在形象之中,讓讀者不知不覺地從這種形象中受到感染,才能產生意味無窮的作用。細心體味我國古代詩詞,不僅會發現這樣的作品是很多的,也有助於領略其獨特的藝術趣味。
出處
所謂“興”,原是賦比興的“興”。賦比興是漢人從《詩經》中總結出來的三種寫詩方法。“興”的寫法就是“託事於物”(鄭眾《周禮》注引),或“托物興詞”(朱熹《晦詩侍說》)。寄託於某種事物以表達感情的“興”,也就是“興寄”或“興托”。“興”字的含意是“起”,詩人所興起的是情,所以,《文心雕龍·比興篇》說:“興者,起也。……起情,故興體以立。”有的便直接說:“興者,情也”(《二南密旨》)。只是這種情是詩人觸發外物而興起,又寄託於物而表達出來的。由上述可見,古典詩歌的所謂“興寄”,主要就是通過具體事物的描寫以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但“興”或“興寄”是一種歷史的概念,它在我國古代漫長的詩歌史上,還不斷有所豐富和發展。
運用
《詩經》民歌富有現實主義的精神,這是文學史家所公認的;加以漢人尊為五經之一,成為儒家的一部經典,更增強了它在古代文學中的權威性,漢魏以後,每當文學創作出現浮華艷麗的嚴重傾向時,評論家鄉強調《詩經》的優良傳統以反對過分地追逐形式。興詩的托物起情,便逐漸受到詩人和評論家的重視,並越來越突出其“起情”的意義。劉勰論比興,就批評漢代文人“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他第一次明確區分比、興的小大輕重,認為詩歌創作拋棄了更重要的興,就遠不如周代詩人的《詩經》了。鍾嶸評張華“興托下奇”,就因他的詩“其體華艷”,“務為妍冶”。到陳子昂提出:“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修竹篇序》)也是為反對“彩麗競繁”,希望恢復“風雅”的傳統而強調“興寄”的。其後,如李白一方面聲稱“將復古道,非我而誰”,一方面強調“興寄深微”
(《本事詩》);直到明人許學夷所論“漢魏五言、深於興寄,蓋風人之亞也”(《詩源辨體》)等,無不是從發揚《詩經》優良傳統的要求來講“興寄”的。
發展過程
“興寄”的這種發展過程中,雖然始終沒有離開“興”的本義,卻逐步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它不僅僅是一種“託事於物”的寫詩方法了,而更側重於用這種表現方法所寄託或興起的情。“興寄”逐漸形成和“彩麗競繁”、“其體華艷”的相對概念,用以指對詩歌應具有充實而有意義的思想內容的要求。這和整個“比興”概念的發展變化過程是一致的。如白居易《與元九書》所論:“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過矣;索其鳳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憧關吏》、《塞蘆子》、《留花門》 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 亦不過三四十首。”從白居易在同文中稱自己有關“美刺興比”的詩為“新樂府”,元稹在《進詩狀》中稱自己的樂府詩“稍存寄興”,可知“比興”和“興寄”的要求是相近的。這種“比興”或:“興寄”,就是要求詩歌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了。用這樣的要求來衡量齊梁時期的詩作,自然是“興寄都絕”。
唐宋以後,詩詞的“興寄”受到詩人們更大的重視。除上舉明人胡應麟、許學夷等多次用 “興寄” 的深淺來評論詩歌的優劣外,到了清代,甚至認為“文無比興,非詩之體也”(馮班《鈍吟雜錄》);“伊古詞章,不外比興”(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自序》)。沒有比興就不成其為詩,以至一切文學作品,無不是用比興寫成的,這就把比興的地位提得更高了。比和興的共同特點都是托物寓情。唐宋以後“比興”連用,就往往指托物寓情的共同要求。清代詩人不僅認識到托物寓情的普遍意義,且不滿足於一般的寄託,如陳延焯所論:“托喻不深,樹義不厚,不足以言興。深矣厚矣,而喻可專指,義可強附,亦不足以言興。”(《白雨齋詞話》卷六)不僅要有深厚的寄託,還要有廣泛的意義而不專指某一具體內容,情與物之間要有內在的聯繫而不是勉強的比附,才算得“興”。 這樣的“興”,就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藝術創作了。 古代對“興寄”的要求,這又是一大發展。
“興寄”之所以能成為一種古代寫詩或評詩的重要要求,並得以不斷地豐富和發展,這是它本身的特點決定的。首先,“興”不是人為的規定,而是從《詩經》的實際創作經驗中總結出來,又為歷代詩人的創作實踐不斷豐富起來的。這樣,它就符合詩歌藝術的基本規律。所謂。“詩以言志”,詩歌必然是為了表達詩人的某種思想感情而寫,沒有任何思想感情的詩是不存在的。但不藉助於一定事物、不通過具體的形象而直陳其情,也不成其為詩,至少不是好詩。托物寓情正是“興寄”的基本特點,它能受到歷代詩人的普遍重視,並不斷有所豐富,就是這個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