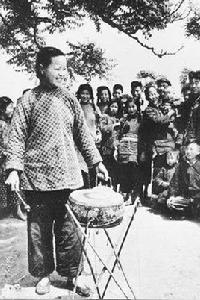人物簡介
門歌做媒促成好姻緣
門歌是流行於皖中地區的一種民間演唱形式,屬民歌、說唱二者兼有的類型。演唱過程中多以鑼鼓伴奏、有些地方稱門歌為“鑼鼓書”。由於門歌為舊時農民乞討時挨門挨戶依於門旁所唱的歌,故得名“門歌”。
1953年,剛剛畢業於滁縣師範的熊遠平,分配到肥東縣文化館,負責指導民眾文化,蒐集整理散失的門歌、民歌等。從小就愛唱民歌的殷光蘭經常到縣文化館去請教熊遠平。兩顆年輕、火熱的心,在共同創作中撞擊出最美的火花。1959年7月,殷光蘭與熊遠平結為伉儷。
門歌送她登上大舞台
對於誕生於安徽的門歌藝術來說,是殷光蘭將它唱到了全國的大舞台。1958年夏,全國舉行曲藝會演。殷光蘭參加安徽省代表團赴京,她帶去的門歌《歌唱總路線》在大會演出後,獲得一致讚揚。由於此次的演出,門歌被正式列為全國曲藝曲種之一。《全國曲藝大辭典》中增添了“門歌”的條目。殷光蘭也因此被中國曲藝家協會吸收為會員。
1958年7月,殷光蘭出席全國民間文學工作者大會,受到了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的接見並留影,她用門歌聲調即興創作了《唱個門歌表心情》。次年下半年,她被選派到安徽大學學習,畢業後被分配至無線電廠工作,後於1992年從肥東縣文化局退休。
門歌相伴幸福晚年
退休之後,殷光蘭夫婦在肥東縣第一中學附近開了一家叫“鄉音”的小雜貨店。小雜貨店裡沒什麼生意時,殷光蘭夫婦就坐在那裡,你一句、我一句地對著門歌的歌詞。他們初步統計了一下,目前已創作1000多首門歌、民歌、詩歌,發表在國內各種刊物上。
殷光蘭夫婦表示,這輩子已經與門歌結下深厚的緣分。作為具有地方特色的藝術,門歌非常值得保護、整理、挖掘,他們要為門歌的傳承繼續貢獻餘熱。
傳奇一生
殷光蘭生來命苦,不滿4個月時父親就死於日本鬼子的屠刀下,母親喪命於惡霸土匪的槍彈中,她被一王姓農民抱去當了童養媳。儘管命運多舛,但殷光蘭生就一個好嗓子、好記性,在放牛崗上,秧田裡,她學會了當地流行的很多“門歌”,幾十種曲調、幾百句唱詞爛熟於心,很快就在村里唱開了。但王家是個貧窮而古板的人家,認為丫頭唱歌有失“家教”亂了“體統”,他們用打、罵、餓飯等手段,企圖阻止殷光蘭唱歌。
1949年1月,殷光蘭的家鄉———肥東縣解放了,村里住進了解放軍。14歲的殷光蘭發現,這支軍隊也愛唱歌,飯前唱,開會唱,有時走路也唱。一天,當地駐軍開聯歡晚會,殷光蘭和小夥伴們在一旁看熱鬧,一位解放軍戰士提出歡迎小朋友們來一段。小夥伴們把殷光蘭推了出來,說她“唱得好,歌子多”。殷光蘭膽怯地連連後退,說:“不能唱,唱了要挨家裡人打。”那位解放軍說:“現在解放了,老封建不時興了。你大膽地唱,我們保證你不會挨打。”就這樣,殷光蘭第一次在大庭廣眾下開口唱歌。她的歌聲第一次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殷光蘭的命運發生了改變,1954年冬,肥東縣選擇殷光蘭家鄉———原定光鄉山王村為全縣興辦農民俱樂部試點,派來了縣文化館幹部王開明駐村業務輔導。頓時黑板報組、歌詠隊、業餘劇團等組織把全村文化生活搞得紅紅火火。村里還籌辦了一個農民“門歌”創作組,殷光蘭積極報名參加。於是,在田間地頭農閒夜晚,王開明不僅教大家認字,還培養大家如何從句式語法上構思歌詞,引導大家觸景生情創作“門歌”。
1955年8月的一天上午,農民在田裡繁忙地栽秧。有著唱秧歌習慣的山王村,秧田裡歌聲蕩漾笑語飛揚。經過創作組“洗禮”的殷光蘭,邊栽秧邊構思,唱起了一首清脆悅耳的《栽秧的人兒愛唱歌》:跳下田來栽秧棵,栽秧的人兒愛唱歌。栽到稗子棵棵死,栽到黃秧都發棵。都發棵來都發棵,萬擔歸倉收成多。支援國家工業化,改善生活笑呵呵!就這樣,連她自己也不敢相信,生平以來創作的第一首民歌誕生了!此刻,正在田間分發秧苗的王開明聽了後連聲叫好,並立即記錄下來。經王開明推薦,不久,安徽省群藝館主辦的《大家演唱》雜誌迅速刊發了這首歌。1956年夏,新華社記者於明慕名來山王村採訪,發現了殷光蘭和她的民歌背後一串串閃亮的故事。不久,長篇通訊《農民女歌手———殷光蘭》很快刊發於《人民日報》等全國各大報紙,“女歌手”的稱號從此誕生,也從此改變了殷光蘭一生的命運!
錯過毛主席專門接見抱憾終生
藝術來源生活。年紀不大卻經歷坎坷的殷光蘭在知識的滋養和行家的指點下進步很快。1957年元月,殷光蘭參加了安徽省文藝會演,演唱了自己創作的“門歌”《整社七日》,第一次把“門歌”搬上省級文藝舞台,演出後評價極高。大會為她頒發特等獎章和獎金60元,這是“門歌”第一次受到省政府的認可與嘉獎。經過數年磨礪,善於在生活中發現創作素材、妙語連珠的殷光蘭已練就一身爐火純青即興說唱的本事。
1958年7月初,全國舉行曲藝會演。殷光蘭參加安徽省代表團赴京演出,她帶去的“門歌”《歌唱總路線》演出後,獲得一致讚揚。殷光蘭在演出的第二天便被派到天安門廣場、王府井大街等地巡迴演唱,在京城紅極一時名聲大噪。此後,“門歌”被正式列為全國曲藝曲種之一。由於殷光蘭表現突出,1958年7月16日,她應邀出席全國民間文學工作者大會。那天,毛澤東、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懷仁堂親切接見了民間文學工作者大會全體代表。回憶起毛主席那天接見時的場景,殷光蘭老人的雙眸里泛出晶瑩的淚花。照相前,大會工作人員特意把殷光蘭的位置安排在二排中間、毛主席身後的絕佳位置,想給她一個單獨與毛主席握手交流的機會,可是殷光蘭不知道內情,也可能是因為膽小之故偏偏跑到了自己熟悉的安徽省代表團團長、省文化局長錢丹輝身旁。照相後,農民詩人王老九大聲說:“殷光蘭,機會太難得了,你應該給大家唱首歌!”在現場,殷光蘭稍作思索,她用“門歌”聲調即興創作演唱了那首經典的《唱個門歌表心情》:“見到毛主席真幸福,好比見到太陽出;太陽一出照四方,毛主席光輝照全國……”毛主席和著歌詞節拍,微笑著向殷光蘭點點頭招招手,看到毛主席的示意,大家散開後殷光蘭依然沉浸在幸福激動中。此刻,一名工作人員走過來批評她說:“小殷啊,毛主席要專門接見你,所以把你安排在主席身後的位置,可你為何不聽從安排?你這是無組織無紀律啊!”殷光蘭一聽,心猛一沉,“天啊,我不知道啊。一念之間我做了一件一輩子也不可挽回的天大錯事!”直到50多年後的今天,殷光蘭一提到此事,禁不住油然流下抱憾的淚水。1959年9月下旬,一封由安徽省人民政府專人送達肥東縣委的中央絕密函件抵達殷光蘭手中。她打開一看,是毛主席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簽名的請柬,邀請她參加國慶10周年招待會與大閱兵、民眾遊行觀禮,殷光蘭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兒:“天呀,這是一種何等高規格的禮遇啊!”9月28日,殷光蘭坐火車抵京。9月29日傍晚,殷光蘭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宴。當周恩來總理和文化部長周揚敬酒到殷光蘭所在的那一桌時,還沒等周揚開口介紹,總理就朗聲與殷光蘭碰杯:“我們的女歌手又來了,歡迎你啊!”總理日理萬機竟然能把自己記得這么清楚,當時殷光蘭竟然激動得沒說出一句話來。同桌的幾個大作家問她:“安徽姑娘,總理為何和你這么熟?”“我們就見過幾次面,而且都是很多人的場合,不想總理就記住我了。”原來,殷光蘭曾陸續來京參加過幾次文藝匯演和婦女建設社會主義積極分子匯報會等活動,每次來總理都在場。10月1日上午10點,殷光蘭登上天安門東側第七觀禮台,參加了動人心魄的國慶十周年慶典,讓年輕的生命經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震撼與豪邁。
一本歌集發行80萬冊
1971年,已經聞名遐邇的殷光蘭被安徽大學盛情邀請去執教,殷光蘭認為自己文化低,所以她只教安徽大學工農兵學院的學生們學唱創作民歌。教學期間,她的學生們把她在《人民日報》、《紅旗》、《詩刊》、《人民文學》等報刊公開發表的60首“門歌”詞收集抄寫好後,建議她出個集子。隨後,歌詞被安徽大學中文系主任徐承志郵寄給了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科院院長郭沫若。殷光蘭本來只是想抱著試試看的想法,希望郭沫若先生抽空看一下,但讓她沒有想到的是,1972年4月中旬,殷光蘭竟然收到了郭沫若的回信。整個校園頓時沸騰了!回函中,郭沫若特別認真,用鉛筆給她的《門歌集》改了30多處,包括有誤的標點符號,還把其中的一首詞添加了兩句,使其表意更貼切。郭沫若在信中鼓勵殷光蘭繼續創作,把“門歌”這種民間藝術傳承下去。郭沫若隨信還給歌集題寫了書名《放聲歌唱紅太陽》。安徽人民出版社聞風而動想要出版,郭沫若得知後再度欣然給歌集作序,隨後安徽人民出版社以最快速度在1972年5月,為殷光蘭出版了精裝本歌集,當時歌集由新華書店發行,全國各地訂單雪片般飛來,購書量突破100萬冊。但因精裝本製作量跟不上,只發行了80萬冊!
隨後,殷光蘭根據自己的生活經歷創作並演唱的《毛主席送我上講台》“門歌”單行本,又被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再度被傳唱到大江南北,在那個火紅的年代紅遍全國。
此後,殷光蘭曾被推舉為第三、第四屆安徽省人大代表和合肥市政協委員;她曾8次赴京演出,4次見到毛主席、周總理,留下了幸福溫馨的回憶。殷光蘭先後被組織分配到無線電廠、農場擔任領導職務,後於1992年從肥東縣劇場經理位置上退休。
2007年6月18日,殷光蘭被安徽省文化廳評為安徽省30位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之一。殷光蘭高興地對筆者說:“如今,‘門歌’從內容到形式都發生了變化,表演形式更加多樣,新人們大膽嘗試用二胡、笛子伴奏,並加上女聲伴唱等手法,取得了很好的藝術效果。”由此,她對“門歌”的發展前途充滿信心:“這么多小青年喜歡,而且唱的也好,肯定能一直傳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