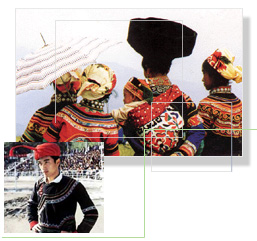 彝族醫學彝族認為萬事萬物的根本是清濁二氣,天、地、人和各種事物都是由清濁二氣產生的,因此清濁二氣是彝醫認識自然、了解疾病和治療疾病的總綱。彝族有本民族文字,現在所能收集到的最早的彝族醫藥文獻是寫於明朝。彝醫不僅重視治療疾病,同時也強調預防疾病。養生和預防是彝醫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彝醫在治療上有內治法和外治法。內治法主要靠口服,劑型有湯劑、丸劑、散劑、酊劑。外治法包括外包、外敷、燒火、熏蒸、洗浴、割治、放血、針刺、拔罐、推拿按摩等。彝藥主要包括植物藥、動物藥、礦物、化學、自然土及水。彝醫治療注重實踐,注重療效,不死守一方,其文獻記載內科疾病有38症,耳科疾病20症,婦科疾病11症,產科疾病28症,外科疾病16症,傷科疾病36症,五官科疾病22症。
彝族醫學彝族認為萬事萬物的根本是清濁二氣,天、地、人和各種事物都是由清濁二氣產生的,因此清濁二氣是彝醫認識自然、了解疾病和治療疾病的總綱。彝族有本民族文字,現在所能收集到的最早的彝族醫藥文獻是寫於明朝。彝醫不僅重視治療疾病,同時也強調預防疾病。養生和預防是彝醫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彝醫在治療上有內治法和外治法。內治法主要靠口服,劑型有湯劑、丸劑、散劑、酊劑。外治法包括外包、外敷、燒火、熏蒸、洗浴、割治、放血、針刺、拔罐、推拿按摩等。彝藥主要包括植物藥、動物藥、礦物、化學、自然土及水。彝醫治療注重實踐,注重療效,不死守一方,其文獻記載內科疾病有38症,耳科疾病20症,婦科疾病11症,產科疾病28症,外科疾病16症,傷科疾病36症,五官科疾病22症。彝藥簡介
彝族藥物是彝族人民長期同疾病作鬥爭的經驗總結和智慧結晶,是中國醫學偉大寶庫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彝族藥物數達千種,包括有動物藥、礦物藥、植物藥,其中以植物藥和動物藥運用較為廣泛。彝醫植物藥多以鮮品入藥,在某些聚居區(如涼山)無準確劑量,並且使用單味藥較多,常見的用法有搗爛、揉爛、外敷、咀嚼、熬水內服和燉雞肉服。彝族地區產名貴藥已有悠久歷史,特別是涼山地區。涼山地區除有豐富的植物藥外,動物藥中珍貴者亦極多。彝族將酒用於藥中,亦有悠久的歷史。
 |  |
| 彝族文化 |
經絡理論
彝醫認為,人以氣血為生命的根本,氣血是維持人體生命活動的基本物質,而氣生於:“大腸與小腸間,臍底之上。”只有氣血在人體內運行通暢,環流不息,貫通三焦,生命活動才能得以延續。彝醫將氣分為清氣和濁氣兩類,認為清氣和濁氣在人體內有著各自的循行路線,並按其路線運行,周行全身,發揮其營養作用。這種被稱為“氣路”的循行路線就是經絡。《西南彝志·論人的血氣篇》說:“清氣三條路。氣路第一條,由心中經過;氣路第二條,是經肝和肺;氣路第三條,發源於中焦。濁氣三條路。為首的一條,起始於中焦,經血海之前,達於頭頂之上;第二條,氣路起始於頭髓,經過臂膀上;末一條氣路,起始於尾根,通過頭頂上,直達於耳底。”雖然對清濁氣運行的道路描述較為粗略,但仍可看出彝醫所指的氣是沿“氣路”即經絡運行的,而不是雜亂無章和運行於“氣路”之外的。
思想:強調無病早防,有病早治是彝醫預防醫學思想的中心內容。彝醫重視疾病的治療,更重視未病先防及既病防變。民間有許多預防方法,如常洗礦泉浴預防皮膚病、風濕病;外搽煙油防山螞蟥、蟲蟻;佩帶雄黃或家中養鵝防蛇等。醫書中所載防病方法更多,如《獻藥經》載:煮食麂子肉,既可治麻風,又可預防麻風傳染;煮食菁雞肉,既可治療麻疹,又可預防麻疹。《明代醫書》載:燒吃人指甲,可預防感冒;隨身攜帶靈貓香,可避毒氣瘴癘及蟲蛇等。此外,彝醫還主張有病早治,防止病情加重,變生它病。如被狂犬或毒蛇咬傷,主張及早劃開傷口拔毒,以防狂犬病或蛇毒中毒。這種無病早防,既病防變的認識,反映了彝醫預防為主,防重於治的學術思想。
發展全覽
彝族醫藥起源於原始社會時期,這個時期的彝族先民吃住都在森林中,並且多數住在樹上,故對植物有了最直觀和最粗淺的認識。也許正是由於這一歷史和自然發展的原因,彝族醫藥與植物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彝族先民們一方面處於惡劣的自然環境中以及面對兇殘的野獸傷害,一方面也處於自身疾病的折磨之中,在與自然災害及疾病的鬥爭實踐中,慢慢地積累了保護身體健康和提高體質的經驗,同時也發展了醫藥知識。
 |  |
| 彝族古畫 |
明代以前,彝族歷代對植物藥的記載非常零星、分散。此時問世的《雙柏彝醫書》一書,將流傳在民間分散的大量植物藥收集起來,它雖然還不是專門的本草書籍,但其中所記載的彝族植物用藥之豐富,是前所未有的。書中記載植物的根、莖、葉、花、果、皮、全草、樹脂及植物寄生的藥材,達數百種之多,如根皮根莖類66種,葉類17種,皮類12種,果、籽類19種,全草類34種,莖木類6種,寄生、樹脂、菌類6種。除此之外,著名醫家趙學敏在《本草綱目拾遺》中,也記錄了一些彝族藥物,證明此期彝族醫藥套用的廣泛性。
15世紀中葉,明代本草學家蘭茂著成《滇南本草》,成為第一部中醫理論與少數民族醫藥經驗相結合的地方性本草專著。在此之前,歷代書籍對民族藥物雖有收載,但都不如蘭茂所收集的規模大、藥品多,尤其是西南地區的民族藥物。《滇南本草》中不僅記錄了藥名,並考證弄清植物及產地,還儘量將當地各民族中的用藥經驗歸納進書中。彝族的許多藥物也記入了。如芸香草、老鸛嘴、鵝掌金星草、韭葉芸香草、救軍糧、橄欖(余甘子)、甘蔗等等。
到了清代,對於植物藥的運用就更加廣泛了。彝著《獻藥經》中說:“植物皆配藥,蔬菜皆配藥”。明確記載了草果、紅果、生薑、胡椒、老母豬趕伴草等藥用植物的主治功效。
 |  |
| 彝族文化 |
特色療法
火罐取 彝醫拔炎罐,主要
 火罐用的是牛角、竹筒、煙桿等。其方法與漢醫略有不同,如火罐筒(牛角、竹筒、木筒)的底部要鑽一小孔,周圍敷上蜂蠟。拔炎罐時,醫者先口對小氣孔,用力吸盡筒里的空氣,待吸穩後。用舌尖將已被溫化了的蜂蠟舐封住小扎即成。若是狂犬病或蛇傷病人,醫者還得口中含白酒才行,以免中毒。待火罐把毒氣扯在一處時,在起包處點針見血再拔,吸出毒血。此法主要用於狂犬病、風證、箭證、蛇證、扭傷等。此外,還可用於子宮傾倒,下垂,但不點針取血。若火罐內放上一些取風的陳艾、花椒、火蔥、韭菜等藥末或藥泥,由扯風、扯毒力強而療效更佳。
火罐用的是牛角、竹筒、煙桿等。其方法與漢醫略有不同,如火罐筒(牛角、竹筒、木筒)的底部要鑽一小孔,周圍敷上蜂蠟。拔炎罐時,醫者先口對小氣孔,用力吸盡筒里的空氣,待吸穩後。用舌尖將已被溫化了的蜂蠟舐封住小扎即成。若是狂犬病或蛇傷病人,醫者還得口中含白酒才行,以免中毒。待火罐把毒氣扯在一處時,在起包處點針見血再拔,吸出毒血。此法主要用於狂犬病、風證、箭證、蛇證、扭傷等。此外,還可用於子宮傾倒,下垂,但不點針取血。若火罐內放上一些取風的陳艾、花椒、火蔥、韭菜等藥末或藥泥,由扯風、扯毒力強而療效更佳。
蠟紙取 此法用於憂思、郁怒、暴氣引起的不思食,口渴欲飲,清瘦無力,肌膚變黑,或咳嗽的氣火伏心證。氣火上沖頭部,則表現出雙側太陽經痛,頭重,昏暈,目發黑或黃。
燈草取 此法用於不慎食入羊蹄岔肉中被肉包裹著的小毛團,而致脘腹劇痛。俗稱“羊毛針痛”。藥物取此法適用於蟲牙痛。方法是把鬧洋花籽研末,置一燒紅的石板上,加豬油,周圍敷上泥土,中間留孔,插上一根竹管,痛牙接在竹管上端,這樣,痛牙里的“小蟲”就會尋香氣而爬進竹管里。
雞取 通過剖雞取象,把病人身上的病灶及毒氣取到雞身上,從而減輕或消除患者身上的毒氣。彝族民間還常用活雞剖開,緊貼患者的胸部,以搶救休克和危重證,挽救病人生命。其他動物也可以用來取象及取毒。臨床套用
近年來,彝醫藥研究一方面在發
 取藥掘整理方面向廣度發展,同時也在實驗和臨床套用方面向深度開展,並已取得一定成就。一些效果獨特的藥物經過系統深入的實驗室工作,已研製成新藥投入生產,並在臨床獲得滿意療效。如:四川涼山發掘的彝藥“木谷補底”,經原植物研究,確認為蟲草屬一新種:涼山蟲草Cordycepsliangshanensis,具有產地海拔低、蟲體大(是冬蟲夏草的3倍)、資源豐富三大優點,經實驗室研究證實其藥理作用、化學成分均與冬蟲夏草一致,已批准供銷試用,為珍貴藥材蟲草開闢了一個很有前途的新藥源。雲南發掘的彝“一妹姑班”系衛矛科植物昆明山海棠,涼山又稱“牛牯史”,經實驗室提取分離,從中得到一萜三萜和生物鹼等成分。其中生物鹼成分雷公藤次鹼為治療類風濕的有效成分,而二萜成分雷藤素甲和雷藤素丙可增強機體免疫活性。臨床套用其片劑、煎劑、酊劑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有一定療效。藥理實驗亦證明其製劑具有抗炎和降低血清谷丙轉氨酶的作用。已有昆明山海棠片正式生產,投入臨床使用。彝藥“落孺症”為龍膽科植物金沙青葉膽,主治小兒痙攣性腹痛,民間廣泛採用已久。臨床套用證明效果甚佳,尤以治療小兒功能性腹痛方面的療效較為突出。已收入《雲南省藥品標準》。彝藥“苯之多七”為罌粟科植大理紫堇Corydalistalien-sis,主治風濕骨牙痛、肝炎、腎炎、結膜炎等。從中分離到乙醯紫堇靈等7個生物鹼。青葉膽Swertiamileensis,用於治病毒性肝炎,從中分離到獐牙菜甙及三個山酮化合物。"利伯喝"為唇形科植物黃花香茶菜Robdosiasculponeata,用治口腔潰瘍、痢疾、皮膚瘙癢等,從其莖葉中分離到延命素(enmein)和三個新的二萜成分(黃花香茶素)等。彝藥“羅鍋底”流傳於雲南嵩明地區,主治腹痛及痢疾。為雪膽屬植物塊根,常用的為大籽雪膽Hemsleyamacrosperma可愛雪膽H.amabilis及中華雪膽H.chinensis,從中分離到雪膽素甲和乙,二者甙元都是齊墩果酸,用於治支氣管炎和燒傷。雪膽素試用於治療麻風及肺結核獲得一定效果,是一種有希望的藥物。燈盞花(菊科短葶飛蓬Erigeronbreviscapus)是治療跌打損傷、風濕疼痛、牙痛、胃痛的彝藥,從中分離出的有效物質燈盞乙素,還可治療腦血栓、腦出血、腦栓塞等腦血管疾病。涼山彝藥“瓦布支”(紫葳科植物兩頭毛Lncarvilleaarguta),治療肝部疾患和痢疾有良效,其製劑用於治療急性菌痢和病毒性肝炎,治癒率高於用西藥治療的對照組。
取藥掘整理方面向廣度發展,同時也在實驗和臨床套用方面向深度開展,並已取得一定成就。一些效果獨特的藥物經過系統深入的實驗室工作,已研製成新藥投入生產,並在臨床獲得滿意療效。如:四川涼山發掘的彝藥“木谷補底”,經原植物研究,確認為蟲草屬一新種:涼山蟲草Cordycepsliangshanensis,具有產地海拔低、蟲體大(是冬蟲夏草的3倍)、資源豐富三大優點,經實驗室研究證實其藥理作用、化學成分均與冬蟲夏草一致,已批准供銷試用,為珍貴藥材蟲草開闢了一個很有前途的新藥源。雲南發掘的彝“一妹姑班”系衛矛科植物昆明山海棠,涼山又稱“牛牯史”,經實驗室提取分離,從中得到一萜三萜和生物鹼等成分。其中生物鹼成分雷公藤次鹼為治療類風濕的有效成分,而二萜成分雷藤素甲和雷藤素丙可增強機體免疫活性。臨床套用其片劑、煎劑、酊劑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有一定療效。藥理實驗亦證明其製劑具有抗炎和降低血清谷丙轉氨酶的作用。已有昆明山海棠片正式生產,投入臨床使用。彝藥“落孺症”為龍膽科植物金沙青葉膽,主治小兒痙攣性腹痛,民間廣泛採用已久。臨床套用證明效果甚佳,尤以治療小兒功能性腹痛方面的療效較為突出。已收入《雲南省藥品標準》。彝藥“苯之多七”為罌粟科植大理紫堇Corydalistalien-sis,主治風濕骨牙痛、肝炎、腎炎、結膜炎等。從中分離到乙醯紫堇靈等7個生物鹼。青葉膽Swertiamileensis,用於治病毒性肝炎,從中分離到獐牙菜甙及三個山酮化合物。"利伯喝"為唇形科植物黃花香茶菜Robdosiasculponeata,用治口腔潰瘍、痢疾、皮膚瘙癢等,從其莖葉中分離到延命素(enmein)和三個新的二萜成分(黃花香茶素)等。彝藥“羅鍋底”流傳於雲南嵩明地區,主治腹痛及痢疾。為雪膽屬植物塊根,常用的為大籽雪膽Hemsleyamacrosperma可愛雪膽H.amabilis及中華雪膽H.chinensis,從中分離到雪膽素甲和乙,二者甙元都是齊墩果酸,用於治支氣管炎和燒傷。雪膽素試用於治療麻風及肺結核獲得一定效果,是一種有希望的藥物。燈盞花(菊科短葶飛蓬Erigeronbreviscapus)是治療跌打損傷、風濕疼痛、牙痛、胃痛的彝藥,從中分離出的有效物質燈盞乙素,還可治療腦血栓、腦出血、腦栓塞等腦血管疾病。涼山彝藥“瓦布支”(紫葳科植物兩頭毛Lncarvilleaarguta),治療肝部疾患和痢疾有良效,其製劑用於治療急性菌痢和病毒性肝炎,治癒率高於用西藥治療的對照組。  |  |
| 彝族醫學 |
彝醫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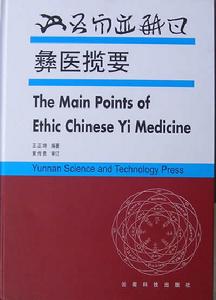 相關書籍《雙柏彝醫書》又稱《明代彝醫書》,是1979年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藥檢所在雙柏縣發掘出的一本古彝文醫書。此次面世的是民國一年(公元1912年)的抄本。此書共有古彝文約5000字,記錄了56個病種,87個處方,324味藥物。全內容豐富,敘述較詳,以病症為納進行編寫,所列病症、症狀或體徵約有60種左右。有的直接以病名出現如瘧疾、蛔蟲、奶瘡等;有的則以病因命名如蛇咬傷、菌子中毒、皮膚濕疹等;但多數還是對症狀的描述,以症狀為病名的。如老母豬風、噁心嘔吐,噎脖子等等。書中內容涉及到臨床各科,其中屬內科者約20多種,屬外科(包括皮膚科、花柳科)者約16種,屬五官科者約有6種,屬婦產科者約有5種,此外,還有少數屬於骨科、神經科和兒科的。在一病一症下,少則一方,多則十餘方,也有一方通治數病的。全書列方劑243個,複方多於單方。複方由二三味或五六味藥物組成,未見10味以上的。書中的治療法多種多樣,在內服外治的基本治法下又衍生出了多種治法,如外治的方法就有藥水外塗,濕布熱敷,藥渣外敷,針挑,拔火罐,小夾板固定等等。某些病症還註明了禁忌,有的禁吃醃菜,有的禁吃雞肉、豬肉,尤其是禁吃母豬肉等等。這些內容體現了當時的彝醫對疾病的產生,病情的進退,藥物的生克關係都有一定的認識。它是對16世紀以前彝族人民醫藥經驗的總結。它的出現,說明了16世紀中葉彝族醫藥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證明當時主要以行醫為業的彝族醫生已出現了。國內有研究彝族醫藥的學者把《雙柏彝醫書》的發現稱之為“彝族醫藥史研究中的第一次重要發展”。
相關書籍《雙柏彝醫書》又稱《明代彝醫書》,是1979年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藥檢所在雙柏縣發掘出的一本古彝文醫書。此次面世的是民國一年(公元1912年)的抄本。此書共有古彝文約5000字,記錄了56個病種,87個處方,324味藥物。全內容豐富,敘述較詳,以病症為納進行編寫,所列病症、症狀或體徵約有60種左右。有的直接以病名出現如瘧疾、蛔蟲、奶瘡等;有的則以病因命名如蛇咬傷、菌子中毒、皮膚濕疹等;但多數還是對症狀的描述,以症狀為病名的。如老母豬風、噁心嘔吐,噎脖子等等。書中內容涉及到臨床各科,其中屬內科者約20多種,屬外科(包括皮膚科、花柳科)者約16種,屬五官科者約有6種,屬婦產科者約有5種,此外,還有少數屬於骨科、神經科和兒科的。在一病一症下,少則一方,多則十餘方,也有一方通治數病的。全書列方劑243個,複方多於單方。複方由二三味或五六味藥物組成,未見10味以上的。書中的治療法多種多樣,在內服外治的基本治法下又衍生出了多種治法,如外治的方法就有藥水外塗,濕布熱敷,藥渣外敷,針挑,拔火罐,小夾板固定等等。某些病症還註明了禁忌,有的禁吃醃菜,有的禁吃雞肉、豬肉,尤其是禁吃母豬肉等等。這些內容體現了當時的彝醫對疾病的產生,病情的進退,藥物的生克關係都有一定的認識。它是對16世紀以前彝族人民醫藥經驗的總結。它的出現,說明了16世紀中葉彝族醫藥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證明當時主要以行醫為業的彝族醫生已出現了。國內有研究彝族醫藥的學者把《雙柏彝醫書》的發現稱之為“彝族醫藥史研究中的第一次重要發展”。《啟谷署》是貴州省仁懷縣政協秘書長王榮輝同志保存的一本彝族醫藥古籍手抄本。經過翻譯整理,記載有5門,38個疾病,263個方劑。此書是一部臨床價值較高的彝醫書,經後人臨床驗證,有效率達95%以上,是研究彝族醫學很參考價值的文獻資料。
《指路書》又名《人生三部曲》,彝語《卓莫蘇》,由金國庫老人和羅希吾戈先生譯定。據推測成書年代在明末清初之際。此書屬彝族喪葬儀式唱誦的經書,內容主要講死者的祖先某人曾在何地生息。“指路”是給死者的靈魂指明道路,把死者的靈魂從當地沿著遷徙來的路線送回彝族祖先的發源地。但是,書中記載了大量的醫學理論,對彝族男子生平活動的描述及對婦幼保健,人體發育,胎產的認識運用唯物主義的思想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供牲獻藥經》是彝族古典文獻《作祭經》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祭奠死者時唄耄唱誦的一種經文,雖然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但是也確實有一部分內容是樸素的唯物思想的認識和反映。《供牲獻藥經》(以下簡稱《獻藥經》),寫於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曾廣泛流傳於雲、貴、川三省。它是著名歷史學家、社會學家馬學良教授1947年在雲南省祿勸彝族苗族自治縣團街區安多康村彝族畢摩張文元家調查時發現的。後經馬教授翻譯整理成彝漢對照本。
《好藥醫病書》又稱《醫病好藥書》。此書抄於乾隆丁已年(1737)冬18日,內容較《醫病書》豐富,涉及範圍亦廣。記載了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和五官科等39種疾病,共有317個處方。由單味藥組成的方劑有171方,占54%。但在複方三味藥以上的方劑明顯地比《醫藥書》多。這充分說明該書對藥物功效的認識已進了一步,不僅掌握了藥物的主要作用,而且對藥物的多種作用和配伍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治療方法上,除了內服外,還採用了外包治療瘡瘍、刀傷和跌打勞傷;外搽治療疔瘡和皮膚病。按摩治療腹痛和頭疼;搔刮治療腹痛、腹瀉;煎湯治療瘡、癬、疥、癩等。具體療法亦有增加,體現了當地彝醫的特色。全書共使用藥物370味,按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分類法大致分為水、火、土、金石、谷、菜、果、木、草及禽類、獸類、魚類和鱗類等13種,但以草類最多。該書比《醫病書》涉及面廣,數量亦多,是內容比較豐富而全面的著作。
 《查詩拉書》《聶蘇諾期》是新近出版的又一部發掘整理出來的古彝醫書。該書內容豐富,除涉及病症、治法、用藥等方面外,還按病症分類收載了許多彝族醫案。這對研究當時彝醫對疾病的觀察和認識以及治療方法都具有很大的幫助,這是該書的特色之一。特色之二是該書所載的273種彝族藥,每種都列出彝文名及相應的漢語音譯,基源(包括拉丁學名和藥用部分),為今後的臨床研究提供了科學依據。特色之三是突出了彝族在用藥方面的一些特點,譬如:彝醫善用植物寄生入藥,書中列舉了多種寄生類藥材,豐富了植物藥藥用部位的研究內容。
《查詩拉書》《聶蘇諾期》是新近出版的又一部發掘整理出來的古彝醫書。該書內容豐富,除涉及病症、治法、用藥等方面外,還按病症分類收載了許多彝族醫案。這對研究當時彝醫對疾病的觀察和認識以及治療方法都具有很大的幫助,這是該書的特色之一。特色之二是該書所載的273種彝族藥,每種都列出彝文名及相應的漢語音譯,基源(包括拉丁學名和藥用部分),為今後的臨床研究提供了科學依據。特色之三是突出了彝族在用藥方面的一些特點,譬如:彝醫善用植物寄生入藥,書中列舉了多種寄生類藥材,豐富了植物藥藥用部位的研究內容。《查詩拉書》是一本流傳在哀牢山地區彝族村寨中較為完整的殯葬祭詞,它系統地介紹哀牢山地區彝族喪葬習俗。但是書中論述了不少彝族醫學知識,如對新生兒期、嬰兒期、幼兒期、幼童期,少兒期的生長發育過程進行了全面的論述。本書在用藥上大膽使用膽類藥,體現了彝族醫藥特色。並提出很多衛生防疫及處理措施。
《尼蘇奪節》是一部彝族創世史詩。全詩由10個神話故事組成,從開天闢地、戰勝洪水猛獸、栽種穀物、發展生產、婚姻戀愛、音樂舞蹈、金屬采煉,一直寫到民族風情,倫理道德和創造文字為止,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情節動人,文字流暢,以浪漫主義的藝術方法描寫了彝族人民歷史發展的過程。
彝醫專家
 方文才方文才 男,彝族,生於1947年,中共黨員。自幼學習彝醫藥,14歲時已攻讀大量醫學名著並開始行醫,18歲時已在滇南地區小有名氣。1971年入伍,在昆明軍區司令部門診斷任醫師,1980年畢業於雲南中醫學院中醫系。現任成都軍區民族民間醫藥研究所所長(主任醫師)、中國民族民間醫藥研究會副主任委員、《民族民間醫藥報》主編、《中國民族民間醫藥雜誌》副主編、雲南省民族民間醫藥研究會副會長、成都軍區醫學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等職務。自60年代從事民族民間醫藥工作以來,在彝醫藥研究方面有一定造詣,能識別和套用於臨床的植物藥達3140餘種,並寫出了約12萬字的藥物分布資料,收集並製作出2200多種藥物標本,撰寫了《民族醫藥教材》《彝族醫藥學》《民族民間藥物治療內科病症》《民族民間方劑選》《彝族醫藥珍本集》翻譯,整理了彝醫古典著作《醫病書》《醫病婦藥書》等。20多年來,診治了省內外及國外病人20餘萬人次,培養了初、中級醫藥人員300餘人。良好的醫德醫風和高超的醫療技術曾先後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光彩的事業》《中國名醫列傳當代卷》,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多家書刊報紙或電台報導。在科研上取得了多項成果:“複方靈芝糖漿”治療冠心病,改善冠狀動脈循環,效果顯著;“杜鵑花糖漿”治療慢性支氣管炎,獲原昆明軍區科技進步三等獎;近8年來,又研製出治療眩暈症的顯效藥物“方氏八仙丹”;抗老防衰的營養保健品“八仙飲”;主治神經性頭痛、外傷後頭痛的良藥“腦康靈”;治療乳腺小葉增生與子宮肌瘤的藥物“方氏婦樂康”;治療關節炎與肩周炎的外擦劑“烏龍酊”;治療潰瘍病、慢性結腸炎的“方氏胃腸樂”等。他在治療中師古而不拘泥。他認為,正氣不能存在,不僅是疾病發生的根本原因,還是疾病發展變化的決定因素,主張“無病善防,增強體質,有病驅邪,慎毋傷正”。
方文才方文才 男,彝族,生於1947年,中共黨員。自幼學習彝醫藥,14歲時已攻讀大量醫學名著並開始行醫,18歲時已在滇南地區小有名氣。1971年入伍,在昆明軍區司令部門診斷任醫師,1980年畢業於雲南中醫學院中醫系。現任成都軍區民族民間醫藥研究所所長(主任醫師)、中國民族民間醫藥研究會副主任委員、《民族民間醫藥報》主編、《中國民族民間醫藥雜誌》副主編、雲南省民族民間醫藥研究會副會長、成都軍區醫學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等職務。自60年代從事民族民間醫藥工作以來,在彝醫藥研究方面有一定造詣,能識別和套用於臨床的植物藥達3140餘種,並寫出了約12萬字的藥物分布資料,收集並製作出2200多種藥物標本,撰寫了《民族醫藥教材》《彝族醫藥學》《民族民間藥物治療內科病症》《民族民間方劑選》《彝族醫藥珍本集》翻譯,整理了彝醫古典著作《醫病書》《醫病婦藥書》等。20多年來,診治了省內外及國外病人20餘萬人次,培養了初、中級醫藥人員300餘人。良好的醫德醫風和高超的醫療技術曾先後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光彩的事業》《中國名醫列傳當代卷》,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多家書刊報紙或電台報導。在科研上取得了多項成果:“複方靈芝糖漿”治療冠心病,改善冠狀動脈循環,效果顯著;“杜鵑花糖漿”治療慢性支氣管炎,獲原昆明軍區科技進步三等獎;近8年來,又研製出治療眩暈症的顯效藥物“方氏八仙丹”;抗老防衰的營養保健品“八仙飲”;主治神經性頭痛、外傷後頭痛的良藥“腦康靈”;治療乳腺小葉增生與子宮肌瘤的藥物“方氏婦樂康”;治療關節炎與肩周炎的外擦劑“烏龍酊”;治療潰瘍病、慢性結腸炎的“方氏胃腸樂”等。他在治療中師古而不拘泥。他認為,正氣不能存在,不僅是疾病發生的根本原因,還是疾病發展變化的決定因素,主張“無病善防,增強體質,有病驅邪,慎毋傷正”。相關條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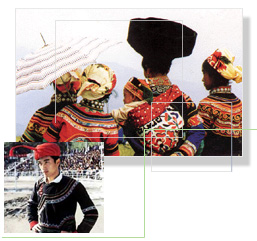 彝族醫學
彝族醫學





 火罐
火罐 取藥
取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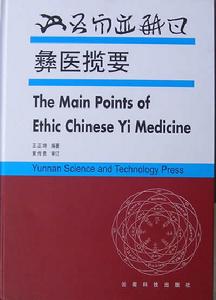 相關書籍
相關書籍 《查詩拉書》
《查詩拉書》 方文才
方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