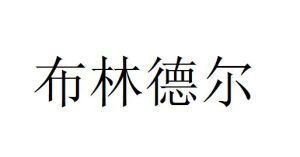簡介
布林德爾在1986年為他1975年出版的《新音樂——1945年以來的先鋒派》的再版所寫《結語》中的一段話是意味深長的:“從我開始寫《新音樂》這本書到現在,12年已經過去了。如果把這12年放在更早的時候,即50和60年代,那么現在這本書該有許多新的音樂發展需要記載。然而相反,值得回顧的名副其實的技術革新事實上幾乎沒有,剛剛過去的這10年基本上沒有什麼創新。”
成就
《新音樂——1945年以來的先鋒派》,[英]布林德爾著
對音樂的理解
從音樂本體看,布林德爾的《新音樂——一九四五年之後的先鋒派》是最有考察力度的。因為布林德爾也是先鋒音樂的參與者(在他所引用的譜例中有他自己的作品),他在解讀同行的先鋒作曲或先鋒行為時就多了一份惺惺相惜。布林德爾幾乎不對任何現象做出評論或解讀傾向。但他也不僅僅是展示。布林德爾的研究最有價值之處是他的觀察角度,他所選的角度明顯地建立在他對音樂解構現象的深廣認識之上,而布林德爾的作曲家身份使他的論述切中實際的創作要害,不顯得空泛。
布林德爾從三個角度觀察“偶然音樂”。他首先將概念進一步細分為“不確定音樂”、“機遇音樂”和“偶然音樂”。這種細分是以“偶然”的程度為依據的。布林德爾的解讀也是從各種不同的“不確定”因素開始。這樣的方式並沒有脫離傳統音樂的分析模式,但無論對於多么怪異的新事物,我們最先能做的也只是多找幾個盲人來摸象,進行地毯式搜尋。布林德爾從“不確定”的音高、時值、演奏法、速度、樂器種類等等譜面的因素分別考察,試圖比較哪一個維度的不確定才會導致最高程度的“偶然”。這樣的比較沒有結論,因為無論哪個維度的“不確定”,聽起來都一樣“偶然”。可以觀察到的是僅僅存在於譜面的較量:誰的“不確定”因素比較多。這顯然是關乎創作的學習角度,學院派的作曲就是這么瑣碎而現實的事情。在未果的“不確定”比較之後,布林德爾深入到“偶然音樂”記譜法觀察。五花八門的記譜法是“偶然音樂”帶給作曲技術的重要革新。特別是在此之前的“整體序列”音樂極其複雜又過分精確的記譜法曾使最傑出的歐洲演奏家們膽戰心驚,作曲家們推卸給數字的責任又被推給了演奏者,尤其叫人惱怒的是這樣艱難的演奏,其效果與胡亂彈奏從效果到本質幾乎都無差別。因此,記譜進入即興化、偶然化變成理所當然的方向。可以說,一九四五年之後的作曲家們或多或少都有自創的記譜法,需要在總譜扉頁附加長長的記譜說明,以致從記譜法的變幻中能窺見音樂觀的演化。“偶然音樂”中出現了斯托克豪森的“比例記譜法”、“文字記譜法”、厄爾·布朗等人的“圖表記譜法”等等。有些作曲家們儼然是製圖專家,圖譜往往像一幅優美非凡的抽象畫,其中甚至有別具深意的圖案隱現。在五花八門的譜例後面,布林德爾似乎也無法總結記譜法的規範,只能匯集有趣的現象,開開讀者的眼界。
布林德爾在書中又另闢一章——《凱奇與其他美國作曲家》,雖然沒有言明,但也暗示了從歐洲和美國兩個不同地域來考察偶然音樂的兩條不同線索,這或許是布林德爾最獨特的視角。其中的確有所發現。從上文的凱奇與斯托克豪森的比較中已可看出些許他們之間的相互啟示。除了凱奇之外,美國還有大量偶然音樂作曲家,比如莫頓·費爾德曼、厄爾·布朗、哈里·帕奇、克里斯琴·沃爾夫等等。費爾德曼的作品有獨特的記譜法,他寫的譜面上是各種各樣的長方形、正方形以及虛線與實線,大致地表示音高、力度與表情。布爾德林意識到了費爾德曼一九五一年的作品《交織I》中業已顯露歐洲式偶然音樂的思路,之後經過《亞特蘭蒂斯》(一九五八)的調整,到一九六○年的《時值》,費爾德曼逐漸走回到精確的傳統記譜法。同樣,另一位美國作曲家布朗也從最激進的圖表式記譜(如一九五四年的《指數》)走回了限定越來越多的歐洲式開放曲式(如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可用的形式》)。從這個角度布林德爾終於有了結論:“歐洲的這一運動基本上是向簡單化方向發展的運動,而美國的這一運動(至少是某些作曲家)卻是從對不確定性的近乎幼稚、初步的觀念向著更加明確、複雜的方向行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