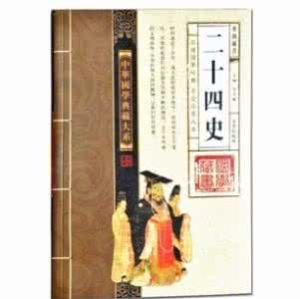簡介
2008年年3月,國寶級學術泰斗、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在北京301醫院接受採訪,高瞻遠矚的提出“大國學”的概念。他說:“國學應該是‘大國學’的範圍,不是狹義的國學。國內各地域文化和56個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國學’的範圍之內。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又共同構成中國文化這一文化共同體。”(季羨林 語)
“大國學”是一種大一統式的‘文化調和’。因此我想,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之學,東西南北凡吾國域內之學,無論在地域上還是學術學科上,無論從歷史回溯還是空域觀照,遠者包括被元代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統一的古西域三十六國文化、古尼雅文化,古樓蘭文化,近者包括學科創建歷史不到百年的西夏學、敦煌學等,都可稱為我國‘國學’。在國際上,近似的名詞稱謂漢學或稱中國學,西方學者把藏學、滿學、蒙學、伊斯蘭學等排除在漢學之外,有故意破壞中國大統一之嫌;現代‘華學’學者針對這種情況,把國學稱謂“華學”,包括中華漢學和古代三皇五帝所有後裔民族之學,均列為中國之‘國學’ ”尤其是藏學、滿學、蒙學、伊斯蘭學,是國學中的四大金剛,應當成為國學中的顯學。(南柯舟 語)。
在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時,季羨林就提出了“大國學”的初步構想:“‘國學’應該是長期以來由多民族共同創造的涵蓋廣博、內容豐富的文化學術,而絕非儒學的代名詞。”
到季羨林逝世後,“大國學”的概念才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這時候,“大國學”的構想已被確定為:國內各地域文化和56個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國學”的範圍之內。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又共同構成中國文化這一文化共同體, 這個共同體是被世界認可的。
季老倡言
 《中國通史》 李伯欽、李肇翔主編
《中國通史》 李伯欽、李肇翔主編98歲高齡的季羨林先生,應北方聯合出版傳媒集團之請,欣然為馬上出版的《中國通史》題辭:“普及中國史,提倡大國學。”季老再次重申應提倡“大國學”,值得引起出版、學術、教育界的關注。
季老倡言“大國學”,並非始於今日。五年多來,他雖然一直在病房休養治療,卻始終關注著社會上“重振國學”的熱潮。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首任院長馮其庸先生曾專門到醫院與季老交流看法,一致認為我們的“國學”應該是長期以來由多民族共同創造的涵蓋廣博、內容豐富的文化學術,而絕非乾嘉時期學者心目中以“漢學”、“宋學”為中心的“儒學”的代名詞。為此,人大國學院專門創辦了“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2007年3月6日,中國書店出版社的於華剛總經理去拜訪季老,談及“國學熱”,季老又說了幾段發人深省的話,明確提出了“大國學”的觀點,他強調:“‘國學’就是中國的學問,傳統文化就是國學”,“現在對傳統文化的理解歧義很大。按我的觀點,國學應該是‘大國學’的範圍,不是狹義的國學”,“國內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個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國學’的範圍之內……敦煌學也包括在國學裡邊……而且後來融入到中國文化的外來文化,也都屬於國學的範圍。”
衍生
國學
“國學”一說,產生於西學東漸、文化轉型的歷史時期。而關於國學的定義,嚴格意義上,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給我們做出統一明確的界定。名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普遍說法如國粹派鄧實在1906年撰文說:“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也。”(《國學講習記》,《國粹學報》第19期)鄧先生的國學概念很廣泛,但主要強調了國學的經世致用性。 國學,復興於二十世紀初,而鼎盛於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來“尋根”熱潮,九十年代“國學”熱再次欣起遂至今而烈矣,究其實無不是今人對於傳統文化的反思與正視。於今而言,則正是對傳統文化在今日中國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國學本為我國之獨有,但在中華近代歷史時期,由於中西之學的分野,國學與西學在國內開始逐漸分流發展;在中國大陸,國學曾因破除四舊而遭塗炭,文革結束的改革開放以來後,國人的思想學術文化自由逐步有所恢復,中華傳統文化學術的空間逐步繁衍擴大,枝盛葉茂復起至今。(南柯舟 語)
“國學“,顧名思義,中國之學,中華之學。秦磚漢瓦,非秦(有英語China為證)即漢(Han Studies),自漢代以降,國力鼎盛,海外又稱大漢民族之學為“漢學”,考據學雖然證實“漢學”一詞至遲在南宋已較常見,狹義所指為兩漢時期的經學學術思想,而漢代人研究經學著重於名物、於訓詁,後世因稱研究經、史、名物、訓詁、考據之學為漢學。(南柯舟 語)
然深究國學的本名原意,原指國家學府,如古代的太學、國子監。單純的說國學,乃獨指經、史、子、集部的語言文字經典訓詁學問。自西學東漸、文化分流轉型以來,為區別於西學,國人把我國的“六藝、五術”統統稱之為“國學”,西學繁衍於東土,東學式微,現代自五四以來的新青年運動前後,一些國學大師們,為保護國學而開始和西學論戰,西學派認為全盤接受西學,而國學家們則誓死保衛祖宗們留下的五千年菁華文化。(南柯舟 語)
國學,一國所固有之學術也。國學和文學、數學的意思不同,並非是國家之學或者治國之學。一般來說,國學是指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國學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學術,也包括了醫學、戲劇、書畫、星相、數術等等。國學以學科分,應分為哲學、史學、宗教學、文學、禮俗學、考據學、倫理學、版本學等,其中以儒家哲學為主流;以思想分,應分為先秦諸子、儒道釋三家等,國學以《四庫全書》分,應分為經、史、子、集四部,以國學大師章太炎《國學講演錄》所分,則分為國小、經學、史學、諸子和文學。 《百度》
傳統國學
傳統上的國學以學科分,則應分為哲學、史學、宗教學、文學、禮俗學、考據學、倫理學、版本學等,其中以儒家哲學為主流;以思想分,應分為先秦諸子、儒道釋三家等,儒家貫穿並主導中國思想史,其它列從屬地位;國學以《四庫全書》分,應分為經、史、子、集四部,但以經、子部為重,尤傾向於經部。
《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叢書,編撰於乾隆年間,由當時的紀曉嵐、王念孫、戴震等等一流學者完成。“四庫”指經、史、子、集四部,“全書”指所收都是全本。“國學”是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與當代文化中的精化相融的學術精髓簡稱。它是新一代應該了解的知識之一。
漢學
海外所指漢學,或者又可理解為漢民族之學,即對中國的研究,尤特指關於對中國的語言文化、文學、歷史和風俗習慣的研究,囊括中華六藝五術範疇。六藝指: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五術指:山、醫、卜、命、相等五術。因此“國學“又有了更寬泛的解釋,把百家之術,如儒、釋、道、兵、法、墨等百家之說統統收於國學囊中,如此,則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之說,都能統稱為“國學”,其中除了佛教是外來宗教,基本全是誕生於中華本土,所以,國學又稱為“中國學”、“漢學”。(南柯舟 語)
教育
在大學裡設定國學學位,首先應對國學的概念做一個科學的界定,從時間、空間、內容上做明確界定,對學科要承擔的使命和本質上做科學界定!
範疇
從概念看
 季羨林
季羨林季羨林曾說,“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雖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其為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因此,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之學,東西南北凡吾國域內之學,都可稱為‘國學’。”
“國學的‘國’是中國的‘國’,不是漢族的‘漢’,漢族是中國的主體民族,但不是中國唯一的民族,如果將國學簡單定義為‘漢學’,無意中就把55個少數民族與漢族割裂開了。一些西方學者將國學譯為‘Sinology(漢學)’,試圖將藏學、滿學等少數民族文化排除在國學之外,是別有用心的。”但同時應該在時間上予以界定,我以為把“五四”以前定做時間界限,“五四”後,中國人用西方的學理創造的學問不能算做國學內容。
從歷史看
中國文化的形成是各民族和地區慢慢融合締造的。中國自古以來從未存在過所謂的漢族國家,即便在唐朝,李氏家族中的很多人都不是漢人;元朝、清朝分別是蒙古族、滿族統治,但仍稱為“中國”;新中國成立後實行的包括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內的各項民族政策,將56個民族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從研究範疇看
從齊魯、荊楚、三晉、青藏、新疆、草原等,到敦煌學、西夏學、藏學、回鶻學、佛學等,都是“大國學”的研究範疇。
從教育看
“大國學”的教育理念是把國學置於整箇中華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既要有儒學等中國傳統文化,也要研究少數民族文化。
內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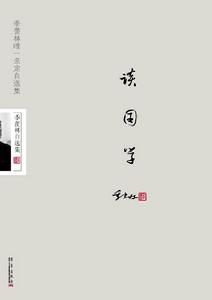 讀國學
讀國學“大國學”思想基本的內涵其實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包容精神。《中庸》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中所體現出的兼容並蓄,就是“國學”的基本精神核心。所謂“大國學”,本質上也是對“兼容並蓄”這一精神核心的再次強調。
大國學蘊含著中國作為由56個民族組成的大民族家庭的和諧統一的思想精髓。這個思想表述的是,中國真正廣義的‘國學’,應該是由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所有文化核心思想的集萃,同時這所有的文化思想又是一脈相承、相輔相成的,它們構成了一個整體的中國文化。
國學和諧論
人文“大國學”論應與現當代西方科學思想和諧共生。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博導陳思和教授在人文復旦講壇提出“海派文化可以容納各種文化,並且保持各種文化之間的和諧與平衡”,我想把它借用到這裡,人文“大國學”論不排斥科學,應與現當代西方科學思想和諧共生。實現陳思和教授所說“多元與規範文化的通體生存”狀態,五術六藝與諸子百家之學可以和諧共生,彼此之間應互不排斥。(陳思和 語)
五術六藝與諸子百家之學也可以和諧共生。五術六藝從誕生開始與就諸子百家連體共生,如果沒有五術六藝,也就沒有中國文化,沒有中國哲學,否定五術六藝等於否定中國哲學,將中國哲學拖入虛無主義泥潭沼澤萬劫不復。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博導陳思和教授提出“只有包容各種文化形態的存在,這個文化自身才可能變得多元和豐富”。這是一種繁榮與腐朽共生的文化現象。如果把五術和六藝取締,中國民間信仰和倫理將失去土壤與根基,秦始皇焚書坑儒都沒有燒掉的《易經》能生存發展到現在,很能說明問題。這同時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礎。只有是更加的中國的,才更加是世界的。。(南柯舟 語)
意義
在中國國學中有豐富的哲學內涵,雖然國學不是哲學,但是國學的發展史囊括著中國幾千年來的哲學發展脈絡,國學無法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單一的揀出來,設立學位要找基本依據,全面復興中國的國學文化,實行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復興包括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之說文化,才是真正的國學復興之日。國學的現代化就是把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中的文藝、文化知識科學化的復興起來、現代化起來。(南柯舟 語)
中華國學其宗旨,乃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國學”實應包括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之說。其中諸子百家,包括“儒、釋、道、刑、名、法、墨”等等各家,乃是“為天地立心”之學;其中六藝,包括“禮、樂、射、御、書、數”,在古代,“六藝”中禮、樂、射、御,稱為“大藝”,是貴族從政必具之術,貴族子弟在太學階段要深入學習;書與數稱為“小藝”,是民生日用所需之術,是在古代“國小”階段的必修課,乃是“為生民立命“之術;其中五術,乃是 “為往聖繼絕學”、“究天人之際”關係的學問,包括“山、醫、卜、命、相”等。被今人疵垢為“迷信”,那些輕易否定一切“究天人之際”關係的學問的人,其實他們很少站在與人生存在狀態息息相關的終極關懷的立場上,去認真的探究天人之際的真切意蘊與內在價值,去拉近生命存在與天人之際之間的間接和直接聯繫,在傳統與時代、學問與生活中架設一架溝通的橋樑。(南柯舟 語)
一切反對中華民族文化大整合的的言論和輿論,都是對民族文化的踐踏,都是極端不負責任的。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的大國學論,有利於中華大民族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有利於五千年來積累的的民族文化大整合,有利於凝聚中華民族文化向心力!有利於中華民族大團結。(南柯舟 語)
大國學的提出,它有利於民族團結、增強民族自信心,也拓寬了少數民族文化發展的思路。如果從“國學”的高度重視少數民族的一些優秀文化,比如有著完整的曆法和文字的水族的文化,那對於這些文化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很少有人知道,水族最早的文字記錄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水書”也因此被稱為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
發展
隨著時代的進步,國學也在含義和範疇上有一定的變動,舊國學適用的範圍已經有所變更,在刪減了一定的含義之後也注入了一些新的內容。比如,以前所說的國學幾乎指代的就是中國古老而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而今,在世界範圍內,它也開始涵蓋近代的文化,乃至向現代文化延伸。所以說事物總是在變化,我們對待事物也要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
界定
迄今為止,學術界尚未對“國學”做出統一明確的界定。季羨林先生生前認為,國學不是“漢學”“儒學”等狹隘的國學,而是集全中國56個民族文化財富於一身的“大國學”。這一論斷被廣泛認為是“國學”定義的一大突破。從概念看“大國學”
“我們應該用‘大國學’這個概念,它是一種大一統式的‘文化調和’。”季羨林曾說,“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雖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其為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因此,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之學,東西南北凡吾國域內之學,都可稱為‘國學’。”對此,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說,國學是中國本土的、傳統的學術體系,當然應該包括我國各少數民族文化。“國學的‘國’是中國的‘國’,不是漢族的‘漢’,漢族是中國的主體民族,但不是中國唯一的民族,如果將國學簡單定義為‘漢學’,無意中就把55個少數民族與漢族割裂開了。一些西方學者將國學譯為‘Sinology(漢學)’,試圖將藏學、滿學等少數民族文化排除在國學之外,是別有用心的。”
從歷史看“大國學”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沈衛榮說,中國文化的形成是各民族和地區慢慢融合締造的。中國自古以來從未存在過所謂的漢族國家,即便在唐朝,李氏家族中的很多人都不是漢人;元朝、清朝分別是蒙古族、滿族統治,但仍稱為“中國”;新中國成立後實行的包括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內的各項民族政策,將56個民族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把少數民族排斥在國學之外是一種荒唐的做法,也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從研究範疇看“大國學”
季羨林認為,今天我們所要振興的“國學”,絕非昔日“尊孔讀經”的代名詞,而是還中華民族歷史的全貌:從齊魯、荊楚、三晉、青藏、新疆、草原等,到敦煌學、西夏學、藏學、回鶻學、佛學等,都是“大國學”的研究範疇。哲學泰斗湯一介回憶說:“季羨林曾專門和我探討‘大國學’與佛教的問題,他指出中國的佛教文化也是多民族共同創造的,當然也是‘大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他欣然同意與我共同編撰《儒藏》,切實推動國家‘儒藏工程’的開展。”
“‘大國學’的研究對象應包括中國各民族的文化傳統,以揭示它們的交流與融合進而構成中華民族的多元文化特徵為主要研究目的。”沈衛榮說。
從教育看“大國學”
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首任院長馮其庸先生曾專門到醫院與季羨林交流看法,一致認為“大國學”教育應以多民族共同創造的涵蓋廣博、內容豐富的文化學術為主要內容。
袁濟喜說,“大國學”的教育理念是把國學置於整箇中華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既要有儒學等中國傳統文化,也要研究少數民族文化。
“人大國學院從課程設定到教學內容,都體現了這一點。”沈衛榮說,“人大國學院既有漢學專業,也有少數民族歷史專業;既有西域研究所,又有漢藏佛學研究中心。國學院三分之一的學生都是研究少數民族文化的;開設了古藏文、西夏文、蒙文、滿文等課程。從教學理念到課堂實踐都要體現‘大國學’的理念。”
理論與現實解讀
季羨林老人安靜地離去,留下了未實施的“大國學” 構想和建構理念——“我們應該用‘大國學’這個概念,五術六藝諸子百家之學,東西南北凡吾國域內之學,都可稱為‘國學’”。
許多學者指出,“大國學”思想毋庸置疑是季羨林留給我們的一筆豐厚文化遺產。作為繼承者,當前我們面臨的問題在於——怎樣科學地確立“大國學”的理念?怎樣理性地去推行“大國學”理論的實踐?無論我們怎樣做,有一點必須肯定,那就是我們不能將大師所留下的“大國學”的寶貴思想遺產永遠停留於構想。
“大國學”思想的基本內涵
“大國學”到底是什麼?季羨林先生所提出的“大國學”的構想並非始於今日。早在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時,季老就提出了“大國學”的初步構想:“‘國學’應該是長期以來由多民族共同創造的涵蓋廣博、內容豐富的文化學術,而絕非‘儒學’的代名詞。”
但是,“大國學”的初步構想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直到季老逝世後,“大國學”的概念才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這時候,“大國學”的構想已被確定為:國內各地域文化和56個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國學”的範圍之內。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又共同構成中國文化這一文化共同體。
面對季老“大國學”的理念,貴州省水書文化研究院副院長潘朝霖認為:“大國學”是一個很可喜的命題,它有利於民族團結、增強民族自信心,也拓寬了少數民族文化發展的思路。如果從“國學”的高度重視少數民族的一些優秀文化,比如有著完整的曆法和文字的水族的文化,那對於這些文化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很少有人知道,水族最早的文字記錄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水書”也因此被稱為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
學界普遍認為,“大國學”思想基本的內涵其實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包容精神。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稱,《中庸》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中所體現出的兼容並蓄,就是“國學”的基本精神核心。所謂“大國學”,本質上也是對“兼容並蓄”這一精神核心的再次強調。
“大國學”蘊含著民族和諧的思想精髓
事實上,研究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可以很清晰地發現這樣一個脈絡——許多少數民族文化和漢族文化長期以來並非各行其道,而是屬於“同源、分化、接觸、吸收”的關係,對於漢文化的一些研究,甚至需要通過對少數民族文化研究來解決。
“譬如許慎《說文解字》中對過年的解釋,‘年,谷熟也’,歷史上的漢族在每年的陰曆八月稻穀豐收之時過年,而現在只有水族仍然傳承著這一文化習俗。理解少數民族的文化,才能反過來理解當時的漢文化習俗。”潘朝霖說。
“很明顯,‘大國學’蘊含著中國作為由56個民族組成的大民族家庭的和諧統一的思想精髓。這個思想告訴並告誡我們的是,中國真正廣義的‘國學’,應該是由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所有文化核心思想的集萃,同時這所有的文化思想又是一脈相承、相輔相成的,它們構成了一個整體的中國文化。”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尹韻公指出。
雖然“大國學”的概念只是剛剛起步研究,但它很顯然指出了一種各民族文化包容並蓄與共同進步的時代趨勢。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傑指出,“大國學”的概念將要影響我們的,或許不只是一種語言上的表述和提法,而是要讓漢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進行更多、更有力的交流,在文化的互補和磨合之中促進整箇中華民族文化的共同繁榮。民族文化的多元共榮是時代的必然趨勢,只有讓56個民族的文化以“大國學”的理念緊密結合在一起,才能組成真正絢爛的中華文化。
王傑說:“漢文化歷來強調一種內斂和中庸的審美,缺乏西方所謂的酒神文化、狂歡文化。而在苗族、侗族等少數民族中,這種狂歡文化則處處可見。文化互補的優點是明顯的,如果將所有的中華民族文化以兼容並蓄的精神進行整合,那將讓傳統‘國學’和少數民族文化處於共榮與互補的良性循環之中,這也許將是‘大國學’理念帶給我們的最好前景。”
“大國學”理念如何落實
事實上,“大國學”兼容並蓄的核心精神已經得到廣泛肯定和認同,下一步,如何將“大國學”的理念落到實處,是擺在人們面前的重要課題。
王傑說,“7月27日至31日在雲南召開的‘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會第十六屆大會’和2010年即將在中國召開的‘國際美學大會’,都不約而同地將‘文化多樣性’列為主題詞。”
不過,“大國學”構想要得以實踐,需要的不僅是全社會對少數民族文化的關注,同時也需要少數民族對自身文化的挖掘和研究。
貴州民族學院教授杜國景說,“少數民族自身的文化挖掘力度還不夠,特別是能站在全國、全世界的平台上和漢文化平等對話的少數民族文化還不多。在我們大力開發少數民族地區旅遊的時候,過於注重物質文化的開發和包裝,相對忽略了對民族精神文化的挖掘和研究,這似乎已成了提‘大國學’概念前最需要改變的問題。”
相關的工作現在已經開始得到重視。據潘朝霖介紹,目前,國家涉及水族文化的社科基金立項就有5項,省級立項也有5項,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現已經收集水書2.2萬冊。近年來,在多方支持下已整理、翻譯、出版水書7部,正在組織出版的還有10餘部。2008年5月,關於保護水書的法規《三都水族自治縣水書文化保護條例》也已獲貴州省人大通過。其他的少數民族文化,現在也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保護。
儘管如此,潘朝霖仍認為,應該進一步以兼容並蓄的心態尋求文化互補和共榮的亮點,同時加強少數民族對自身文化的挖掘,以科學理性的態度來逐步實踐“大國學”。
“唯有這樣,才能讓‘大國學’理念不只是停留於構想。”潘朝霖說。
與中華古籍保護
“國學”是相對於“西學”的概念而提出的。清末民初以來,國學一般指人文科學內的本國之學、本國固有的歷史文化。近二十年,學界對“國學”問題的討論成為熱點,看似爭論不斷,但國學範圍的擴大是一個共同趨勢。提倡國學已不是守舊和倒退,而是強調對於民族文化傳統的自覺意識,彰顯出一種深切的現實關懷。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首任院長馮其庸先生專門到醫院與季羨林先生交流對於“國學”的看法,一致認為“國學”應該是長期以來由多民族共同創造的涵蓋廣博、內容豐富的文化學術。2007年,季羨林先生與中國書店總經理於華剛談話時,明確提出“大國學”觀點。他認為,現在的所謂“國學”,是中國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不是單一的“漢學”,也不是單一的儒學或者道家文化。國學是文化交流的產物,對內是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對外則不斷吸收外來的文化,以豐富和發展傳統文化。2008年,馮其庸先生髮表《大國學即新國學》,指出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國學,甲骨文、簡帛文書、敦煌遺書的發現,乃至西學東漸的過程,都極大擴展了國學的領域。國學有新拓展新進步,就是大國學、新國學。國學的研究對象不能畫地為牢,凡有利於學術問題解決的方法都是國學的研究方法,國學應該堅持中國的學術立場。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就是在“大國學”指導下建立的,其中“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設立是一個標誌。對此,沈衛榮論述說:“我們今天所倡導的國學,理當突破以研究漢族傳統文化為主要內容的舊國學的樊籬,與時俱進,成為與我們民族、國家認同相一致的新國學。也就是說,國學研究的對象,應當是整箇中華民族的歷史和傳統文化;國學研究的目的,應當是揭示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展現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和文化財富;國學研究的成果,應當對加深國人對中華民族這一民族認同的認識,加快我們共同的精神家園的建設做出應有的貢獻。”
“大國學”的提出是中國文化傳統自覺自醒的產物,產生在當代社會有其歷史必然性。雖然提出時間不長,但以其博大胸懷和寬廣的學術視野,在教育、學術界獲得了廣泛認同,在實踐中不斷結出碩果。“大國學”這種建設中華民族共同精神家園的旨歸,對全國古籍保護工作的開展具有借鑑意義。
2007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正式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中華古籍保護計畫”,對全國古籍進行普查、保護、修復,加強對古籍保護人才的培養,強調保護和利用並重,通過公布《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和“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重點加強對珍貴古籍的保護。中華古籍保護計畫實施以來,在全國圖書館、文保單位、宗教單位,乃至古籍收藏界都引起了強烈反響。各省古籍保護中心紛紛成立,政府撥款加強古籍保護和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
典籍是文明的主要載體。古籍中保存著中華傳統文化精髓,其保護、利用和傳承,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基礎工作,也是國學重構的根基和養分。“中華古籍保護計畫”自實施起,就特別重視各民族文獻的共同保護問題。國務院頒布的兩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中,除漢文古籍外,收錄歷史上各民族文字古籍376部,包括焉耆-龜茲文、于闐文、藏文、回鶻文、西夏文、白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滿文、東巴文、傣文、水文、古壯字、布依文、多文種合璧和其他文字古籍文獻,充分體現出保護中華民族共同精神財富的指導思想。特別是《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中對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縣街子清真寺藏十三世紀阿拉伯文寫本《古蘭經》的收錄,體現出對融入到中國文化的外來文化的包容,這與“大國學”的觀念是相通的。古籍保護的對象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典籍的全貌,只有繼承和發揚生活在神州大地上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傳統文化學術,研究其交流歷史和內在聯繫,才能真正建立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
為此,在實施“中華古籍保護計畫”中,要特別重視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要加緊保護少數民族文字文獻,關注其揭示和傳承。少數民族一般居住生活在偏遠地區,民族古籍收藏在地域遼闊的眾多單位和個人手中,不少地區保管條件不善和管理制度不健全,古籍家底不清、保護狀況堪憂。許多少數民族經師年事已高,文化傳承面臨危險。國內缺乏民族古籍修復室和技術熟練的修復技工,與漢文古籍修復相比,在人才上面臨的問題更加突出。“中華古籍保護計畫”開展以來,許多少數民族聚居的省份都成立了古籍保護工作領導小組,組建古籍保護中心,積極組織開展《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申報工作,逐步改變過去行業和部門分割狀況,在古籍普查、編目和登錄方面加強協作。公藏單位、寺廟和個人開展古籍整理和保護的熱情高漲,古籍保護工作逐步深入人心。國家民委也啟動了民族古籍的搶救和提要整理工作,取得了階段成果。政府加大投入,更好地保護民族古籍瑰寶,已經成為加強各民族相互理解和尊重的重要內容,也是各族各地民眾的殷切期待。
二是要注意收集和保護新發現的民族文獻。新材料的發現往往對學術研究起著重要作用。近些年來,在西藏佛塔考古中,不斷發現八世紀左右與敦煌藏文文獻同時代的珍貴文獻。在新疆吐魯番考古和和田地區民間,也發現了南北朝至唐代的多語種文書,對研究該地區政治、經濟制度和民族交流歷史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國家圖書館先後收集到4批500多件和田文書,涉及焉耆-龜茲文、于闐文、藏文、梵文、漢文等文種。段晴對其中非漢語文書進行了初步研究,關於于闐文《對治十五鬼護身符》等文獻的研究成果已經在國際學術界引起震動。榮新江及其弟子對於闐文-漢文木簡和于闐鎮守軍勘印歷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觀的成就。季羨林在世時,對這批文獻的收集給予高度重視,認為是對過去發現的新疆歷史文獻的一個補充。這些文獻揭示了新疆各民族和漢族的交往和融合,是學術研究領域的重要資料。
三是要關注融入中國的外來文化典籍的保護。中國傳統文化不是孤立形成的,受外來文化影響很大。印度佛教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即如此,目前西藏自治區還保存了數百夾五至十四世紀的印度梵文典籍,是研究印中文化交流的重要資料。季羨林主張要了解和研究佛教,最少應懂梵文。他特別推崇玄奘那樣的偉大學者,認為中華幾千年的文化之所以永盛不衰,就是因為通過翻譯外來典籍,使舊文化中隨時能注入新鮮血液。他還認為,我國的佛教文化是多民族共同創造的,在探討“佛教中國化”論題時,應特別關注印度原始佛典的研究,也要關注古代新疆地區“西域三十六國”用“胡語”翻譯佛典的問題。古代新疆地區是各民族文化交匯之地,國家圖書館和田文書中還有一件《希伯來文猶太波斯語書信》,是猶太商人在新疆經商時用希伯來文拼寫波斯語的信件,反映了絲綢之路中外交流的狀況,很有意義。唐代宮廷對外來文化採取開放態度,唐高祖把佛教引入國學,與儒、道並為講授內容。清高宗在編修《四庫全書》時,也把西學東漸的產物歐幾里得《幾何學》譯作等作為經典收錄。我們今天在談古籍保護時,應該關注融入到中國文化的外來文化典籍,這樣才能使傳統文化典籍的傳承更加全面。撒拉族阿拉伯文《古蘭經》入選《中華珍貴古籍名錄》就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四是要重視“大國學”的宣傳,這對正確的中華古籍保護理念在民眾中的傳播非常重要。圖書館界應該聯合組織“文化使者”大講堂,通過系統宣傳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的特點,介紹其內在關聯和交流歷史,探索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歷程,促進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立。
中華古籍保護不是簡單的保存和利用問題,而是傳承中華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的神聖使命。在這個過程中,應通過開放的胸襟和寬闊的視野,重構新時代的國學,造就更加充滿活力的中華文化,探索中華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的普遍意義和普世價值,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