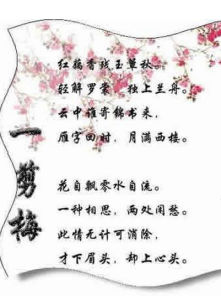原文
 意境畫
意境畫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注釋
“裳”,古音cháng,古人穿的下衣。也泛指衣服。玉簟:音diàn ,光華如玉的精美竹蓆。
雁字:指雁群飛時排成“一”或“人”形。相傳雁能傳書。
詞牌
一剪梅,亦稱“臘梅香”。得名於周邦彥詞中的“一剪梅花萬樣嬌”。雙調六十字,前後闋句句用平韻,一韻到底。八個四字句一般都用對仗。有一體只須前後闋的一、三、六句用韻。格律
趙雁君行草書法《一剪梅》本詞前後闋一、三、六句用韻。(○平聲●仄聲⊙可平可仄△平韻腳▲仄韻腳)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
作者
 李清照
李清照譯文
荷已殘,香已消,冷滑如玉的竹蓆,透出深深的涼秋,輕輕脫換下薄紗羅裙,獨自泛一葉蘭舟。仰頭凝望遠天,那白雲舒捲處,誰會將錦書寄來?正是雁群排成“人”字,一行行南歸時候,月光皎潔浸人,灑滿這西邊獨倚的亭樓。花,自在地飄零,水,自在地漂流,一種離別的相思,你與我,牽動起兩處的閒愁。啊,無法排除的是——這相思,這離愁,剛從微蹙的眉間消失,又隱隱纏繞上了心頭。
賞析
【賞析一】
這首詞在黃升《花菴詞選》中題作“別愁”,是趙明誠出外求學後,李清照抒寫她思念丈夫的心情的。伊世珍《琅嬛記》說:“易安結褵未久,明誠即負笈遠遊。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剪梅》詞以送之。”電影《李清照》沿襲了伊世珍之說,當趙明誠踏上征船出行時,歌曲就唱出《一剪梅》的“輕解羅裳,獨上蘭舟”。把這首詞理解為送別之作,於詞意不盡相符,就是“輕解羅裳”兩句,也難解釋得通。“羅裳”,不會是指男子的“羅衣”,因為不管是從平仄或用字看,沒有必要改“衣”為“裳”。“羅裳”無疑是指綢羅裙子,而宋代男子是不穿裙子的。要是把上句解為寫李清照,下句寫趙明誠,那么,下句哪來主語?兩者文意又是怎樣聯繫的呢?因此,應該以《花菴詞選》題作“別愁”為宜。
李清照和趙明誠結婚後,夫妻感情甚好,家庭生活充滿了學術和藝術的氣氛,十分美滿。
 一剪梅
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
寫出時間是在一個荷花凋謝、竹蓆嫌涼的秋天。“紅藕”,即紅色荷花。“玉簟”,是精美的竹蓆。這一句涵義極其豐富,它不僅點明了時節,指出就是這樣一個蕭疏秋意引起了作者的離情別緒,顯示出全詞的傾向性。而且渲染了環境氣氛,對作者的孤獨閒愁起了襯托作用。如“紅藕香殘”,雖然是表示出秋來了荷花凋謝,其實,也含有青春易逝,紅顏易老之意;“玉簟秋”,雖然是暑退秋來,所以竹蓆也涼了。其實,也含有“人去席冷”之意。
就表現手法及其含義來看,這一句和南唐李璟《浣溪沙》的首句:“菡萏香銷翠葉殘”相類似。同樣是說荷花凋殘,秋天來了。但後者不如前者那么富有詩意:“菡萏香銷”,無疑是不及“紅藕香殘”那樣既通俗又是色澤鮮明;“翠葉殘”意思仍然和“菡萏香銷”一樣,是指秋來荷葉落。但“玉簟秋”,卻不同了,又有一層新的意思。如果說,“紅藕香殘”是從客觀景物來表現秋的到來,那么,“玉簟秋”就是通過作者的主觀感受——竹蓆生涼來表達秋的到來。一句話里把客觀和主觀、景和情都融化在一起了。顯然,同是七個字,但它的涵義就比之李璟句豐富得多。怪不得清朝陳廷焯讚賞說:“易安佳句,如《一剪梅》起七字云:‘紅藕香殘玉簟秋’,精秀特絕,真不食人間煙火者。”(《白雨齋詞話》)李清照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的人,但這一句“精秀特絕”,卻是事實,並非過譽。
李清照本來已因丈夫外出而有所牽掛,如今面對這樣一個荷殘席冷、萬物蕭疏的景象,免不了觸景生情,其思夫之情必然更加縈繞胸懷,內心之苦是不言而喻的。凡人受愁苦的煎熬,總是要想辦法排愁遣悶的,這是人之常情。李清照也不例外。她究竟想如何來消除這愁悶呢?此刻,她不是借酒消愁,也不是悲歌當泣,而是借遊覽以遣悶,下兩句就是這樣引出來的:
輕解羅裳,獨上蘭舟。
就是說,我輕輕地解開了綢羅的裙子,換上便裝,獨自劃著名小船去遊玩吧!上句“輕”字,很有份量,“輕”,是輕手輕腳的意思。它真實地表現了少婦生怕驚動別人,小心而又有幾分害羞的心情。正因為是“輕”,所以誰也不知道,連侍女也沒讓跟隨就獨自上小船了。下句“獨”字就是回應上句的“輕”字的。“羅裳”,是絲綢制的裙子。“蘭舟”,即木蘭舟,船的美稱。這裡用“羅裳”和“蘭舟”很切合李清照的身份。因為這是富貴人家之所獨有。這兩句的涵義,既不同於《九歌·湘君》中的“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寫湘夫人乘著桂舟來會湘君;也不同於張孝祥的《念奴嬌》:“玉鑒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寫張泛舟在廣闊的洞庭湖上的興奮心情。而是極寫李清照思夫之苦,她之所以要“獨上蘭舟”,正是想借泛舟以消愁,並非閒情逸緻的遊玩。這是李清照遣愁的方法之一。其實,“獨上蘭舟”以消愁,若非愁之極何以出此?然而,它不過是像“舉杯消愁愁更愁’一樣。過去也許雙雙泛舟,今天獨自擊楫,眼前的情景,只能勾引起往事,怎能排遣得了呢?不過,李清照畢竟跟一般的女性不同,她不把自己的這種愁苦歸咎於對方的離別,反而構想對方也會思念著自己的。所以,她宕開一筆,寫道:
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前兩句是倒裝句。這幾句意思是說,當空中大雁飛回來時,誰托它捎來書信?我正在明月照滿的西樓上盼望著呢!“誰”,這裡實際上是暗指趙明誠。“錦書”,即錦字回文書,這裡指情書。作者這么寫,看似乎淡,實則含蓄有韻味:一、它體現了李清照夫妻感情的極其深厚、真摯,以及李清照對她丈夫的充分信任。因為如果她對趙明誠感情淡薄,或有所懷疑,就不會想像“雲中誰寄錦書來”,而是必然發出“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或是“盪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古詩十九首·青青河畔草》)的怨言。所以,這裡作者這樣寫,不言情而情已自見。這種借寫事來抒情,正是在藝術創作上最富有感染力的。二、寓抽象於形象之中,因而更覺具體生動。單說“誰寄錦書來”,未免顯得抽象。作者藉助於雁能傳書的傳說,寫道:“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這就通過大雁翔空,形象地表達了書信的到來,使人可看得到,摸得著。雖然這種寫法,並非自她始,但她的雲中雁回比之一般的飛雁傳書,顯然畫面更為清晰,形象更為鮮明,這種點化仍然是值得肯定的。三、它渲染了一個月光照滿樓頭的美好夜景。在這夜景里,即使收到情書,無疑是高興的。但光是這樣理解,還不可能發掘“月滿西樓”句的真正含義。雁傳書信,固可暫得寬慰,但不可能消除她的相思。其實,在喜悅的背後,蘊藏著相思的淚水,這才是真實的感情。“月滿西樓”句和白居易《長相思》的“月明人倚樓”含義相似,都是寫月夜思婦憑欄望遠的。但李作較之白作似乎進了一步,關鍵在於“西”字,月已西斜,足見她站立樓頭已久,這就表明了她思夫之情更深,愁更極。由於李清照既然思念著自己的丈夫,又相信丈夫也會思念著自己,所以,下片也就順此思路開展了:
花自飄零水自流。
有人說,這是寫李清照慨嘆自己“青春易老,時光易逝”。要是這樣,那么,下面“一種相思,兩處閒愁”兩句,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其實,這一句含有兩個意思:“花自飄零”,是說她的青春像花那樣空自凋殘;“水自流”,是說她丈夫遠行了,像悠悠江水空自流。“自”字,是“空自”或“自然”的意思。它體現了李清照的感嘆語氣。這句話看似平淡,實際上含義很深。只要讀者仔細玩味,就不難發覺,李清照既為自己的紅顏易老而感慨,更為丈夫不能和自己共享青春而讓它白白地消逝而傷懷。這種複雜而微妙的感情,正是從兩個“自”字中表現出來的。這就是她之所以感嘆“花自飄零水自流”的關鍵所在,也是她倆真摯愛情的具體表現。唯其如此,所以底下兩句:
一種相思,兩處閒愁。
就自然地引出來了。如果說,上面沒有任何一句提到李清照和他的丈夫的兩相恩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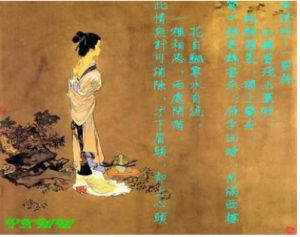 一剪梅
一剪梅那么,李清照的“閒愁”究竟達到了什麼程度呢?下面三句就作了回答:
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就是說,這種相思之情是沒法排遣的,皺著的眉頭方才舒展,而思緒又湧上心頭。一句話就是時刻在相思著。這裡,作者對“愁”的描寫,極其形象。人在愁苦時總是縐著眉頭,愁眉苦臉的。作者正是抓住這一點才寫出“才下眉頭,卻上心頭”兩句,使人若見其眉頭剛舒展又緊蹙的樣子,從而領會到她內心的綿綿痛苦的。“才下”、“卻上”兩個詞用得很好,兩者之間有著連線的關係。所以,它能把相思之苦的那種感情在短暫中的變化起伏,表現得極其真實形象。這幾句和李煜《烏夜啼》的“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意境相似,有異曲同工之妙。
王士禎在《花草蒙拾》中說:“然易安亦從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語胎出,李特工耳。”誠然,李作比之范作已勝一籌。“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總不及“才下眉頭,卻上心頭”那么形象地反映李清照愁眉變化的情景,怪不得成為千古絕唱。
由上看來,李清照這首詞主要是抒寫她的思夫之情。這種題材,在宋詞中為數不少。若處理不好,必落俗套。然而,李清照這首詞在藝術構思和表現手法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因而富有藝術感染力,仍不失為一篇傑作。其特點是:一、詞中所表現的愛情是旖旎的、純潔的、心心相印的;它和一般的單純思夫或怨其不返,大異其趣。二、作者大膽地謳歌自己的愛情,毫不扭捏,更無病態成份;既像蜜一樣的甜,也像水一樣的清,磊落大方。它和那些卿卿我我、扭捏作態的愛情,涇渭分明。三、李詞的語言大都淺俗、清新,明白如話,這首詞也不例外。但它又有自己的特點,那就是在通俗中多用偶句,如“輕解羅裳,獨上蘭舟”、“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才下眉頭,卻上心頭”等等,既是對偶句,又淺白易懂,讀之琅琅上口,聲韻和諧。若非鑄詞高手,難能做到。
【賞析二】
這首詞作於清照和丈夫趙明誠遠離之後,寄寓著作者不忍離別的一腔深情,是一首工巧的別情詞作。詞的起句“紅藕香殘玉簟秋”,領起全篇,上半句“紅藕香殘”寫戶外之景,下半句“玉簟秋”寫室內之物,對清秋季節起了點染作用。全句設色清麗,意象蘊藉,不僅刻畫出四周景色,而且烘托出詞人情懷。意境清涼幽然,頗有仙風靈氣。花開花落,既是自然界現象,也是悲歡離合的人事象徵;枕席生涼,既是肌膚間觸覺,也是淒涼獨處的內心感受。起句為全詞定下了幽美的抒情基調。
接下來的五句順序寫詞人從晝到夜一天內所作之事、所觸之景、所生之情。前兩句“輕解羅裳,獨上蘭舟”,寫的是白晝在水面泛舟之事,以“獨上”二字暗示處境,暗逗離情。下面“雲中誰寄錦書來”一句,則明寫別後的懸念。接以“雁字回時,月滿西樓”兩句,構成一種目斷神迷的意境。按順序,應是月滿時,上西樓,望雲中,見回雁,而思及誰寄錦書來。“誰”字自然是暗指趙明誠。但是明月自滿,人卻未圓;雁字空回,錦書無有,所以有“誰寄”之嘆。說“誰寄”,又可知是無人寄也。詞人因惦念遊子行蹤,盼望錦書到達,遂從遙望雲空引出雁足傳書的遐想。而這一望斷天涯、神馳象外的情思和遐想,無時無刻不縈繞於詞人心頭。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句,承上啟下,詞意不斷。它既是即景,又兼比興。其所展示的花落水流之景,是遙遙與上闋“紅藕香殘”、“獨上蘭舟”兩句相拍合的;而其所象喻的人生、年華、愛情、離別,則給人以淒涼無奈之恨。
下片自此轉為直接抒情,用內心獨自的方式展開。“一種相思,兩處閒愁”二句,在寫自己的相思之苦、閒愁之深的同時,由己身推想到對方,深知這種相思與閒愁不是單方面的,而是雙方面的,以見兩心之相印。這兩句也是上闋“雲中”句的補充和引申,說明儘管天長水遠,錦書未來,而兩地相思之情初無二致,足證雙方情愛之篤與彼此信任之深。這兩句既是分列的,又是合一的。合起來看,從“一種相思”到“兩處閒愁”,是兩情的分合與深化。其分合,表明此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其深化,則訴說此情已由“思”而化為“愁”。下句“此情無計可消除”,緊接這兩句。正因人已分在兩處,心已籠罩深愁,此情就當然難以排遣,而是“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了。
“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三句最為世人所稱道。這裡,“眉頭”與“心頭”相對應,“才下”與“卻上”成起伏,語句結構既十分工整,表現手法也十分巧妙,在藝術上具有很強的吸引力。當然,這兩個四字句只是整首詞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並非一枝獨秀。它有賴於全篇的烘托,特別因與前面另兩個同樣工巧的四字句“一種相思,兩處閒愁”前後襯映,而相得益彰。
【賞析三】
以詞來抒寫相思之情,這並不是什麼新鮮的題材,但李清照這首《一剪梅》以其清新的格調,女性特有的沉摯情感,絲毫“不落俗套”的表現方式,給人以美的享受,顯得越發難能可貴。“紅藕香殘玉簟秋”,首句詞人描述與夫君別後,目睹池塘中的荷花色香俱殘,回房欹靠竹蓆,頗有涼意,原來秋天已至。詞人不經意地道出自己滯後的節令意識,實是寫出了她自夫君走後,神不守舍,對環境變化渾然無覺的情形。“紅藕香殘”的意境,“玉簟”的涼意,也襯托出女詞人的冷清與孤寂。此外,首句的語淡情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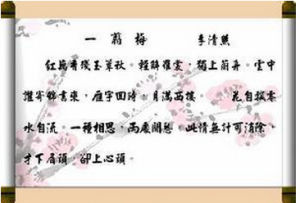 一剪梅
一剪梅下片。“花自飄零水自流”,詞人的思緒又由想像回到現實,並照映上片首句的句意。眼前的景象是落花飄零,流水自去。由盼望書信的到來,到眼前的抒寫流水落花,詞人的無可奈何的傷感油然而生,尤其是兩個“自”字的運用,更表露了詞人對現狀的無奈。“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次寫詞人自己思念丈夫趙明誠,也構想趙明誠同樣在思念自己。這樣的斷語,這樣的心有靈犀,是建立在夫妻相知相愛的基礎上的。末三句,“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詞人以逼近口語的詞句,描述自己不僅無法暫時排遣相思之情,反而陷入更深的思念境地。兩個副詞“才”、“卻”的使用,很真切形象地表現了詞人揮之又來、無計可消除的相思之情。
這是一首相當富有詩情畫意的詞作。詞人越是把她的別情抒寫得淋漓盡致,就越能顯出她的夫妻恩愛的甜蜜,也越能表現出她對生活的熱愛。此外,這首詞在意境的刻畫,真摯、深沉情感的表述,以及語言運用的藝術上,無不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輯評
一、元伊世珍《琅嬛記》卷中引《外傳》:易安結縭未久,明誠即負岌遠遊。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剪梅》詞以送之。詞曰(略)。二、明楊慎批點楊金本《草堂詩餘》卷三:離情慾淚。讀此始知高則誠、關漢卿諸人,又是效顰o
三、明茅映《詞的》卷三:香弱脆溜,自是正宗。
四、明李攀龍《草堂詩餘雋》卷五眉批:“多情不隨雁字去,空教一種上眉頭。”評語:“惟錦書、雁字,不得將情傳去,所以一種相思,眉頭心頭,在在難消。”
五、明王世貞《弇州山人詞評》:李易安“此情無計可消除,方下眉頭,又上心頭。”可謂憔悴支離矣。
六、明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時本落“西”字,作七字句,非調。是元人樂府妙句。關、鄭、白、馬諸君,固效顰耳。
七、明李廷機《草堂詩餘評林》卷二:此詞頗盡離別之情,語意超逸,令人醒目。
八、明張醜《清河書畫舫》申集引《才婦錄》:易安詞稿一紙,乃清秘閣故物也。筆勢清真可愛。此詞《漱玉集》中亦載,所謂離別曲者耶?卷尾略無題識,僅有點定兩字耳。錄具於左:“(詞略,唯“月滿西樓”,作“月滿樓”)”。右調(一剪梅)。
九、明徐士俊《古今詞統》卷十:“樓”字上不必增“西”字。劉伯溫“雁短人遙可奈何”亦七字句,仿此。
十、清王士禛《花草蒙拾》:俞仲茅小詞云:“輪到相思沒處辭,眉間露一絲。”視易安“才下眉頭,卻上心頭”,可謂此兒善盜。然易安亦從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語脫胎,李特工耳。
十一、清沈雄《古今詞話·詞辨》卷上:周永年曰:《一剪梅》唯易安作為善。劉後村換頭亦用平字,於調未葉。若“雲中誰寄錦書來”,與“此情無計可消除”,“來”字、“除”字,不必用韻,似俱出韻。但“雁字回時月滿樓”,“樓”字上失一“西”字。劉青田“雁短人遙可奈何”,“樓”上似不必增“西”字。今南曲只以前段作引子,詞家復就單調,別名“剪半”。將法曲之被管弦者,漸不可究詰矣。
十二、清萬樹《詞律》卷九:“月滿樓”,或作“月滿西樓”。不知此調與他詞異。如“裳”、“思”、“來”、“除”等字,皆不用韻,原與四段排比者不同。“雁字”句七字,自是古調。何必強其入俗,而添一‘“西”字以湊八字乎?人若欲填排偶之句,自有別體在也。
十三、清張宗橚《詞林紀事》卷十九:此《一剪梅》,變體也。前段第五句原本無“西”字,後人所增。舊譜謂脫去一字者,非。又按:《汲古閣宋詞》,此闋載入《惜香樂府》,恐誤。
十四、清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卷三:易安《一剪梅》詞起句“紅藕香殘玉簟秋”七字,便有吞梅嚼雪,不識人間煙火氣象,其實尋常不經意語也。
十五、清陳世焜(廷悼)《雲韶集》卷十:起七字秀絕,真不食人間煙火者。梁紹壬謂:只起七字已是他人不能到。結更淒絕。
十六、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二:易安佳句,如《一剪梅》起七字云:“紅藕香殘玉簟秋”,精秀特絕,真不食人間煙火者。
十七、清況周頤《〈漱玉詞〉箋》:玉梅詞隱雲,易安精研宮律,所以何至出韻。周美成倚聲傳家,為南北宋關鍵,其《一剪梅》第四句均不用韻,詎皆出韻耶?竊謂《一剪梅》調當以第四句不用韻一體為最早,晚近作者,好為靡靡之音,徒事和暢,乃添入此葉耳。
十八、王學初《李清照集校注》卷一:又按,清照適趙明誠時,兩家俱在東京,明誠正為太學生,無負岌遠遊事。此則(指本輯評“一”)所云,顯非事實。而李清照之父(李格非)稱為李翁,一似不知其名者,尤見蕪陋。《琅嬛記》乃偽書,不足據。
十九、陳邦炎:……從上闋開頭三句看,決不像柳永《雨霖鈴》詞所寫的“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那樣一個分別時的場面,而是寫詞人已與趙明誠分離,在孤獨中感物傷秋、泛舟遣懷的情狀。次句中的“羅裳”,固明指婦女服裝;第三句中的“獨上”,也只能是詞人自述。至於以下各句,更非“構想別後的思念心情”,而是實寫別後的眼前景、心中事……“一種相思,兩處閒愁”二句,在寫自己的相思之苦、閒愁之深的同時,由己身推想到對方,深知這種相思與閒愁不是單方面的,而是雙方面的,以見兩心之相印。這兩句也是上闋“雲中”句的補充和引申,說明儘管天長水遠,錦書未來,而兩地相思之情初無二致,足證雙方情愛之篤與彼此信任之深。前人作品中也時有寫兩地相思的句子,如羅鄴的《雁立首》之二“江南江北多離別,忍報年年兩地愁”、韓偓的《青春》詩“櫻桃花謝梨花發,斷腸青春兩處愁”:這兩句詞可能即自這些詩句化出,而一經熔鑄、剪裁為兩個句式整齊、詞義鮮明的四字句,就取得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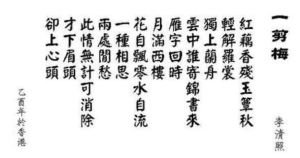 一剪梅
一剪梅二十、謝桃坊:此是清照名篇,前人評論頗多,以為其“離情慾淚”,“香弱脆溜,自是正宗”,但關於全詞意脈,則語焉不詳。關鍵在於上片的“蘭舟”一詞乃清照的自我作占,常被注家誤訓,如王仲聞先生雲“即木蘭舟”,胡云翼先生謂“獨上蘭舟”乃“獨自坐船出遊,都與上下文義扦格。這是因為詞的上片描敘抒情環境,“紅藕香殘”暗寫季節變化;“玉簟秋”謂竹蓆已有秋涼之意;“雁字回時”為秋雁南飛之時;“月滿西樓”,西樓為女主人公住處,月照樓上,自然是夜深了。若以“蘭舟”為木蘭舟,為何女主人公深夜還要獨自坐船出遊呢?而且她“獨上蘭舟”時,為何還要“輕解羅裳”呢?這樣解釋顯然與整個環境是矛盾的。清照有一首《浣溪沙》(應為《南歌子》)與《一剪梅》的抒情環境很相似,其上闋云:“天上星河轉,人間簾幕垂。涼生枕簟淚痕滋。起解羅衣,聊問夜何其。”“涼生枕簟”與“玉簟秋”,“起解羅衣”與“輕解羅裳”“夜何其”與“月滿西樓”,兩詞意象都相似或相同。兩詞的上片都是寫女主人公秋夜在臥室里準備入睡的情形。此時她絕不可能忽然“獨自坐船出遊”的。“蘭舟”只能理解為床榻,“輕解羅裳,獨上蘭舟”,即是她解卸衣裳,獨自一人上床榻準備睡眠了。“玉簟秋”乃睡時的感覺,聽到雁聲,見到月光滿樓,更增秋夜孤寂之感,於是詞的下片抒寫對丈夫的思念便是全詞意脈必然的發展了。(《百家唐宋詞新話》,四川文藝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
二十一、吳功正:在中國文學史上,妻子對遠離的丈夫的思念之作,可謂史不絕朽。這幾乎是一種共同的文化現象,而又正反映了一種普遍的、共同的心理現象,揭示出我們民族的女子多愁善感的心理特徵。正因為這類情感具有普遍性、共性,李清照的《一剪梅》等詞作揭示了它,這才使這類詞篇產生了普遍意義,能夠引起不同時代的人們的相同的情感體驗和共鳴。但是,問題又有另一面,車載斗量般的思婦之作,自《詩經》以降,能傳世者又能有多少?只有用詩人、詞人經過獨特地感受和體驗出的情感表達出來,以個性另闢蹊徑地揭示出心理共性,這才能獲得典型價值。美學範疇的典型形象、典型情緒,所涵蓋的正是這一意義。這首《一剪梅》具備了上述的審美特徵,方能傳世不朽,令九百載後的今人不禁為之動容。李清照,這位女性、女性詞人、具有不同凡近的氣質的女性詞人,既有女性的一般心理特徵,又有她獨得天籟靈性的個性特徵。這就使得她能在《一剪梅》中表現出雙重的審美功能:精微的審美體驗、精妙的審美傳達。這就是我們把握、賞析這首詞的美學依據……“才下眉頭,卻上心頭。”這兩句是絕妙好詞!是女詞人筆底甩出的“豹尾”,……從審美內容上分析這兩句詞,是女詞人對相思情的獨特體驗和捕捉。相思之情,特別是心心相印的思念情,是人類最普遍的情感之一。它“剪不斷,理還亂”,一旦萌發,難以消遏;它銘心刻骨,像遊絲一般地附著、粘著。它可以從外在情態的“眉頭”上消除,卻又會不自禁地鑽入“心頭”。李清照對這種情感作了獨特、深細的體察和把握。從美學結構上分析這兩句詞,詞人一路寫來,或融情於景,或景中寓情,意象或隱或顯,時露時藏,於結尾處猛然一甩,如群山的高峰、塔頂的裝飾、爆亮的燈蕊,給讀者強烈的美感刺激,使之震動、深思、遐想,體驗箇中三昧。女詞人以她獨特的方式感知到人類最普遍存在的一種情感,又以她獨特的技巧表達出這一情感,凝為審美的晶體,這首詞就產生了永久的藝術魅力。任何能夠傳世的作品都是在深、廣、高的層次上個性化地傳達出人類的普遍意識、情感,從而喚起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國土的人們的審美體驗。
擴展閱讀
不朽丹神http://www.7kwx.com/0/49/光明紀元http://www.7kwx.com/0/202/
獨裁之劍http://www.7kwx.com/0/146/
造神http://www.7kwx.com/0/195/
大聖傳http://www.7kwx.com/0/206/
武動乾坤http://www.7kwx.com/0/10/
天下梟雄http://www.7kwx.com/0/205/
明朝好丈夫http://www.7kwx.com/0/100/
八零後少林方丈http://www.7kwx.com/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