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鄉土小說是要有意地寫出這鄉土的特徵、滋味和魅力來。表層是風物習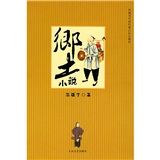 圖書封面
圖書封面作者簡介
馮驥才,當代作家和畫家,生長於天津。1960年高中畢業後到天津市書畫社從事繪畫工作,對民間藝術、地方風俗等產生濃厚興趣。1978年調天津市文化局創作評論室,後轉入作協天津分會從事專業創作,任天津市文聯主席、國際筆會中國中心會員、《文學自由談》和《藝術家》主編等職。其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巳出版各種作品集近五十餘種。其中《啊》、《雕花菸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蓮》、《俗世奇人》等均獲全國文學獎。《感謝生活》由《炮打雙燈》改編的同名電影獲“夏威夷電影節”和“西班牙電影節”獎。作品被譯成英、法、德、意、日、俄、荷等十餘種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種譯本三十種。目錄
關於鄉土小說(代序)市井人物
蘇七塊
酒婆
馮五爺
認牙
好嘴楊巴
張大力
小楊月樓義結李金鰲
炮打雙燈
鷹拳
奇人管萬斤
逛娘娘宮
閒扯——《怪世奇談》序
神鞭——《怪世奇談》之一
三寸金蓮——《怪世奇談》之二
陰陽八卦——《怪世奇談》之三
神燈前傳
精彩書摘
市井人物蘇七塊
蘇大夫本名蘇金傘,民國初年在小白樓一帶,開所行醫,正骨拿環,天津衛掛頭牌。連洋人賽馬,折胳膊斷腿,也來求他。
他人高袍長,手瘦有勁,五十開外,紅唇皓齒,眸子賽燈,下巴頦兒一綹山羊須,浸了油賽的烏黑鋥亮。張口說話,聲音打胸腔出來,帶著丹田氣,遠近一樣響,要是當年入班學戲,保準是金少山的冤家對頭。他手下動作更是“乾淨麻利快”,逢到有人傷筋斷骨找他來,他呢?手指一觸,隔皮截肉,裡頭怎么回事,立時心明眼亮。忽然雙手賽一對白鳥,上下翻飛,疾如閃電,只聽“咔嚓咔嚓”,不等病人覺疼,斷骨頭就接上了。貼塊膏藥,上了夾板,病人回去自好。倘若再來,一準是鞠大躬謝大恩送大匾來了。
人有了能耐,脾氣準格色。蘇大夫有個格色的規矩,凡來瞧病,無論貧富親疏,必得先拿七塊銀元碼在台子上,他才肯瞧病,否則決不搭理。這叫嘛規矩?他就這規矩!人家罵他認錢不認人,能耐就值七塊,因故得個挨貶的綽號叫做:蘇七塊。當面稱他蘇大夫,背後叫他蘇七塊,誰也不知他的大名蘇金傘了。
蘇大夫好打牌,一日閒著,兩位牌友來玩,三缺一,便把街北不遠的牙醫華大夫請來,湊上一桌。玩得正來神兒,忽然三輪車夫張四闖進來,往門上一靠,右手托著左胳膊肘,腦袋瓜淌汗,脖子周圍的小褂濕了一圈,顯然摔壞胳膊,疼得夠勁。可三輪車夫都是賺一天吃一天,哪拿得出七塊銀元?他說先欠著蘇大夫,過後準還,說話時還哼喲哼喲叫疼。誰料蘇大夫聽賽沒聽,照樣摸牌看牌算牌打牌,或喜或憂或驚或裝作不驚,腦子全在牌桌上。一位牌友看不過去,使手指指門外,蘇大夫眼睛仍不離牌。“蘇七塊”這綽號就表現得斬釘截鐵了。
牙醫華大夫出名的心善,他推說去撒尿,離開牌桌走到後院,鑽出後門,繞到前街,遠遠把靠在門邊的張四悄悄招呼過來,打懷裡摸出七塊銀元給了他。不等張四感激,轉身打原道返回,進屋坐回牌桌,若無其事地接著打牌。
過一會兒,張四歪歪扭扭走進屋,把七塊銀元“嘩”地往台子上一碼,這下比按鈴還快,蘇大夫已然站在張四面前,挽起袖子,把張四的胳膊放在台子上,捏幾下骨頭,跟手左拉右推,下頂上壓。張四抽肩縮頸閉眼齜牙,預備重重挨幾下,蘇大夫卻說:“接上了。”當下便塗上藥膏,夾上夾板,還給張四幾包活血止疼口服的藥面子。張四說他再沒錢付藥款,蘇大夫只說了句:“這藥我送了。”便回到牌桌旁。
今兒的牌各有輸贏,更是沒完沒了,直到點燈時分,肚子空得直叫,大家才散。臨出門時,蘇大夫伸出瘦手,攔住華大夫,留他有事。待那二位牌友走後,他打自己座位前那堆銀元里取出七塊,往華大夫手心一放。在華大夫驚愕中說道:
“有句話,還得跟您說。您別以為我這人心地不善,只是我立的這規矩不能改!”
華大夫把這話帶回去,琢磨了三天三夜,到底也沒琢磨透蘇大夫這話里的深意。但他打心眼兒里欽佩蘇大夫這事這理這人。
酒婆
酒館也分三六九等。首善街那家小酒館得算頂末尾的一等。不插幌子,不掛字號,屋裡連座位也沒有;櫃檯上不賣菜,單擺一缸酒。來喝酒的,都是扛活拉車賣苦力的底層人。有的手捏一塊醬腸頭,有的衣兜里裝著一把五香花生,進門要上二三兩,倚著牆角窗台獨飲,逢到人擠人,便端著酒碗到門外邊,靠樹一站,把酒一點點倒進嘴裡,這才叫過癮解饞其樂無窮呢!
這酒館只賣一種酒,使山芋乾造的,價錢賤,酒味大。首善街養的貓從來不丟,跑迷了路,也會循著酒味找回來。這酒不講餘味,只講衝勁,進嘴賽鏹水,非得趕緊咽,不然燒爛了舌頭嘴巴牙花嗓子眼兒。可一落進肚裡,跟手一股勁“騰”地躥上來,直撞腦袋,暈暈乎乎,勁頭很猛。好賽大年夜裡放的那種炮仗“炮打燈”,點著一炸,紅燈躥天。這酒就叫做“炮打燈”。好酒應是溫厚綿長,絕不上頭。但窮漢子們掙一天命,筋酸骨乏,心裡憋悶,不就為了花錢不多,馬上來勁,暈頭漲腦地灑脫灑脫放縱放縱嗎?
要說最灑脫,還得數酒婆。天天下晌,這老婆子一準來到小酒館,衣衫破爛,賽叫花子;頭髮亂,臉色黯,沒人說清她嘛長相,更沒人知道她姓嘛叫嘛,卻都知道她是這小酒館的頭號酒鬼,尊稱酒婆。她一進門,照例打懷裡掏出個四四方方小布包,打開布包,裡頭是個報紙包,報紙有時新有時舊;打開報紙包,又是個綿紙包,好賽裡頭包著一個翡翠別針;再打開這綿紙包,原來只是兩角錢!她拿錢撂在櫃檯上,老闆照例把多半碗“炮打燈”遞過去,她接過酒碗,舉手揚脖,碗底一翻,酒便直落肚中,好賽倒進酒桶。待這婆子兩腳一出門坎,就賽在地上劃天書了。
她一路東倒西歪向北去,走出一百多步遠的地界,是個十字路口,車來車往,常常出事。您還甭為這婆子揪心,瞧她爛醉如泥,可每次將到路口,一準是“噔”地一下,醒過來了!竟賽常人一般,不帶半點醉意,好端端地穿街而過。她天天這樣,從無閃失。首善街上人家,最愛瞧酒婆這醉醺醺的幾步扭--上擺下搖,左歪右斜,悠悠旋轉樂陶陶,看似風擺荷葉一般;逢到雨天,雨點淋身,便賽一張慢慢旋動的大傘了……但是,為嘛酒婆一到路口就醉意全消呢?是因為“炮打燈”就這么一點勁頭兒,還是酒婆有超人的能耐說醉就醉說醒就醒?
酒的訣竅,還是在酒缸里。老闆人奸,往酒里摻水。酒鬼們對眼睛裡的世界一片模糊,對肚子裡的酒卻一清二楚,但誰也不肯把這層紙捅破,喝美了也就算了。老闆缺德,必得報應,人近六十,沒兒沒女,八成要絕後。可一日,老闆娘愛酸愛辣,居然有喜了!老闆給佛爺叩頭時,動了良心,發誓今後老實做人,誠實賣酒,再不往酒里摻水摻假了。
就是這日,酒婆來到這家小酒館,進門照例還是掏出包兒來,層層打開,花錢買酒,舉手揚脖,把改假為真的“炮打燈”倒進肚裡……真貨就有真貨色。這次酒婆還沒出屋,人就轉悠起來了。而且今兒她一路上搖晃得分外好看,上身左搖,下身右搖,愈轉愈疾,初時賽風中的大鵬鳥,後來竟賽一個黑黑的大漩渦!首善街的人看得驚奇,也看得納悶,不等多想,酒婆已到路口,竟然沒有酒醒,破天荒頭一遭轉悠到大馬路上。下邊的慘事就甭提了……
自此,酒婆在這條街上絕了跡。小酒館裡的人們卻不時念叨起她來,說她才算真正夠格的酒鬼。她喝酒不就菜,向例一飲而盡,不貪解饞,只求酒勁。在酒館既不多事,也無閒話,交錢喝酒,喝完就走,從來沒賒過帳。真正的酒鬼,都是自得其樂,不攪和別人。
老闆聽著,忽然想到,酒婆出事那日,不正是自己不往酒里摻假的那天嗎?原來禍根竟在自己身上!他便彆扭開了,心想這人間的道理真是說不清道不明了。到底騙人不對,還是誠實不對?不然為嘛幾十年拿假酒騙人,卻相安無事,都喝得挺美,可一旦認真起來反倒毀了?
馮五爺
馮五爺是浙江寧波人。馮家出兩種人,一經商,一念書。馮家人聰明,腦袋瓜賽粵人翁伍章雕刻的象牙球,一層套一層,每層一花樣。所以馮家人經商的成巨富,念書的當文豪做大官。馮五爺這一輩五男二女,他排行末尾。幾位兄長遠在上海天津開廠經商,早早的成家立業,站住腳跟。惟獨馮五爺在家啃書本。他人長得賽條江鯽,骨細如魚刺,肉嫩如魚肚,不是賺錢發財的長相,倒是舞文弄墨的材料。凡他念過的書,你讀上句,他背下句,這能耐據說只有宋朝的王安石才有。至於他出口成章,落筆生花,無人不服。都說這一輩馮家的出息都在這五爺身上了。
馮五爺二十五,父母入土,他賣房地、攜家帶口來到天津衛,為的是投兄靠友,謀一條通天路。
他心氣高,可天津衛是商埠,毛筆是用來記帳的,沒人看書,自然也沒人瞧得起念書的。比方說,地上有黃金也有書本,您撿哪樣?別人發財,馮五爺眼熱,腦筋一歪,決意下海做買賣。但此道他一竅不通,乾哪行呢?
中國人想賺錢,第一個念頭便是開飯館。民以食為天,民為食花錢;一天三頓飯,不吃腿就軟,錢都給了飯館老闆。天津的錢又都在商人手裡,商界的往來大半在飯桌上。再說,天津產鹽,吃菜口重,寧波菜鹹,正合口味。於馮五爺拿定主意,開個寧波風味的館子,便在馬家口的鬧市里,選址蓋房,取名“狀元樓”。擇個吉日,升匾掛彩,燃鞭放炮,飯館開張了。馮五爺身穿藏藍暗花大褂,胸前晃著一條純金表鏈,中印分頭,滿頭抹油,地道的老闆打扮,站在大廳迎賓迎客,應付八方。念書的人,講究禮節,談吐又好,很得人緣。再說,狀元樓是天津衛獨一家寧波館,海魚河蝦都是天津人解饞的食品,在寧波廚子手裡一做,比活魚活蝦還鮮。故此開張以來,天天坐滿堂,晚上一頓還得“翻台”,上一長,賺錢並不多。馮五爺納悶,天天一把把銀錢,賽一群群鳥飛進來,都落到哪兒去了?往後再瞧帳,喲,反倒出了赤字!
一日,一個打寧波幫工來的小夥計,抖著膽子告訴他,廚房裡的雞鴨魚肉,進到客人嘴裡的有限,大多給廚子夥計們截牆扔出去,外邊有人接應。狀元樓有多少錢經得住天天往外扔?
馮五爺盛怒之後,心想自己嘛腦袋,《二十四史》背得滾瓜爛熟,能拿這幫端盤子炒菜的沒轍?這就開刀了。除去那個打寧波老家帶來的胖廚子沒動,其餘夥計全轟走,斬草除根換一撥人,還在後院牆頭安裝電網,以為從此相安無事,可帳上仍是赤字,怎么回事?
又一日,住在狀元樓鄰近一位婆子,咬耳朵對他說,每天後晌,垃圾車一到,一搖鈴鐺,打狀元樓里抬出的七八個土箱子,只有上邊薄薄一層是垃圾,下邊全是鐵皮罐頭、整袋鹹魚、好酒好煙。原來內外勾結,用這法兒把東西弄走。這不等於拿土箱子每天往外抬錢嗎?馮五爺趕在一個後晌倒垃圾的時候,上前一查,果然如此。大怒之下,再換一撥人。人是換了,但帳本上的赤字還是沒有換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