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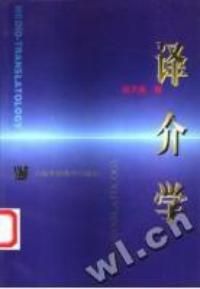 《譯介學》
《譯介學》作/譯者:謝天振著
出版社: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年02月
ISBN:9787810465267[十位:7810465260]
頁數:336
內容簡介
譯介學是比較文學視野下迥異於語言研究的跨文化研究.本書通過大量例子具體討論翻譯過程中出現的文化信息的失落與變形、"創造性叛逆"、翻譯文學的承認以及翻譯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關係等譯介學問題.
譯介學,從寬泛意義上來講,就是指從文化層面上對翻譯,尤其對文學翻譯所進行的一種跨文化研究。隨著當前各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已經有學者預言,這種研究將成為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界的熱點。
目錄
序一
序二
緒論
第一章翻譯和翻譯研究中的文學傳統
第一節西方翻譯史上的文藝學派
第二節俄國翻譯史上的文藝學派
第三節中國翻譯史上的文藝學派
第二章二十世紀文學翻譯研究的趨向
第一節文學翻譯的空間發達
第二節不僅僅史語言學派
第三節蘇聯與歐盟--強勁有力的文藝學派
第四節中國:文學翻譯主體意識的覺醒
第三章文學翻譯的叛逆性翻譯
第一節文學翻譯的創造性與叛逆性
第二節媒介者的創造性叛逆
第三節接受者與環境的創造性叛逆
作者簡介
謝天振,1944年3月生,浙江蕭山人,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翻譯理論家。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翻譯研究所所長,《中國比較文學》季刊主編,《中國翻譯》編委,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暨翻譯研究會顧問,上海翻譯家協會理論組組長,中國翻譯協會翻譯理論與教學委員會委員,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翻譯委員會委員。復旦大學兼職博士生導師(比較文學譯介學方向),北京大學、暨南大學、四川大學、四川外語學院等校兼職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比較文學研究中心顧問。
譯介學的相關評論
一、譯介學在中國的提出及尷尬
目前,從比較文學和文化角度進行翻譯研究被國內學界普遍稱為譯介學,置於比較文學之下。譯介學倡導者首推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翻譯研究會會長謝天振。謝教授自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起開始發表譯介學系列論文,1993年在國內出版第一部譯介學專著《譯介學》,得到眾多學者的肯定。賈植芳認為,《譯介學》的研究,不僅在國內處於學術的前沿,即使在國際學術界,也同樣處於學術發展的前沿。《譯介學》的出版,揭開了從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角度研究翻譯的新層面,開拓了國內翻譯研究的新領域。①王向遠認為,謝天振從比較文學切入翻譯研究,逐步系統地建構了譯介學的理論體系,在比較文學及翻譯研究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②目前,譯介學的提法在國內已經被廣泛採納,大多數比較文學論著和教材都有專章論述譯介學或譯介論。比如,陳惇、孫景堯、謝天振主編的《比較文學》(1989)首次將譯介學納入全書的框架體系中;張鐵夫主編的《新編比較文學教程》在“影響研究”下,把“譯介學”與傳統的“流傳學”、“淵源學”和“媒介學”並列進行評介;曹順慶教授在2003年主編的《比較文學論》中把“譯介學”歸在“媒介學”下,在2006年的《比較文學教程》第二章“變異研究”中從“文學變異與文化過濾”、“譯介學”、“形象學”、“接受學”、“文學的他國化研究”等角度探討比較文學研究中的變異研究;而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2002)則把“譯介論”列為專章講述。由此觀之,譯介學概念及其內涵、外延已經確定,並深入學術重地,譯介學研究也成為當下學術發展的增長點和推動力。
儘管這個概念在學術權威的推動下逐步成為公認的學術史實,但是我們不得不懷疑:這個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其內涵、外延以及自身邏輯邊界是否清晰,它的能指與所指是否有矛盾,其與西方的翻譯研究概念的異同何在?張寧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譯介學與翻譯研究這兩個概念在使用上的混亂:“‘譯介學’的法文對應詞應是latraductologie,詞根由‘翻譯’與‘學問’兩部分構成;而英文常見的說法則是TranslationStudies,可直譯為‘翻譯研究’或‘翻譯學’。總之,它是關於翻譯的學問。譯介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包括文學翻譯、翻譯文學文本和翻譯理論三個方面。由於它所關注之重心在於兩種文化轉換中的語言媒介,故被稱做譯介學,亦可稱之為譯介理論。”①這顯示了譯介學作為一種翻譯研究學問在外延和內涵上與比較文學關係的混淆;而廖七一甚至認為,時至今日,“譯介學”仍無法找到相應的英文術語,使謝天振教授面臨杜撰術語“Medio-translatology”的尷尬;西方至今仍然沒有與譯介學理論相關、較為系統和完整的專著問世。②那么,譯介學為什麼會遭到如此尷尬,西方為什麼沒有出現“Medio-translatology”的術語和專著呢?真的是西方翻譯研究界和比較文學界缺乏這種創新嗎?凡是進入比較文學視野中的翻譯研究都可以稱為譯介學嗎?讓我們針對當前西方翻譯研究現狀作一番梳理,來看看其中的究竟。
二、進入比較文學視野中的當代西方翻譯研究流派
我們知道,文化轉向使翻譯研究的眾多領域都進入了比較文學的視野,並具有文學、文化研究的性質。與語言學派以原文為中心不同,文化轉向以來的翻譯研究另闢蹊徑,把目光投向了譯本,逐步形成了“譯本研究派”(或稱“翻譯研究學派”)。該派關於翻譯理論的許多語料都是文學性的,都是基於比較文學的研究需要提出的:“‘翻譯研究’學派所從事的研究是在比較文學的框架下進行的,它力圖解決的問題正是比較文學所要解決的問題,使用的也正是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③王東風、鍾鈺將成立於1976年的TranslationStudies學派譯成“譯本研究派”,該派的主要特點是採用歷史描寫主義的方法,對譯本生成的文化和詩學意義以及譯本生成與文化背景的互動進行描寫,因此,其理論導向以描寫性為主。該派以強勁的勢頭很快便把語言學翻譯研究推出了舞台。論者指出,由於歷史和習慣的原因,使用這個術語的學者大多有比較文學的學術背景,他們將比較文學中文本研究的方法用在文學翻譯研究上,其主要的方法論就是譯本研究,從而形成了與傳統翻譯理論所不同的獨特的視角和方法論。④簡言之,相對於翻譯研究的語言學派,譯本研究派注重以譯本為中心巨觀歷時地描述翻譯的功能,具有鮮明的文化意識,是多個相交相迭的分支流派的合稱。具體來說,該學派大致包括霍姆斯(JamesS·Holmes)代表的早期譯本研究派、埃文-佐哈爾(ItamarEven-Zohar)代表的多元系統學派、圖里(TouryGideon)代表的描寫或常規學派、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和勒弗維爾(AndréLefevere)代表的文化學派、斯內爾-霍恩比(MarySnell-Hornby)代表的綜合學派、韋努蒂(LawrenceVenuti)代表的解構學派、西蒙(SherrySimon)代表的女權主義學派、尼蘭加納(Te-jaswiniNiranjana)代表的後殖民主義學派或國際政治學派等。而且我們可以發現,這些西方翻譯研究流派與譯介學在比較文學的關係互動上其實是背道而馳的,在概念的內涵、外延與邏輯上有著互逆的對立關係。下面試以西方翻譯研究流派的具體特徵與譯介學特徵進行比較。
霍姆斯從比較文學的立場出發,認為翻譯者的目標是雙重的,“翻譯出來的文本一方面必須是原詩的譯本,同時它也必須是可以在譯語中單獨存在的一首詩歌”⑤。許冬平、王東風在評論霍姆斯的貢獻時指出:譯本研究派應研究分析譯文(作為從屬性的文本)與原文的關係以及譯文(作為原生文本)對目標文化中文學傳統的影響。因此,霍爾姆斯“描寫分支”中對翻譯進行描述的方法很快為譯本研究派所推崇。①霍姆斯開創的譯本研究派已經成為當代翻譯研究的主流,使翻譯研究與比較文學、文化研究融為一體。多元系統論是針對文化、文學層面的,對比較文學非常偏重。張柏然、辛紅娟認為:“多元系統論把翻譯結果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文學翻譯與整個文學體系和文化體系的關係及其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其實質是研究譯入語文化對以翻譯為媒介的外國文學的接受問題以及該翻譯文學對譯入語文學和文化的影響問題。外國文學的接受問題實質上是一個文學史問題,確切地說,是比較文學的問題,主要研究一個民族在接受外國文學時接受什麼、怎樣接受、接受的效果以及接受過程中的各種因素和現象。”②多元系統論注重探討歷時的演變與發展,試圖探索經典化與非經典化、主要與次要、中心與邊緣等文學類型的互動關係,這些對文學翻譯研究和比較文學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描寫翻譯學派(亦稱“常規學派”)的骨幹分子都有文學研究的背景,對比較文學與文學史有濃厚的興趣,並利用自己的影響,在比較文學界擴大翻譯研究的作用、提升翻譯研究的地位。圖里以多元系統理論為框架,提出以譯語為中心的翻譯觀,認為描述性翻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發現制約翻譯活動的潛在性規範。該論產生於對同一原文在不同歷史時期由不同譯者翻譯的文本所進行的比較研究。而這與比較文學的研究並無二致。特奧·赫爾曼斯最先把“操縱”觀用於翻譯理論研究。之後勒弗維爾的《翻譯、重寫和文學名聲的操縱》等又發展了這一理論。關於操縱學派及其與比較文學的關係,斯奈爾-霍恩比做過這樣的總結:“操縱學派的著作著重描寫和分析譯本,比較同一著作的不同譯本,著重調查不同譯本的接受並追溯廣闊的歷史調查;總之,除了所研究的翻譯作品不是原作外,操縱學派的著作與比較文學的傳統研究有許多共同點。”③巴斯奈特和勒弗維爾把翻譯置於文化研究的廣闊背景中,強調歷史意識和文化觀點。二人把翻譯和翻譯研究的學術地位提升到了相當的高度。在他們看來,譯文與原文享有平等的地位,有時甚至會超過原文。譯者作為翻譯活動的主體,被提升到了“操縱者”的地位上。他們在1990年出版的論文集《翻譯、歷史與文化》中正式提出了“翻譯的文化轉向”這一口號。該文集對文論、比較文學、文學史及翻譯學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文化學派試圖尋找系統制約翻譯文學文本接受、認可和拒斥的非常具體的因素,即諸如權力、意識形態、體制和操縱的問題。這些正是翻譯研究和比較文學發生文化轉向後所要面對的問題。斯奈爾-霍恩比的《翻譯學的綜合研究法》(1987)客觀地分析了相關學科,如語言學、比較文學、心理學、哲學等對翻譯研究的影響。霍恩比批評萊比錫學派將翻譯研究視做套用語言學的分支,同時又批評操縱學派將翻譯研究視做比較文學的分支。她吸收了兩派理論之長處,強調翻譯是一門獨立學科。她強調文化背景對翻譯研究的重要作用,指出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活動。“綜合學派”主張將文化、歷史、社會、文學和區域研究等綜合起來研究翻譯,突顯翻譯研究的跨學科、跨語言和跨文化特質,這為跨學科翻譯研究開闢了途徑。④勞倫斯·韋努蒂將翻譯的歸化/異化放在後殖民的語境下來考察,揭示翻譯話語中的民族中心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的實質,提出了異化翻譯策略。異化是對當今世界事務的一個聰明的文化干預,是對民族中心主義、文化自戀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的一種抵制,有利於在全球地域政治關係中推行民主。⑤解構主義理論對當前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產生深遠影響,反對西方文化霸權成為翻譯研究和比較文學共同面對的主題。此外,比較文學與後殖民翻譯、女性主義翻譯對東西方、男女之間不平等權力關係、文化形象再現等的研究都有著很多重合和一致的地方。
通過對以上學派的內涵和特質進行分析就會發現,譯本研究派都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進行比較文化研究,也就是說翻譯研究並不從屬於比較文學研究,而是相反。譯本研究派與“譯介學”概念其實就是一種互逆的關係:西方翻譯學派注重的是翻譯本體和語言本體,比較文學從屬於它,而“譯介學”注重的是比較本體,它從屬於比較文學研究。那么,同樣是翻譯研究,為什麼東西方在它與比較文學研究的從屬關係上觀點卻截然相反呢?這值得我們反思。
三、譯介學反思
謝天振認為,《譯介學》是從比較文化的角度出發對翻譯(尤其是文學翻譯)和翻譯文學進行的研究。嚴格而言,譯介學的研究不是一種語言研究,而是一種文學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關心的不是語言層面上出發語與目的語之間如何轉換的問題,而是原文在這種外語和本族語轉換過程中信息的失落、變形、增添、擴伸等問題,是翻譯(主要是文學翻譯)作為人類一種跨文化交流的實踐活動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和意義。①這樣來看,其內涵正與當前西方譯本研究派重合。譯介學學科建構中包括創造性叛逆、翻譯文學史等全部涵蓋在譯本研究派之內。可以說,所謂譯介學不過是譯本研究派的整體挪用。譯介學的內涵還意味著,文化轉向以來30多年的西方翻譯研究及其所努力做出的學科建構仍然只是比較文學的一部分。但是,隨著接受美學、解構理論和文化研究的興起,翻譯研究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翻譯研究與比較文學的關係也因此發生了根本轉變,翻譯研究屬於比較文學研究分支學科的說法受到質疑。巴斯奈特甚至提出:“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已經過時了。女性研究、後殖民理論和文化研究這三個方面涉及的跨文化研究,已經改變了文學研究的面貌。從現在起們應把翻譯學視為一門主要學科,並把比較文學視為其中的一個有價值但卻是輔助性的研究領域。”②中國學者雖然反對,認為這種觀點“混淆了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翻譯研究與作為比較文學一個研究分支的翻譯研究之間的界限”③,“比較文學所從事的並不是一般的跨文化研究,而是跨文化的文學研究,我們所談的翻譯也不是一般的翻譯而僅指文學翻譯,因此,對比較文學學科來說,翻譯永遠是其十分重要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但從學科定義出發,永遠不會有巴斯奈特所說的那樣的顛倒”。④但是,譯本研究派中的多元系統派、文化派、女性主義派和後殖民主義派與譯介學研究幾乎完全重合,而將這些派別置於比較文學之下顯然有悖於西方學界的初衷。也就是說,將譯介學置於比較文學之下實際上就是將譯本研究派即文化轉向翻譯研究30多年的成果置於比較文學之下,這等於否定了西方學者所有的努力。從整個西方來看,在比較文學瀕臨危機,廣大學者大張旗鼓提升翻譯研究地位,迅速擴充翻譯研究內涵,積極建構翻譯研究學科的時候,自然不會再將翻譯研究歸於比較文學之下,因此西方所謂譯介學的稱謂也就無從談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