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牛破車》
《老牛破車》本書收錄
 《老牛破車》
《老牛破車》《我怎樣寫老張哲學》、《我怎樣寫趙子曰》、《我怎樣寫二馬》、《我怎樣寫小坡的生日》、《我怎樣寫大明湖》、《我怎樣寫貓城記》、《我怎樣寫離婚》、《我怎樣寫短篇小說》、《我怎樣寫牛天賜傳》、《談幽默》、《景物的描寫》、《人物的描寫》、《事實的運用》、《言語與風格》等14篇文章,再現了一代大師的心路歷程。讀完使人感慨,如此樂天的一代大家,怎么會自沉而死。。。
序
 《老牛破車》
《老牛破車》書名《老牛破車》,在第一段開頭有簡單說明,即不再叨嘮。從(一)到(九)都是照原來計畫,自評作品——打《老張的哲學》說到《牛天賜傳》。作品只有此數,本當就此打住,哪知還得出書,相應湊些字兒。所以又寫了(十)至(十四)。不能預評將來的書,勉強談點作小說的技巧。對否,不敢說,有用不呢,您瞧著辦。是為序。
老舍
一九三六年秋,青島。
小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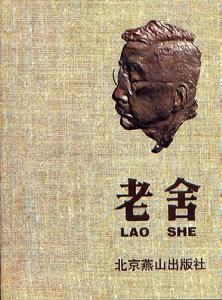 《老牛破車》
《老牛破車》籌備會的錢已花光,成立大會的補助金還沒能全領下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成立大會
是輝煌燦爛的過去了,拿什麼去辦事呢?窮自有窮辦法:先召集理事會,推舉出常務理事
來;有人就有辦法!常務理事馬上就職,開會、籌款。請會員交會費,自是最合理的,可是
遠水不能近喝,山南海北,一時哪能交齊?以身作則,常務理事先掏錢吧。當場收了幾十
塊,趕緊就去印信封信紙,買各樣的簿冊,刻圖章,備筆墨。有了這些東西,才能上公文,
請求黨政機關發給補助——分頭去接洽自然是必要的,車錢自己墊。誰來管理這些檔案呢?
總務部按章應設庶務會計文牘等人員,可是薪水並不能自天而降。於是大家決定先請一位略
受津貼的幹事,自兼三職,自拉自唱;而各部幹事都須到會辦公,發動一切。
就是這么樣,會務開始活動開。該寫的、該印的、該發出的、該存記的、該辦的、該籌
劃的,大家七手八腳都一擁而上。到前線慰勞的代表出發了,帶著錦旗和慰勞書;盤費先自
己墊上,回來再算賬。為武漢各界擴大宣傳周所寫的文章也連夜趕齊,特刊、小冊子、函
信,都交了卷。還得出會刊,是的,出版部主任,你就去辦吧。他忙起來,許多人自動的願
作幹事,好在章程上幹事是若干人,多多愈善。座談會也要舉行的。給軍士寫讀物也事在必
辦……的確是沒閒著,自然外間也許不大理會。一切都剛開頭,而錢是那么不寬綽。外埠的
理事和會員也許連會裡的信還沒接到一封。請別忙,郵遞是真慢,而我們的文牘只有兩隻
手,又兼任會計與庶務!
慢慢來,一定都有辦法。請求補助已有批示,不久就能拿到錢;會刊一出來,各地訊息
自然靈通,而該進行的事必定一樁樁的都辦起來。希望各處的會員早交會費,多一個錢就多
作一分事,決不存在銀行專為生利。希望大家都給會刊寫文章,多給會裡來信,說明各處要
本會作的是什麼,和大家要給本會作的是什麼。在武漢的與在各處的朋友都能忙起來,會務
才能日見發展。凡是本會不周不到之處,請大家不要只友善的原諒,還要發問,指示,以期
共勵齊進。好,算是會務報告的帽兒。
載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抗戰文藝》第一期
著作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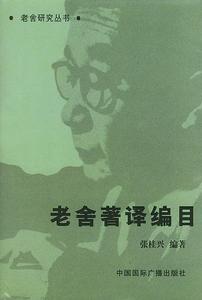 《老牛破車》
《老牛破車》(1)我怎樣寫《大明湖》
在上海把《小坡的生日》交出,就跑回北平;住了三四個月;什麼也沒寫。
被約到濟南去教書。到校後,忙著預備功課,也沒工...故事的進展還是以愛情為聯繫,這裡所謂愛情可並不是三角戀愛那一套。痛快著一點來說,我寫的是性慾問題。在女子方面,重要的人物是很窮的母女兩個。母親受著性慾與窮困的兩重壓迫,而扔下了女兒不再管。她交結過好幾個男人,全沒有所謂浪漫故事中的追求與迷戀,而是直截了當的講肉與錢的獲得。讀書的青年男女好說自己如何苦悶,如何因失戀而想自殺,好像別人都沒有這種問題,而只有他們自己的委屈很值錢似的。所以我故意的提出幾個窮男女,說說他們的苦處與需求。在她所交結的幾個男人中,有一個是非常精明而有思想的人。他雖不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
(2)我怎樣寫《二馬》
《二馬》中的細膩處是在《老張的哲學》與《趙子曰》里找不到的,“張”與“趙”中的潑辣恣肆處從《二馬》以後可是也不多見了。人的思想不必一定隨著年紀而往穩健里走,可是文字的風格差不多是“晚節漸於詩律細”的。讀與作的經驗增多,形式之美自然在心中添了分量,不管個人願意這樣與否。《二馬》是我在國外的末一部作品:從“作”的方面說,已經有了些經驗;從“讀”的方面說,我不但讀得多了,而且認識了英國當代作家的著作。心理分析與描寫工細是當代文藝的特色;讀了它們,不會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劣,我開始決定往“細”里寫...
(3)我怎樣寫《火葬》
在“七七”抗戰那一年的前半年,我同時寫兩篇長篇小說。這兩篇是兩家刊物的“長篇連載”的特約稿,約定:每月各登萬字,稿酬十元千字。這樣,我每月就能有二百元的固定收入,可以作職業寫家矣。兩篇各得三萬餘字,暴敵即詭襲蘆溝橋,遂不續寫。兩稿與書籍俱存在濟南的齊魯大學內,今已全失。十一月,我從濟南逃出,直到去年①夏天,始終沒有想過長篇。為稍稍盡力於抗戰的宣傳,人家給我出什麼題,我便寫什麼;好壞不管,只求盡力;於是,時間與精力零售,長篇不可得矣。還有,在抗戰前寫作,選定題旨,可以從容蒐集材料,而後再從容的排列,從容的修改。抗戰中,一天有一天的特有的生活,難得從容,乃不敢輕率從事長篇。再說,全面抗戰,包羅萬象,小題不屑於寫,大題又寫不上來,只好等等看。去年夏天到北碚,決定寫箇中篇小說...
(4)我怎樣寫《劍北篇》
我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天才,但對文藝的各種形式都願試一試。小說,試過了,沒有什麼驚人的成績。話劇,在抗戰中才敢試一試,全...是這么一回事:一九三九年夏天,我被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會派遣參加北路慰問團,到西北去慰勞抗戰將士。由夏而冬,整整走了五個多月,共二萬里。路線是由渝而蓉,北出劍閣;到西安;而後入潼關到河南及湖北;再折回西安,到蘭州,青海,綏遠,榆林和寧夏。這些地方幾乎都是我沒有到過的,所以很想寫出一點東西來,以作紀念。到處忙於看與走,事事未能詳問,乃決定寫長詩...
(5)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
七月七剛過去,老牛破車的故事不知又被說過多少次;小兒女們似睡非睡的聽著;也許還沒有聽完,已經在夢裡飛上天河去了;第二天晚上再聽,自然還是怪美的。但是我這個老牛破車,卻與“天河配”沒什麼關係,至多也不過是迎時當令的取個題目而已;即便說我貼“謊報”,我也犯不上生氣。最合適的標題似乎應當是“創作的經驗”,或是“創作十本”,因為我要說的都是關係過去幾年中寫作的經驗,而截至今日,我恰恰發表過十本作品。是的,這倆題目都好。可是,比上老牛破車,它們顯然的缺乏點兒詩意。再一說呢,所謂創作,經驗,等等都比老牛多著一些“吹”;謙虛是不必要的,但好吹也總得算個毛病。那末,咱們還是老牛破車吧...
(6)我怎樣寫《離婚》
也許這是個常有的經驗吧:一個寫家把他久想寫的文章撂在心裡,撂著,甚至於撂一輩子,而他所寫出的那些倒是偶然想到的。有好幾個故事在我心裡已存放了六七年,而始終沒能寫出來;我一點也不曉得它們有沒有能夠出世的那一天。反之,我臨時想到的倒多半在白紙上落了黑字。在寫《離婚》以前,心中並沒有過任何可以發展到這樣一個故事的“心核”,它幾乎是忽然來到而馬上成了個“樣兒”的。在事前,我本來沒打算寫個長篇,當然用不著去想什麼。邀我寫個長篇與我臨陣磨刀去想主意正是同樣的倉促。是這么回事:《貓城記》在《現代》雜誌登完,說好了是由良友公司放入《良友文學叢書》里。我自己知道這本書沒有什麼好處,覺得它還沒資格入這個《叢書》。可是朋友們既願意這么辦,便隨它去吧,我就答應了照辦。及至事到臨期,現代書局又願意印它了,而良友撲了個空。於是良友的“十萬火急”來到,立索一本代替《貓城記》的。我冒了汗!可是我硬著頭皮答應下來;知道拚命與靈感是一樣有勁的...
(7)我怎樣寫《駱駝祥子》
從何月何日起,我開始寫《駱駝祥子》?已經想不起來了。我的抗戰前的日記已隨同我的書籍全在濟南失落,此事恐永無對證矣... 這本書和我的寫作生活有很重要的關係。在寫它以前,我總是以教書為正職,寫作為副業,從《老張的哲學》起到《牛天賜傳》止,一直是如此。這就是說,在學校開課的時候,我便專心教書,等到學校放寒暑假,我才從事寫作。我不甚滿意這個辦法。因為它使我既不能專心一志的寫作,而又終年無一日休息,有損於健康。在我從國外回到北平的時候,我已經有了去作職業寫家的心意;經好友們的諄諄勸告,我才就了齊魯大學的教職。在齊大辭職後,我跑到上海去,主要的目的是在看看有沒有作職業寫家的可能。那時候,正是“一二八”以後,書業不景氣,文藝刊物很少,滬上的朋友告訴我不要冒險。於是,我就接了山東大學的聘書。我不喜歡教書,一來是我沒有淵博的學識,時時感到不安;二來是即使我能勝任,教書也不能給我象寫作那樣的愉快。為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獨斷獨行的丟掉了月間可靠的收入,可是我的心裡一時一刻也沒忘掉嘗一嘗職業寫家的滋味...
(8)我怎樣寫《貓城記》
自《老張的哲學》到《大明湖》,都是交《小說月報》發表,而後由商務印書館印單行本。《大明湖》的稿子燒掉,《小坡的生日》...在思想上,我沒有積極的主張與建議。這大概是多數諷刺文字的弱點,不過好的諷刺文字是能一刀見血,指出人間的毛病的:雖然缺乏對思想的領導,究竟能找出病根,而使熱心治病的人知道該下什麼藥。我呢,既不能有積極的領導,又不能精到的搜出病根,所以只有諷刺的弱點,而沒得到它的正當效用。我所思慮的就是普通一般人所思慮的,本用不著我說,因為大家都知道。眼前的壞現象是我最關切的;為什麼有這種惡劣現象呢?我回答不出。跟一般人相同,我拿“人心不古”――雖然沒用這四個字――來敷衍...
(9)我怎樣寫《牛天賜傳》
《牛天賜傳》,就是和我自己的其他作品比較起來,也沒有什麼可吹的地方。一篇東西的好壞,有許多使它好或使它壞的原因。在這許多原因里,作家當時的生活情形是很要緊的。《牛天賜傳》吃虧在這個上不少。我記得,這本東西是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廿三日動筆的,可是直到七月四日才寫成兩萬多字。三個多月的工夫只寫了這么點點,原因是在學校到六月尾才能放暑假,沒有充足的工夫天天接著寫。在我的經驗里,我覺得今天寫十來個字,明天再寫十來個字,碰巧了隔一個星期再寫十來個字,是最要命的事。這是向詩神伸手乞要小錢,不是創作...
(10)我怎樣寫《小坡的生日》
離開倫敦,我到大陸上玩了三個月,多半的時間是在巴黎。在巴黎,我很想把馬威調過來,以巴黎為背景續成《二馬》的後半。只是...離開歐洲,兩件事決定了我的去處:第一,錢只夠到新加坡的;第二,我久想看看南洋。於是我就坐了三等艙到新加坡下船。為什麼我想看看南洋呢?因為想找寫小說的材料,像康拉德的小說中那些材料。不管康拉德有什麼民族高下的偏見沒有,他的著作中的主角多是白人;東方人是些配角,有時候只在那兒作點綴,以便增多一些顏色――景物的斑斕還不夠,他還要各色的臉與服裝,作成個“花花世界”。我也想寫這樣的小說,可是以中國人為主角,康拉德有時候把南洋寫成白人的毒物――征服不了自然便被自然吞噬,我要寫的恰與此相反,事實在那兒擺著呢:南洋的開發設若沒有中國人行么?中國人能忍受最大的苦處,中國人能抵抗一切疾痛:毒蟒猛虎所盤據的荒林被中國人剷平,不毛之地被中國人種滿了菜蔬。中國人不怕死,因為他曉得怎樣應付環境,怎樣活著...
(11)我怎樣寫《趙子曰》
我只知道《老張的哲學》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和登完之後由文學研究會出單行本。至於它得了什麼樣的批評,是好是壞,怎么好和怎么壞,我可是一點不曉得。朋友們來信有時提到它,只是提到而已,並非批評;就是有批評,也不過三言兩語。寫信問他們,見到什麼批評沒有,有的忘記回答這一點,有的說看到了一眼而未能把所見到的保存起來,更不要說給我寄來了。我完全是在黑暗中。
(12)我怎樣寫短篇小說
我最早的一篇短篇小說還是在南開中學教書時寫的;純為敷衍學校刊物的編輯者,沒有別的用意。這是十二三年前的事了。這篇東西...這可就有了文章:合起來,我在寫長篇之前並沒有寫短篇的經驗。我吃了虧。短篇想要見好,非拚命去作不可。長篇有偷手。寫長篇,全篇中有幾段好的,每段中有幾句精彩的,便可以立得住。這自然不是理應如此,但事實上往往是這樣;連讀者仿佛對長篇――因為是長篇――也每每格外的原諒。世上允許很不完整的長篇存在,對短篇便不很客氣。這樣,我沒有一點寫短篇的經驗,而硬寫成五六本長的作品;從技巧上說,我的進步的遲慢是必然的。短篇小說是後起的文藝,最需要技巧,它差不多是仗著技巧而成為獨立的一個體裁。可是我一上手便用長篇練習,很有點象練武的不習“彈腿”而開始便舉“雙石頭”,不被石頭壓壞便算好事;而且就是能夠力舉千斤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笨勁。這點領悟是我在寫了些短篇後才得到的...
(13)我怎樣寫通俗文藝
在抗日戰爭以前,無論怎樣,我絕對想不到我會去寫鼓詞與小調什麼的。抗戰改變了一切。我的生活與我的文章也都隨著戰鬥的急潮...抗戰以後,濟南失陷以前,我就已經注意到如何利用鼓詞等宣傳抗戰這個問題。記得,我曾和好幾位熱心宣傳工作的青年去見大鼓名手白雲鵬與張小軒先生,向他們討教鼓詞的寫法。後來,濟南失陷,我逃到武漢,正趕上台兒莊大捷,文章下鄉與文章入伍的口號既被文藝協會提出,而教育部,中宣部,政治部也都向文人們索要可以下鄉入伍的文章。這時候,我遇到了田漢先生。他是極熱心改革舊劇的,也鼓勵我馬上去試寫。對於舊劇的形式與歌唱,我懂得一些,所以用不著去請導師。對於鼓詞等,我可完全是外行,不能不去請教。於是,我就去找富少舫和董蓮枝女士,討教北平的大鼓書與山東大鼓書。同時,馮煥章將軍收容了三四位由河南逃來唱墜子的,我也朝夕與他們在一道,學習一點墜子的唱法。馮將軍還邀了幾位畫家,繪畫抗戰的“西湖景”,托我編歌詞,以便一邊現映畫片,一邊歌唱...
(14)閒話我的七個話劇
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我並不明白什麼是小說,同樣的,當我開始寫劇本的時候,我也並不曉得什麼是戲劇。文藝這東西,從一方面說,好象是最神秘的,因為到今天為止,我已寫過十好幾本小說和七個劇本,可是還沒有一本象樣子的,而且我還不敢說已經懂得了何為小說,哪是劇本。從另一方面說呢,它又象毫不神秘――在我還一點也不明白何為小說與劇本的時節,我已經開始去寫作了!近乎情理的解釋恐怕應當是這樣吧:文藝並不是神秘的,而是很難作得好的東西。因此,每一個寫家似乎都該記住:自滿自足是文藝生命的自殺!只吹騰自己有十年,廿年,或卅年的寫作經驗,並不足以保障果然能寫出好東西來!在另一方面,毫無寫作經驗的人,也並無須氣短,把文藝看成無可捉摸的什麼魔怪,只要有了通順的文字,與一些人生經驗,誰都可以拿起筆來試一試。有些青年連普通的書信還寫不通,連人生的常識還沒有多少,便去練習創作,就未免又把文藝看得過低,轉而因毫無所獲,掉過頭來復謂這過低的東西實在太神秘了...
(15)言語與風格
小說是用散文寫的,所以應當力求自然。詩中的裝飾用在散文里不一定有好結果,因為詩中的文字和思想同是創造的,而散文的責任則在運用現成的言語把意思正確的傳達出來。詩中的言語也是創造的,有時候把一個字放在那裡,並無多少意思,而有些說不出來的美妙。散文不能這樣,也不必這樣。自然,假若我們高興的話,我們很可以把小說中的每一段都寫成一首散文詩。但是,文字之美不是小說的唯一的責任。專在修辭上討好,有時倒誤了正事...
(16)人物的描寫
按照舊說法,創作的中心是人物。憑空給世界增加了幾個不朽的人物,如武松、黛玉等,才叫作創造。因此,小說的成敗,是以人物...可是近代文藝受了兩個無可避免的影響――科學與社會自覺。受著科學的影響,不要說文藝作品中的事實須精確詳細了,就是人物也須合乎生理學心理學等等的原則。於是佳人才子與英雄巨人全漸次失去地盤,人物個性的表現成了人物個性的分析。這一方面使人物更真實更複雜,另一方面使創造受了些損失,因為分析不就是創造。至於社會自覺,因為文藝想多盡些社會的責任,簡直的就顧不得人物的創造,而力求羅列事實以揭發社會的黑暗與指導大家對改進社會的責任。社會是整個的,複雜的,從其中要整理出一件事的系統,找出此事的意義,並提出改革的意見,已屬不易;作者當然顧不得注意人物,而且覺得個人的志願與命運似乎太輕微,遠不及社會革命的重大了...
(17)景物的描寫
在民間故事裡,往往拿“有那么一回”起首,沒有特定的景物。這類故事多數是純樸可愛的,但顯然是古代流傳下來的,把故事中的人名地點與時間已全磨了去。近代小說就不同了,故事中的人物固然是獨立的,它的背景也是特定的。背景的重要不只是寫一些風景或東西,使故事更鮮明確定一點,而是它與人物故事都分不開,好似天然長在一處的。背景的範圍也很廣:社會,家庭,階級,職業,時間等等都可以算在裡邊。把這些放在一個主題之下,便形成了特有的色彩。有了這個色彩,故事才能有骨有肉。到今日而仍寫些某地某生者,就是沒有明白這一點...
(18)事實的運用
小說中的人與事是相互為用的。人物領導著事實前進是偏重人格與心理的描寫,事實操縱著人物是注重故事的驚奇與趣味。因靈感而設計,重人或重事,必先決定,以免忽此忽彼。中心既定,若以人物為主,須知人物之所思所作均由個人身世而決定;反之,以事實為主,須注意人心在事實下如何反應。前者使事實由人心輻射出,後者使事實壓迫著個人。若是,故事才會是心靈與事實的循環運動。事實是死的,沒有人在裡面不會有生氣。最怕事實層出不窮,而全無聯絡,沒有中心。一些零亂的事實不能成為小說...
(19)談幽默
“幽默”這個字在字典上有十來個不同的定義。還是把字典放下,讓咱們隨便談吧。據我看,它首要的是一種心態。我們知道,有許多人是神經過敏的,每每以過度的感情看事,而不肯容人。這樣人假若是文藝作家,他的作品中必含著強烈的刺激性,或牢騷,或傷感;他老看別人不順眼,而願使大家都隨著他自己走,或是對自己的遭遇不滿,而傷感的自憐。反之,幽默的人便不這樣,他既不呼號叫罵,看別人都不是東西,也不顧影自憐,看自己如一活寶貝。他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點,而技巧的寫出來。他自己看出人間的缺欠,也願使別人看到。不但僅是看到,他還承認人類的缺欠;於是人人有可笑之處,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處一想,人壽百年,而企圖無限,根本矛盾可笑。於是笑裡帶著同情,而幽默乃通於深奧。所以Thackeray(薩克萊)①說:“幽默的寫家是要喚醒與指導你的愛心,憐憫,善意――你的恨惡不實在,假裝,作偽――你的同情與弱者,窮者,被壓迫者,不快樂者。”...
老舍簡介
 《老牛破車》
《老牛破車》老舍(l899.2.3—1966.8.24),滿族,原名舒慶春,字舍予,生於北京。父親是一名滿族的護軍,陣亡在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城的炮火中。母親也是旗人.靠替人洗衣裳做活計維持一家人的生活。1918年夏天,他以優秀的成績由北京師範學校畢業,被派到北京第十七國小去當校長。1924年夏應聘到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當中文講師。在英期間開始文學創作。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是第一部作品,由1926年7月起在《小說月報》雜誌連載,立刻震動文壇。以後陸續發表了長篇小說《趙子曰》和《二馬》。奠定了老舍作為新文學開拓者之一的地位。1930年老舍回國後,先後在齊魯大學和山東大學任教授。這個時期創作了《貓城記》、《離婚》、《駱駝樣子》等長篇小說,《月牙兒》、《我這一輩子》等中篇小說,《微神》等短篇小說。1944年開始,創作近百萬字的長篇巨著《四世同堂》。他擔任全國文聯和全國作協副主席兼北京文聯主席,是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常委。1966年“文革”中不堪躪辱投湖自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