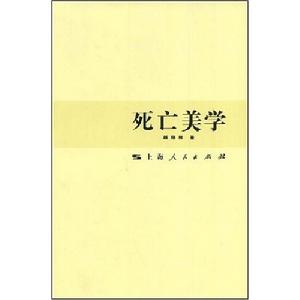 《死亡美學》
《死亡美學》基本信息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頁碼:386 頁 ·
出版日期:2008年
ISBN:9787208079854
條形碼:9787208079854
版本:1版
裝幀:平裝
開本:16 ·
中文:中文
作者簡介
 顏翔林
顏翔林內容簡介
《死亡美學》從美學、文化哲學、神話學、解釋學等世界對人類精神現象學的最高命題——生與死予以本體論、生存論、價值論的詩意運思,進而進入生存與毀滅和藝術的美學探究,在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前提下,結合文化史、藝術史的豐富資料,提出一系列富有審美發現意義的見解。
《死亡美學》分為五個邏輯相承的部分。導論部分,簡述思想文化對於生存與毀滅這一永恆精神主題的沉思。價值論部分,對生死命題予以價值論的沉思,並結合藝術文本加以分析。本體論部分。闡釋東西方富有代表性的生存哲學及其死亡意識。對生與死予以生存論的領會。創造論部分,援引豐富的藝術史現象論述死亡意象及其表現方式。欣賞論部分,從闡釋學、接受美學角度分析欣賞者對於死亡意象的藝術欣賞和審美發現。
目錄
第一編 美與藝術的永恆家園
第一章 走向美學的終極
第一節 永遠的玄學
第二節 藝術宮殿里的常春藤
第三節 美學的鐘情目標
第二章 終極與誕生
第一節 終點與起點
第二節 理性和情感的對峙與和解
第三節 哲學、藝術的永恆母題
第二編 死亡的價值追問
第三章 死亡價值是什麼
第一節 孔子云:殺身以成仁
第二節 基督教曉諭:善者人天堂
第三節 今道友信說:死是最高的美學命題
第四章 死亡價值為什麼
第一節 生與死、藝術與美走向什麼目標
第二節 藝術如何言說死亡的意義
第三節 林中路:何謂美學意義的死亡價值
第三編 人類精神的黑色花冠
第五章 死亡的本體論話語
第一節 死亡文化
第二節 精神界無法超脫的二律背反
第六章 生與死的詩性沉思
第一節 徘徊於真假之間的死亡
第二節 死亡的悲與喜的雙重變奏
第三節 美的死亡和死亡的非美
第七章 死亡意象的美學巡視
第一節 死亡·藝術·美學
第二節 繽紛的現象
第三節 相關性的觀照
第四節 特殊性之詮釋
第四編 面對死亡的藝術靈感
第八章 藝術和死亡的親和力
第一節 與生俱來的死亡意識
第二節 歷史殘酷性的普遍決定力量
第九章 審美選擇
第一節 死亡:美、自由、超越
第二節 蒙克說:我的家庭是疾病與死亡的家庭
第三節 藝術家超越死亡的工具
第十章 詩性的迷霧
第一節 不與物交,淡之至也
第二節 生死皆著我之色彩
第三節 白鹿精靈與畢卡索的牛頭
第五編 如何解讀藝境中的死亡意象
第十一 章藝術即智慧
第一節 文化語境
第二節 觀千劍而後識器
第三節 歷史的魔圈
第十二 章以心悟道
第一節 價值的槓桿
第二節 理性--藝術的標尺
第三節 走向虛無
第十三 章高山流水
第一節 披文人情還是物我兩忘?
第二節 心靈之橋
第三節 康德說:我理解柏拉圖甚於柏拉圖對自己的理解
結語: 黑色的魔語 主要參考文獻 主要人名、術語對照
作者後記:最後的江南
文摘
第一編 美與藝術的永恆家園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
日暮秋煙起,蕭蕭楓樹林。
仰視遠古的天宇:神話巫術交糅浪漫楚風所孕化的那顆孤獨而痛苦、空靈而灑脫的詩星,以生命的軌跡勾畫出輝煌不朽的文學經典——《楚辭》 ,它既是對人生終極價值的追問:生死的最高意義是什麼?如何得以可能?也是對美和愛的絕對信仰:普遍的倫理原則和個體的完善人格是逾時間之維的永恆力量。與此相關,美善的個體生命可以逾越死亡的限定而獲得精神之不朽。詩人對於“死亡”——這個最高的哲學問題和最高的美學問題予以詩意的沉思和哲學化的想像,他努力藝術性地克服死亡和想像性地超越死亡,乃至在意志的實踐行為方面棄生赴死,以死的衝動(Necrophilious orientation)實現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達到最本真的存在。屈原用“驚采絕艷”的神話之網交織詩意的死亡空間,他是中華文化史上第一個吟詠死亡的詩人,也是第一個熱戀死亡和 超越死亡的詩人!
漫遊濠梁,觀望清澈秋水中悠然從容的游魚,分享生命律動的快樂,和它們進行以心會心、超越語言的神秘對話;從曳尾於污泥中的烏龜和展翅扶搖的鯤鵬,感悟到生命自由的美。這些都是莊周“生的衝動”(Biophilious orientation)潛意識的自然流露,是他生命智慧和詩意情懷的審美釋放。然而,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當妻子死亡,莊子卻“方箕踞鼓盆而歌”。他和髑髏夢中對話,暗藏哲學的玄機,以寓言表達如此的思想:生存是人生之累,是精神和肉體的雙重勞苦,死亡反倒是痛苦之解脫,是自由和歡樂的復歸。
後記
最後的江南
由江淮負笈瀟湘,多少次途經皖贛線,透過車窗讀皖南,不禁有誤入南宋詞境的感喟,這也許就是讀書人的夢裡江南了。
一次秋雨濛濛的傍晚車行,臉貼玻璃,看流動的雲,依戀地包裹青山,一隻山羊在青草密密的山坡上悠閒,小溪兩岸是濕漉漉的樹木或竹子,綠得使人不得不動心卻又無法說點什麼。三兩隻白鷺,在黃綠駁雜的水田,或立,或徘徊,或飛,讓人懷疑是從明清兩代的哪幅寫意畫而來。依我看,更像是從自己童年記憶中的洪澤湖西岸的那片沼澤飛來。田埂間,犄角如彎弓的黑水牛溫和謙恭地低頭吃草,間或停頓喘息,無言四望,仿佛哲學家模樣地沉思,它也許在追問:何謂世界的本質和可能?草是什麼?自我是什麼?我為何吃草?為何而活?活著何為幸福和痛苦?黑乎乎的斗笠下,披著破舊蓑衣的蒼老農夫,猶如一件鮮活的文物,蹲在一株茂密的柳樹下抽旱菸,周身繞以淡淡的煙霧,似乎忘卻世界上還有一種叫時間的東西。車外拂面而來悠然而去的灰瓦粉牆,木雕門窗,滄桑的石拱橋,還有長著青苔的石牌坊,寂寞地守望著清澈的河水從自己的身影里了無聲息地穿過,它們是對於喜歡追問和懷舊的讀書人的悄悄提醒,引誘我們沉浸古老的建築空間而忘卻現實時間,一步邁回到古典江南,重回歷史母親的柔軟腹中……
透過雨簾,車窗外幾許朦朧,皖南是一片讓人百讀不厭和百讀不透的風景。現代化的魔杖已經攪亂了幾乎所有的“江南”,繁榮和污染、進步和墮落以正比例的方式撕碎了讀書人的江南夢。也許,皖南就是夢幻中的最後江南了。當然,皖南有朝一日也會被現代文明最終蠶食,成為陳舊蒼黃和霉變發酸的夢,零落為一堆沾滿塵埃的感傷故事……
列車在蜿蜒的山谷間緩慢行駛,不時地喘氣鳴笛,像一個疲憊的行吟詩人。幽靜古雅的皖南誘惑每一個經過者駐足觀望,投去感懷的一瞥。
評論
上個世紀的最後一個十年之交,中國詩壇在連續五年中失去了五位卓有才華的年輕詩人。從1987年女詩人蝌蚪為情割脈開始,海子臥軌,駱一禾病故,戈麥投水,顧城懸樹。即便上溯文學史,這種爆發式的詩人非正常死亡現象也屬罕見。它帶著鮮明的時代色彩,連同詩人們潛藏悲劇意識的詩作一起被人長久記憶。有意味的是,當人們現在屢屢回首那段歲月,似乎仍舊對當時直指終極價值的詩情與理性不能忘懷。所以才有人急切地想要開始追憶:閃開!讓我歌唱八十年代。
某種意義上來說,“死亡”之於今日都市裡行色匆忙的人群,更像是傳媒刻意製造的一個最大公約數。它不再高居最高哲學命題的神壇,而時常屈身茶餘飯後的娛樂八卦,供人消遣——這倒應了《死亡美學》序言最末引用的濟慈的一句詩:“死亡是人自己創造的。”在我看來,這樣一個不怎么起眼的句子,豐富地涵蓋了《死亡美學》所構建的美學理論體系和創作意圖。儘管它探討“死亡”的邏輯範圍只限於藝術文本中死亡現象的表現形態,但通讀全書,卻或許可以找到現實世界那群早逝的詩人和那個時代被人懷念的原因。
無論肇始於古希臘的西方文化還是依託於儒釋道的中古思想,人類擁有與生俱來的死亡意識。按照歷史和邏輯不同層面的劃分,死亡的本體論、價值論和審美論展現出多元的複雜樣貌,可這不妨礙長久以來各類藝術形態對死亡主題毫不吝嗇的偏愛。生與死的對話,承載著跨越地域時空的生命體悟,愛與歡笑。赫伯特•紐曼什在他的《懷疑論美學》中說:“一切藝術基本上也是對‘死亡’這一現實的否定。事實證明,最偉大的藝術恰恰是那些對‘死’之現實說出一個否定性的‘不’字的藝術。”對死亡的否定和反抗,寄託了人類創造永恆存在的生命本能。第二章統領全書要旨的三個命題展現了作者的思考脈絡:第一,從藝術的審美創造過程體驗到生命的不朽,人唯有在時刻意識到死亡的情境中,才能迫使自己進行有意義的創造活動;第二,以藝術文本的物化形式象徵生命的不朽,巨大堅固的物質媒介契合人類的不朽的願望;第三,用想像力虛設生命永恆的藝術空間來滿足不朽的欲望,在這一理想化的虛設境域中,生命排斥了死亡,相對性地征服死亡。作者認為,在向死而生的過程中,藝術既作為一個主體生命的延續,也使死亡成為生命存在的另一種方式。
閱讀中,一個小細節引起了我的興趣。對於創造死亡意象的藝術家來說,死亡是“懷著鄉愁的衝動返回精神的家園”,心理本能中存在著對它的強大迷戀。那么,在自然法則之外,死對於它的創造者,是生命的超越還是退而求其次的審美成全?作者在書中提到前者。但這個問題顯然脫離不開藝術家身處的時代。常態的生活環境中,沒有專制、暴力和精神壓迫,對死亡的選擇確實可被理解成為對於領悟生命終極意義和最高幸福的追求。比如正逐步走出人性遭受極度壓抑的八十年代。但如果現實情境相反,那些通常理解中屬於“厭世者”的選擇,恐怕未必是超越那么簡單。
憑心而論,讀這本《死亡美學》大可不必正襟危坐。建立在大量藝術現象上的美學闡釋非但不是僵化的邏輯理論操作,反而明白曉暢,靈氣飛揚。加之作者詩性理性交融的悟性思考,讀來頗讓人沉迷。
作為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人終有一死。作為自己生命的勾畫者,人人都是藝術家。作為藝術家——儘管現實生活中選擇終結自己生命的藝術家也只是極少數——請暫時拋開年薪、房貸和股票,以死亡的名義,不妨問問自己,向著那個終究會到來的終點,我們正在創造怎樣的死亡?
參考連結
三味書屋http://www.wenxueboke.cn/book/book.asp?id=bkbk8552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