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收穫》
《收穫》《收穫》在1957年7月24日由巴金和靳以創刊,是新中國第一本大型文學雙月刊雜誌,屬於中國作協主管。創刊之後,靳以負責具體事務,巴金側重組稿。1960年5月,我國處於三年困難時期,《收穫》被迫停刊。1964年,《收穫》復刊,由上海作協主管,仍為雙月刊,由巴金擔任主編。1966年5月,《收穫》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停刊。1979年1月,文化大革命結束,《收穫》再次復刊。
《收穫》“發刊詞”提及刊載的作品,應符合六個“有利於”的政治標準及呼籲作家“不僅應該是有靈魂的人,而且應該成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以作品來建立和提高人民的靈魂”,提倡作家可以選擇不同的風格,不同的體裁,不同的形式,甚至不同的流派。今天讀來,仍頗有現實意義。
《收穫》創刊號上的作品擲地有聲。被譽為“民族魂”、現代文學旗幟的魯迅,於1924年7月在西安講學時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記錄稿,作為創刊號的開篇,頗有深意。“長篇小說”有作家艾蕪的《百鍊成鋼》、康濯的《水滴石穿》;“劇本”有劇作家老舍的《茶館》;“童話”有著名兒童文學家嚴文井的《唐小西在“下一次開船港”》;“詩”有著名詩人冰心的《我的秘密》、作家嚴辰的《蘇聯行》;“短篇小說”有作家沙汀的《開會》、劉白羽的《我們的早晨》;“電影文學劇本”有作家柯靈的《不夜城》,以及巴金的《和讀者談談“家”》等大家力作,奪人眼球。
《收穫》是新中國第一本大型純文學雜誌,其視點敏銳,注重觀念的更新,有一定理性思辨色彩、深邃的人文精神,能夠傳遞豐富的文化感悟,深為人們喜愛。當代文學史上有影響的作家,幾乎均與《收穫》有過親密合作,如馮驥才的《啊!》《神鞭》、王蒙的《活動變形人》、柳青的《創業史》、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諶容的《人到中年》、陸文夫的《美食家》、葉辛的《磋砣歲月》、蘇童的《妻妾成群》、路遙的《人生》、王朔的《動物兇猛》、莫言的《師傅越來越幽默》、周梅森的《國家公訴》、余華的《活著》等都在《收穫》雜誌上與讀者見面。
《收穫》是幾代人的文學圖騰,《收穫》是一根標桿,《收穫》是中國當代文學的簡裝本。
大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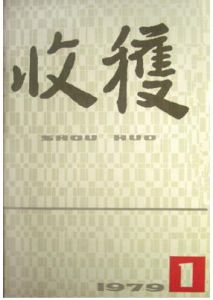 《收穫》
《收穫》1957,“老作家的新收穫”
《收穫》的創辦是由時任中國作協負責人的劉白羽提議的。劉白羽曾回憶,“三十年代的《文學季刊》就卓然不群……我們為什麼不恢復這樣的刊物,由巴金、靳以來編……我說服了中宣部的領導,但是領導同志說:不一定都在北京,上海從前就是文化中心,可以在那裡出,更何況巴金、靳以都在上海。”鍾紅明還補充說,當時許多老作家都創作了大量作品,發表的刊物卻很有限,所以急需這樣一個大型的載體;《收穫》刊名的原意,即為“老作家的新收穫”。
於是,《收穫》成為一個獨特的文學刊物:中國作協主辦,編輯部卻設在上海,有上海和北京兩個編委會。肖元敏和鍾紅明介紹,1957年7月24日出版的創刊號由錢君匋先生設計,封面採用厚重的紫紅色,字型則不是美術字型,創刊號厚達328頁。
創刊號《發刊詞》的第一句話是:《收穫》的誕生,具體實現了“百花齊放”的政策。而第一期的帶頭文章,是未發表過的魯迅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艾蕪的長篇《百鍊成鋼》和康濯的《水滴石穿》、老舍的三幕話劇《茶館》、柯靈的電影劇本《不夜城》。
此後,這個時期的《收穫》刊發了如《大波》、《上海的早晨》、《野火春風斗古城》、《平原槍聲》、《創業史》、《山鄉巨變》等長篇小說和《林則徐》、《蔡文姬》等劇本。
1959年11月,主編靳以先生因病去世。1960年5月,《收穫》停刊,理由是“三年自然災害”。不過,鍾紅明說,自然災害是一個原因,當時還是《收穫》讀者的現任主編李小林回憶,她看到紙張都慢慢變黃了,因為紙的質量越來越差。但當時政治上也是很敏感的時期,後來人們評價說當時的《收穫》是“統一戰線的體現”,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了停刊的原因。
1964,“大毒草”
1964年1月,在大家的呼籲和努力下,《收穫》復刊,但換成了由上海作協主管。這個時期發表了《艷陽天》、《歐陽海之歌》、《大學春秋》等作品。
這段簡短的歷史卻更加驚心動魄。在1962年5月上海第二次文代會上,巴金髮言說自己這些年來“講得多,寫得少,而且寫得很差”,並且做了《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的談話。當時主管上海市宣傳的張春橋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對巴金不槍斃就是政策,槍斃與不槍斃就在一線之間。”但巴金和靳以開啟了《收穫》的追求:創建一股百花自由競放的陣地,多出作品多出人才。即使在壓力重重下,在“文革”中,戰戰兢兢,依然初衷不改。
“《收穫》雖然只是一本文學期刊,但她的發展歷史也是時代的晴雨表。”肖元敏說,看當時雜誌的目錄,很多都是直接轉載的政論性文章,“雜誌都排好了,上面就下一道命令,讓你發社論。看目錄就可以知道當時辦雜誌的壓力和發作品的無奈。沒有辦法。”
隨著周而復在《收穫》上發表的《上海的早晨》被四人幫批為“大毒草”,一批在這一時期登上《收穫》的作者被打倒,《收穫》也沒有逃離歷史的厄運。1966年“文革”開始,5月,《收穫》被迫停刊,編輯部成員都被下放。
1979,“新生”
第三個《收穫》從1979年1月開始。但其復刊號的總期數為15期,和“文革”前的14期是首尾相連,而1957年《收穫》的那18期《收穫》,則不被納入它的總期數內。
有人據此發出疑問:它們難道不是一家嗎?難道《收穫》的歷史並沒有50年?鍾紅明說她也很納悶當時為什麼把期數寫成了“15”,可能是失誤,但三個《收穫》為一家是毋庸致疑的。因為1960年第一次復刊時,主編沒變,編輯部成員也沒變,只是主管單位變成了上海作協。
但1979年再次復刊時,主編還是巴金,編輯部成員卻全換了。肖元敏回憶,當時是蕭岱、吳強(《紅日》作者)、李小林等人。蕭岱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著名詩人,當時已經70多歲了。
但《收穫》很年輕。”在《收穫》50年紀念特刊的目錄上方,巴金的親筆字跡很醒目:“《收穫》是向青年作家開放的,已經發表過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還要發表青年作家的處女作。”
這是《收穫》的“新生”,從此,一部當代文學史就和《收穫》緊密聯繫在一起。1979年時,現任《收穫》副主編的程永新在上海附近一個農場工作,在農場看到了《收穫》復刊後的幾期。“那幾期上面,有馮驥才的《啊!》、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那時候的作品非常有影響力,也不知道是誰買的,反正大家都在傳看,我看到的時候,連雜誌封面都沒有了。”而在肖元敏的記憶中,馮驥才、史鐵生、從維熙、張抗抗等“新時期文學”的代表人物,都在《收穫》上集體亮相。1980年評選的“首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中,有6篇作品發自《收穫》,占總獲獎篇目的1/3以上。
1988,傳奇
上世紀80年代末的那場先鋒文學浪潮,更是《收穫》歷程中不得不說的故事。鍾紅明說,幾天后即將出版的2007年第5期《收穫》上,就是“向80年代致敬”的紀念專刊,因為那個時代最有才華的作家,寫出了他們成名並流傳至今的作品。那個時代的文學盛況和作家質量,是《收穫》也是中國文學的傳奇。
鍾紅明介紹說,上世紀80年代中葉開始,小說的敘事和語言中都崛起了新的美學原則,以前所未有的姿態進行了敘事革命、語言實驗和生存狀態3個層面的探索,對文壇形成強烈的衝擊。這批作家的共同特點是寂寂無名屢屢碰壁卻才華橫溢。肖元敏說,當時還有別的刊物問自己:余華的作品能發嗎?他吃不準。她的回答是:“反正我們已經定了要發了。”而格非剛剛大學畢業,他拿著自己的小說衝進了編輯部,程永新接待了他,他從此成名。
一連串的名字首先出現在這一時期的《收穫》雜誌上,1988年、1989年《收穫》的兩次青年文學專號隆重推介先鋒作家群,馬原、余華、蘇童、格非等非凡的想像力和精妙的敘述語言,打開了中國文學另一扇寬廣的大門。
這一時期的《收穫》成為新人亮相併為文壇矚目的最重要的舞台,許多作家的處女作和成名作刊發在《收穫》上。蘇童說:就像梨園藝人忘不了初次粉墨登場的舞台,他至今難忘屢次投稿碰壁後,《收穫》給他的知遇之恩,或許是提前了一兩年,或許是在關鍵的時刻把他推上了文學舞台。余華說:“我和《收穫》有著唇齒相依的關係,我有三分之二的作品都是首先在《收穫》上發表的。如果我新創作了什麼作品,第一個想發表的地方就是《收穫》。”
此後,《收穫》刊發了大量在當代文學史上引起重大反響的作品,《浮躁》、《活著》、《九月寓言》、《丹青引》、《許三觀賣血記》……王安憶超過20次登上《收穫》,代表了她各個時期的變化。
2007,漲價?
人們能記得1988年“先鋒文學”的耀眼,卻可能忽略了《收穫》經營的暗淡。這一年,《收穫》是借債度日。自1986年第1期開始,《收穫》率先作出面向市場的抉擇,自負盈虧,沒有撥款。而巴金一直不願意讓文學沾染商業的因素,所以《收穫》也不刊廣告。兩年後,紙張價格猛漲,還沒摸著市場脾氣的《收穫》虧損嚴重,連發工資都成問題,於是分別向上海市作協和上海市文化基金會借錢,一共借了20多萬元,才勉強渡過難關。
現在,《收穫》的發行量穩定在12.3萬份左右,依然是文學期刊的佼佼者,是中國作家們的必讀雜誌。它還獲得上海市著名商標,是純文學期刊中獲此稱號的唯一一家。只是,昔日韶華不再,閱讀《收穫》逐步成為了一種特定人群的特定品味。
一般而言,一本文學期刊發行5萬份左右就能自負盈虧,《收穫》的日子並不算難過。但肖元敏和鍾紅明還是感到壓力重重:“今年國家大量關閉小紙廠,紙張又要漲價,我們該不該漲價呢?從讀者角度考慮,能靜下心來看文學作品的一般不會很富裕,什麼都漲了,我們再漲,流失這12萬多讀者,就很難再回來了;從我們的角度,不漲價壓力實在太大了。我們很猶豫。一個品牌倒下來,再起來就比登天還難。”
封面設計
 《收穫》
《收穫》抗戰時期,身在重慶的靳以主持《國民公報》的文藝副刊《文群》。《文群》被迫停刊以後,靳以曾經想以“文群”為名創辦一份大型刊物,終於未能如願。在靳以的書桌抽屜里,一直保留著當年請錢君匋篆刻的“文群”印章。
靳以創辦《收穫》的時候,再次請來錢君匋設計刊物的封面。錢君匋最初的設計稿採用宋體字作為素材,占去了雜誌封面的絕大部分空間,封面的底色,從雜誌頂端以極濃的暗紅色開始,越往下越淡,淡到最後不能再淡告終。巴金和靳以對這個設計都拍手叫好。但是由於印刷條件的限制,錢君匋的這一創意並沒有在刊物上得到體現,《收穫》創刊號的封面一色到底,沒有任何變化。這個設計一直用到“文革”停刊為止。
1979年,《收穫》第二次復刊以後不久,《收穫》再次請錢君匋設計封面,錢君匋以“198”的年代字樣反覆排列,作為設計的底紋,鋪滿整個封面,以集魯迅所寫的“收穫”用黑色壓在“198”的底紋上,這個設計用了一年。
魯迅所寫的“收穫”刊名後來更換過一次。有人提出《收穫》封面上魯迅的字型與原件不符。由於《收穫》的刊名是用手工描畫的,越到後來,字型走樣走得越厲害。後來替換了標準的魯迅體,用到現在。
復刊後的《收穫》內文開始配有知名畫家畫的插圖,賀友直為陳白塵的話劇劇本《大風歌》作了插圖,吳祖光的五幕話劇《闖江湖》的插圖作者則是丁聰。《收穫》的版式設計別具匠心,每篇作品附加的飾圖也力求精緻新穎。在小說的開頭和結尾,請篆刻家刻篇名印章,作為裝飾,代替“頭花”和“尾花”。1994年第4期發表了萬方中篇小說《殺人》,沒有用傳統的宋體字製作標題,而是請書法家張森寫了隸書,“殺人”兩個大字占了整整兩頁。
其主編
 《收穫》創始人巴金、靳以在創刊的日子裡。靳以、巴金的合作開始於1930年代創辦《文學季刊》
《收穫》創始人巴金、靳以在創刊的日子裡。靳以、巴金的合作開始於1930年代創辦《文學季刊》兩個主編
1956年,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劉白羽在中宣部的一次會議上建議出版一個大型的刊物,以改變當時文學刊物多以地名命名的單調局面。劉白羽參照的樣本是1930年代鄭振鐸、靳以辦的《文學季刊》。隨後舉行的中國作協會議,正式決定創辦這本新的刊物,主編由巴金和靳以擔任。
1957年7月24日,《收穫》創刊,這是一本70萬字、320頁的文學雙月刊,定價1元4角。冰心曾經建議刊名為《創作》,靳以最終還是定名《收穫》,意在表明社會主義文藝到了一個收穫的季節。靳以認為,長篇小說、話劇、電影劇本在正式出版和上演之前,發表在刊物上,可以得到讀者來自不同方面的意見,有助於作者進一步修改。
《收穫》創刊時是中國作協的刊物。由於靳以不願去北京,編輯部就設在上海,編好了刊物以後再送到北京出版發行。由於很多著名作家居住在北京,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成了《收穫》駐京辦事處。
《收穫》創刊號上有靳以執筆、巴金共同署名的發刊詞:“《收穫》的誕生,具體實現了‘百花齊放’的政策,《收穫》是一朵花,希望它成為一朵香花……有利於社會主義祖國,是人民的有益的精神食糧。”發刊詞用了相當多的篇幅寫到了毛澤東提出的六大標準:“我們的刊物和所刊載的作品,應該符合毛主席所提出來的六大標準:一、有利於團結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在這個明確的政治標準之下,作家可以選擇不同的風格、不同的體裁、不同的形式,甚至不同的流派。
“作家不僅應該是有靈魂的人,而且應該成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以作品來建立和提高人民的靈魂。”原本第一期沒有發刊詞,雜誌編完之後,紙型從上海寄到北京,正在北京開會的巴金突然收到靳以寄來的發刊詞,巴金在文章中回憶道:“我一看便知道是為了‘六大標準’。‘六大標準’的發表無疑是一件好事。可是我卻感到一點緊張,我似乎看到了一頂懸在空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今天翻看三十年前的表態文章,我還仿佛接觸到兩顆戰慄的心和兩隻顫抖的手。我們就是這樣熬過來的。”
“反右”中,指責《收穫》最多的罪名是“同人刊物”、“獨立王國”,靳以和巴金都不是黨員,是不要黨的領導。第2期《收穫》發表了巴金、靳以聯合署名、靳以執筆的《寫在“收穫”的時候》:“在反動派殘酷的統治下,我們所編輯的‘文學季刊’、‘文季月刊’和‘文叢’都先後被扼殺了。那時,我們不僅失去了編輯的自由,和許多作家一樣,甚至失去了寫作的自由;可是在今天,黨信任我們,給我們勇氣和力量,中國作家協會給我們任務,編一個大型的文學刊物,和其他的兄弟刊物興起社會主義競賽,這就足以證明一個文學工作者和編輯人作者,在解放前後的天地懸殊的遭遇了。”文章還對施蟄存和王若望的批評給予了回應,將《收穫》與“同仁雜誌”的指責劃清界限。
《收穫》創刊後不到半年,靳以就和大部分作家一樣,被要求上山下鄉到工廠農村深入生活。身患心臟病的靳以不得已選擇了國棉一廠,每天上午在國棉一廠清花車間體驗生活,下午趕回編輯部看稿寫作。
政治風雲的變幻,讓靳以倍感壓力。《收穫》創刊時原來有13個編委,後來艾青被打成右派,很快就被調整出了編委會。靳以排定了1958年第3期稿子,正準備簽字付型時,突然收到一位作者所在組織的來信,信中說這位作者有“問題”,不同意發表他的作品。靳以只得趕緊換稿。1958年第3期發表的方紀小說《來訪者》遭到了嚴厲批判,編輯部被要求表態,在第4期雜誌上,靳以增闢了“讀者論壇”,刊登了兩篇批判《來訪者》的讀者來稿,又由羅蓀寫了評論文章,才躲過一劫。
靳以於1959年11月因心臟病發作去世,年僅50歲。在去世之前數月,靳以終於如願入黨。由於靳以很早去世,在《收穫》創刊40年時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收穫》選萃1957-1997”中,附錄里的“歷屆負責人名單”獨獨遺漏了靳以,主編巴金的名字旁成了一片空白。原來是出版社一位年輕編輯在校對時,不知靳以是何許人,未和《收穫》聯繫,就自作主張,刪去了靳以的名字。
相關評論
 50歲《收穫》再現名家手跡
50歲《收穫》再現名家手跡多少年來,在《收穫》的背後始終有著一個高大的身影,那就是巴金先生。談到與這份雜誌的關係,他不斷重複的話是:我只是《收穫》的掛名主編,當初答應做主編也不過替老朋友靳以助陣而已。在這樣的輕描淡寫中顯示出的是一位傑出作家的為人本色,也讓我們看到了他對待朋友的純淨之心。哪怕老朋友靳以已經去世多年,但談到《收穫》,巴金必然首先想到他。在今年第四期《收穫》上,有一個小細節很讓人感動。那是《收穫》創刊30周年(1987年)時冰心的一段題詞,她談到對《收穫》的喜愛,其中有一句話原文是這樣寫的:“因為《收穫》是我的好友巴金創辦的,我一看到《收穫》就想起巴金一家。”現在刊出的手跡中,兩處“巴金”前面分別加上“靳以”的名字,而最後“一家”兩個字也劃掉了。這三處改動分明不是冰心的筆跡,仔細辨認原來這是巴老的改動!
雖然巴老不曾參與到雜誌的具體編輯工作中,但這位從未領過工資的“掛名”主編,卻對《收穫》一直非常關心,哪怕在多病的晚年,自己閱讀困難的情況下他還是不斷聽身邊的人讀《收穫》,余秋雨、李輝等人的專欄,還有一些小說,他都認真地讀完了。對於《收穫》的編輯而言,巴金是這份雜誌的靈魂,是將五四新文學精神帶到這份雜誌中一面旗幟。這樣的影響是虛的,也是實實在在的。巴金也會如同當年拍板鼓勵靳以消除顧慮推出曹禺的《雷雨》一樣,在一些重要時刻和關鍵作品上給予編輯部以明確的支持。著名作家從維熙就曾滿懷深情地回憶起上世紀八十年代,他的中篇小說《遠去的白帆》在被其他雜誌拒絕的時候,是巴老親自拍板讓《收穫》發表了它。他也談到《大牆下的紅玉蘭》在《收穫》上發表後遭到一些思想保守的人的批評,而此時巴老鼓勵編輯部要“百無禁忌更進一步”,“因而使當年的《收穫》,成了歷史新時期解放思想的一面文學旗幟。”他還舉了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的例子,“也是在《收穫》死而後生的,這又是巴老在文學新時期勇往直前、義無反顧的一個佐證。”
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例如賈平凹的長篇小說《浮躁》在《收穫》發表後,上海當時一位主要領導在一次幹部萬人大會上,點名批評了這部作品,編輯部的同志感到壓力很大,巴老得知此事後,立即閱讀全文,他說:我覺得這部作品沒有什麼問題。時間也證明了這一點,《浮躁》還在國外獲了大獎,也被文學界公認為是反映城鄉時代變遷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巴老簡短的一句鼓勵,給編輯部的是做好工作的更大的信心和動力,《收穫》副主編蕭元敏就曾說過:“巴老在時,他是我們的主心骨;有了他的護佑,我們的勇氣會更大一些。現在他不在了,他的精神始終在激勵著我們,如何選擇,如何取捨有時卻會變得難以想像的艱難,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偏離前輩們創建的這個圓心和跑道。”
巴老不是一個喜歡張揚的人,他對作家和雜誌的支持常常是那種春風化雨、潤物無聲。老作家陳荒煤寫了散文《夢之歌》,以此抒發內心積鬱的情感,原來並不打算立即發表。但巴老了解陳荒煤的心境:新時期以來,荒煤一直支持和鼓勵青年作家的寫作和探索,然而,他的做法一度不被人理解甚至遭人非議。巴老沒有多說什麼安慰他的話,只是指示《收穫》立即發表荒煤的這篇散文。得知這一情況,荒煤很激動,1984年3月1日給巴金的信上說:“我的散文《夢之歌》,原未打算就發表。沒想到,卻得到您的鼓勵,認可。既然您批准了,就稍作修改寄小林發表吧。”“我很高興,到今天為止,您還鼓勵我寫點東西!”同日給李小林的信上他又寫道:“文化部整黨仍在進行中,大部時間都去開會。我今年也七十一了,總想擠點時間寫點東西;但實在是疲勞不堪。”“此篇原不準發,既然你爸爸覺得還可以,就發吧。我覺得大概不致被認為有污染吧。”荒煤的感動不是毫無緣由的,他也一定會想起50年前,作為一個無名的投稿者巴金將他的作品看後又交給靳以決定在《文學季刊》第三期發表,從此將他領入文壇的往事。想不到,年逾古稀,巴金還在背後默默地支持著他!
有了陳荒煤、從維熙、賈平凹這樣的經歷,我們才能夠體會到青年作家李洱這段話的分量:“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的中國文學甚至中國文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如果沒有巴金,其情形都很難想像。這不僅是指巴金給後來的中國文學提供了道德基石,也是指巴金以自己的偉大存在給中國文學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發展空間。經歷了這個時期的文學史家當然會注意到這一點,但未來的文學史家卻未必會留意。”《收穫》因為“主編巴金”讓人感受了一種歷史的滄桑和文學的尊嚴,在人們的心中也有了不一樣的位置。
《收穫》的這期50周年的紀念號,目錄的上方醒目位置刊發的是巴金先生的一段題詞:“《收穫》是向青年作家開放的,已經發表過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還要發表青年作家的處女作。”這段第一次公開發表的手跡,是1979年巴老回答外國記者提問時寫下的,當時《收穫》剛剛復刊不久。無論在當時,還是多年後公開這段話,都表明了《收穫》雜誌的一貫的開放態度,那就是“不惟名家,不薄新人”。最新一期的《收穫》就是最好的例子。這一期推出的主要是一組青年作家的作品,長篇小說是何世華的《陳大毛偷了一枝筆》,中短篇的作者是於曉威、丁伯剛、喬葉、須一瓜、葉彌、田耳、戴來、徐則臣等人,都不是什麼文壇宿將,但卻是有創作實力的青年作家。瀏覽《收穫》50年的目錄,你能夠看到很多在文學界閃光的名字,但你也會發現,其中很多人在《收穫》上發表作品的時候並非已經在文壇上紅得發紫,包括大家已經非常熟悉了的余華、蘇童這樣一批當年的先鋒作家。但這話或許可以這樣說,是《收穫》給許多優秀作家提供了展示才華的機會,通過《收穫》這個舞台,他們才閃光起來了。
支持青年作家的創作,並非是沒有原則的捧場,而是為他們提供舞台、創造機會,是讓他們不斷完美而不是曇花一現,為此,《收穫》的編輯們與作者反覆溝通、不斷修改稿件,這成了文學界出了名的“編輯特色”。作家格非曾在14年前撰文談到過這些:“……但是當作品寄往編輯部之前,稿件中仍會有些不盡人意的地方,這個時候,我們的心情通常比較矛盾。完成一件工作後的喜悅與輕鬆常使明知存有缺陷,仍然硬著頭皮送往編輯部。但是,我的僥倖心理很快就會破滅。”《收穫》的編輯不會將這些缺陷輕易放過的。“我的小說,比如《迷舟》,《邊緣》,《湮滅》等作品都經歷了這樣一個修改過程。如果說我從改稿中所學到的東西往往超過創作所得,這也並非是一種誇張之語。”格非還說,就他所知,余華、洪峰、孫甘露等作家都經歷過與他相似的改稿經歷,在交談中,他們曾多次談到編輯們對刊物以及作品一絲不苟的精神給他們留下的深刻印象。都說“文章是自己的好”,都說作家們最忌諱別人動他的稿子,但也不盡然,關鍵是作者與編輯之間要建立起一種互信,一種坦誠的溝通,還有一點更重要,那就是編輯們的奉獻精神、敬業精神也會打動作家們,同時為雜誌贏得尊嚴。在這樣一種平等、互信、開放和坦誠的氣氛中,《收穫》以海納百川的胸懷迎接著每一位作者,也和每一位作者一起成長。
所引發的思考
 《收穫》
《收穫》由《收穫》風波引發的兩點思考
一,對歷史人物的重塑問題
前面談到,對魯迅的顛覆有學理式和非學理武(即流氓式)兩種,但比顛覆更值得警惕的是對魯迅的重塑,即根據當前的祉會變遷或個人的政治理念對魯迅進行重新描述,以致改變了魯迅的歷史原貌。
歷史有沒有原貌?有人說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西方有些學者就不再相信歷史的客觀存在和客觀意義。他們認為人不能完巨準確地認識歷史,或者說,人對歷史的認識永遠不能同歷史本體達到絕對的同一;因為對任何歷史的再現都無法擺脫後人價值觀念的支配,以往的歷史知識當中都滲透了史家的各種主觀性和見解性的因素。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歷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是通過小說、戲劇中編織情節的技巧才變成了歷史。所以。歷史因交家的立場不同而具有相對性,絕對永恆的歷史本體並不存在。比如同一法國大革命,有人將其描繪成浪漫主義的戲劇,也有人將其描繪成令人啼笑營非的悲劇。
歷史總是由歷史本體和認識歷史的客體兩方面構成。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有兩種歷史:一種是曾經實實在在發生過並作為獨立存在的歷史,另一種是保留在記憶之中井經過後人思考和理解的歷史。所謂魯迅研究,就是作為認識主體的研究者跟作為客體的魯迅之間進行的精神對話———這種主體與客體之間相互作用的連續不斷的過程,也就是’現在”和“過去”之間的永無止境的交流過程。
因為魯迅研究者總是在現的現刻進行他的思考和判斷,他的學術活動不能不受到現時興趣的推動和生存環紀的制約,因而使魯迅研究無法避免其當代性。但從另一方面看,魯迅又是一個在中國近現代確鑿存在的而不是向由虛構的人物,儘管對他的認識可以不斷深化,而他的生平史實卻具有無法改變的客觀性。對於越優秀的魯迅研究者,翔實可靠、逼近歷史的史料就具有越重大的意義。所以,我認為不應該改變作為歷史人物的魯迅的“本相”,使魯迅成為當代標準的載體,使魯迅研究成為研究主體的想像活動。魯迅在他的學術生涯中,一貫直視史料的確鑿性,反對以論代史、以主觀意識改變客觀存在。比如,魯迅並不同意日本評論家鶴見佑輔的某些見解,但仍客觀地將其作品譯介到中國。他說:“因為我的意思,是以為改變本相,不但動不起作者,也對不起讀者的。”(((思想·山水·人物》題記》)不改變事物的“本相”,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目前改變魯迅“本相”的“重塑”現象有多方面的表現,把魯迅描繪成中國最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即為一例。事實上,一被意義上的“自由”眼有著特定政治內涵的“自由主義”不能混同。自由主義(liberaliam)觀念有從古典向現代演化的歷史過程,因此要對它作出簡易的理論界定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不過,自由主義畢竟有其基本原則和鮮明標幟。作為一種以個體主義為根本特徵的社會價值觀、自由主義的總綱領是維護生產資料私有制。在自由主義營壘之中,有人主張對私有制進行放任,也有人主張對私有制進行干預,雙方無論分歧多大,都強調財產許可權生命權、目由權共同構成了人權的基石。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引進自由主義理論體系的同時,還積極主張在政治上移植西方多黨制,以此作為個人造本自由的保障。他們反對暴力革命,謀求改良漸進,因而只能在部分知識分子中擁有市場,始終未能成為激勵勞苦大眾為爭取自身解放和社會進步的思想旗幟。魯迅雖然崇尚個性,主張獨立思考,獨立判斷,但他並不認同“以眾虐獨”的西方民主制,尤其反感自由主義者口頭上鼓吹寬容而在實際上並不寬容的行為方式。他甚至明確表示,歌德“自由與平等不能並求,也不能並得“意見要比自由主義理論更有見地(參閱魯迅:《(思想·山水·人物)題記》)。因此,要把自由主義大師的紙冠截在魯迅頭上,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地親自撕毀。
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選擇的趨利避害問題
由於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交通快捷,遠程交流實現,人類村會逐步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過渡,廣定無垠的世界緊縮成為“地球村”。特別是近二十年來,以已開發國家為主導,以跨國公司為主要動力,世界範圍的產業調整加快了速度,越來越多的國家進入同一世界幣場,產品生產階段的可分性與經濟發展的相互依存住日趨加強。在這樣一種國際背景之下,文化與經濟的關係愈趨密切,從而由經濟霸權衍生出一種文化霸權。西方文化通過網際網路、多媒體和遍及全球的傳播媒介滲透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均衡的文化雙向交流還只是一種理想化的境界而遠未成為事實。美國總統柯林頓宣稱,21世紀全球化即21世紀美國化。美國式的生活方式業已成為世界時尚的參照系。價值觀念輸出,成為了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出西方強勢文化的一種霸權心理。他們深深懂得,在錯綜複雜的國際鬥爭中,誰家的文化成為主流文化,誰就將導終成為贏家。
總之,我們的學術研究應該與時俱進,與世僅進,但也應該像魯迅在《拿來主義》一文中強調的那樣,拿來時要“有辨別”,不能“口無遮攔”把人家”拋來”的東西,不分有益、無益、有害統統一口咽下。二十世紀末魯迅研究領域的這一場風波目前是平息了。《收穫》雜誌又刊出了《我愛魯迅》一類文章,更給人以風平浪靜的觀感,然而從社會發展和文化發展的規律來看,這只不過是暫時的現象。文壇只要有了魯迅就永遠不會沉寂。這種風波即使“外狀若寧,暗流仍伏,時劫一會,動作始矣。”(魯迅:《摩羅詩力說》)這是魯迅的宿命,也是魯迅研究者的宿命。好在魯迅不會逃避更不會害怕一代又一代讀者的重新審視,重新評估。《抱朴子》一書中有句名言:“滄海(氵晃)漾,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我想,這也同樣適用於魯迅文化遺產的汪洋大海。
評價
 《收穫》
《收穫》《收穫》是一份承續著五四新文學血脈的雜誌,五四新文學精神是它的歷史傳統,也是它以一貫之的品格和與其他文學雜誌最為不同的精神氣質。不論當今學界對所謂的“新文學”、“純文學”的概念怎么反思,我認為這種不是將文學作為消遣,而是看重它的精神性,不媚時、不媚俗、拒絕商業化的文學精神仍然是最有意義的一種文學追求。
對於新文學精神的承續和發揚,是《收穫》在醞釀創刊時有意識的追求。提議創辦《收穫》的人都是對鄭振鐸、靳以、巴金等人創辦的大型期刊《文學季刊》,以及後來巴金、靳以聯手編輯的《文季月刊》、《文叢》等系列期刊充滿感情的人,時為中國作協負責人的劉白羽在回憶錄中就明確地說想恢復《文學季刊》這樣“卓然不群”的刊物,為此,他去說服了中宣部領導同意創辦這樣一份雜誌,並明確建議編輯部設在上海,由巴金、靳以主編。從刊物的篇幅、選稿的氣度、編輯風格而言,《收穫》與《文學季刊》等三十年代“文”字系列期刊的確一脈相承。《文學季刊》創刊的1934年,號稱中國的“雜誌年”,當年定期出版的雜誌約三百多種,百分之八十是文藝或半文藝性質的“軟性讀物”,用茅盾的話說,它們幾乎全是幽默與小品的“合股公司”。《文學季刊》卻不取媚市場、以純正的嚴肅的創作為主打,以切實從事文化建設的決心,贏得讀者的尊重和文學雜誌的尊嚴。
半個多世紀後,《收穫》也面臨著同樣內外交困的境況:1987年,全球性的紙價上漲,本來就微利甚至無利經營的文學刊物迅疾陷入了經濟困境;九十年代以後中國文學的市場化傾向越來越嚴重,文人下海,休閒文學、影視對純文學的衝擊,這使得許多文學刊物被迫改刊,但在困難中《收穫》沒有輕言“變革”,而是選擇了堅守。主編巴金非常堅定地表示:不希望《收穫》做商業化的改變。他鼓勵編輯部:《收穫》是大有希望的,文學是大有希望的。危難時刻方顯英雄本色,憑著這樣的信念,《收穫》一如既往地堅持自己的精神追求。我常常想《收穫》真正輝煌可能不僅是發表了莫言、余華、蘇童等人的那些名篇,更重要的是在這樣時刻對於新文學精神堅持的象徵意義,從這個角度講,有了這種歷練之後,《收穫》已經不單是《收穫》,而成為一個符號,它承載著作家、讀者對於文學精神性追求的信心。在這一點上,《收穫》一下子就在讀者的心中擁有了不同的位置。記得好久,我都珍藏著《收穫》的一份征訂單,上面有這樣一句話:在世間所有虛妄的追求都過去以後,文學依舊是一片靈魂的淨土。
《收穫》這樣的努力,為文學贏得了尊嚴,也給了作家們以信心和勇氣,大家相濡以沫捍衛著一種文學精神。老作家蕭乾當時給主持工作的副主編李小林的信中談到:“收到你的來信,既佩服你們堅守陣地的勇氣,又為文藝前景感到憂慮。”“潔若和我近來採取用稿酬或版稅來捐獻。……目前浙江文藝出版社正在印我譯的《里柯克諷刺幽默選》,不久可出版,共十數萬字。我想把出書的稿酬(連同《堡》的——請千萬勿匯)一併捐給《收穫》。”“向(像)其他捐款一樣,我這點心意不外乎表示對《收穫》(它的前身是《文學季刊》《文季月刊》)的支持和擁護,並藉此推動一下。”(蕭乾1993年11月15日致李小林信,本信及下文中所引諸信均為首次公開的未刊稿。)這樣的支持不在於金錢,而是道義,是一份雜誌的價值觀為更多熱愛它的人所認同。作為文學邊緣化時代中的一份文學期刊,《收穫》最為難得的是能夠將作家和讀者的精氣神兒凝聚起來,讓大家為了共同的文學理想而奮鬥。
純文學期刊
| 《兒童文學》《少年文藝》《青年文學》《人民文學》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這些陶冶了無數人情操,滋養了無數人心靈的期刊,這些傳播人類精神文明,關注社會,歷史與人生,人性的期刊也是許多文學名家發表作品的陣地。 | |||
| 《散文》 《鐘山》 《山花》 《芙蓉》 《天池》 《天涯》 《寫作》 《當代》 《收穫》 《詩刊》 《星星》 《滇池》 《芒種》 《芳草》 《飛天》 | 《雨花》 《躬耕》 《黃河》 《遼河》 《鴨綠江》 《小溪流》 《含笑花》 《青海湖》 《啄木鳥》 《詩選刊》 《北極光》 《六盤山》 《短小說》 《滿族文學》 《民族文學》 | 《散文百家》 《小說選刊》 《詩歌月刊》 《中華散文》 《散文選刊》 《兒童文學》 《少年文藝》 《青年文學》 《中國作家》 《四川文學》 《北京文學》 《天津文學》 《上海文學》 《長江文藝》 《廣西文學》 | 《當代小說》 《黃河文學》 《小說月報》 《北方文學》 《青年作家》 《西藏文學》 《安徽文學》 《山西文學》 《清明》[雜誌] 《金山》[文學期刊] 《微型小說選刊》 《小小說選刊》 《台港文學選刊》 《中篇小說選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