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蘭德公路》
《弗蘭德公路》作者簡介
 《弗蘭德公路》
《弗蘭德公路》克勞德·西蒙(Claude Simon),法國作家,1913年出生於法屬殖民地馬達加斯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西蒙被應徵入伍,參加過著名的梅茨戰役。1940年5月被德軍俘虜,同年10月逃出戰俘集中營,回國後繼續參加地下抵抗運動。二戰中的人生經歷,給西蒙以後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獨特的感受。
1985年10月,瑞典學院宣布將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法國新小說派作家克勞德·西蒙,以表彰他“在對人類生存狀況的描寫中,把詩人、畫家的豐富想像和對時間作用的深刻認識融為一體”。訊息傳來,不僅使法國文學界感到震驚,也使世界文學界深感意外。自20世紀50年代法國“新小說派”形成以來,評論界一向是把阿蘭·羅布-格里耶推崇為這一流派的首領,而資格遠比西蒙老的女小說家娜塔麗·薩洛特和作品遠比西蒙多的米歇爾·布托拉居第2、第3,西蒙一向是位居第4。西方的傳媒和評論界驚呼西蒙獲獎是“爆出冷門”,連一向以訊息靈通著稱的《紐約時報》也臨時到處打聽這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生平。法國有家大報甚至暗示,西蒙與蘇聯的克格勃有關係,瑞典學院的這一選擇是受克格勃操縱所致,結果弄得西蒙不得不在獲獎演說中對此進行駁斥。
西蒙的重要作品還有《歷史》 (1967)、 《雙目失明的奧利翁》 (1970)和 《農事詩》 (1981)等。
內容概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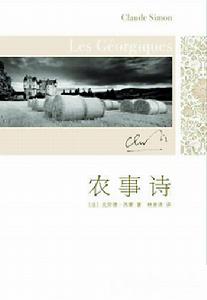 《弗蘭德公路》
《弗蘭德公路》小說是以1940年春法軍在法國北部接近比利時的弗蘭德地區被德軍擊潰後慌亂撤退為背景,主要描寫3個騎兵及其隊長痛苦的遭遇。小說以貴族出身的隊長德·雷謝克與新入伍的遠親佐治的會晤開始,以德·雷謝克謎一般的死亡結束。所有這一切,是由佐治戰後與德·雷謝克的年輕妻子科里娜夜宿時所引發的回憶、想像所組成。
隊長德·雷謝克手裡拿著一封信,抬眼看著我。自從他的騎兵隊減損到僅剩我們4個人起,隊長德·雷謝克可以說是擺脫、免除了軍官的職責,從中解放了出來。在一切的土崩瓦解中,現狀和精神的表現都在剝蝕分化,變為粉末、流水,最終歸於虛無。天色漆黑,時間的行進是看不見的。然而也就在這種神秘的時間的行進過程中,佐治感到自己坐在馬上,冰冷、僵直。後來他們在穀倉里安頓下來,面前出現一位少女,像一個聖靈的陰影。接著他們開始漫無邊際地談論女人。
在夢鄉中,腦子充滿幻想的佐治,看到了德·雷謝克的妻子科里娜。雷謝克拿著槍管——把槍管對著自己的太陽穴,使勁扣下扳機,接著響起了乾枯、沉悶的聲音。雷謝克就是這樣把臂肘支在壁爐架上開槍自殺的。
佐治感到那肉體溫熱的氣味,呼吸到嘴唇朦朧的黑色花形狀物的氣息……佐治醒過來過了好久,他才辨認出來,那是一雙瘦骨嶙峋的馬腳,這是一匹馬。佐治和布呂姆兩人在口袋裡收刮菸絲,收集一點僅剩的麵包屑。佐治由此回憶起隊長、科里娜和依格萊茲亞的三角關係及大家一起賽馬的情景。接下來,他們談論隊長的自殺,認為他是以自殺掩蓋失敗的真相,並由此聯想到隊長家族中一位將軍自殺的事件。
我們在黑暗中摸索,我什麼也回想不起來。那時我大概睡著了。在神情恍惚中,佐治再次想起自己和科里娜幽會、親熱的情形。我們已和任何正規部隊失去了聯繫,我們不知道該如何行動。我真以為是看見的,或許只是想像,或是做夢。也許我在大白天睡著了。四周空空洞洞。世界風化了,剝落了,逐漸成為碎片崩潰了,像一座無用的被廢棄的建築,是時間通過缺乏條理和漫不經心的作用把它毀滅的。
欣賞導航
 《弗蘭德公路》
《弗蘭德公路》《弗蘭德公路》通過主人公佐治戰後與戰時神秘死亡的騎兵隊長德·雷謝克的妻子在旅店夜間幽會時斷斷續續的回憶,用斑斕濃重的色彩、千變萬化的巴洛克文體、重複迴旋的筆法繪成的色塊,創造一種類似現代派繪畫的效果,以貼切地表現作者對人類境遇的感受及其瞬間的情緒噴發,展現3個騎兵及其隊長在戰爭中的遭遇。小說沒有傳統意義上的人物,也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情節,更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敘述結構。
在小說中,作者採取對稱和互見的手法,同時寫了隊長的一位先人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中悲劇的下場,還通過隊長與他的年輕妻子和他們所僱傭的騎師依格萊茲亞的三角關係,從側面寫了法國上層社會的窮奢極欲、空虛無聊,放縱荒唐的生活。同時,通過佐治意識活動,小說用巴洛克式迴旋曲折的結構描述了戰爭對大自然的破壞、人的異化、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畸形。既有詩情畫意,又有幽默嘲諷,使人含淚而笑,含笑而泣。作者利用冗長繁複的語句,把所有的敘述內容都包容在一起,從而在雜亂無章的文字逐漸展開的過程中,反映出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西歐人的普遍感受:世界失去了理性,個人受到時間和莫名其妙的歷史事件的支配,既無法改變歷史,也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
小說中的回憶、想像、印象、幻覺等等片段沒有一個貫穿的中軸線。有時一個人物的回憶中,會套上另一個人物的回憶;另一個人物的回憶,又會反轉回來套上其他的回憶或者想像。無數零碎的畫面拼接在一起,畫面中包含畫面,幻覺中連線幻覺,色彩濃郁,光影強烈,使人感到眼花繚亂。
作品啟示
 《弗蘭德公路》
《弗蘭德公路》作品後記
1960年,西蒙接受媒體的訪問談到《弗蘭德公路》的創作經過:“當我們想寫一部小說時,當我們開始想敘述一個故事時,實際上這故事已完結。我們轉過身來,朝後看自己剛走過的道路,看到的全程全部呈現一片混亂。遠景與前景一樣地清晰、逼近,像從望遠鏡里看去一般。”也就是說西蒙在創作過程中致力於把世界表現為一團亂麻似的混亂,用自我的書寫表現這個世界的時候,同時毫不降低它無法擺脫的複雜性。傳統的寫法是用小說的秩序對現實世界進行整理和規劃。所以大家已經習慣了一種環境、人物和情節這樣的傳統小說,直線型的敘事講述起來清晰而且有條理,開始和結束都能一目了然。但是在西蒙的小說中雖然大家能大致概括出主題是關於戰爭的災難和大自然的美景對比中人的處境和感受。有人物是幾個騎兵,但是模糊不清。有情節,但是可以忽略不計。開始和結束也令人難以捉摸。唯一貫穿全書的是無窮無盡的描述,動用身體的所有感官能體驗到的所有感覺和意象,根本沒有喘息的時間一幅幅的畫面接踵而至,令人應接不暇。小說中充斥著大量的“這是說”、“或者可以說”、“更確切說”這樣的短語對描述的畫面進行補充說明,這些還不夠的時候甚至運用大量的括弧意猶未盡似的再一次解釋。西蒙對細節有些過於病態的迷戀,一個場景會從不同的角度不厭其煩地進行書寫,繁複的畫面擁擠不堪,似乎在刻意考驗著讀者閱讀的承受能力。這點不時的讓我想起普魯斯特那個眾所周知的例子,為了描寫自己在把一片餅乾浸泡在茶里時回憶起的幼時在鄉下的美好時光,他竟然為此寫了八十頁的篇幅。在西蒙的小說中大家似乎看到了這種繁複的小說傳統悄悄的延續。
西蒙的所有的小說似乎都有自傳和戰爭的影子,他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夕,父親戰死沙場,其後西蒙也參加過西班牙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弗蘭德公路》就取材於二戰的經歷。戰後的西蒙在故鄉一邊種植葡萄園,一邊開始寫作。他遠離塵囂,隱居故土,生性孤獨,沉默寡言,深居簡出,除了寫作似乎與人也沒有交流。這種沒有公共生活的獨居經歷對他的創作不可能不產生影響,沉迷於過往的戰爭經歷,自我過於主觀的沉思,讓回憶成為了他寫作中不可忽略的部分。本雅明評價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的時候說:“對於回憶著的作者來說,重要的不是他經歷過的事情,而是如何把回憶編織出來。”也就是說,在作品中,作家不可能按照生活原來的樣子描繪生活,而是把它作為經歷過它的人回憶描繪出來。回憶是一種加工,是一種再創造,是一種想像中的主觀內射。世界的存在本來是沒有意義的,意義不過是後人強加的而已,為了恢復世界這種赤裸裸的本真的混亂,需要動用身體的各種感覺,儘可能的用各種方式從不同的角度描述那個世界。在這裡,西蒙的筆下,繁複的小說世界是現實世界的表象,也是它的本真。
卡爾維諾曾就小說的繁複美學進行過闡述,他認為雖然過分宏偉的構想在許多領域中都可能令人厭倦,但是在文學中則恰恰相反,我們需要的正是一種百科全書式的甚至可以囊括宇宙的文學,“文學所面臨的重大挑戰就是必須能夠把知識各部門、各種‘密碼’總匯起來,織造出一種多層次、多面性的世界景觀來”。從歌德到福樓拜,從普魯斯特到現在寫《弗蘭德公路》的西蒙,似乎從未放棄過這種不可能的理想和勇氣。幾百年的努力嘗試,西蒙延續了可貴的小說傳統,也創造了新的繁複美學的傳統,一九八五年的諾貝爾獎授予他,多多少少撫慰了這位在小說的探索之路上越走越遠的孤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