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夢珂》是女作家丁玲的處女作。1927年底發表於《小說月報》。《夢珂》的原型王劍虹。
內容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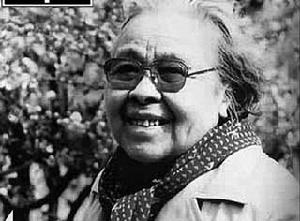 丁玲
丁玲“夢珂,她是一個退職太守的女兒。當太守年輕時,他生得確是漂亮,又善於言談,又會喝酒,又會花錢。從起身到睡覺,都耽樂在花廳里。自然有一般時下的詩酒之士,以及販古董,字畫的掮客們去承奉他,終日鬥雞走馬,直到看看快把祖遺的三百多畝田花完了,沒奈何只好去運動做官。靠了曾中過一名舉人,又有兩個在京的父執,所以毫不困難的起始便放了一任太守。原想在兩三年後再調好缺,誰知不久就被革了,原因是受了朋友的欺騙,在不知不覺中做了一點被牽涉到風化的事。於是他便在怨恨,悲憤中灰起心來,從此規規矩矩的安居在家中,忍受著許多不適意的節儉。但不幸的事,還毫不容情接踵的逼來,第二年他妻子便在難產中遺下一個女孩死了。這是他在十八歲上娶過來的一個老翰林的女兒,雖說也是按照中國的舊例,這婚姻是在兩個小孩還吃奶的時候便定下的,但這姑娘卻因了在母家養成的賢淑性格,和一種自視非常高貴的心理,所以從未為了他的揮霍,他的遊蕩,以及他後來的委靡而又易怒的神經質的脾氣發生過齟齬。他自然是免不了那許多痛心的嘆息和眼淚,並且終身便在看管他那唯一的女兒中,夾著焦愁,憂憤,慢慢的也就蒼老了,在那所古屋裡。”(出自《丁玲《夢珂》》
這裡涉及的是王劍虹的父親。其父王勃山,愛文物,諳醫道,悉詩文,是辛亥革命時期的老同有盟會員,曾任孫中山廣州國民政府秘書;解放後,先後任川東行政公署監委委員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1957年去世。王劍虹早年喪母。夢珂的父親與王劍虹的父親,很有些靠譜。也就是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交融。
1919年,“五四”波濤傳到桃源第二女師,王淑生運動的主要負責人,領導同學罷課、示威、遊行、演講。這時王淑蔣冰之(即當代女作家丁玲),並成為“不是姐妹,勝似姐妹”的好朋友。是年底,王勃山決定把女兒帶到上海讀書。行前,王勃山根據龔自珍《夜坐》中的詩句“萬一禪關砉然破,美人如玉劍如虹”,將女兒的名字淑改為劍虹。
“這幼女在自然的命運下,伴著那常常喝醉,常常罵人的父親一天一天的大了起來,長得象一枝蘭花,顫蓬蓬的,瘦伶伶的,面孔雪白。天然第一步學會的,便是把那細長細長的眉尖一蹙一蹙,或是把那生有濃密睫毛的眼瞼一闔下,就長聲的嘆息起來。不過,也許是由於那放浪子的血液還遺留在這女子的血管里的緣故,所以同時她又很會象她父親當年一樣的狂放的笑,和怎樣的去煽動那美麗的眼,只可惜現在已缺少了那可以從揮霍中得到快樂的東西了。”(出自丁玲《夢珂》)
這裡描寫的夢珂是個美女。而丁玲在同學間算不上美人。而沈從文描述的丁玲是“那么一個樸素圓臉的女孩子”(《記丁玲》116頁)“這個圓臉長眉的女孩子,她同我想像中的平凡女子差不了多少。就因為她不知道如何去料理自己,即如女子所不可缺少的穿衣撲粉本行也不會,年輕女子媚人處也沒有,姑比起旁的女人來,似乎更不足道了。”(《記丁玲》63頁)而丁玲的同學摯友王劍虹,沈從文是這樣描述:“當時丁玲女士還不過十七歲,天真爛漫,處處同一個男子相近,那王女士卻是有肺病型神經質的女子,素以美麗著名,兩人之間從某種相反特點上,因之發生特殊的友誼,一直到那王女士死去十年後,丁玲女士對於這友誼尚極其珍視。在她作品中,常描寫到一個肺病型身體孱弱性格極強的女子,便是她那個朋友的剪影。”(《記丁玲》57頁)對照沈的文字,我們自然會懂得其實,丁玲筆下的夢珂就是她那個美麗的同學王劍虹。
“她在酉陽家裡曾念過好幾年書,也曾進過酉陽中學。到上海來是兩年前的事。為了讀書,為了想藉此重振家聲,她不得不使那老人拿嘆息來送別她的獨女,叮嚀又叮嚀的把她託付給一個住在上海的她的姑母,他的堂妹。”(出自《夢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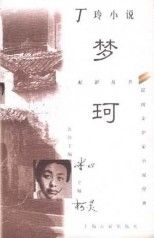 夢珂
夢珂王劍虹,原名王淑王番,與趙世炎同鄉,1902年出生,比丁玲大兩歲,四川酉陽龍潭鎮人,土家族,是丁玲的同窗好友。曾與丁玲一塊就讀與湖南的桃源第二女子師範學校,1923年7月,中共在上海創辦了“上海大學”,王劍虹與丁玲經瞿秋白同志的介紹,就讀於上海大學文學系,瞿秋白同志時任教務長兼社會科學系主任。
丁玲回憶說王劍虹女士“有一雙智慧、犀銳、堅定的眼睛”,她口才流利,能言善辯,口若懸河,見解精闢,常反駁學潮的校長老師啞口無言、瞠目結舌,同時,她又“象一團烈火,一把利劍,一支無所畏懼、勇猛直前的隊伍的尖兵”。
在二十年代初的中國,王劍虹應算是一位優秀而出色的女性,丁玲說她“是堅強的,熱烈的”。由於她自幼喪母,同時,她又是一個很儉樸的女性,在她和丁玲一塊求學的日子裡,“如果能買兩角錢一尺布做衣服的話,也只肯買一角錢一尺的布。我們沒有買過魚、肉,沒有嘗過冰淇淋,去哪裡都是徒步,把省下的錢全買了書。”但這樣艱苦樸素的生活,絲毫不影響她樂觀的生活態度,她依然是“生活得很有興趣,很有生氣”。
對於愛情,王劍虹女士有著沉穩而熱烈的追求,同時,又那么真摯,那么含蓄。“她在熱烈地愛著秋白。她是一個深刻的人,她不會表達自己的感情;她是一個自尊心極強的人,她可以把愛情關在心裡,窒死她,她不會顯露出來讓人議論或訕笑。”但文采極好的王劍虹,將自己對異性的愛慕藏在心底,對瞿秋白同志真熱的愛戀,她會用詩表達出來。
1923年寒假,瞿秋白與王劍虹喜結良緣,可惜,好景不長,紅顏薄命,這么一個出眾的新女性,被瞿秋白稱為“夢可”的王劍虹,婚後不久便被瞿秋白同志的肺病染上,病勢沉重,最後香消玉殞,秋白劍虹竟相隔於天上人間了。
相關內容
瞿秋白致王劍虹的詩作
“虹:
……你偏偏愛我,我偏偏愛你——這是冤家,這是“幸福”。唉!我恨不能插翅飛回吻……
愛戀未必要計較什麼幸福不幸福。愛戀生成是先天的……單只為那“一把辛酸淚”,那“暗暗奇氣來襲我的心”的意味也就應當愛了——這是人間何等高尚的感覺!我現在或者可以算是半“個”人了。
夢可!夢可!我叫你,你聽不見,只能多畫幾個“!!!!!”可憐,可憐啊!
秋白
一月十二日”
由此可見,甚至連夢珂這個名字,也是瞿秋白曾經對王劍虹的暱稱愛語,法文意為“我的心”這更能說明王劍虹就是夢珂的生活原型。“夢珂看見那老太太的親熱,倒不好意思起來,也就笑了。到晚上吃麵時,老太太看到那綠色的,新擀的菠菜面,便不住的念起故鄉來。是的,酉陽的確不能拿上海來相比。酉陽有高到走不上去的峻山,雲只能在山腳邊蕩來蕩去,從山頂流下許多條溪水,又清,又亮,又甜,當水流到懸崖邊時,便一直往下倒,一倒就是幾十丈,白沫都濺到一二十尺,響聲在對面山上也能聽見。樹呢,總有多得數不清的二三個人圍攏不過來的古樹。算來裡面也可以修一所上海的一樓一底的房子了。老太太不住的說,勻珍的父親捻著鬍子盡笑。”(出自《夢珂》)
這裡描寫的酉陽風光,深得龍潭神韻。沈從文二十年代曾駐紮過酉陽龍潭,後在其自傳里描述過龍潭景色,記載於《一個大王》一章里。這是種人生機緣吧。沈大概沒有親見過王劍虹女士,但在丁玲的相冊里看到過王女士的芳容,聽到過丁玲描述王女士的故事。
“老太太還自有她的見地。本來,酉陽是不必有那樣多學校的,並且酉陽的聖宮——中學校址——是修得極堂皇的,正殿上的橫樑總有三尺寬,柱頭也象桌子大小。便是殿前的那一溜台階,五六十級,也就夠爬了。“哼,單講你那學校的鞦韆,看是多么笨,孤零零的站在操坪角上,比起我們學堂里的來,象個什麼東西!未必你們忘記了?想想看,好高!從那桐子樹的橫枝上墜下來,足足總有五六丈,上面的葉子,巴斗大一匹匹的,底下從不曾有過太陽光,小孩子在那裡盪著時,才算標緻。你大哥在時,還常常當打到東邊就伸手摘那邊杈過來的桂花,只要有花,至少也可以抓下一把來,底下看的人便搶著去撿花片。勻兒總該記得吧!””(出自《夢珂》)
這裡描寫酉陽中學,很是逼真,至今酉陽人還引以為傲。至於丁玲是真的與王劍虹到過酉陽遊玩,還是聽同學描述家鄉風物的結果,那還有待於專家深入研究。1922年春節前夕,王劍虹利用回川探親之機重返湖南,把日夜惦念的好友丁玲也接到上海平民女校讀書。至於這回是不是丁玲與好友同到酉陽龍潭,可能性很大。
丁玲小說《夢珂》,後來夢珂不滿學校教育。驕傲負氣,脫離上海姑姑家,跑到明星劇社當了一名演員。改名叫林琅,那是丁玲自己的一段經歷的縮影。但總的說來,夢珂一角,實出於王劍虹的人生經歷的影子為多,也是丁玲悼念緬懷好友的一種方式。可見她們感情深厚,友誼真摯。以至於瞿秋白在王劍虹死後不久,就迷戀上楊之華而耿耿於懷,為好友抱不平。人生的快恨情仇,男女的恩恩怨怨,誰說得清楚,誰能不感慨?好在有小說《夢珂》,丁玲與王劍虹,都可以因此不朽了。永遠活在文字里。
“現在,大約在某一類的報紙和雜誌上,應當有不少的自命為上海的文豪,戲劇家,導演家,批評家,以及為這些人吶喊的可憐的嘍羅們。大家用“天香國色”和“閉月羞花”的詞藻去捧這個始終是隱忍著的林琅——被命為空前絕後的初現銀幕的女明星,以希望能夠從她身上,得到各人所以捧的**的滿足,或只想在這種**中得一點淺薄的快意吧。”這個小說的結尾,倒是丁玲的一種虛構與幻想,其實,丁玲根本就不適於當演員。她無功而返。
女作家丁玲作品
| 丁玲,現代女作家。1930年5月,丁玲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1年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斗》的主編,成為魯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響的左翼作家,1986年3月4日,丁玲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