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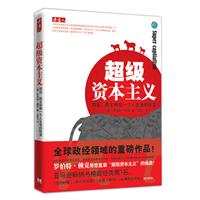 超級資本主義
超級資本主義隨著經濟一體化和貿易自由化的發展,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超級資本主義”。隨之而來的是財富兩極分化日趨嚴重、中產階級逐漸消失、就業不穩定、生存環境不斷惡化……原因何在?
同樣,所有這些“超級資本主義”大國面臨的問題,在迅速融入全球化的中國也正初露端倪。
如何創建民主公平法制的社會,做到民主與經濟的和諧發展?
被譽為“美國三位在商業及經濟領域最具影響力的意見領袖之一”,曾任美國柯林頓政府勞工部長,歐巴馬競選委員會顧問,美國著名的政治經濟學者,現任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公共政策學院教授羅伯特.賴克,緊扣時代脈搏提出 :面對席捲而來的對民主制度和人們的生活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的超級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的公民又應當何去何從?賴克認為,要擁有活力無限的民主制度,不能讓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侵犯了民主的界限,二者必須涇渭分明。政府有必要通過新的法律法規來約束資本行為,避免正在惡化的各種社會問題給社會帶來大的災難。要創建一個民主公平的社會,關鍵在於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在“消費者、投資人、社會公民”三種角色中找到平衡,發揮公民的角色,積極以立法制定遊戲規則,避免讓超級資本主義超越界限影響到民主制度,這是唯一有建設性的解決之道。
上述這些對於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社會難題,也同樣大有裨益。
作者簡介
羅伯特.賴克,著名的政治經濟學者,被譽為“美國三位在商業及經濟領域最具影響力的意見領袖之一”,曾任美國柯林頓政府勞工部長,歐巴馬競選委員會顧問,現任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公共政策學院教授。賴克以經濟與社會思想創見聞名,曾在2003年獲頒哈維爾基金會獎,其論述多見於《紐約客》、《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等各大媒體。同時,他還是《美國展望》雜誌的共同創辦人暨編輯、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知名節目“市場”的每周評論員,經常出現於電視評論節目中。本書是他的第十一本著作,已出版《國家的職責:迎接21世紀資本大潮》、《美國新視野》、《成功的未來》、《困在內閣》等。
主要觀點
本書的創新之處就在於,它打破了人們的思維定式,從我們作為消費者與投資者的利益考慮出發,從一個比較新的視角透視民主衰落的問題。在每個人的身上尋找民主衰落的原因,反對人們把企業看做具有公民身份的主體,要求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把保持經濟發展與民主制度之間的平衡和諧作為解決問題的關鍵。
業內精英推薦
本書呼籲我們迫切需要重新評估資本主義,並為我們目前深陷的混亂困境提出矯正建議,這是一本我們必讀的重要著作。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史蒂格利茲
羅伯.瑞奇是我們這一代的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他對政治與經濟的大貌具有精闢可靠的睿見,並以無礙的辯才和清澈的判斷力傳達值得我們警醒的訊息。這是一本令人贊嘆佩服的傑作!」
--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民主的不滿》作者麥克.沈岱爾
瑞奇以獨樹一格的睿智與辯才呼籲我們正視顯而易見的道理:資本主義應該為民主制度所用,而不是倒反過。這是一本罕見的佳作,破解迷思,引人入勝,適時地重塑最重要的公共議題。
--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風險大轉移》作者/雅各布.海克
瑞奇再一次為美國人深陷的困境提出強而有力的新觀點,這本書凸顯新類型的社會衝突―-介於身為消費者與投資人的我們和身為民主社會公民的我們,這兩者之間的衝突。
--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獨自打保齡球》作者/羅伯.普南
本書提醒我們:加入清晰思考,我們的政治勇氣與力量才會增強。瑞奇分析企業在我們現今的民主制度中扮演的角色,並極具說服力地主張必須對此加以限制,他提出把掌控政府的權力還諸人民的解決方法。透過這本書,瑞奇已盡了他的責任,我們若想要一個更公平正義的社會,現在該是身為公民的我們作出回應的時候了。」
--前美國參議員、《新美國故事》作者/比爾.布萊德利
目錄
序 言 悖論 1
第一章 並非絕對意義上的黃金時代
第二章 通往超級資本主義之路
第三章 難下決斷
第四章 被淹沒的民主
第五章 轉向的政治
第六章 通往超級資本主義的公民指南
致 謝
精彩書摘
美國人對民主制度漸漸失去了信心,其他許多民主國家的公民也同樣信心不再。正如我在本書開篇所談及的,35年前,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我們的民主政府是為所有人謀福利的,但是幾十年後的現今,這種信心普遍地發生了動搖。現在,絕大多數人認為,政府由極少數大利益集團操控,是它們謀求私利的工具。其他民主國家的調查也顯示出,公民對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呈現類似的下滑態勢。這到底是為什麼?
如前所述,對於這一轉變的解釋都缺乏說服力。對於美國以及這種現象目前程度略輕、但同時愈演愈烈的其他國家來說,更可能的原因是金錢在政治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特別是來自大公司的政治獻金。正如我後面將要證明的,那些獻金正是促使經濟繁榮的超級資本主義產生的副產品。隨著公司開始利用公共政策尋求競爭優勢,競爭擴展到了政治領域,其負面結果就是:民主制度回應公民意願的能力下降了。
1
人們對於正在發生的事基本上不存在爭議——來自公司的越來越多政治獻金注入了華盛頓和其他州首府城市,這一事實顯而易見。令人困惑的是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如果仔細觀察一下這種態勢從何時起開始逐漸升級,就可以發現一條重要的線索。
在公司的政治獻金開始湧入之前,華盛頓是一個相當破落的地方——正如約翰·甘迺迪所言,華盛頓是“一座兼有南方效率和北方魅力的城市”。即便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作為聯邦貿易委員會的官方代表在那裡工作的時候,市區的大部分地段仍然相當破敗。如果某位說客要留下來吃午餐,我就把他帶到賓夕法尼亞大街對面蟑螂肆意橫行的三明治店去,那樣,飯後我就永遠都不會再見到那位說客了。但是當我在20世紀90年代重返華盛頓的時候,這個城市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三明治店早已不見蹤影,大街上遍布著耀眼的豪華旅館、高檔餐廳以及時尚酒吧。從喬治城一直到國會山,到處是光鮮奪目的建築:由玻璃、鉻和拋光木料建造的各具特色的寫字樓群;設施完善的公寓,其門衛清楚地知道每一家住戶的姓名和需求;有著大理石門廊、厚地毯、輕音樂和花崗岩前台的旅店;使用亞麻餐巾紙、皮面裝訂選單和沉甸甸銀器的餐廳,它們提供75美元的牛排和400美元的法國大瓶裝美酒。位於國會山底層的查理帕爾默牛排店憑藉其存有上萬瓶佳釀的酒窖聞名遐邇。緊鄰喬治酒店的bistroBis餐廳為客人提供裹著薄薄一層麵包屑的鬆脆油炸雞腿和吉普賽風味牛雜。位於第19街的Palm餐廳推出了更為昂貴的餐飲,那些精心設計的美食甚至可以讓最疲憊不堪的公務員胃口大開。
獻金流所到之處,一切都貴了起來——不僅包括酒店和餐館裡的賬單,還包括華盛頓的律師、說客和專業公關人員的報酬,以及華盛頓房地產的價格,甚至周邊城鎮房地產的價格也隨之高漲起來。2005年,華盛頓有7個縣進入人口調查局選出的美國人均收入最高的20個縣。
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給予候選人選舉辦公室的政治獻金也有了大幅增加。隨著政治獻金的增加,每位候選人對於可能有多少錢流向競爭對手都十分敏感——除非這位候選人的競選款項龐大得足以嚇退其他競爭者。這樣一來,曾經熱衷於所在州或區的“多元”利益集團的參議員和代表們——特別是那些加入了全國聯合會的人——日益把注意力集中於如何募集更多的競選資金。而最大的競選資金來源就是各家公司的政治行動委員會(PAC)、公司高管,以及“鎖定”了來自公司高管和商業聯合會的政治獻金的公司說客。
直接捐款不過是龐大的權力販賣活動的冰山一角,正如圖4.2至圖4.4所呈現的,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遊說活動愈演愈烈了。
這並不僅僅是20世紀中葉令政治哲學家們感興趣的利益集團多元主義的一種膨脹而昂貴的形式。所有這些大量增加的遊說活動幾乎都由公司贊助。與之相比,非商業集團的遊說活動就不足掛齒了,比如,2005年美國勞工聯合會與產業工業聯合會在國會山僅有6位支付報酬的說客。當年在遊說支出最大的100家機構之中,美國商會名列前茅,而美國勞工聯合會僅排第74位。大多數公共利益團體,比如宣揚環境保護、兒童福利或者人權事業的團體等甚至未能入榜。
我再次提請讀者注意,遊說支出大增始於20世紀70年代。1950年,在華盛頓設有辦公室的公司不足100家,而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後,公司的遊說活動就開始活躍起來。美國國家製造商協會於1973年把總部搬到了華盛頓,幾乎與此同時,商業圓桌會議—— 一個由各公司高層管理人員組成的聯合會,他們會親自到華盛頓進行遊說——在華盛頓成立了。到了20世紀90年代,超過500家美國公司在華盛頓設有長期辦公室,總共雇用了大概6.1萬名說客,其中包括為它們自身的利益進行遊說的律師。此外還有許多由公司贊助並專門配置政策專家和行銷人員的各種基金會、中心和機構,以及一些專門負責為符合某公司利益的公共政策進行廣告和行銷的公司。
近些年來,隨著超級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傳播和發展,公司的這類遊說大潮席捲了全球的資本市場。2005年,歐盟委員會和歐盟行政辦公室所在地布魯塞爾聚集了大約1萬名說客,其中大多數代表著大型全球性公司和行業集團的利益。今天的de Cortenbergh大街與華盛頓的K街極為類似。
2
流入政治領域的公司政治獻金的激增始於羅納德·里根的當選,之後一直延續到喬治·布希當政時期。有些人認為,這是由於當時大公司與共和黨達成了一筆交易,根據這種假定,大公司為共和黨人提供足夠的資金,以保證共和黨人保持永久性的多數席位,作為回報,共和黨推行堅決的重商政策。布希執政期間臭名昭著的“K街計畫”就是一筆典型的交易,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湯姆·迪萊以及其他共和黨領袖向公司和貿易團體施壓,要求它們只雇用大老黨(美國共和黨的別稱)的說客。
然而這種解釋太過簡單了。它並沒有解釋為什麼公司政治說客的人數在全世界範圍呈增加態勢,也無法解釋這樣一個重要事實:流向美國政界的日益增加的資金大體上兩黨兼顧。民主黨人在1994年喪失了對國會的控制權時,已經開始依賴於來自公司的政治獻金了。民主黨代表托尼·科埃略叫囂道:“不管喜歡還是不喜歡,企業都不得不和我們打交道,因為我們是多數黨。”作為20世紀80年代的民主黨國會競選委員會的領袖,他開始勒索美國的公司。科埃略極力尋求獲得與共和黨所擁有的數額大體相當的政治獻金,並最終達到了目的。美國無黨派組織政治回應中心的數據顯示,1990年,卡車運輸業把151萬美元政治獻金劃分為大致相等的兩份,分別捐予民主黨和共和黨。這種均衡狀態一直持續到共和黨人在1994年重新執政才有所變化,並在2006年民主黨獲勝之後重新恢復。(根據一家追蹤政治捐贈的組織——政治獻金線的數據,政治行動委員會在2007年第一季度把獻金的56.6%給了民主黨人。)當然,科埃略所構想的公司對於民主黨國會的依賴,也使民主黨依賴於公司的施捨,這一點在1994年他們敗北之前的幾個月表現得尤為明顯,許多民主黨人投票反對比爾·柯林頓的醫療保險計畫,因為他們的贊助公司反對這樣做。
儘管柯林頓政府——我很榮幸曾任職於其中——出台了醫療保險計畫,但它仍不失為美國歷史上最重商的政府。在柯林頓上任後的前兩年,民主黨人控制了國會兩院,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後,他們又推動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建立——這兩件事對於大公司來說可謂意義非凡。如同華爾街券商希望的那樣,柯林頓也曾致力於削減聯邦預算赤字。經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政治環境,公司利潤飛漲,股市飆升,CEO們的收入屢創新高。
僅憑這些事實並不足以證明柯林頓或者其政府中的某個人接受了大公司的特別恩惠,也不足以證明公司支配了柯林頓政府的議事日程。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多少政治獻金注入了柯林頓的第二次競選活動和民主黨國家委員會,以及柯林頓多么勤於向公司示好以獲得這些資金。對希望在林肯臥室中過夜的CEO們,柯林頓表現出的慷慨友善驗證了那句古老的格言——白宮是唯一一家能讓客人把巨款留在枕頭上的旅店。儘管不一定能實現目的,但金錢仍是成功的保障。石油大亨羅格·坦拉茲向民主黨國家委員會捐獻了30萬美元,只為與柯林頓有一次會面。於是共和黨參議員弗雷德·湯普森在國會競選金融改革聽證會中質問坦拉茲,他是否認為自己擁有“憲法賦予的權利,讓美國總統親自考慮你的經濟交易”。坦拉茲的回答直白坦率:“參議員,我的行為超出了界限。可是為什麼不呢?是你們設定了規則,我們不過在遵循規則。這就是政治慣例。”
近些年,遵從兩黨路線使用政治獻金的方式為許多民主黨人做好了職業規劃,他們在華盛頓卸任之後,就在大公司中找到薪水頗豐的工作。當日益明顯的跡象表明,民主黨可能在2006年中期選舉中獲勝時,K街計畫實際上就泡湯了。選舉開始前的幾個月,華盛頓的一家主要法律和遊說公司歐華公司就將其政府事務運作方向從共和黨的托馬斯·奧尼爾轉向了民主黨的詹姆斯·布蘭佳—— 一位來自密西根的前任州長和國會議員。布蘭佳向《華盛頓郵報》表示:“作為一位民主黨人對我沒有壞處,那是一定的。今年必將是民主黨年。”高層民主黨人在眾議院中的中級席位也突然增加了。
遊說活動中的兩黨路線已經成為大公司的現實必然選擇,因為要爭取國會中大多數席位對某項特定政策的支持,需得同時說服兩黨才能實現。參議院民主黨少數派領袖湯姆·達施勒在2004年第二次選舉落敗之後,加入了前任共和黨多數派領袖鮑勃·多爾的遊說公司——奧斯頓-伯德公司。多爾風趣地說:“他在參議院有很多朋友,我在參議院也有不少朋友。合在一起,我們也許會得到51%的票數。”
堅持兩黨路線的遊說公司的服務名單里都是藍籌客戶公司。為了推動布希政府在國會山推行醫療保險處方藥福利法,醫藥製造商希爾聘請了民主黨籍說客、前民主黨國會議員維克·法奇奧,阿爾·戈爾前任首席民主政策顧問大衛·貝爾以及柯林頓總統和達施勒參議員的前首席助理喬爾·詹森。為了推動他們的決策,仿製藥{1}製造商們聘請了克里斯·詹寧斯,他曾經幫助柯林頓設計了廣受讚譽的醫療保險計畫,還聘請了前任共和黨助理馬克·伊薩科維茲,他曾經幫助共和黨挫敗了柯林頓計畫。同樣,1998年,菸草公司為了向國會兜售它們與州律師協會達成的關於菸草健康宣言的協定,而求助於共和黨和民主黨雙方的說客,其中包括戈爾的前任助理彼得爵士、前任民主黨州長安·理查茲和前任民主黨參議院多數派領袖喬治·米切爾。
非商業團體在民主黨執政時期要比在共和黨執政時期更容易獲得權力,而商業團體不論哪個黨執政,都擁有強大的權力。在柯林頓政府中,半數以上的官員在離職之後都成為公司的說客。柯林頓的首位立法主任上任不足1年就離職了,繼而就任偉達公司的主席。柯林頓的副總參謀長也在任期未滿1年時離職,轉而加入了美國電話協會。據美國公務員廉政中心數據顯示,從1998年到2004年之間,來自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的超過2200名前任聯邦政府高層官員成了註冊說客,還有200名前任國會成員也成為註冊說客。到了2003年,前任國會成員中的註冊說客有一半曾屬於民主黨人陣營,他們幾乎都在為大公司的利益進行遊說。
真正有意義的不是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對比,而是幾十年前在華盛頓供職的人與最近在遊說界供職的人之間的對比。在20世紀70年代,僅有大約3%的退休國會成員成為華盛頓說客。而到了2005年,不論是在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這一比例都超過了30%。越來越多的前任官員和助理投身於遊說界,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不再像他們的前輩們那樣,對利用在政府服務期間獲得的經驗去賺取外快深感不安,而是因為遊說活動的資金回報遠遠高於以前。與餐飲價格、房地產價格一樣,遊說佣金隨著公司的政治獻金大量湧向華盛頓而節節攀升。說客們向新客戶收取的費用從1995年的大約每月2萬美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每月4萬美元。到了2006年,與國會或者白宮有密切關係、且有意轉行到K街的人士起薪已經飛漲到每年50萬美元。國會委員會和分會委員會的前任主席們可以左右以前所在委員會的立法,因此每年有200萬美元收歸囊中。
這些年來,國會中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特別是在所謂的文化戰爭(如墮胎、同性結婚、幹細胞研究和對美國的效忠宣誓)和對外政策方面。這些議題通常出現在各大報紙的頭條,因為它們就像公眾人物之間的激烈衝突一樣,能夠吸引大眾的關注。但是,這些並不是公司可以不分黨派地用錢買通的國會日常工作的全部。
另一種理論把政治獻金的增加歸結為聯邦政府規模和權力範圍的擴大。“花費在華盛頓的錢高達2.6萬億美元,能夠為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規則。”前任共和黨眾議院發言人紐特·金里奇說,“你猜怎么樣?人們會用聳人聽聞的巨額資金來對此施加影響。這樣問題就來了,政府的規模越來越大,公司的獻金也越來越多。”
這一觀點也不符合事實。在政府的各個層級中,戰後公共支出增加最多的時期發生在1947年到1973年間,這正處於並非絕對意義上的黃金時代。1983年,聯邦支出在整體經濟中的比重約為24%,達到了頂點,之後又穩步降低到20%以下。同時,越來越多的聯邦支出被用於社會安全、醫療保險和國防工業中。說客們也確實聚集在這些領域,而非國防裁量性支出——這是你可能會認為大多數遊說活動都集中的領域,因為每年這一領域的支出比例都在波動——在1980年曾達到頂點,占國民經濟總值的5.2%,之後就回落了。由於經濟的整體增長,聯邦支出也增長了很多。但是流向華盛頓的公司的政治獻金的攀升速度比聯邦支出的增速更快。
流向政界費用的攀升也不能用經濟監管的增加來解釋,正如我們所見,在過去的40年裡,大多數重大的經濟監管都被廢止或放鬆了。根據《聯邦公報》公布的最終規則或提議規則的數量來看,1980年之後,監管一直呈下降趨勢。
最後,流向政界費用的攀升也不能用公司要抵制工會的對抗力量來解釋。正如我們所見,工會的力量在過去幾十年一直處於衰落之中,而且與公司遊說活動的活躍相比,現在工會在國會山的遊說活動只是勉強可以見到而已。
第三種理論把流向政界的公司政治獻金的日益增長歸因於大公司和華爾街圖謀操縱國家機器、支配兩大政黨。這種觀點認為,大公司和華爾街的目標,就是維持低工資,避免代價高昂的監管,減輕富人稅負,掠奪開發中國家,以所有人的利益為代價中飽私囊。經濟政策研究所的創始人和前任所長傑夫·法克斯寫道:“美國兩黨合作的管理階層一心保護其特權對象,而把我們其他人拋給了沒有監管、野蠻無情的全球化市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新聞主持人盧·道博斯認為,大公司和政府正在進行針對普通勞動者的“階級戰爭”。
不論這種陰謀論觀點如何吸引人,都難以在事實面前站住腳。各家公司非但沒有彼此勾結、共謀,它們之間的競爭反而越來越激烈了。就像我在下文中將要談到的那樣,這種競爭已經延伸到了政治領域。這些每日占據國會注意力、花費了國會成員不計其數的時間、讓華盛頓說客和公關專家激烈爭論的鬥爭,大都是同一行業內部、彼此存在競爭關係的公司或部門之間的鬥爭,有時也可能是存在競爭關係的行業間鬥爭。
現在在華盛頓和世界上的其他政治中心,作為公民,我們的呼聲更加難以傳達出去,這不是因為大公司變成了更為強大的統一體,而恰恰相反——公司之間的競爭越發慘烈了。公司為了獲得或者保持相對競爭優勢而開始涉足政治,結果公司間爭奪商業利益的喧囂震耳欲聾,幾乎淹沒了所有對於公共利益的認真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