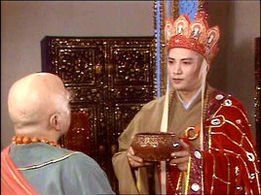紫金缽盂
 紫金缽盂
紫金缽盂《西遊記》中的重要道具,是唐太宗李世民欽賜給御弟三藏法師路上化緣與飲水用的。不過這
似乎不是它的最大功效,當師徒四人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到達西天大雷音寺時,如來應允了三藏經書,取經時如來佛祖的兩個徒弟阿儺、伽葉索要好處未果時,送給唐僧的是無字經。當孫悟空他們告到如來時,如來並不以為過,還說“不能讓後代兒孫沒錢使用。”唐僧無奈便用唐王欽賜的紫金缽盂送
給阿儺並許諾“奏上唐王,定有厚謝。”才換取了那有字的真經。因此這紫金缽盂功不可沒!另外如來對弟子索要人事的態度也引人深思。這一段也是原小說中很有趣的一筆。
讀者誤讀
《西遊記》寫 唐僧先從觀音菩薩得佛祖所賜三寶,即錦襴異寶袈裟一領, 九環錫杖一根,金、禁、緊三箍並咒語三篇;後又從唐太宗受通關文牒一通,紫金缽盂一個,供“途中化齋而用”。這些都是唐僧取經上路必需的寶貝,第56回甚至說“通關文牒、錦襴異寶袈裟、紫金缽盂,俱是佛門至寶”。最後金、禁、緊三箍依次各派了用場,錦襴異寶袈裟、九環錫杖在唐僧成佛後仍服用如故,通關文牒在唐僧取經回東後仍繳納於唐王。唯是紫金缽盂被作為取經的“人事”,送給了 阿儺、 迦葉,等於被佛祖沒收了。此書問世以來,讀者幾無不注意此一情節,而很少人不以這個紫金缽盂送“人事”的故事,是對西天佛國也貪求財賄的諷刺。其實是絕大誤會。
本來無一物
按佛教自初來中土,僧人托缽乞食,化齋為生,遂成傳統。因此,《西遊記》寫玄奘取經上路,唐王贈紫金缽盂,送一個飯碗,是極自然而合理之事。唐僧“肉眼凡胎”,途中飢餐渴飲,也實在少不了它。但在作者筆下,紫金缽盂的用處卻不止於此,更在於它是一個絕妙的象徵,以其被佛祖索要為“人事”,在諷刺“人事”的同時,表達了佛教禪宗頓教“本來無一物”之義。
這要從《西遊記》寫佛祖造經說起。按書中所寫,佛祖造真經三藏,分“白本”、“有字”兩種。“白本”即“無字真經”,因是“空本”之故,可以“空取”即不須“人事”。唐僧等第一次所取,即是此種本子。雖然唐僧等以為“似這般無字的空本,取去何用”,並指“阿儺、迦葉等索財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將無字的白紙本兒教我們拿去”,但那是他們尚未“九九歸真”時殘存的“迷人”之見,或其高明終不如佛祖處。而佛祖說“白本者,乃無字真經,倒也是好的”云云,似輕描淡寫,其實最堪玩味,是此書“悟空”的正義。然而,佛祖同時說“他兩個(按指阿儺、迦葉)問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經不可輕傳,亦不可以空取”,並舉了為趙長者家念經一遍“只討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黃金回來,我還說他們忒賣賤了”之例,明告唐僧等非送“人事”不可以傳經,並且後來也確實是唐僧送了紫金缽盂後才準其“換經”。這就不僅使向來讀者惶惑,認為佛祖也貪財好貨,而且把他說“無字真經,倒也是好的”,也看作哄人的話,其實是被作者哄了。
無字真經
《西遊記》“三教歸一”,大旨是一部寫取經成佛的書。其中佛中主禪,而按傳統的說法,禪分南北宗即頓漸二教。北宗漸教為唐釋神秀所創立,主張通過念佛誦經、打坐參禪以體認佛性,漸修以成佛;南宗頓教為神秀的同學慧能所創立,其說以 《壇經》為代表,認為漸修不可能成佛,主張“不假文字”,“直指人心”,“頓悟”以“見性成佛”,當然就用不著“有字的”經;而念經也就只成了愚人的事,所謂“迷人口念,智者心行”《壇經》。《西遊記》正是本南宗頓教之義,以孫悟空為頓悟的代表,一則寫他聽了菩薩說“悟空,菩薩、妖精,總是一念;若論本來,皆屬無有”的話,即“心下頓悟”第17回;二則寫唐僧也道“悟能、悟淨,休要亂說。悟空解得是無言語文字,乃是真解。”第93回暗示“無言語文字”即“無字真經”,才是上乘大法,諸佛妙理的所在。終至於由佛祖說出“白本者……倒也是好的”,其貌似輕忽,是以對唐僧等人,尚不足以悟此等妙理,而真實的意思卻是“無字真經”才是最好的。與對悟空的有關描寫相參照,可知這才是作者本意。
有字真經
至於“有字真經”,乃專為“迷人”而設。《壇經》雲“一切經書,及諸文字,小大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一切經書皆因人有。”這些“人”就是佛祖所說“愚迷不悟”之人。而所謂“愚迷不悟”,根本也只在不悟“三世諸佛,十二部經,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所以打坐參禪、誦經禮佛,唯重“外修”《壇經》,從而“有字真經”是“迷人”學佛幾乎唯一的憑藉。佛祖無奈,“只可以此傳之耳”。此乃因緣生法,隨俗設教,不得已而為。作者以此顯示其對世俗學佛只在文字中打攪,而不重“心行”第11回、86回、99迴風氣的不滿。也就因此,唐僧回東土交付經卷已畢,“長老捧幾卷登台,方欲諷誦”就有“八大金剛現身高叫道‘誦經的,放下經卷,跟我回西去也。’”不早不晚,剛好在“方欲諷誦”時打斷,就是明示唐僧既已“心行”,又“何須努力看經”第11回“誦經”之事,就由“東土眾生”盡其蠢鈍而好自為之吧。
“有字真經”既為“迷人”而設,則其授受也應當循“迷人”世界之法即市井之道,以錢物交易,自然以金為貴,“換經”的價格也必高昂。因此,佛祖說為趙長者誦經一遍,“只討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黃金回來,我還說他們忒賣賤了”,乃對“人”說“人”話,並非佛祖真的愛錢和西天缺錢,而如黃宗周評說“豈佛祖真將經賣錢耶,不過設詞以示珍重耳。”因此之故,乃有阿儺索要“人事”、唐僧以紫金缽盂“換經”之事。其不曰“禮物”而稱“人事”,應是點明此“事”在西天,卻屬仿“人”為,是佛祖以“人”之道行對人之“事”。換言之,正如“東土眾生”只識“有字真經”,如果“有字真經”可以“空取”而不必換,又如果“換經”而“忒賣賤了”,那么以其“愚迷不悟”之性,就連“真經”也要看輕,甚至於以為“無用”了。總之,取經要“人事”以及誦經討黃金之事,不是一般文學寫實,只是佛祖為傳經而設的一樁公案。其意在表明,世俗唯知以錢論重輕之俗牢不可破,連佛祖也只好因勢利導、以勸誘為功了。這就根本不是對佛祖西天,而是對“人事”的諷刺了。
唐僧送“人事”
然而,唐僧送“人事”何以正是紫金缽盂而不是其他這一則由於唐僧西遊,所攜除佛祖賜予之外,只有此缽盂系唐王所送世俗之物,可以當得起“人事”;另是由於一件佛教的公案,需稍為詳說。
按《壇經》載六祖慧能對神秀禪機有偈雲“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台。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其中“佛性常清淨”一句,後來各本都竄改為“本來無一物”,流傳甚廣。而據《五燈會元》卷一《五祖弘忍大滿禪師》載,慧能說如上偈語畢,仍請別駕張日用書之於壁。這就與其所主張“諸佛妙理,不關文字”相矛盾了;同卷《六祖慧能大鑒禪師》又載五祖弘忍歷述前代祖師傳法,只憑衣即袈裟為信,而囑六祖慧能以下,並袈裟亦不復傳,唯“以心印心”,更不關乎缽盂。但是,同篇又載慧能說法,得唐中宗所賜“磨衲袈裟、絹五百匹、寶缽一口”,這就又與“本來無一物”相矛盾了。以致宋代禪僧黃龍悟新誤信“本來無一物”是慧能偈語原文,作詩諷刺雲“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物,卻受他人一缽盂。”
繞路說禪
《西遊記》寫唐僧受唐太宗所賜紫金缽盂,正由惠能受中宗“寶缽一口”事脫化而來;而結末寫唐僧把這唯一俗世最為寶貴的飯碗——紫金缽盂,作為“人事”獻給了佛祖,則是推衍悟新詩意,顯示唐僧一路“心行”,終至“本來無一物”。而佛祖假借傳經以設公案,收沒了唐僧的紫金缽盂,也在對“東土眾生”因俗設教的同時,為“心行”將盡的唐僧消除了這最後的滯礙,使之達到“本來無一物”的境界,以至最後成佛。試想,如果唐僧成佛之後,還托著唐王賜予的紫金缽盂,將成何體統。
所以,以紫金缽盂送“人事”的描寫,既是照應,又是公案,又是象徵。這在宋明佛教是所謂“繞路說禪”,在小說則是融禪宗哲理於物象的藝術象徵。讀《西遊記》,不知此一事來歷,則不知佛祖收沒唐僧紫金缽盂,實為禪宗因緣生法“公案”之機;而不明其為藝術的象徵,則不知此一“公案”,佯為諷佛,而實以刺世,並彰顯禪宗頓教“本來無一物”,而其實應是“佛性常清靜”的“性空”之義。
缽盂(缽盂)bō yú
亦作“缽釪”。僧人的食器。亦指傳法之器。 南朝 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賞譽》:“ 王 劉 聽 林公 講, 王 語 劉 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更聽, 王 又曰:‘自是缽釪後 王 何 人也?’” 唐岑參《太白鬍僧歌》:“窗邊錫杖解兩虎,牀下缽盂藏一龍。”《西遊記》第五三回:“聖僧啊,這缽盂飯是孫大聖向好處化來的。”
人生感悟
“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紫金缽盂,那就是輪迴的根源。”
“慚愧道人”的《仙凡影塵錄---一名道士的三十年靈異經歷》,我相信這是一個道緣極深之人的真實經歷,徐徐讀來受益匪淺,但我承認,最打動我的是這句話,以及聖師的故事。是的,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紫金缽盂,真修行者,必須打碎這缽盂,才能成就,即使修持如聖師者,也是如此。
。。。。。。
聖師的事,是深刻給過我一定疑惑的,曾幾何時,我是如此的放不下,經過與悟性道友的談道,終於打開了這個謎團,有些事情,沒有自己的親身體悟和經歷,是無法了知真實的。
XX寺傳戒期間,在妙師的介紹下,我結識了很多師父,在那個時候,這些師父從很多方面,指引了我這個渴望出世解脫的俗人,是我所最為敬佩的人天楷模,寺院出事以後,後來發生了很多事情,師父們畢竟還是人,還不是佛,面臨棘手的事件,也生出了一些,作為我們居士,不願接受或是逃避的事情,你逃避他也好,你看不開也好,可事實就是事實,真真切切的擺在那裡,但是戒律的事,我們還是明白的,破戒沙彌猶為人天師表,人家出塵了,而你沒有出塵,人家能夠放下一切,走上了出世之路,這一點上,作為俗家,你無權評判,這一點,很重要!在思索這篇文章之前,一直在考慮這個事情,所以才與以往一樣,隱蔽了真實的人名與地名,寫出來唯恐引起一些人的非議,不寫又不客觀真實,但是這個事件,反應了一個很真切的道理,如何是輪迴,如何是修行,大概是師父,在以身作則的示現給我們,讓我們深刻的開悟,刻骨銘心,反過來說,師父付出的代價也是無比慘痛的,就在你怎么發心,怎么信仰,總之,視師如佛,功德百倍!所以我也本著真實客觀的角度,如實的記錄下這段事情,也許,無常的真理,永遠的伴隨著我們,直到絕對的證悟前,直到達到常樂我淨,這個無常一直伴隨著我們的生活包括修行,也許以後的漫長修行之路,還會有許多的刻骨銘心,但是如實觀照,才是一個修行者的真實內心,如如不動而了了分明,那才是真實的心性所在,古德說,臨流不止意如何?無邊真照說似他,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剎土自他不隔於毫端,真實觀照了知一切的那個,就是那個,不是其他,你在看這篇文章,你在伴隨這篇文字思考,你的右手在按動著滑鼠,知道你正在看文章的那個,知道你在思考的那個,知道你按動滑鼠的那個,無量劫來,只是在觀,別無其他,無增無減,無生無死。。。。
聖師的事件,是伴隨著一個預記,那是一個開悟者,一個禪師,聖師的師爺,但是他的預記是真的,表述了一個真實的定律,不以人力為轉移的客觀。現實就是現實,現實是殘酷的,容不得你半點幻想。
聖師的身世也很苦痛,他是東北人,黑龍江的,自幼喪失父母雙親,但他很有佛緣,也很有悟性,所以機緣巧遇,本村的一個長輩,早年出家為僧,回鄉探親時,一見之下很有緣法,就隨這位師父,披剃出家了,那時年幼,所以只是給這位師父,做了侍者,幹活勞作,但是日子過的很充實,也沒有別的想法,只是有時看到人家的母親帶著小孩子來燒香,聖師總是駐步多看幾眼,請注意,這個情節要記得,這個很重要,也是足以生起生死煩惱的癥結所在,悟性道友確實人如其名,是她明確的點出了這點,一語中的,她雖不如我在佛道方外經歷豐富,但是她的世間磨礪紮實,所以才能看到真實,此點我不如也。聖師後來就受了具足戒,成為了一個正式的比丘僧,東北的修行氛圍很濃郁,許多的高僧大德,正如現在的大悲寺頭陀行眾師父,當時,聖師機緣巧遇,依止高僧培法師坐下,修行清淨法門。大概二十多歲時,去了天下修道聖地,稱為十萬獅子吼秦嶺,八百祖師震終南的,天下茅棚第一的終南山,住山住茅棚,為何要去終南,聖師說,當時是因為仰慕他的師爺,一位年過百歲的老禪師,他一直隱居終南茅棚,在與世隔絕的深山老林,獨立守神,遨遊天地,正因如此,聖師也去了終南,像當年的虛雲老和尚那樣,結廬而居,住山修道了。禪宗古德說,不破初關不閉關,不破重關不住山,不破牢關不下山,可以說,當時的聖師,修行是很有實證的,各種境界十分殊勝。
聖師是聽從師爺的教導,意圖中興弘揚南山律宗,所以參禪之餘他主要修持戒律的事相,律宗的修持很不容易,所以才以至於律宗湮沒無聞,但是,佛的遺訓我們要記得,包括正確的看待這篇真實的故事,我們都要秉持佛祖遺訓,依戒不依師,依經不依論,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依了意不依不了意,這幾個依與不依,是正確的修學與發心,一定要記得。聖師的八萬細行,修持的很如法,見者無不感嘆,那種戒律的執持,確實是能令人升起殊勝信心的。聖師與我的談論中,談及過兩件事情,足證僧寶功德,不可思議。
聖師所住的終南山,秦嶺山脈,原始森林鬱鬱蔥蔥,其中有一段鮮為人知的,人跡罕至之處,那裡的野生動物相當的豐富。那年的春天,就發生了一件,令人拍案驚奇的神奇事件,以前只認為是傳說當中的事,活生生的發生在了現實當中。春天來臨的時候,許多有冬眠習慣的動物,在春暖花開的時候,都一時間甦醒了,這其中就有幾隻黑熊。每當冬季來臨,它就能打上3~5個月的“瞌睡”。在此期間,熊既不飲食,也不排泄。冬眠一結束,就像睡覺醒來一樣,精神瞬即恢復如初。春天來臨了,黑熊們也嗅到了生命的氣息,它們醒來了,而醒來的地方,就是聖師和其他幾個師父們,住山的茅棚所在。經過了一個冬天飢餓的黑熊們,剛醒來,飢腸轆轆急不可耐的要尋找食物,活的生物遇見它們都是可怕的,當一群黑熊出現在這幾位僧人面前時,師父們驚呆了,人和熊的相遇,並且是剛冬眠結束的黑熊的相遇,無疑是及其危險的,但是,我們不可能更真實的了解當時師父們的心理,只能這樣揣摩著,師父們當中,禪定與戒律最高的聖師,並沒有如正常人那樣的恐慌,因為他秉持著,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的道理,所謂,但能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則虛而靈,空而妙,慌個什麼?多年的禪定使得聖師養成了從容的道理,面對這些飢餓的野獸,聖師擋在了最前,雙手合十,對黑熊們說,居士!我若欠你命,你儘管拿去,我若不欠你命,你我皆是緣分,來來!我為你們打個皈依,看似一般話語,修行者嘴裡說出來,就非一般意義了,只見很奇怪的,黑熊們搖搖擺擺的,帶著好像一絲善意,就都蹲在了聖師身前,聖師心中很平靜,一點疑惑也沒有,很自然的伸出手,撫摸著黑熊的腦袋,念起了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不墮地獄,皈依法不墮餓鬼,皈依僧不墮旁生,皈依佛兩足尊,皈依法離欲尊,皈依僧眾中尊,皈依佛竟皈依法竟皈依僧竟,同時給幾隻熊居士都皈依了,都起名叫妙音居士,源自無量壽經,願它們都能往生淨土。皈依後,聖師拿出僧眾的食物,給黑熊居士們吃了,吃完後熊居士就搖擺著走了,消失在山林里。
聖師下山是因為又一件神奇事件,這件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也可以說是試道也可以說是魔障。終南深處的冬季,幾個月都是大雪封山,出不去也進不來,對於俗人來說,那是艱難困苦,但是對於山裡的修道者,那是正好的安冬。聖師內心具有強烈的道心,那年的冬季,他發心獨自辦道,所以就選擇了一處山洞,用厚木板做了門,準備了安冬的食物,就從裡邊用槓子頂住洞口,在裡邊安心修道了。每天就是簡單的食物,然後什麼也不思量,就是一心坐禪,不知不覺的他就入定了,內心深處處於無比寧靜的狀態,但是無始以來的微細惑和根深蒂固的執著,就浮現出來了,在那一刻,聖師的心靈,浮出了一些煩惱執著,渴望母愛的他,仿佛在那一刻,他又回到了幼小的時候,依偎在母親的懷裡,母親是他遮風擋雨的港灣,不知他的眼角有沒有淚水,反正聖師跟我描述這段時,我分明看到他眼中的淚水,所以我能理解他的內心,也能夠深刻理解修行中出現的障難,其實就是自己心裡最薄弱的部分,也是自己最缺少和最深深抓住的東西,那是每個人的命根,輪迴的根本,命運的根源,有位研習盲派八字的師父講了一個盲派八字的道理,她說人命里最缺的,沒有的,在此生就會成為推動命運的力量,正因你沒有,你就會不由自主的去找,去追,命運就在此處體現出來,此點很真實,佛理也是這樣講,因果律就是如此,果依眾緣,報通三世,有先熟有後熟,最重執念,引導著你去處境逢源,去後先來做主公,所以才有了千差萬別的果報,你內心深處,最執著的最抓住不放的,內因外緣就會反覆的在此點上,反覆的折騰你,直到你坦然放下,徹底磨平,內心深處的東西就像是光碟上的劃痕,雖然肉眼看不到,但是只要走到那裡就會卡,承認不承認都是這樣。那個紫金缽盂的公案,正是說明了這點。
明朝朱元璋建國後,賜給五台山碧山寺方丈金碧峰禪師一個紫金缽,很珍貴。禪師也非常喜歡。禪師定功非常了不得,有一天閻王派一小鬼來抓他,到處找不到。小鬼問監齋菩薩,金碧峰禪師哪裡去了?菩薩告之在房間坐禪,但是小鬼說怎么就是找不到。菩薩教小鬼一個辦法,禪師最愛那個紫金缽,去敲響它即可。果然禪師聞聲動了念頭,這念頭一動,無常鬼就看到了,鐵鏈過去就將禪師綁住了。後來禪師說:麻煩你給閻王老子說,過七天后再來找我,我把事情安排好了跟你去。無常鬼聽信其言放了他。禪師明白緣由,待無常鬼走後,立即把紫金缽摔破,不再為心裡有這一念愛好放不下而掛念。禪師於是再七天七夜大精進,七天限期到了,無常鬼再來找金碧峰禪師,卻哪裡也找不到金碧峰禪師。只見禪師在牆上留的幾句話:“若要抓我金碧峰,除非鐵鏈鎖虛空;若能鎖得虛空住,再來抓我金碧峰。
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紫金缽盂,那就是輪迴的根源。聖師定中浮現出了他的紫金缽盂,那就是他渴望而沒有的母愛,正因為他沒有,所以他才堅固渴望,以至於形成了顛倒妄想。定中景象,浮起又消失了,無始的執著,使得他用心去追,各種生死幻夢,都浮現了,在那時他不知時間,也不知空間,甚至忘記了自己姓什名誰,但是就這個紫金缽盂在執著,忽然,他感覺自己好冷好冷,強烈的寒冷,使得他不得不出定了,睜眼一看,太神奇了,他竟然打坐在洞外的雪地里,而洞門還是在裡邊結實的頂著,想進去已是不可能了。聖師在這樣的因緣下出定了,內心卻久久不能平靜,一些內心的積聚,往往在一定時刻,壓抑不住了,它們像雨後的春筍,阻擋不住的生根發芽了。聖師來到後山,跪在師爺面前求開示,師爺閉目無言,進入深深禪定,觀察著這個緣起,一時明了,他告知聖師說,你的障緣生起了,定中打岔,被山神扔出了山洞,你下山行腳吧。聖師不願意下山,不知為什麼,只是內心有一絲對於紅塵和未來的恐懼,仿佛山下的世界裡,有著一種不可名狀的纏繞。但是師爺說,不下山度生積德,恐怕住山,也還是這樣的境界,直到瘋魔,但是師爺很慈悲,給他授了記,告訴他,全國各地都可以去,就是別去XX省。得到了這個預記,聖師收拾行囊就走了。本以為能夠憑著師爺的授記而抵擋纏繞的業緣,但是未能證得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任你聰明才智,對不起,依然還是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聖師下山了,第一站就住在西安城郊的一座寺院,在那裡小住了一些時日,山居的僧人與鬧市的僧人,還是不同的,聖師在山中的清淨,在這座大寺院裡,被徹底打破了,每日絡繹不絕的香客,和世俗的名聞利養,使得這位長期住山的僧人,煞是煩心。這時,正巧有一撥居士團體,來此大寺進香拜佛,一時被聖師的清淨威嚴所傾倒,紛紛邀請聖師去他們的家鄉弘法,這是正巧的因緣會遇,也是冥冥中因果律的體現,該來的終歸還是來了,逃也逃不掉。聖師後來說,當時還是很慎重的,專門看了地圖,一看這個地方屬於XX省,不是師爺說的XX省,所以就放心隨眾居士前去了,這一去不當緊,一場磨難就像穀子碾米那樣如期而至了。直到到了該地,若干時日後,接上了若干緣分後,聖師才後悔不已,這個地方是XX省與XX省的交界處,離省會很遠,離XX省卻只有30里路,所以聖師才錯會了此處的歸屬,真是福至心靈,禍至心迷啊!
人生中就是這樣,有些事情真的不是兒戲,有些人見不如不見,有些事做不如不做,覺得自己很厲害,可是一旦見了某些人,一旦做了某些事,因和緣會遇了,那時就會了解因果的力量,不是以人力為轉移的,那就不是你說了算的了,只能隨波逐流,直到緣盡為止。聖師發現了自己的錯會,很恐怖,就想馬上改變,但是談何容易,緣是很複雜和堅固的東西,從時間到地方再到人再到事,一旦踏入了這個緣時緣地緣人緣事,繁瑣的糾纏,你是很難脫身的。更何況,人還有一個劣根性,就是不見棺材不落淚,不到黃河不死心,當時並沒有出現任何障緣的緣起,每天還是許多的居士前來拜見,皈依,請法,古德說,度眾要有度眾的福德,因為度生的過程中,會有許多的違緣,所以,對於度生的事業,也要隨緣不能攀緣,隨緣就是功德,攀緣就是利害。
聖師山居的性格,使得他與都市中的師父們,脾氣不太相投,因為戒律的事相或是某些法理的見解,時常會有一些爭執,而他的法緣這么好,看似好事,卻帶給他許多的煩惱。所以他那一段,時常就是從這寺換到那寺。我和聖師的相遇,就是在XX寺的傳戒活動時,聖師當時作為三師,被迎請在此。XX寺本地,有一位香童,年紀不大的一個女孩,號稱是泰山奶奶的弟馬,自幼就很響名了,XX寺就坐落在她的莊子上,她很擁護佛法,號召她的信徒們捐款幫忙,護持這座寺院,在寺院傳戒期間,原先寺院的東南角,有一棵大樹,因為枝葉太繁茂,在蓋一間大殿時,有些礙事,所以眾師父誦持了金剛經回向,就把這棵大樹給伐了,這棵樹的根很繁亂,伐樹時很不容易,當時小香童站在旁邊觀看,不知從哪就冒出一句,咱們這些人忙的跟猴似的,一旦樹倒,咱們猢猻也散,後來寺院被毀時,許多人都想起了這句話。他的一些信徒也在那時皈依了,有人就請她觀觀眾師父,小香童當面就說,某師父頭頂有文殊菩薩,某師傅身後是阿羅漢,就是不觀聖師,聖師的隨從弟子就問她,她說,這位師父,逢小雨想回家,逢大雨想還俗,當時眾人權當戲言,沒有在意。
眾生業力交感互相影響,錯綜複雜一環扣一環,有時候我們不知在一些事件里扮演了什麼角色,寺院出事後,眾師父都各自散了,聖師住在西郊一座古寺,妙師回五台後,我和幾位朋友就去該寺看望聖師,那天下著小雨,聖師當時說要離開這裡,我問他去哪裡,他說沒地方去,四處雲遊吧,我當時正好開了一家法屋,外邊是佛像,裡邊是一間房子,有床有桌子,就邀請聖師去我那裡住,他就答應了。我找了一輛計程車就把師父接到了我那裡,中午時候,在一家,也是我們城市唯一的一家素菜館,專門定桌供養了聖師,聖師很高興,那場面至今記憶猶新,想起時還是法喜充滿。飯店老闆也是信佛的,還特意免費送了幾個菜,誰知沒過幾天,這家可憐的素菜館就倒閉關門了。聖師就開始住在我的法屋裡,他還是遵守著戒律,過午不食,早晚功課,施食拜懺,很多的居士又涌到了我這家小小的法屋。大概有一個月時間,聖師和我很談得來,因為他認為我有山居的味道,並且極力的勸我出家,若是我出家,他馬上帶我走,一切有他安排,但是我當時因緣不具備。有一天聖師對我說,他要走,要去一位居士家住,我說我這裡雖然小而簡陋,但是個法屋,還是比住在居士的家裡方便的,但是聖師執意不肯,說已經和居士說定了,晚上就走了。我說送他,他也不肯,說有車來接他。六點打烊我就騎著腳踏車回家了,吃了晚飯,我心裡還是想著這個事,就騎腳踏車出來了,來到法屋發現已經鎖門了,我又走到路口,剛好看見聖師正往一輛車上上,車上還坐著一個人,沒看清是誰。
我跟聖師相處了一段時間,雖然他走了,可我還是很想他,就四處打聽,有幾位居士知道他住在哪裡,但是跟我說時,卻帶著支支吾吾的狀態,好像裡邊有什麼隱情,聖師是住在一位居士老太太家裡,老太太有五十多歲,孀居多年,家中小有積蓄房子很大,也是老佛教徒了。我與她的外甥是同事,以老太太的一慣為人和年齡,我當即反駁這幾位居士,我說千萬莫要議論出家人,即使有什麼,我們居士也沒資格議論,更不要說子虛烏有了。當晚,我就趕去見到了聖師,他坐在床上,打著雙盤,見我來了點了點頭,沒說話,繼續打坐。一會,他的臉上好像有種很痛苦的表情,一會又鬆弛下來了,一會又痛苦的皺眉,老居士說,這是師父的煩惱來了,來找他來了,我還很納悶呢,這個煩惱還是活的啊,還能來回的跑,後來我才知道,那個時候,聖師陷入了痛苦的掙扎,他在與自己內心深處的執著做鬥爭。中間有一段我沒去,後來聽說,聖師正式的在僧眾前,自誓舍戒還俗了,那天下著瓢潑大雨,後來他與老居士結婚了,當時確實是對一些人有一定打擊,這件事,實際無可厚非,比起一些暗地隱惡者,聖師沒有破戒,還俗成家了,作為一名居士,他還可以修行,只是反差很大,一時間理解不透這個事,但是世界就是這樣,你理解與不理解,願意與不願意,都沒有什麼用,師爺的預記還是驗證了,前世如夢,我們沒有他心道眼,無法知曉,但是今生的事情,究竟是怎樣一個過程呢?聖師的定中障礙,其實是他心底最執著的部分,他一直沒有釋懷自己的缺少母愛之事,那是他的紫金缽盂,他執持自己認為自己是個可憐的孤兒,他在時刻盼望和想像著母愛,所以遇見了老居士對他無微不至的關懷,因和緣會遇了,結出了果實,不管果實的甜苦,那都是他自己渴望出來的,原來命運和輪迴都是自己盼望出來的。昨天與悟性道友的談話,提到了念相住三個根本上,這是個很基本的思維狀態,可以說眾生都在這三層里迷惑顛倒。
六祖大師提出了三個無,無念,無相,無住,這是菩提正受,是與實相相應的真實解脫,而反過來我們可以這樣想,去掉這三個無,念,相,住,這三層也就是眾生煩惱的根源了,這三層是從外到內,念就是念頭,想法,對於事物,我們會升起這樣那樣的想法,但是這樣的想法,本身就是顛倒虛幻的,我們只是活在自己封閉的主觀世界裡,對於世界的理解,只是個人的意願,在每個念頭和語言前邊,其實應該加上幾個詞,才能符合客觀,應該加上,我認為。。。。我希望。。。。符合這個認為和希望,就覺得是對是樂,不符合這個認為和希望,就覺得是錯是苦,這不是顛倒么,只是自己一廂情願而已,卻希望事物都能符合自己的意願。而這個念就是導致各種業緣生起的根,念從哪來呢?念還沒出來前,心裡有個東西,雖然沒形成想法,但是比想法更掩藏,那就是相,也就是感覺,處境逢源時,我們不由自主的會升起這樣那樣的感覺,這個感覺最壞事了,一直我們被這個感覺騙著走,同樣一件事,任何人感覺都不同,首先是產生感覺,感覺又產生了念頭,升起了想法,才出現了各種事件,那么念和相的根源又在哪呢?那即是住,住是什麼,住就是認為,就是執持,就是情節,自己抓住了一個東西,自己認為這個東西就是自己,比如最基本的認為我是男人,我是女人,等等,認為自己是個什麼,為什麼同樣一個女人的皮膚,一個男人摸就會產生一些樂受,而一個女人摸只會感到排斥和厭惡,為什麼呢?就是這個住的作用,認為自己是什麼,然後產生感覺,感覺升華成念頭,一動想法,事情就出來了,這是簡單而俗的講念相住的道理,但是仔細想來,確實是這樣的,比如,住為自己是個修行人,對一些事物產生了一些感覺,而又升華出了念頭,就會出現一些事件。
我們在處境逢源,順緣逆緣之時,生出了這樣那樣的煩惱事端,反覆自己折騰著自己的身心,內心渴望著解脫,但不能明白束縛來自何方,怎談解脫大事?究竟是誰束縛了你,導致了你的重重煩惱?
。。。。。。
如實的描述這個事件,仿佛是個警鐘,點醒我們顛倒的心,看清我們心中緊抓不放的紫金缽盂,應把聖師看作是示現妙悟的菩薩,大家能從中獲得些許感悟,進而努力的修正這顆迷妄的心,達到真如實相,真正了脫幻夢的根源,才不虛為人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