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滿江紅題冷泉亭
直節堂堂,看夾道冠纓拱立。漸翠谷、群仙東下,佩環聲急。誰信天峰飛墮地,傍湖千丈開青壁。是當年、玉斧削方壺,無人識。
山木潤,琅玕濕。秋露下,瓊珠滴。向危亭橫跨,玉淵澄碧。醉舞且搖鸞鳳影,浩歌莫遣魚龍泣。恨此中、風物本吾家,今為客。
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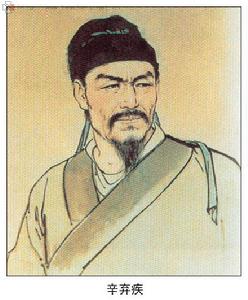 作者辛棄疾
作者辛棄疾(1140-1207)南宋詞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別號稼軒,歷城(今山東濟南)人。出生時,中原已為金兵所占。二十一歲參加抗金義軍,不久歸南宋。歷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東安撫使等職。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論》與《九議》,條陳戰守之策,顯示其卓越軍事才能與愛國熱忱。但提出的抗金建議,均未被採納,並遭到打擊,曾長期落職閒居於江西上饒、鉛山一帶。韓侂胄當政時一度起用,不久病卒。
其詞抒寫力圖恢復國家統一的愛國熱情,傾訴壯志難酬的悲憤,對當時執政者的屈辱求和頗多譴責;也有不少吟詠祖國河山的作品。題材廣闊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詞,風格沉雄豪邁又不乏細膩柔媚之處。在蘇軾的基礎上,大大開拓了詞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後人遂以“蘇辛”並稱。有《稼軒長短句》。今人輯有《辛稼軒詩文鈔存》。
賞析
作者在南歸之後、隱居帶湖之前,曾三度在臨安做官,但時間都很短。公元1170年(乾道六年)作者三十一歲時,夏五月受命任司農寺主簿,至次年春出知滁州。這段時間是三次中較長的一次,此詞可能就是這次在杭州作的。
冷泉亭在杭州靈隱寺前的飛來峰下,為唐剌史元所建。白居易《冷泉亭記》說:“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冷泉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概,物無遁形。”它不但靠近靈隱寺和飛來峰,而且就近登山,還有三天竺、韜光寺、北高峰諸名勝。詞的上闋寫冷泉亭附近的山林和冰來峰;下闋寫游亭的活動及所感。
上闋自上而下,從附近的山林和流泉曲澗寫起。
“直節堂堂,看夾道冠纓拱立。”說山路兩旁,整齊排列的高大的樹木,象戴冠垂纓的官吏,氣概堂堂地夾道拱立。這在修辭上是擬人手法;在句法上是形容句置在主句之前。“直節堂堂”,形容“拱立”的樹木高大挺拔,倒戟而出,形成突兀雄偉的氣勢,並寄託了作者的志趣;第二句綰合上句,並形容樹木枝葉的茂盛垂拂。“漸翠谷、群仙東下,佩環聲急。”說兩旁翠綠溪谷的流泉,漸次流下,聲音琤琤琮琮,像神仙衣上的環佩叮噹作響一樣。其意本於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這也是擬人的寫法。上一層以列隊官吏擬路旁樹木,有氣勢,但讀者不易領會,稍嫌晦澀;這一層比擬,由粗入細,形象自然、優美,比較容易理解。“辛詞才氣橫溢,常不擇粗細”,信手拈來,但都能靈活驅使,此處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下面四句,集中寫飛來峰,由“誰信”二字直領到底。飛來峰並不高,但是形勢奇矯如靈鷲《淳祐臨安志》引晏殊《輿地記》說:“晉鹹和元年,西天僧慧理登茲山,嘆曰:‘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佛在世日,多為仙靈所隱,今此亦復爾耶?’因掛錫造靈隱寺,號為飛來峰。”岩有矯龍、奔象、伏虎、驚猿等名稱,是因為遠看有高峻之感。“天峰飛墮地”,狀飛來;“傍湖”,指在西湖之濱;“千丈”,狀高;“青壁”指山峰,承“天峰墮地”;“開”承“飛”字。“誰信”二句描寫飛來峰,氣勢雄偉,但和起兩句比較,則辭意細密,峭而不粗。“是當年、玉斧削方壺,無人識。”玉斧泛指仙人的神斧;方壺,《列子·湯問》所寫的海上五個神山之一。句中意思是:飛來峰像是仙人用“玉斧”削成的神山一樣,可惜時間一久,滄桑變幻,現在已無人能認識它“當年”的來歷和面貌。以補充解釋、描寫飛來峰作結,調子轉為舒和。
下闋“山木潤,琅玕濕。秋露下,瓊珠滴”,寫亭邊的木石。琅玕,美石;瓊珠,即秋露。因秋露結成瓊珠般的水點下滴,所以木石都呈濕潤。這四句形式平列,但前後有因果關係。“向危亭橫跨,玉淵澄碧。”上句寫游亭,下句寫冷泉秋天流水澄清如碧玉。
以上幾句,調子承上闋的歇拍,仍然舒和。“醉舞且搖鸞鳳影,浩歌莫遣魚龍泣。轉寫自己游亭活動,觸動豪情和身世,調子又轉為豪邁激昂。”“醉舞”句寫豪情,“鸞鳳”自喻,“浩歌”句寫感慨,“魚龍”因泉水而聯想。“恨此中、風物本呈家,今為客。”為什麼醉舞還會發出悲痛的“浩歌”,怕歌聲會使“魚龍”感泣呢?這二句正可說明其內在的,複雜的原因。作者的家鄉在歷城(今濟南),是山東的“家家泉水,戶戶垂楊”的勝地,原有著名的七十二泉,其中也有叫冷泉的;那裡大明湖、趵突泉附近有許多著名的亭子,如歷下亭、水香亭、水西亭、觀瀾亭等,也有可觀的美景“風物本吾家”,即謂冷泉亭周圍景物,有和作者家鄉相似的地方。為什麼又會因此而產生“恨”呢?原因是作者南歸之後,北方失地未能收復,不但素願難酬,而且永難再回故鄉。只能長期在南方作客,鬱郁不得志,因而觸景懷舊,便有了無限傷感。要想排遣這種傷感,只能通過醉中的歌舞,但事實上是排遣不了的。話說得平淡、含蓄,“恨”卻是很深沉的。
這個“恨”,不僅是關係個人思鄉之“恨”,而且是關係整個國家、民族命運之“恨”,自然會引起讀者強烈的同情。這首詞由西湖景物觸動作者的思鄉之情聯想到國家民族的悲哀,表達含蓄悲憤深廣;寫景形容逼肖,而開闔自然。它並非作者刻意經營之作,卻能見出作者詞作的風格特點和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