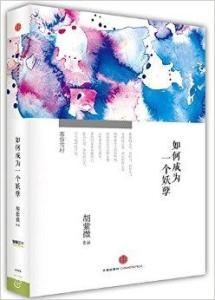作者簡介
 如何成為一個妖孽
如何成為一個妖孽胡紫薇,就讀於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1993年畢業後進入北京電視台。曾擔任《北京特快》《溫馨的家》
《證券無限周刊》和《身邊》等名牌欄目的製片人、主持人、主播等。2007年淡出螢屏後,先後在《部落格天下》、財新《新世紀》周刊開設專欄,也活躍於部落格、微博等新媒體平台。
目錄
自 序 高興就寫 V
情不重不生娑婆
3 章子怡的氣象
13 你看她來勢洶洶
22 遇見才女繞著走
32 給世界留點破綻
37 善哉,食無比
43 情不重,不生娑婆
51 青春不是青春期
57 女人啊,你到底要什麼?
61 愛我,並給我一幢房子
67 什麼樣的婆婆最可怕
73 什麼樣的兒媳要不得
76 不動,就這樣
80 如何成為一個妖孽
93 堅持點什麼比死還難
這是我的立場
103 對於罪惡我們無法一分為二
115 “子彈無法擊落我們的聲音”
121 悲智雙運,再造共和
132 我讀王朔和石康
137 陰雨天就來讀止庵
140 我床頭的那些好書
145 我們離開的那些深情的年代
148 財富去哪兒了
153 入腸是苦
164 失望,照常升起
169 投名狀
169 —兄弟殺我兄弟者,必殺之
172 電影外四篇
是真名士自風流
181 無關風月
191 答案出來了,但問題依然存在
196 明人不說暗話
199 他人即地獄
203 如果我是胡玫
208 唯有月知君去處
211 我寫完了,你醒來吧,好么?
寫的都是心思
217 最好的告別
229 不想說話
233 必也正名乎
238 生於清明
241 一般人
244 那些年,我們背過的男孩兒
246 裂窗記
附.錄.自個兒覺得是顆星,其實不過是棵草.253
序言
"自.序
高興就寫
壹
四十歲以後的人生,就像一鍋燴飯,什麼食材,都不是原來的味道了。那是什麼味道呢?不一定。只是肯定不會砸鍋就是了。不知怎么的,你就是有了這個自信。菜可能炒得失敗,但燴飯無法不成功。區別只在這種好吃還是那種好吃。
燴飯,又叫折籮。將隔夜的剩菜剩飯倒進炒鍋,略加一點水,小火燜透。掀蓋翻炒均勻,趁熱起鍋。
總覺得不同的飯菜,司職的使命不同。有的負責好看,有的負責好吃,有的負責營養,有的負責氣氛。而燴飯,則負責吃得舒坦。
學做飯的時候,調糖醋汁總是調不對味兒。請教我爸,老頭兒一語中的:酸甜口調汁只記著一點,甜要壓著酸,酸要壓著鹹。想想真對。
人生的食材,多是苦辣,酸甜再多也是一層包漿。把這層想透了,認頭了,於是有的人把心思花在調味的學問上,有的人把心思花在適應於這些苦辣上,總不過是為了讓生活這桌流水席變得易於吞咽,原沒有甘與不甘。
寫文章時,心裡是很摻雜的味道,就像酸甜苦辣鹹,用隔夜的折籮,做成了這一鍋燴飯。一頓亂攪和,趁著熱乎氣兒,上桌了。
貳
正看到李碧華小說《青蛇》結尾的地方,樂了。小青說:“感情上不可能再奢侈了,必得作長期儲存休養生息,只好寄情於寫作成名……”呵呵,每個妖孽都不乏一顆凡心。
不知道別人怎樣,寫文章對於我,向來有種拒斥。尤其是寫那種雜文式的平地起風雷的文章,總覺得難堪。感受性的文字好像自慰,有就有了,需要叫得很大聲么。更何況,你的那些所謂念頭,也不一定真的有人要聽。
後來,成長了些,慢慢活明白了一些事,知道了很多的不甘心,來源在於未及發生。活到最後,我們總是寧可因為做了什麼而後悔,也不願意因為錯過什麼而抱憾。既然舉心動念,無非是罪,那就不要把念頭只是隆重地供奉在心裡吧。你寫了,別人要不要聽,也是別人的因緣,何必把眾生的因果背負在自己身上。太自矜了,反而是因為在乎。
近些年來,一直活在崩潰的邊緣。寫東西在我,全為了能活得通順一點。這些東西雖然都是我寫的,但是集起來看,怎么顯得那么亂。不過倒真是我,懷揣著一顆散亂心,東一榔頭西一棒槌,亂七八糟地活著,倒也不見得活出什麼凌亂的美感。
如果非捋出一條線索來自欺欺人的話,我覺得女性的處境和一個女人對於時下境遇的思考,可算吧。
文字有它的意義在。文字自己會形成生命,形成一個語言的場,這個場有它的力量在。
維吉尼亞•伍爾夫是一個鍛造詞語的能手。她曾說,在女性體驗和語言相遇的一剎那,能夠折射出這一性別的聲音具有的某種完美的特點。這個特點由伍爾夫式的語詞來形容就是:漂浮、抑制、急速滑向中心。
寫字對我最大的困擾,在於詞不達意的焦慮。多么希望我的文字具有伍爾夫所說的那種漂浮的、抑制的、急速滑向中心的能力;有多么銳利就多么克制的能力。那種感覺有時候似乎馬上可以碰觸到了,只剩一個腳尖的差距;但是好多時候越飛越遠,反覆琢磨不能究竟,並時時為此苦惱。但知道那境界實有,也知道那境界多么美,多么令人沉醉,並因此而不能放棄。
有人說,沒有人會因為你秘而不宣的思想記住你。畢竟,你說的每一句話,加起來就是你的人生。近來倒是不大經常拿這樣堂皇的勸勉給自己上弦了。記住你又怎樣呢。終究一
新土。
寫作,有點像走夜路,大聲說出來,不過是為了給自己壯膽。人生是一場夜路,我們且歌且行,用內心製造的熱鬧遮掩那來自無量劫的憂傷。雖然一路荒涼,雖然路盡之後也未必是天亮。
叄
我經常說,自己是一個爛人。這時候往往得到朋友,哎,其實就是老郭的當頭棒喝,別跟這兒炒作自己了。你以為爛女人誰都有資格當的,那需要智商。
其實,我自覺還是一個挺聰明的人。只不過,我的聰明並不妨礙跟自己過不去,而且,幾乎可以說,我的聰明大多數都用在跟自己過不去上了。所以當我傷了誰,你一定得知道,我先對自己幹了更狠的。希望這樣說能讓大家覺得好受些。
我有時候挺文藝的,天氣特好和特遭的時候,時常主動追求一種被小布爾喬亞的情愫所籠罩的氛圍,以便於很有審美地陷入沉思。比如,我會突然想,散亂心……該用什麼來對治呢。這時,坐我對過的朋友,哎,其實就是老郭,翻了翻眼睛,說:對……全聚德?好吧,整得我這九曲迴腸的小心臟啊,頓時升起了醬爆之後的焦香。
我是一個氣場很強的人。不是誇張。只要有我在,方圓100米以內手機信號總是弱爆。所以不管我換了哪款手機,信號一律不好,經常撥不出去打不進來顯得行蹤很詭秘的樣子。我不禁佩服自己,嘖嘖,姐的氣場。朋友,哎,其實又是老郭,說,這不是因為氣場大,是因為人品差吧。
我說要寫東西,可能口味還挺重的。我的朋友,哎,還是老郭,說,好好,我給你推薦一個題材,於是一路上給我講了發生在波蘭的一個著名的實驗——他說轟動歐美,我怎么沒聽說過——國際性愛博覽會第一屆性交錦標賽。比賽的內容是一個女性一次可以跟多少異性發生性關係。幾個女性的種子選手,從各自家鄉層層選拔,產生各州的州冠軍,最後決出全國總冠軍。 全世界計有3000名男性參與者自願報名。結果,一位神勇的女將,最終以不停氣地跟六百餘位男性性交而奪得錦標。這時在我眼前恍惚出現了這樣的盛況,幾千位男士組成的志願者隊伍,長蛇般蜿蜒在比賽場地的大門口外,烈日驕陽綿延數里。偌大的體育場裡,幾張四角粗壯的行軍床焊在場地中央,像一張張桌球案,一場激戰正在上演。我詫異地問,怎么會有那么多男的志願報名。老郭詫異地答,當然是為了科學獻身啊。我說,喔,這樣啊。老郭一直為那位卡到最後一步沒能共襄盛舉的報名者扼腕,這哥們,等了 個小時,馬上輪到自己,終場哨聲就特么那么不盡如人意地吹響了。我說你們男的為科學獻身的精神還真迫切啊。老郭說,你沒發現么在很多事上,我們男的都比你們女的更無私。昨天我說書要出來了,他一直追問我做愛大賽那事寫沒寫上,如果沒寫,他就覺得這書意思不大了。所以,喏,寫這兒了。
前幾天,跟老郭說,我們家要是有了小朋友,你來做舅舅啊。老郭馬上警覺地問,那乾爸誰當呢。我說,乾爸這頭銜敏感,被我取締了。老郭想了想,說:那……讓我當姨夫吧。我說:嗯,等回頭問問我妹夫再說。
估計你會說,哎,怎么說來說去就一個老郭。你是不是那種特愛跟男的混,一見男的就起膩那種身邊都是男的綠茶婊。以前算是吧,紅玫瑰說,年輕的時候,兜來轉去,總不過是男人。漸漸地年華老去,身邊女人就多了起來,常年處在雌性荷爾蒙爆表的氛圍里,低頭過事抬頭辦差,旁邊和對過兩公里以內跟我有關聯的都是女的,像“二戰”結束時候的俄羅斯鄉下。好多年儲備下來的所謂男閨蜜也就這一個,說來說去也是這一個,原本想顯得熱鬧點,結果反而暴露了荒涼。
現在流行男閨蜜,我覺得,男閨蜜,最好像老郭這樣的,天真爛漫,有粗俗活潑的趣味,正好可以對沖你幽暗曲折的內心。特逗,不熟就沒什麼廢話,熟了就抄你後路,直言不諱,妙語連珠,雖然是食草動物,但是圓滾滾的一身肉,關鍵時刻雖然不能當擋箭牌衝鋒陷陣,但是占腳助助威那還是很有看點的。你看他那微信簽名,再不相愛就軟了,充分暴露了此人一副飢不擇食的
絲情懷,非常的親民。鐵打的美女,流水的男人。為什麼這么多年這份交情能留下,依我看,老郭的好處全在一個俗字,每當我懷疑自己是一俗人的時候,往他旁邊一站,立馬就剩赤裸裸的道德優越感了。每個事了吧唧的女的,都需要一個俗了吧唧的男閨蜜。
也不是。老郭對於我本人的意義,參見拙文《最好的告別》,文中有提。
肆
人最難的就是認清自己,尤其是在用文字勾畫自己這方面。魯迅先生說過大概這樣的話,要認清一個作家,你倒是最好看看他給別人寫的傳。因為,在他對別人的評價里很清楚地折射了自己的內心;而他的自傳,則大體說的是另外一個人。
時下的名人聰明,講究的是有策略的暴露。放一個比較自謙的姿態,開些明貶實褒的玩笑,賣個無傷大雅的破綻,屬於另一種對自己的小罵大幫忙。這是時下這類自況小文里比較流行的做法,聰明而無害。但是,可不可以更加真誠一點呢?我試試。
不過,對於自毀長城授人以柄迅速成為街坊笑料這事,我倒是一直挺在行的。
不用問,你也應該猜得出,我是那種活得漏洞百出的人。其實漏洞百出的性格,如果夠善良,也未嘗不是一種迷迷糊糊的粉可愛——韓劇里的女主角通常都那樣。我的麻煩是,除了漏洞百出,我還挺計較的。也就是說,足夠貪。
我曾經是一個深信“寸有所長尺有所短”的人。見好就求,見利益就上,而且只要求了,就自動把這好處歸在內心的應收賬款里,一廂情願地等著更大的餡餅掉腦袋上,先進啊,現金啊,榮譽啊,頭銜啊,在掌聲歡呼聲中頻頻頷首啊,就像電影《中國合伙人》里的第一個鏡頭。我想這是所有想像力不足的
絲都特別愛做的黃粱夢。在我的字典里,從來沒有“鳴鑼收兵”這四個字,只能旗開得勝,迎鳳還朝。也就是說,我特別善於給自己上弦,心老是繃得緊緊的,按通俗的話講,擰巴。凡是擰巴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肢體特徵,看上去雄赳赳的。上班十幾年,我雄赳赳地拼搏進取,那顆功名利祿的心一直繃得緊緊的,多種業因,卻不知回頭。
我寫《你看她來勢洶洶》,不只為鄧文迪。
愛給自己上弦,斷弦也是遲早的事。就像錘擊花崗岩,你掄了它九百九十九大錘,花崗岩穩如泰山,連一絲裂紋都不見。直到迎來最後一下錘擊,花崗岩突然間崩潰了,由一塊頑石直接碎成了齏粉。那最後的一擊,是命運的敲打。我的第一千下來自200 年。不到半年的時間裡,處境急速惡化、生活失速脫軌,內心飄墜羅剎鬼國。
上弦的時候,聽著內心嘣嘣作響,豪氣乾雲。一朝弦斷,這世界突然間安靜了。你向隅而泣,自怨自艾,連死的勇氣都沒有。弦斷有誰聽。
據說逆緣是最大的福報。因為,它會迫使你停下來,思考一些人生中真正重要的,卻一直無暇顧及或者刻意逃避的問題。比如如何迎接死亡,比如如何與自己的內心相處,比如如何誠實地面對自己,比如應該給自己定幾條活著的基本原則。
後來,不上班了,專心致志跟自己算賬。這是一份外松內緊的工作,天天觀察自己的念頭,生生滅滅,只恐覺遲。杜欣問我出了什麼事,我說沒什麼,就是突然覺得無法面對自己的內心。杜欣說,你的問題還真文藝。
伍
杜欣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個女人。有句話講,即使全世界都背叛你,我也會站在你的一邊,背叛全世界。對於別人,沒這個把握,對於杜欣,我有足夠自信她幹得出來。雖然這種情感因為看起來蠻不講理而顯得有些狹隘,但是,當你眾叛親離危在旦夕的時候,你就知道一份狹隘的友情有多么重要了。台灣人有時候愛對朋友說,我撐你。我想,這個撐的意思是說,友情才是你的世界坍塌前最後一個支點。
北京台曾經有過一個家喻戶曉的欄目廣告語,叫:生活,就是一個七日,接著另一個七日。杜欣,曾經不捨晝夜地護著我,挨過了生命里最寒冷的七日。可以說,她比我生活里出現過的所有人陪伴我的時間都要長,是我上班後的第一個師傅,我幾乎全部職業生涯的直接上司和半輩子的閨蜜。所有我的故事和事故,特別是事故,她都是見證人,出謀劃策的影子內閣,宣洩情緒時的垃圾桶和大事臨頭時的著急人。杜欣知道我幾乎所有的秘密。我們的會面有時會以這樣的對話互相起頭——這事太機密了,我都不敢跟自己說,只能跟你說——喔,喔。趕緊說。杜欣是這樣的,不管你什麼時候需要她,她永遠是這兩句話:我這就過去;我一直都在。跟杜欣在一塊兒,你就是可以這么敞開了、不講理地、長驅直入地占據她的目光和心靈。杜欣,是我不散的宴席。
杜欣很強勢,但是對我不一樣。她媽媽說,杜欣在家裡接電話,只要是我來的電話,她們都聽得出來。杜欣說話的口氣,一下子就變了。杜欣說我永遠不可能忘了她的生日,連裝著忘了都沒機會。因為跟我媽是同一天, 月13日。 我相信,我們之間有著甚深的緣分。
有一次,我們倆鬧翻了,因為誰跟誰好、誰跟誰不好之類的破事。兩個人關在杜欣的辦公室大吵了起來,驚天動地。所有人都在樓道里聽著,沒人敢進來勸。等杜欣衝出辦公室,摔門而去,辦公室一地的餐巾紙,我們哭得鼻涕一把淚一把。屋裡的相對濕度比樓道高了好幾度。後來很長時間,杜欣見到我,總是禮貌地點點頭,之後匆匆而去,把我留在當地,心如刀絞。後來和好了,我們共同決定,以後不能再吵架了。因為誰都禁不起,都是內傷。
杜欣的媽媽也是一位人物。新中國成立前後外文系大學畢業生,大家閨秀。快 0歲了,每次出門必嚴妝素裹。一頭美麗的銀白色捲髮,配上嬰兒般白皙的皮膚和耳環項鍊戒指手串全套首飾,讓一旁陪襯的我們黯然失色。2013年夏天,我們去奧運村附近的法蘭克福音樂大棚喝啤酒, 歲的老太太一邊喝酒一邊隨著震耳欲聾的音樂起舞,教孫子媳婦跳倫巴。周圍人漸漸圍攏來,紛紛要求跟老人合影留念。伯母回到桌上來指點著說:這,這,這,都是我今天剛收的冬粉。正說著,一個很精神的中年男子上前來特意跟老太太告別,說看著您這樣樂觀,我們都活得更有信心了。目送著男子走遠了,老太太一句話把我們樂噴了。她說:哎,要是再年輕五歲,我就跟他走了。
後來想,我們還沒到 3歲,還有的是機會。
杜家老太太就是這么勵志。杜欣一家人,說起話來逗來逗去有點沒大沒小,但是自然得並不逾矩,有好萊塢輕喜劇的風格,全體招人喜歡。
杜欣是一個工作狂。作為領導,最愛幹的事就是帶著我們跑外勤,穿越大街小巷,拍片子。記得是國家剛剛宣布雙休日的那一天,我們正在趕赴去外景地的路上,她問我和攝像想不想雙休日,我們說想啊想啊。並且一路上在暢想多出來那個休息日,用來幹嗎。過了好一會兒發現坐在前座上的杜欣不吭聲了。我湊過去一看,她把頭別向窗外,已經淚流滿面。我們嚇壞了,自覺說了錯話。但是錯在哪兒了呢?過後,杜欣告訴我,一想到節假日不能上班了就不開心。現在更多了假日,我還以為你們也捨不得我呢。沒想到,明月怎么就照了溝渠。
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領導,不滿意員工的話就用哭的。但是也沒怎么見識過別的領導。電視台1 年,一直在杜欣的羽翼下生存,我離職後不久,她也退休了。現在再見面,四目相對,只覺得,奇葩都是互相成就的。
如果說人生是一齣戲,那么大多數人是平實的底子,少數人是跳動的激情。杜欣顯然屬於後者。
有一次我問她,我好在哪兒啊。她說:你這人特別逗,跟你在一塊兒,總是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我說我怎么沒覺得。心裡得意極了。夸一個女人有趣,在我看來是很大的肯定。順便得瑟一句,自從寫了《遇見才女繞著走》,我發現自己確實有點逗。杜欣是這個世界上少數發現我有這個優點的人,我想,原因是,她就是一個有趣的人。
杜欣有很多語錄。杜欣說,我不離婚是因為怕麻煩。如果退休沒事幹整天跟舟舟的爸爸相對枯坐,那對於我就是四個字——生不如死。這番話竟然是在舟舟爸爸的老同學聚會上說的。而這時候,舟舟爸爸也緊跟著附和了一句:嗯,對對,我不離婚也是怕麻煩。但是其實,杜欣愛玩兒,每次不管去哪兒,都帶著老伴兒。我戲謔她,呦,不怕麻煩啊。杜欣說,唉,看他可憐。
拍了閨蜜合影,大家都在紛紛表示臉長肚子大怎么一副衰相之類的自我批評。只有杜欣看著照片裡的自己,說,嘖嘖,怎么看都沒硬傷。
女人間總是愛刺探相互間的風流韻事。每逢這個時候,杜欣總是率先大方地說:別小看我喔,我可是有故事的人。之後,等著大家追問。
遇到感情問題左右為難進退失據的時候,杜欣說:比如說,你已經站到山頂,是抬頭看四周美麗的風光呢,還是低頭看腳下的垃圾呢?男人就是這個山頭,沒什麼好與不好的。看什麼風景,俯仰之間,全在你自己。
於是,就寫了《青春不是青春期》。
2013年秋天,四個密友一起下午茶,不知怎么就說到了安樂死。我盯著杜欣的眼睛,握著她的手說,如果有朝一日我先於你離開的話,我真的不想進ICU,不想氣管被切開,想安安靜靜地走。但是我擔心的是,到時候沒人會照辦。家人為了他們自己不惹閒話,也會讓我把所有罪都受一遍才肯放過我。所以,我委託你到時候替我做主,結束這一切,好么?杜欣愣了一下,想了一會兒,說:好,你放心吧,我來辦。就這樣,我們執手相看,眼淚也要落下來。
丹姐適時插了一句:唉唉,先別悲壯了行么你們倆。這事兒好像得做公證,到時候公證書送醫院就行了。杜欣出馬也沒用。拿那種大主意,誰會聽一非親非故的老太太的啊。
想想也是。
但是,不管什麼事,你的底線是好歹有她,而她的底線是好歹也擔。這就是閨蜜。
陸
話說回來,我是個懦弱的人。怕死是我上半生的主旋律。下半輩子,爭取把這山頭翻過去。
我經常覺得可以不活了,崩潰起來有點像歇斯底里的老太太。其實,真到那份兒上了,真捨不得死。崩潰,是一次性的行為藝術。真崩潰的人都已經不住在這個世界上了。經常把崩潰掛在嘴邊上的人,離崩潰還有八萬由旬吧至少。
我喜歡逃避,什麼事不逼到跟前兒就耗著。有網上對我念念不忘的“五毛”朋友,有時候SB娘兒們實在罵得無聊了,也會在自己的智商範疇里試圖編纂些邏輯,以便進一步打擊我。其中流傳甚廣的一則微博里形容我:“並無內涵,卻以公知面目示人,機關算盡,心機極深……”每當我心情黯淡自暴自棄的時候——我經常有這樣的時候—這句話總是能夠及時把我從苦惱的深淵裡拯救出來。“我其實是一個心機極深的人啊。我可不是那省油的燈。”就這么點事,動動腦子!頭過身就過。於是我便假裝自己真的像任何一個心機極深的人那樣,千里伏線,暗度陳倉,貓一樣的堅持,不動聲色。
託了辱罵的福,逼著自己偽裝成公知想了一陣兒正經事,寫了幾篇正經文。結果有了《悲智雙運,再造共和》,這篇文章寫得挺好,被好些真正的公知點了贊。
所以你看,你真的不知道,到了兒,會是什麼救了你。
柒
人間是劇場。
我這人好像特別熱衷於角色扮演,從小就是。 歲的時候,我已經無師自通地學會通過COSPLAY榨取剩餘價值了。那時候休息日只要我媽出去逛街,就愛安排我跟妹妹打掃房間,生怕我們閒著享受生活。每逢這時,我就跟我妹妹說:咱們玩小姐和丫鬟的遊戲吧。我妹妹說:好!怎么玩?我說:我演小姐,你演丫鬟。我妹妹說:好!怎么演?我說:那什麼,來!先把小姐的房間收拾乾淨。於是丫鬟就開始收拾屋子,我就坐在小馬紮上,看小人書,吃小孩兒酥。三小時過去了,滿頭大汗的妹妹跑過來:稟報小姐,屋子收拾好了。然後呢?我說:小姐睏倦了,扶我更衣侍寢吧。因為老是這樣子,過了一陣子,六歲的妹妹就對飾演丫鬟的遊戲不那么熱衷了。直到現在,一提起丫鬟這職業,我妹妹還喊腰酸腿疼,產生反胃等生理反應。
長大了,大學畢業照例找不到工作,我想,扮演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似乎不錯。於是,我去應聘了。那是當時一檔曾經很紅火但是年久失修的文藝節目。招聘挺正式的,還有口試和筆試。主考老師問我對於欄目改版的看法。我這樣開了頭:節目做到這份上就比較難辦了。因為,做什麼事都是這樣,從不好做到好比較容易,從好做到更好就難了。估計這樣貌似富有哲思其實涉嫌拍馬屁的回答給領導留下了應有的印象,因為不久之後,我就被通知錄取試用了。真是天上掉餡餅。當然不是做主持,而是到劇組打雜,畫畫大黑板,抄抄通訊錄什麼的。記得第一頁第一個名字,是蔡國慶——那個時代北京市民心中的都教授。到後來才知道,不是誰都有資格給製片人抄通訊錄的。那得把你當自己人,是待遇。
記得我上班的第一天,欄目組的領導在帶我去食堂打飯的路上,不失時機地進行了入職教育:從今以後,你就是你們家掙得最多、路子最廣、能量最大的家庭成員了。換句話說,從踏進電視台這個大門開始,你就要以家庭的頂樑柱來要求自己。你從此可以讓家人過上更有尊嚴的生活。
從此後,我那顆被藝術學府壓抑了四年的小市民的心突然間不可遏制地被點燃了。一門心思想著轉了正,就趕緊結婚,結婚了就趕緊占上分房的名額,分了房子就趕緊生個孩子,從此以後過上這樣的生活:早上八點騎車到崇文門,趕單位的班車,下午三點半去澡堂洗澡,回辦公室的路上拐一趟食堂,買一斤烙餅半斤素丸子,之後一路噴香地接孩子,籠火做飯。這中間再把老公時刻拴褲腰帶上,以求現世安穩,做一個渾身散發著豬蹄和蜂花洗髮水混合香型的上班族。後來,我如願轉了正,並且排上了單位分房的末班車。唯一不遂心的是,原本的結婚對象在我持續的逼婚之下落跑了。我跑到西安,希望追回自己的愛情。結果當然像所有有勇無謀的前女友那樣,氣急敗壞,鎩羽而回。失魂落魄的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成了一個憂傷的工作狂。每天晚上睡在位於地下室的宿舍里,天亮提上鞋就上樓進機房,經常幾天幾夜不出西三環蘇州街那座支有高高避雷針的白色建築。到了晚上,電視台大樓打出紅色綠色和藍色的霓虹燈,映照著我蒼白的四肢和靈魂,就像特別土氣遇上了特別喪氣。後來,有一個同事指著那燈光跟我說,你看你看,咱台是不是顯得特別剔透。這人竟然把電視劇《西遊記》似的霓虹燈看出剔透來了,還真讓我豁然開朗。我想如果嫁給這樣一個善於把周邊事物構想得很陽光的人,對於我這種剛剛被初戀男友淘汰掉的悲觀主義者來說,一定很療傷。
經過輾轉,我到底成了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後來,在扮演了一陣子生活節目《溫馨的家》的主持人之後——在那兩年,我活活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個擅長各種生活小竅門和家長里短的長舌婦,謝天謝地領導實在看不下去了,覺得我離他心目中的生活女神央視張越大姐的神髓還是差得太遠,於是我被轉崗,並分配到了一系列新開辦的欄目,這才終於有機會開疆拓土,野蠻生長。接下來十多年,我又分別扮演過《北京特快》中的新聞主播,這個角色扮演得風起雲湧煞有介事;《證券無限周刊》和《微觀視界》里的財經主播,這個角色扮演得相當矯情,而且足夠假正經;和民生節目《身邊》主持人等跨度很大的角色,並一度榮膺“北京小媳婦”的光榮稱號,可見入戲之深。後來不上班了,在微博里露出了真實嘴臉,爆粗,刷屏,冷嘲熱諷,口無遮攔。很多人表示不適應。我跟他們說,要不是看著自己每天確實這么幹了,連自己都不相信,我竟然是個性格演員。一個記者問我,我覺得您主持節目的時候還是很投入很專注的,有一種樂在其中的感覺。您一定很享受這份工作吧。我告訴她,裝的。她半晌回過一句:您這么說,還真挺傷人的。
後來,坐在家裡,成天無所事事,晃來晃去,顯得有些落拓。本來是為了行遊方外了此殘生的,沒想到,反倒暴露了自己。愛我的人們紛紛用審視的眼神打量我無法被歸類的生活。為了不成為每次見面時被民眾追問的靶子,我告訴他們我其實沒那么荒誕不經,我在寫作。凡事大多這么著,說著說著你就當了真。於是我開始扮演一位作家,偶爾寫些時令小文,冒充一個深邃的女人。並想像著一個作家的態度,和他們會怎么行文怎么思維怎么起承轉合怎么嬉笑怒罵,怎么提煉警句以便坊間流傳。至於下一步,想扮演的是一個寫小說的人。風雪交加的冬日,我抱著孩子,蜷縮在咖啡店裡取暖爐的一角,天馬行空離題萬里,把那些栩栩如生的情節用筆名偷偷發表,一輩子不說,留待後人慢慢索引。
除了作家,我還曾經想像過自己扮演一個室內設計師,一名寵物醫生,或者一個賣煎餅的——當然,是那種撩起裙擺,金色的晨光便會穿過手臂、在臉上身上恰巧勾出一層柔和的光暈、如倍賞千惠子般忙碌而唯美的賣煎餅的。《不想說話》里寫了賣煎餅的緣起,寫完之後,看著文章唏噓吟詠,半天拔不出來,那回是真把自己惆悵著了。
還有下輩子。下輩子我也想到了。我想扮演一個歌女,為了得到一份駐唱的工作,跑到酒吧骯髒的衛生間裡,把廉價的長裙齊著大腿根刺啦一聲扯斷,變成一個包臀小禮服的樣子,面對著滿臉油光的老闆,坐上高高的腳幾,長頭髮披在肩上,低著頭撥動琴弦。下午的陽光順著窗欞斜斜地灑下來,沉默的灰塵在細長的光帶里熱烈地升騰。此時此地,我的心塵盡光生。後來我得到了那份工作,每到晚上,就塗上鮮艷的口紅,唱著悲傷的歌。我的嗓音不是那么出色,並沒怎么學過,可是也可以輕易唱哭一個人。
所以,你想當一個作家么?以我的體會,最快捷的辦法就是假裝自己已經是個作家,並且像個作家那樣坐在電腦前,像個作家那樣敲下第一行字。並且,假裝那一行字非常殊勝,因為它已經是“一流文本”的開頭。於是你輕輕呵了口氣,這時有一個分身從座位上漂移出去,漂移出去的你的分身看著電腦前那個穿著秋衣衛生褲痛嚼黃飛紅的傢伙想,這,就是文學史新的篇章。這樣的話,如果裝得足夠久,八成你會成為一個作家。聽我的,作家,基本只需要一個功夫,坐得住。
這一年間,也有些不怕冒風險的出版社和書商找到我,拜見人家老闆和編輯時,我總是忙不迭地搶先承認,我從來不是一個有全國知名度的主持人,你們可別打算靠胡紫微這仨字賣錢。沒有人會因為要聽我說什麼而破費的。我這么說不是因為老實,而是不想有朝一日讓自己卡在別人的期待和真實的現實之間那道令人尷尬的夾縫裡動彈不得,被人看扁。最後這本書籤到財新,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我也跟“財新思享家”叢書的主編徐曉老師嘀咕,簽了好幾萬冊,相當於三個整編師的編制了,賣誰啊。之後又安慰自己,人家財新和中信都是大買賣,輸贏也不在我這一本上。這才勉強放過自己。
捌
要感謝那些逼過你的人,他們是你們的恩人,因為是他們讓你有所作為。最後,來歷數一下我的恩人們。
兔子老愚。新星出版社的副總編輯老愚是一位眼光獨特的編輯。他說看好我。不少人說過,你文筆挺好的,又儲備了那么多歪理邪說,應該寫寫啊。但是老愚是第一個把這事當真的人。2013年初,老愚向我約稿,我們約在新星五樓的陽光大棚里見面。房間大而空曠,正好適合一次充滿禪機的對話。我說:不知道該寫些什麼。老愚說:寫什麼都成,沒一定,想到哪兒寫到哪兒。我說:沒人看怎么辦?老愚說:一定有人看。我問:為什麼呢?老愚說:你沒發現你想事的路子跟別人不一樣么?我說:跟別人不一樣也不意味著有什麼價值。老愚說:這么說吧,你們女的一般都不習慣深度思考,在這裡頭你就算有點頭腦的。這是比較優勢。他這最後一句,說服了我。我總覺得寫作跟文筆的關係不大,寫作是一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當然,對於老愚的大多數女人沒有深度思維能力的判斷,我好像必須在此攔一句,表示說什麼也不能同意。雖然心裡暗暗地認為真相未必不如此,也暗暗地認為幸虧如此,這是多少男人之幸。
關於寫和寫不出來這事,老愚則充分彰顯了男士的風度,從來不逼我。結果,稿子拖了兩個月。等我好容易湊得七七八八,把大部分稿子整理上交了,又遇到了新星的編輯周期。等新星有信兒了,又因為已經應了別家的承諾而與新星擦肩而過。但是,心裡一直覺得老愚是知音。沒有老愚就沒有這本書。他知道我能寫,而且沒把寫東西當一件不得了的事兒跟我渲染,輕輕推動了我這條原本蜷縮在海港里幾乎鏽蝕的小船,用他的善意和不疾不徐。
趙楚老師。趙楚是另一位推動我成材的專欄作家。趙老師搞戰略研究的,有著軍人式的殺伐決斷和說一不二的氣場。在一次茶聚上,他老人家一針見血地指出,對於我能否如願成為一名寫手,主要的障礙不在寫什麼,而是寫不寫。我問他有嚴重的拖延症啊怎么辦。他說,好辦。走到桌子旁邊,坐下去,打開電腦,要求自己每天必須寫出2000字。自然而然,書就寫成了。日日行不懼千萬里。之後,又放下身段諄諄教育我,不可一味憊懶,人有時要逼自己一下。被趙老師富有感召力的言辭所鼓動,我當時頭腦一熱,在分手時鄭重地委託趙老師撥冗監督我,幫我克服拖拉的痼疾。趙老師說好。結果,趙老師果然言出令隨,回到上海後便不定期地在私信里關懷我的書稿進展。結果迫使我在逃避寫稿之外又添新病,對出版社屢屢搪塞之餘,還要晝夜逃避冥冥中趙老師探照燈般犀利的眼神。兩個月之後,趙老師終於被我寡廉鮮恥的拖拉行為徹底激怒了。因為,有一天,一覺醒來我發現,我已經無法再給趙楚老師留言。趙老師竟然把我從他的微博冬粉里踢了出去並且一舉拉黑。這可怎么好?希望我上進有出息的朋友很多,但是大多是和風細雨順水推舟式的。以拉黑這種決絕的方式來表達立場提攜後進的,除了趙老師還沒有第二個。不過自從趙老師拉黑了我,內心到底受了些衝擊,臊眉搭眼地終於有一度開始認真寫字了。
近來文稿終於有望付梓,趕緊把這好訊息告訴趙老師。趙楚老師很欣慰,特別開恩允許我也拉黑他一次,以示公平。我回了四個字:不給機會。
慕容雪村。雪村是我心目中很會寫文章的人,有著溫文爾雅的幽默感和正大軒敞的價值觀。我很羨慕他這么會寫,又這么多產。雪村說,他的辦法是找到一個人跡罕至的酒店住下來,不要帶網線,之後再把手機卡和電腦網線的接口一一搗毀——必須讓自己死了心——然後坐下來,憋!想到他因為知道終究管不住自己而悲壯自裁,吭哧吭哧把電腦的網線接口搗毀的樣子,忍不住大樂。其實我知道他並沒有,如此說只是為了解脫我的自卑感。但是,果然,在那之後,每當我照例又荒廢了一天一夜面對隻字未寫的空空的稿紙時,我就會這樣安慰自己,沒關係,作家都是這樣的。因為有了這個強大的心理暗示,我才在幾次拖期之後終於沒有放棄,勉強湊出了這十幾萬字的小冊子。雪村慈悲。
徐曉老師。徐曉是圈子裡的狠角色,眼光高標,又有著令人瞠目的操作能力。 她當年寫的《半生為人》影響深廣,觸動了萬千讀者的心。作為財新的首席編輯,近年又給很多知識分子集結出書,能把有深度的書出得有影響,這是本事。
跟徐曉老師打交道,是從給財新寫女性專欄開始的。蒙徐曉老師法眼垂青,覺得我能在她那大家雲集的文化版面上占有一席之地。於是,請劉蘇里兩口子作陪,第一次見識了著名的“徐曉的客廳”。那天,王力雄、慕容雪村、陳冠中伉儷、劉蘇里伉儷、梁文道、梁曉燕等一屋子讀書人。去之前我就打定主意婉拒,沒那個金剛鑽,沒的忝列門牆折辱了人家版面。結果,徐曉老師一直不說約稿的事。倒是先用她奇絕的紅燒肉和鹹蛋南瓜餡兒的餃子一舉拿下了在座的各位賢達。總是這樣吧,嘴裡吃了好吃的,心裡就不由得軟和了。後來,刷碗的時候,徐曉老師用一種徐曉式的,就是那種既輕描淡寫又不容置喙的口吻說:我要開一個女性專欄,你來寫吧,就寫當代社會女性的心理處境。筆觸可以輕鬆一點。把八卦寫出意味,這方面你成。支吾了半天,我說您怎么知道我成。徐曉說:你先寫一篇我看成不成。結果,三周之後,《章子怡的氣象》發給了她,第二天,徐曉老師回信說,甭提多喜歡了,祝賀你紫微。
說實話,我挺怕徐曉的。每次給財新《新世紀》周刊寫專欄,都像給老師交作業,緊張、焦慮、神思恍惚、悔稿重寫,各種犯病。但是,每次都僥倖過關。心裡又是一樂,等著雜誌發表了徐曉老師在郵件里惜字如金的首肯。這次,徐曉幫我張羅出版這本書,不止是緣分,也是因為,我明白自己需要一個嚴厲點的人管束,這書才能按照出版節奏按時面世。否則以我這大拖星的性子,不知道猴年馬月才能截稿。另外,當然了,雖然徐曉老師從不多說什麼,但是我心裡知道,她還是喜歡我的。
勞工。勞工在家裡,就像一頭沉默的雄獅。除了睡和吃,便是盤踞在一個可以俯瞰全局的戰略要地,看球。我當然是輕易不會用自己的小破文去打擾他的清修。只是日子長了,應了兩家專欄,一到交稿前便如熱鍋上螞蟻般,也不免在他面前念叨一句半句,怎么沒思路了,怎么不會弄了。我當不了作家,至少有一個證據。大凡作家,在寫作的過程中,總會在某個階段遇到寫不下去的情況,叫瓶頸期。而我,每寫一篇都遇到瓶頸。
我跟他念叨,雄獅便往往眯起眼睛不知是假寐還是思索。經常是,一會兒工夫,便響起了均勻的鼾聲。偶爾也會突然醒轉來,冒那么一兩句給我點下迷津:你知道你的問題在哪兒么?名利思想太重。不要老想著把每篇稿子都弄成核子彈,偶爾也要允許自己生產一批常規武器。說完一翻身,又沉沉地進入了他獅子的世界。
雄獅先生不睡覺的時候相當勤奮,每周要給幾家高大上的周刊撰寫好幾篇專欄。一寫就是幾年,筆耕不輟。有一次,寫著寫著,他忽然轉過身來說:有朋友給我發簡訊,一定讓我轉達他的敬意。因為你的那篇《古拉格:對於罪惡我們無法一分為二》。我問他,你喜歡么。他想了想,說:我覺得我寫的文章全是見識,你寫的文章全是心思。這句話我一直記著,是因為就我寫的東西,如果還算個東西的話,他只評價過這一句。也是因為,每次想起這句話,就會在心裡對自己說,看來也不見得完全不聞不問啊。於是就覺得可以坐那兒微笑一會兒,再出發。"